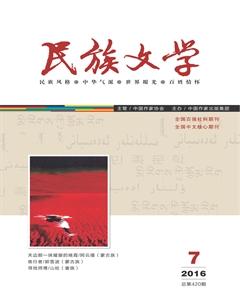尋找?guī)煾?/h1>
2016-05-14 08:42:55山哈
民族文學 2016年7期
山哈 (畬族)
“人有三尊,君、父、師。”
——《白虎通·封公侯》
引 子
從地圖上看,杭州是一只美麗的蝴蝶,而東面的余杭區(qū),則是那只漂亮的左翅。余杭區(qū)是一個古老又年輕的城區(qū)。說它古老,是因早在6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時期,已經(jīng)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了,后來,余杭之名,又多見春秋史籍。當時,余杭屬于吳、越的領地,比鄰富庶天下的杭州,小安偏居。說余杭年輕,則是它2001年方撤市設區(qū),融入主城,成為杭州的一翼。現(xiàn)在看來,1993年創(chuàng)設的余杭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可以說是余杭發(fā)展的一個縮影,原本江南水鄉(xiāng)的一片田野,如今有了成片的高樓大夏,有了花園式的廠房,有了筆直寬闊的東西大道。都說栽得梧桐樹,引得金鳳凰,我所走訪的“三只”藥業(yè)界的“金鳳凰”,都是設區(qū)后良禽擇木而居。
隨著采訪的深入,一個話題在腦海里跳了出來:尋找?guī)煾怠?/p>
自古以來,中國人對“師傅”和“師父”懷著深深的敬意,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寫一個企業(yè),不能不寫傳承,不能不寫師傅和徒弟的關(guān)系,正是師徒關(guān)系構(gòu)成了企業(yè)的文化核心,這里既有技術(shù)層面的傳承,更有人文方面的潛移默化。
如今,“師父”早已褪去了宗親的印痕,傳道授業(yè)者早已成為令人敬重的“師傅”。
小時候,我母親常常會指著醫(yī)師對我說:叫藥師傅。
師傅王貴忠
每天清晨六點半,家住翠苑一區(qū)的王貴忠就早早起了床。今年58歲的老王麻利地收拾好家,輕輕帶上門,大步趕往翠苑公交站臺,風雨無阻,他要趕這趟七點鐘始發(fā)的廠車。這輛和杭州馬路上行駛的公交車外觀一致的廠車,屬于民生藥業(yè)集團全城九部班車中的一輛,這九輛班車每天就像九條金魚,從杭州城區(qū)的四面八方出發(fā),在城市的車水馬龍中游動,最后穿城而過,總能在八點前游到一個共同的目的地:余杭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民生藥業(yè)集團。
上了車,王貴忠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年坐下來,大家?guī)缀跽J可了自己的座位。每天這個時候,是王師傅每天睡一小時回籠覺的美好時光。自從2014年初從市區(qū)的余杭塘路搬到余杭區(qū)后,王師傅已經(jīng)適應了現(xiàn)在這樣的日子,現(xiàn)在,他頭一落靠背,眼睛就如拉上了簾子。
初冬的江南晨光明媚,光影穿過樓群和樹葉,斑斑駁駁落進車廂,落在王師傅關(guān)上了雙眼的臉上,汽車走走停停,輕柔如搖籃一般晃動著,周圍響起了起起伏伏的鼾聲。
師傅王貴忠是1976年進的民生藥廠。
那年我正好20歲,高中畢業(yè),當時街道通知我:民生藥廠要招工了。民生藥廠屬于地方國營,當時叫杭州第一制藥廠,那個時候的杭州伢兒都相信進工廠吃勞保。當時招工還要政審、考試,我這一批,有六十多個一起招進來的。
那時候,我住下城區(qū),家四周絲綢廠比較多,天天路過這些廠區(qū),總能聽到里廂邊機器咣當當,咣當當,很是羨慕。民生藥廠離城區(qū)比較遠,廠區(qū)四周當時還是農(nóng)村,有田,有桑樹,接到錄取通知后,我報到前一天悄悄遛進廠區(qū)考察了一下。記得偌大的廠區(qū)靜靜的,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藥水味,說不上好聞不好聞,廠區(qū)里走的人不多,偶爾遇到的,大多穿著白大褂,神情嚴肅,倒像是做藥廠的樣子。廠里的樹都很高大,馬路也很寬暢,環(huán)境干凈清爽,心里一下子就喜歡上了。
一進廠,我被分到大輸液的蒸氣車間,面對的是數(shù)不清的500毫升大瓶,工作就是蒸氣消毒、配料灌裝。
從76年到現(xiàn)在快退休了,我這輩子都在民生藥廠,前前后后跟過五個師傅。當然,印象最深的還是第一個師傅沈秀清,她是我的第一個師傅,我是她的最后一個徒弟,帶出我后,沒半年,她就退休了。
那天,廠辦領導把我送到調(diào)配車間,指著瘦瘦小小的沈秀清說:這是你的組長,也是你的師傅,以后你就跟她了。那時候的人關(guān)系挺簡單的,就連拜師這樣的大事也沒啥花式,就這樣,簡簡單單的開場白,我平生有了第一個師傅。
沈秀清是民生藥廠的老人了,算起來她應該是公私合營那一撥的職工。那時候,大輸液車間沒什么現(xiàn)代化的設備,就是幾只不銹鋼大桶,放進蒸餾水后,按處方比例添加原液,比如,加5%、10%的葡萄糖,這些全靠手工操作,經(jīng)常是沈師傅看著我調(diào)配方,指出這里那里的關(guān)節(jié)點,做藥的人來不得半點馬虎,那可是人命關(guān)天的事。三個月后,她認為我可以上崗了,才放手。
沈師傅走的時候,廠里舉行了老職工退休歡送會。那辰光,退休是件很光榮的事,好的單位要敲鑼打鼓,送“光榮退休”鏡框、送大紅熱水瓶、臉盆,離開廠時,胸口還要別一朵大紅花。
沈師傅走的時候,最后一次到車間來轉(zhuǎn)了轉(zhuǎn),她拿了塊抹布,東擦擦西擦擦,也不講話,看得我們一幫徒弟心里酸酸的。
在大輸液車間我做了兩年,后來聽說廠里要辦個制藥中專班,憑著高中生的底子,我大著膽子報名,全廠一千多個人,最后有17個人通過文化考試,錄取脫產(chǎn)讀書。我讀的是藥劑學,這個中專班是自己廠里辦的,當時廠里有個教育科,有自己的教師,外聘的也有。經(jīng)過兩年集中學習,專業(yè)知識提高不少,兩年后,回到針劑車間,到了小針部門做實驗,專門做新產(chǎn)品試制,老產(chǎn)品工藝改制。記得民生暢銷很多年的門冬氨酸鉀鎂就是我們這些中專生做出來的,門冬氨酸鉀鎂是電解質(zhì)平衡藥,后來一直生產(chǎn)了二十多年,成為民生藥廠的拳頭產(chǎn)品。
想想老底子的廠,一千多人,開個運動會,搞個籃球比賽都熱乎乎的。廠部還每半個月停工開一次全廠大會,開會的時候,禮堂里黑壓壓一片,書記廠長的聲音透過喇叭洪亮有力。
其實,那時候物質(zhì)生活并不富裕,剛進廠時,我領15塊工資,還有兩塊錢的米貼,印象最深的是年底評先進,上臺領個臉盆,拿張獎狀就開心得不得了。除了工資,平時也沒啥福利,后來,在余杭辦了個養(yǎng)雞場,從那以后,逢年過節(jié),一車車雞拉來,你一只我一只,鬧忙得像集市。別的廠職工看了都眼紅:還是你們民生靠得牢。
你看,一眨眼,當年的青工王貴忠,已經(jīng)快成為退休老頭兒了,再過兩年,我就六十了,民生經(jīng)過幾次改制,已經(jīng)由國營企業(yè)改制成股份制企業(yè)了。像我,退休工資也由社保發(fā),退休后同廠里實際關(guān)系不再像原先國營廠那辰光密切了。
你問我,帶過幾個徒弟?說實在的真的數(shù)不過來,不過我想想,正正式式拜師認徒的有過五個。
2004年后,廠里每年都要舉行“拜師帶徒”儀式,每次開會的時候,也是風風光光的,大紅會標墻上一掛,師傅和徒弟一對一簽字畫押。“拜師帶徒”年年搞,十年下來,有288對師傅徒弟結(jié)了對子,我因為徒弟帶得好,又超過三次以上,被評為內(nèi)部培訓師。
我手里有一張“杭州民生藥業(yè)集團有限公司2008年第五批‘拜師帶徒考核表”。考核表師傅欄里填著“王貴忠”,徒弟欄里填著“黃雙英”,有一段專家評語是這樣說的:“此次拜師帶徒的目標是徒弟掌握小容量針劑產(chǎn)品的配制、過濾、手灌封,封口等技能,以便于對各種產(chǎn)品進行生產(chǎn)前小試,判斷分析小試方案可行性及結(jié)果。師徒間有良好的互動,師傅身兼組長工作繁忙,但仍能細心教導,徒弟也能虛心學習,推陳出新,基本達到了預定的拜師帶徒效果。”
我沒有采訪到黃雙英,聽說她已經(jīng)離開民生了,但她是這樣評價王師傅的:“08年度的拜師帶徒活動已近一年。08年對于師傅王貴忠來說是很繁忙的一年。調(diào)配小組處于缺員狀態(tài),身為調(diào)配分析組的組長,不僅要管理好整個小組,很多工作都要他親力親為。這么繁忙的情況下他還是抽出了時間來教我小試技能。通過一年的學習,經(jīng)過師徒雙方的共同努力,我已熟練地掌握了小容量注射劑的配制、過濾和手工灌封、封口等技能。同時,對小試的目的、方案和結(jié)果能作出分析和判斷。基本達到了拜師帶徒協(xié)議中所規(guī)定的要求,使自己的專業(yè)技能水平又上了一個臺階。應用所學知識,相信在我今后的工作中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第五屆“拜師帶徒”活動結(jié)束的時候,王貴忠又一次拿到了“合格獎”:“……一年來,王貴忠等20名同志,積極履行‘拜師帶徒簽約的師傅職責,悉心傳授,徒弟認真學習,師徒雙方在教學中,知識、技能等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為提高企業(yè)各項工作的質(zhì)量奠定了基礎。經(jīng)考核,全部合格。根據(jù)‘拜師帶徒約定,給予王貴忠等20位師傅,每人720元獎勵,給予徒弟適當?shù)奈镔|(zhì)獎勵……”
2014年4月,民生藥業(yè)集團工會在綜合樓大會議室舉行了第十一批“拜師帶徒”簽約儀式,又有26對員工簽訂合約結(jié)拜為師徒,同時,第十批21對師徒受到了表彰獎勵。
民生藥業(yè)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王自強在儀式上說:今年是民生“十二五”發(fā)展戰(zhàn)略的第二年,也是民生“二次創(chuàng)業(yè)”的關(guān)鍵之年,這項“拜師帶徒”活動,既是提高員工素質(zhì)和勞動技能的一種載體,又能培養(yǎng)造就愛崗敬業(yè)和專研的員工隊伍,促進公司的不斷發(fā)展。王副書記要求師傅發(fā)揚傳、幫、帶作用,徒弟要虛心地把師傅的寶貴經(jīng)驗學到手,成為公司發(fā)展的重要人才。
在民生藥業(yè)集團,傳統(tǒng)的師徒關(guān)系被賦予了新的形式,新的內(nèi)容,在這家現(xiàn)代化的著名制藥企業(yè),“拜師帶徒”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血脈得已保留延續(xù)、開花結(jié)果,那種植根人心的師徒關(guān)系沒有因為市場經(jīng)濟而凋謝,沒有因為現(xiàn)代化而疏遠,人際關(guān)系因為師徒的存在而多了一份溫情,因為師徒的存在而多了一份責任與擔當,多了一份尊敬和關(guān)懷。
祖師傅周師洛
1977年2月,當民生藥廠新員工王貴忠喜氣洋洋開始規(guī)劃自己人生的時候,遠在寧波的鄉(xiāng)村,有一個80歲的老人悄無聲息溘然長逝,老人的去世在周圍并沒有引來多少關(guān)注,尤其是他的身世,更不被別人所知曉。直到1984年,當這位老人沉冤昭雪時,人們忽然才發(fā)現(xiàn),哦,原來那個清瘦的周師傅,是一生吃苦無數(shù),赫赫有名的民生藥廠創(chuàng)始人周師洛。
如今,走進民生藥業(yè)集團公司,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這位老人。
我去的時候,周師洛便坐在那里,穿著西裝,大耳大腦門,臉頰清瘦,目光炯炯,不拘言笑。這座半身雕像的底座上,一段介紹非常簡單:周師洛,1897年生于浙江諸暨,1977年病逝于浙江寧波。1926年6月,周師洛等7人籌資創(chuàng)辦了杭州民生藥廠的前身——同春藥房。百年身后事,評說任由人,站在周師洛面前,我想越是簡單的背后越不簡單。
我對周師洛感興趣的倒不是因為他是民生藥廠的創(chuàng)始人,我最感興趣的是:在上個世紀初,在西藥被東洋人、德意志人、美利堅人瓜分的中國,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民生藥廠的前身——同春藥房?
民國的時候,民族西藥工業(yè)相當落后,只有杭州的“民生”與上海的“海普”、“新亞”、“信誼”,號稱我國“四大藥廠”。正是這四家藥廠,支撐了整個中國的民族西藥工業(yè)。若按創(chuàng)辦時間順序,民生制藥位居第二位;但民生一開始就生產(chǎn)制劑和針劑,是名副其實的西藥廠,應該是國內(nèi)第一家西藥企業(yè)。
現(xiàn)在,我手里握著一份泛黃的珍貴資料,這份行楷印刷的33頁資料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周師洛。這份《經(jīng)營民生藥廠26年回憶錄》,為我們勾畫出一幅近代民族醫(yī)藥工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史卷。讓我們隨著周師洛的目光,回到那個動蕩不安的歲月吧。
恍惚中,我看見一個老人,坐在低瓦度昏暗的白熾燈下,正一筆一劃認真地回憶自己和民生走過的非凡道路。
我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吾家塢山村,世代業(yè)農(nóng)。我于1897年(光緒23年)出生,六歲時,大哥進取清朝末科秀才在家辦私塾,我七歲上學于大哥處,1912年畢業(yè)于翊忠高小,1915年畢業(yè)于諸暨縣立中學。那時二哥要我進師范或法政,因家中常遭地主惡霸的欺侮,倘我進師范法政后可以結(jié)交一些官僚豪紳,家中可以免受別人欺侮。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因師范畢業(yè)只能做個教員,法政畢業(yè)只能做個律師,還不如學醫(yī)藥和工業(yè),可以自力更生發(fā)展生產(chǎn)。遂于1917年考入浙江公立醫(yī)藥專門學校藥科,1919年與連瑞琦等參加過五四運動,至1920年夏畢業(yè)。畢業(yè)后與同學湯伯熊、姚典、馮繼芳等到諸暨開設諸暨病院,我負責藥局,至1922年因族侄周恩溥醫(yī)專畢業(yè)后,留日回國,開設同春醫(yī)院,邀我去主持藥局,我就到杭州同春醫(yī)院,七月浙江公立醫(yī)藥專門學校成立附設診察所,我由老師周冠三介紹擔任該所藥局調(diào)劑員。1923年春杭州第一師范發(fā)生中毒案,街頭巷尾傳說紛紜,謂系狐仙作祟,我未信之,去該校視察,情況非常嚴重,系頭天晚膳中毒,全校六七百人,幾無幸免,當即建議校長何炳松,化驗飯食,結(jié)果證實為砒霜中毒。當即用砒石解毒急救,因毒太重,定量結(jié)果,每碗內(nèi)砒霜含量達到致死量的六至七倍,雖經(jīng)急救,而死者竟達二十八人。事后確認,砒霜系該校會計貪污事發(fā),懷恨下毒。
從回憶錄上看,當年杭州第一師范中毒案對周師洛走上制藥道路起著不同尋常的作用,他意識到:沒有好藥化解,只能眼睜睜看著28人死于非難。
后來,周師洛經(jīng)朋友介紹,進入杭州中英藥房擔任藥師,除配方外,同時試制針藥,供應醫(yī)師和部隊的需要。所用設備因陋就簡,沒有煤氣燈,安瓿封口就用酒精燈裝上吹管和二連球送氣,試制成功后,周師洛建議老板擴大生產(chǎn),屢遭拒絕,萌生了辭職自辦藥廠的念頭。
一個窮孩子要辦藥廠幾無可能,好在周師洛有幾個鐵哥們。1926年6月,周師洛和當年藥科同學范文蔚、沈仲謀、周思溥、馮繼芳、陳樹周、田曼稱等七人決定籌資一萬銀元,創(chuàng)辦“同春藥房股份有限公司”,囊中羞澀的周師洛回老家向大哥借田二畝六分,抵押得現(xiàn)款250元,再向股東韓士芳借得250元入股。因股東大多是醫(yī)藥界和醫(yī)專同學,所以業(yè)務發(fā)展迅速,起家時主要販賣國外的醫(yī)藥原料和化學藥品,同時開始制造針藥和各種成藥丸散膏丹等,以民生制造廠化學藥品部名義出售。獲得資金后逐漸轉(zhuǎn)向制造,以國貨抵制外貨,滿足國內(nèi)需要。
1927年,一筆軍隊的采購大單給民生制藥提供了發(fā)展機遇。那年,國共合作后,北伐軍來到浙江,由白崇禧為東路前敵總指揮的部隊先到杭州,他的軍醫(yī)處長李鏡湖是醫(yī)專同學,就向同春藥房采購衛(wèi)生材料三萬元。
周師洛冒險接下了這一大單,派人轉(zhuǎn)道寧波、上海采購,貨到款清在醫(yī)藥圈內(nèi)樹立了良好口碑。后來,上海的中英、五洲、華美、中西、中法、萬國、科發(fā)、濟華堂等藥企都紛紛委托同春藥房代銷,代銷的好處就是銷售款項可以有三四個月的沉淀期,資金一活,民生的生產(chǎn)有了資本,慢慢有了自己的廠房,有了自己的品牌。
從同春到民生,周師洛是怎么想的?
民生藥業(yè)集團公司總部的一樓有一個企業(yè)展覽廳,里面收藏著一些民生藥廠珍貴的史料,其中就有一份當年《民生醫(yī)藥》的創(chuàng)刊詞,周師洛在其中闡發(fā)了自己關(guān)注民生、醫(yī)藥救國的思想。
“民生”為三民主義之一,意義的重大,事實的需要,先總理“三民主義”一書中,早已經(jīng)昭示我們了。
“醫(yī)藥”直接關(guān)系到每個人生命,常言道,好死不如惡活,沒有劇烈的刺激,誰也不愿自尋死路。可是英雄只怕病來磨,于此而需求救濟,便不得不乞靈于醫(yī)藥。
“東亞病夫”是我們中華民族最不名譽的一個綽號。醫(yī)藥的不深求,不進取,影響于民生極大,這個綽號,便成了世襲似的,而永遠地無法卸除。
是的,事實告訴我們,天災人禍,民不聊生,醫(yī)藥學術(shù),淪落人后,民窮財盡,更無力于求醫(yī)藥,有心人都興著其亡之嘆,然而處于驚濤駭浪之中,豈是一嘆可了的么?必也人盡其職,分工合作,奮力前進,殊途而同歸,“醫(yī)藥”“民生”也許可獲最后的成功!
……
但激情澎湃的周師洛怎么也沒想到,醫(yī)藥救國的道路竟是如此的曲折艱辛。
1926年6月,民生藥廠初創(chuàng)時期經(jīng)歷了軍閥戰(zhàn)亂幸存;1928年2月,一萬七現(xiàn)大洋在上海采購藥物時被盜,幾乎置民生于死地;1933年淞滬大戰(zhàn)爆發(fā),局勢動蕩,民生又一次面臨經(jīng)濟危機;1937年12月,杭州淪陷,為了避免日偽政權(quán)的控制和利用,周師洛響應省政府令,把民生藥廠分批撤出杭州,輾轉(zhuǎn)于蘇浙皖閩贛五省,八年抗戰(zhàn)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磨難,直到抗戰(zhàn)勝利回遷。
1949年,民族大義在周師洛身上再一次閃光,當時,國軍潰敗逃臺,董事長羅霞天極力主張把工廠遷往臺灣,周師洛嚴詞拒絕。由于他的反對,“民生”得以在大陸幸存。
解放以后,民生藥廠和大多數(shù)舊社會過來的企業(yè)一樣,經(jīng)歷了“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地方國營工廠。周師洛的人生也因為“三反五反”于1952年墜入谷底,蒙冤32年,那是后話。
后來的民生藥廠,假如周師洛還能活著見證,一定會開心釋懷。1985年,他一手創(chuàng)辦的民生藥廠,經(jīng)歷了無數(shù)風雨后,又從杭州第一制藥廠更名為民生藥廠,那些日子,舉國上下,誰人不知“21金維他”?一家心系“民生”的企業(yè),以赤誠之心,把抗腫瘤類藥、抗心血管病類藥、治療肝病用藥、大輸液等源源不斷交給急需的患者手里。
2013年12月16日,臨平大道36號的民生新廠彩旗飄揚,鞭炮齊鳴。這座總體投資7億多,占地11.4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的新廠,嚴格執(zhí)行了國家新版GMP要求,建立了現(xiàn)代化的各類針劑、輸液、片劑、膠囊等制劑和眼藥外用藥等生產(chǎn)廠房及其他各輔助設施,設計產(chǎn)能比老廠區(qū)提升兩至三倍,設計年產(chǎn)值近20億元。
董事長竺福江站在新廠房的土地上對員工們揮臂感言:功崇惟志,業(yè)廣惟勤。民生人要將搬遷新址作為一個新的歷史起點,面對新機遇與挑戰(zhàn),堅守“發(fā)展企業(yè),貢獻社會,造福員工”的宗旨,堅守盡心盡力盡責的精神,把企業(yè)做好做強。繼續(xù)發(fā)揚堅韌不拔、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努力實現(xiàn)民生人的“三個夢想”,為人類的健康事業(yè)和地方經(jīng)濟做出新的貢獻。
歷史常常和我們開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比如民生藥廠,這家流淌著中國企業(yè)家實業(yè)興國,西藥中興夢想的藥企,在創(chuàng)設之初以股份制企業(yè)走入市場,在歲月更替中經(jīng)歷了公私合營、地方國營、廠長負責制等等體制改革后,最后又回歸到原點,成為一家現(xiàn)代股份制企業(yè)。當然,如今的民生藥業(yè),不再是周師洛他們的私人股份,如今的民生,更多寄托了民生人再次創(chuàng)業(yè),走出國門的理想。
離開民生的時候,我又站在周師洛面前默默對視,西下的陽光正透過巨大的玻璃門溫暖地灑在他的身上,有了陽光,周師洛的嘴角仿佛多了一絲笑意。
我想,如果在民生藥業(yè),想找一位“最老的師傅”聊聊,那便一定是他了,周師洛,一位有著民族工業(yè)振興夢想的中國藥師傅。
臺灣師傅王昭日
世上的藥,傳說都是“神農(nóng)鞭草”而得。
中藥服務華夏數(shù)千年至今仍深得國人信賴,只是在現(xiàn)代制藥面前,“神農(nóng)鞭草”早已過時,中藥西制,擺脫陶罐煎取的束縛也早已成現(xiàn)實,提煉、粹取中藥主要藥用成分,便是現(xiàn)代“神農(nóng)”們的工作。
在臺灣獨資的杏輝天力藥業(yè)公司,我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味傳奇的中藥,同時也結(jié)識了臺灣師傅王昭日。
說起這味藥的獨特,是因為這味藥是江湖上傳聞很神奇的壯陽神藥:管花肉蓯蓉。也有一種說法它是“沙漠人參”,傳說成吉思汗就是吃了它,轉(zhuǎn)敗為勝,神勇殺敵,最后統(tǒng)一了蒙古,開創(chuàng)了新時代。
在大陸拓疆十多年的杏輝天力總經(jīng)理游能盈先生是個白面書生,說起肉蓯蓉,他更是如數(shù)家珍:肉蓯蓉只寄生在沙漠的梭梭林根系上。杏輝天力或許是第一家在大陸從事肉蓯蓉制藥的廠,早在2002月,他們就在新疆于田縣創(chuàng)辦了“和田天力沙生藥物開發(fā)有限責任公司”,現(xiàn)在有500畝科研基地和5.7萬畝GAP生產(chǎn)基地。
但從管花肉蓯蓉中提取有效成分卻不是件簡單的事。
在遠離新疆萬里之遙的杭州,杏輝天力藥業(yè)集團有著體量巨大的廠房,那些方方正正的巨大“盒子”被掩藏在高大、修剪得精精神神的柏樹后面,在這里,我沒有聽到機器轟鳴的聲音,也沒看到工廠慣有的高矗煙囪,當然,也沒看到肉蓯蓉如何從植物成為齏粉的過程,因為工廠有著極嚴格的防菌要求,不便參觀。
其實,我內(nèi)心對臺資企業(yè)的經(jīng)營模式更感興趣:這里的師傅又是怎么帶徒弟的呢?
王昭日博士就坐在我跟前,他是臺灣來的師傅,是杭州杏輝天力研究所的所長,奔五的人,長得白凈、壯實,顯然,因為是初次見面,有點局促。
我們公司也有師傅帶徒弟啊,只是說法不一樣,臺灣人叫技傳,而且有一套嚴格的制度規(guī)定。
在杭州杏輝天力最核心的部門要數(shù)我們這個研究所了,全所25人,三個博士,兩個是本地的。
我到大陸才一年,原來在臺灣總部做研發(fā),總部搞研發(fā)的人比較多,有一百多人。我的課題主要就是中草藥這一塊。杏輝天力是一家跨國公司,除臺灣總部外,加拿大有一家,大陸有杭州和新疆和田兩家。
說到技傳,我們大多是老師和學生一對多,每個學生也是同仁,他們專長不一樣,個性也不一樣,必須用實際行動去幫帶。醫(yī)藥研發(fā)和傳統(tǒng)技能不一樣的地方是:科技上的東西更適合以老師帶學生的方式傳授。在杏輝,我建立了一套技術(shù)標準、體系,遇到問題,不是先告訴他們怎么做,而是首先讓他們?nèi)ゲ檎屹Y料,自己討論尋求解決的方式。比如在植物有效成分提取上,我會先要求功效做一個報告,提取做一個報告,專利可行性再做一個報告,在完成報告評估后,請同仁再往下做,做的時候就開始做分工了,提取的專門做提取,分析的專門做分析。
王昭日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也是臺灣醫(yī)學界的資深博士,但從他身上卻看不到絲毫權(quán)威的傲氣,用新員工黃佳慧的話說,他更像一個大哥哥。
這位“大哥哥”討人喜歡的一面是總能和80后玩到一處,附近的黃山、塘棲、周莊、西湖景區(qū)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特別是當課題遇到瓶頸時,王昭日會帶著他的團隊出去“放松放松”。那次,ST02項目又卡住了脖子,大伙想盡了辦法,提純度依然達不到生產(chǎn)所需要的標準。第二天是雙休日,王昭日建議去不遠的上海金山“放松放松”。
和往常一樣,大家聚在一處喝茶,聊天,忽然,不知誰高高舉起茶杯說:假如把溫度提高十度二十度,再改進一下過濾回流的辦法,ST02會不會提高提純度呢?大伙一聽興奮不已,你一言我一語,“放松”活動又成了學術(shù)研討會,于是急急結(jié)束了“放松”趕回實驗室。
果然,這一實驗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連師傅王昭日都直拍腦袋:我怎么就沒想到呢,我怎么就沒想到呢。
杏輝天力研究所里,大多數(shù)是70、80后,這些獨生子女出生的員工身上,有著與他們父輩不一樣的獨立性,少數(shù)人還缺少團隊精神。一次,王昭日從臺灣回來,除了帶回臺灣特產(chǎn)外,還帶了一包書名叫《執(zhí)行力》的書,這是一本在臺灣企業(yè)很有影響的書,他覺得企業(yè)目前最缺的就是執(zhí)行力。他像發(fā)臺灣特產(chǎn)一樣把《執(zhí)行力》發(fā)到每位中層干部手上,又按照全書九個章節(jié),讓他們?nèi)芜x一個章節(jié),做一次讀書分享報告。同時,他讓員工投票打分,評分高的,獎勵購書券一張。這件事,前后花了九個禮拜,最后得到的效果喜人:大家都愛看書了,企業(yè)執(zhí)行力文化也無形中得到了加強。
走進現(xiàn)代化的杏輝天力,依然能感受到濃濃的儒家文化細節(jié),比如高大門樓的兩側(cè),置放著一人多高的花瓶,寓意“進出平安”;而門廳里,最顯眼處還供著一尊觀音像,觀音前電子蠟燭長明著,因為不是特別的日子,香爐里剩著燃盡了的香尾巴,三只酒杯是空的。這些,總讓人聯(lián)想到這些擺弄高科技設備的人,心里存續(xù)的對神靈的敬畏。
我對總經(jīng)理打趣說:您的名字很好啊,姓游,名能盈,就是說走到哪里都能贏啊,大伙聽得哄堂大笑。
杭州杏輝天力就是游總?cè)谈M落地的項目,杏輝與杭州結(jié)緣已久。1999年臺灣大地震的時候,他們收到一份特殊的問候。原來,先前他們在考察杭州時,與老余杭一家叫天力的醫(yī)藥企業(yè)有過接觸,沒想到,當臺灣遭災時,天力老總專門發(fā)來郵件表示慰問。
隔年西博會的時候,游能盈和總經(jīng)理受邀來到杭州,有點時間,就一起去老余杭拜訪天力,應了那句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老話,聊著聊著,僅一個星期,雙方就談妥了杏輝出資1700萬收購天力的方案。這家由國企轉(zhuǎn)制而陷入困境的企業(yè),迎來了新東家,游能盈對一百多名員工說,新廠房在余杭新區(qū)建成后,有職工宿室,我們熱烈歡迎老員工過來。結(jié)果,天力80%老員工都穿過整個杭州城市跟了過來。
“杏輝”是“心靈光輝”的別稱,早在1977年臺灣起家的時候,杏輝人便在企業(yè)文化高地確立了兩個字:誠與靜,誠以待人,處事以靜。
游能盈說,在杏輝,企業(yè)文化最重要的底色,就是最最簡單的三句話:請,謝謝,對不起。簡單的禮貌用語正是構(gòu)建人與人之間和諧關(guān)系的基礎。這家只有163名員工的企業(yè),2014年的產(chǎn)值達到1.1億元。
杭州是個宜居的城市,從2010年開始,每年十一月都要舉辦國際馬拉松賽,這已成為國內(nèi)最重要的馬拉松賽事之一。
自從杭州有了馬拉松賽事以來,杏輝天力總會第一時間報名參加,他們把它當作一年一度的企業(yè)文化來經(jīng)營。
2013年11月3日,西子湖畔拉起了警戒線,人們在道路兩側(cè)為奮力奔跑的參賽者加油,前頭跑得快的,有人已經(jīng)穿過湖濱步行街跑到了南山路了,跑得慢的,還落尾巴掉在北山路一帶。
師傅王昭日穿著短衫短褲,跑在杏輝天力隊的最前頭,他不時回頭,大聲喊著:保持節(jié)奏,調(diào)整呼吸,不要搶快,慢一點,堅持就是勝利。
這一天,杭州的天格外藍,碧空如洗,陽光溫暖,秋天的金黃把素顏西湖裝點得色彩斑瀾。
采訪結(jié)束的時候,王昭日笑著說:馬拉松最考驗人的意志力,只要還能跑,杏輝人永遠都不會放棄奔跑的機會。
法國師傅衛(wèi)平
印象中法蘭西是一個浪漫多情的民族,但法國雜志《Esprit》編輯Paul Thibaud自豪地說:“我們有多么視自由和平等為權(quán)利,就多么有義務以博愛去尊重他人。”
醫(yī)者仁心,制藥的人也應該有一顆博愛的心。
走進杭州賽諾菲民生,我被大門前一座黑色的大理石紀念碑所吸引,這座紀念碑上用金字鐫刻著中法英三國文字:深切緬懷賽諾菲亞洲區(qū)高級副總裁衛(wèi)平(1968-2011)。
長得小巧優(yōu)雅的代萍萍總監(jiān)告訴我:賽諾菲在中國有六家生產(chǎn)基地,六家基地的大門前,無一例外都安放著這塊統(tǒng)一制作的紀念碑。
衛(wèi)平是誰?衛(wèi)平怎么啦?
在代萍萍眼里,衛(wèi)平(Thomas Kelly)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更不容易的是他的骨子里,早已融入了中國文化。從1993年入職西安楊森,到后來的諾和諾德,再從先靈葆雅到賽諾菲-安萬特,衛(wèi)平深耕中國藥業(yè)幾十年,從藥企市場拓展一直做到中國區(qū)賽諾菲副總裁。
衛(wèi)平在中國高速拓疆擴土,他領銜賽諾菲后,每一天都在中國的天空上飛翔。衛(wèi)平堅信中國代表著未來,中國的發(fā)展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前進,前進。更好的醫(yī)療服務,更好的藥品會給富裕后的中國人帶去最重要的東西:健康。
拼命三郎法國人衛(wèi)平把整個中國市場拓展計劃細化到具體的幾百個城市,如果不是因為太過勞累英年早逝,他所領導的賽諾菲會如他的夢想,讓法國和中國的聯(lián)系從未有過的緊密。
從1982年進入中國市場以來,賽諾菲這家在全球有11萬員工,業(yè)務遍及全球100個國家,112個生產(chǎn)廠家的跨國醫(yī)藥企業(yè),僅2012年度凈銷售額就達349億歐元。
一直堅持“超高超快增長”發(fā)展思路的賽諾菲,在中國大肆招兵買馬,并購企業(yè)、建立工廠。2010年,賽諾菲與杭州民生藥業(yè)組建了合資公司,核心資產(chǎn)包括民生藥業(yè)的拳頭產(chǎn)品“21金維他”。接著,又在2011年以5.206億美元收購了藥品生產(chǎn)商兼分銷商太陽石集團,并借此擁有了國內(nèi)最大的小兒感冒咳嗽藥品牌“好娃娃”,同時也擁有了太陽石集團在感冒咳嗽和女性健康領域的強大平臺。
這兩項交易使賽諾菲獲得了渴望已久的品牌和渠道。2012年,賽諾菲在華銷售額超過10億歐元,成為中國第三大處方藥物公司和第一大跨國疫苗公司。
被賽諾菲CEO魏巴赫稱為“賽諾菲的核心市場”的中國,正在逐漸成長成為這家法國醫(yī)藥企業(yè)可靠而巨大的盈利支柱。
2011年11月3日,在山東忙于收購太陽石的賽諾菲中國副總裁衛(wèi)平因心臟病不幸謝世。
這位法國師傅的離去,并沒有影響賽諾菲在中國的布局腳步,截至2012年底,賽諾菲在中國擁有7000名員工。并在上海建立了研發(fā)中心,北京、成都配備了研發(fā)團隊,具備了從藥物靶點發(fā)現(xiàn)到后期臨床研究的整體研發(fā)隊伍。
如今,我還能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讀到衛(wèi)平在中國各地與政府官員見面、商談的新聞,還能看到他和媒體互動的鏡頭,可惜,那位充滿活力的法國人現(xiàn)在只活在賽諾菲人的記憶里。
與浪漫主義不同的是,在賽諾菲民生,我只看到兩個字:嚴謹。
總監(jiān)代萍萍的辦公室墻上,我被密密麻麻的中英文提示所吸引,那塊叫做QC管理看板的黑板上,標注著賽諾菲民生的生產(chǎn)計劃,存在問題,各項進度。可以說企業(yè)各條線匯聚的所有問題、目標管理都集中在這里,可以說,總監(jiān)辦更像是一場戰(zhàn)役的指揮中心,而代萍萍墻上的QC板,無疑是作戰(zhàn)地圖了。
這是我在其他藥企所不見的,如果你以為這只是總監(jiān)才有的QC板,那就錯了,在后來的走訪中,從科室到最基層的操作間,墻上無處不有QC看板,法國企業(yè)文化中的嚴謹,在這里被發(fā)揮到了極致。
賽諾菲和民生藥業(yè)好比一對模范夫妻,早在1995年,賽諾菲安萬特就曾牽手民生制藥有限公司,到了2010年,民生藥業(yè)以拳頭產(chǎn)品“21金維他”作為嫁妝,按4:6比例共同成立了“賽諾菲民生”合資公司,現(xiàn)如今,民生藥業(yè)和賽諾菲民生共伴共生,卻因為文化基因的不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企業(yè)文化。
和“21金維他”一起嫁到法資控股 “賽諾菲民生”的,還有當時幾十位民生藥業(yè)的“老人”。
我叫孫華強,57出生,全家兩代都是民生藥廠職工,我父親今年84歲了,叫孫壽炎,解放前就在民生制藥廠工作,說起來還是民生的中層干部。我是77年進入民生藥廠的,實際上,74年就算民生藥廠的人了,為啥呢?因為當年城市青年都要上山下鄉(xiāng),為了不讓子女到邊疆吃苦,也算是規(guī)避政策吧,民生藥廠和富陽萬仕那邊一個公社簽訂了協(xié)議,租了一塊土地,搞廠社掛勾,把我們十個民生職工的子女下放到萬仕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
“文革”結(jié)束后,我就作為知青回到了民生藥廠,眨眼就是一輩子。兩年前,我從賽諾菲民生退休了,退休后又返聘回賽諾菲工作,你問我為啥愿意返聘?其實想聘我的杭州藥廠很多,有的開的條件也很高,但我還是愿意每天來來去去坐二三個鐘頭到賽諾菲來做,為啥?一是我對賽諾菲有感情,二是賽諾菲能給我除了鈔票以外的東西,比如尊嚴。
我這一輩子跟過兩個師傅,一個是李海龍,現(xiàn)在還在民生藥廠做采購物流經(jīng)理,另外一個是張志良。在民生藥廠跟師傅還是老傳統(tǒng),多少帶著點師徒感情,而在法國企業(yè)里,一切都是有量化標準的,哪一道工序怎么做,程序怎么樣,標準怎樣都非常具體,上崗前都會集中培訓,每個崗位墻上也都有QC板,細化到每個人都清楚自己做什么,怎么做。可以這樣說,只要識字,只要嚴格按標準化程序操作就不會出錯。
在賽諾菲我也當過師傅,但我們這一輩人文化不高,外語也看不懂,主要是講具體操作的經(jīng)驗,一般都是集體上課,賽諾菲這點讓我很佩服,他們有個分級制度,每個辦公、工廠區(qū)域都是用指紋開門的,你沒有這個區(qū)域的權(quán)限,就進不了這個區(qū)塊,同樣,每個區(qū)塊的員工只要做好做精本職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額外學習更多的生產(chǎn)技能。講得通俗一點,賽諾菲民生好比一架精密的機器,每個員工就是機器上固定的一個零件,只有每個零件良好,才能保證機器優(yōu)質(zhì)高效運轉(zhuǎn)。
70后韓獻偉是浙江金華人,大學畢業(yè)后,他一直在杭州幾家外資企業(yè)的設備動力部門工作,來到賽諾菲民生后,他分管著整個生產(chǎn)基地的設備管理。說起賽諾菲,他認為賽諾菲全球就像一個大家庭,你在這里生活,工作,成長,只要努力,你是有空間的。去年,印度賽諾菲一個小伙交流到杭州工作了一年,回去擔任了更好的職位,而他,也因為賽諾菲,有了一個法國女兒。
原來,賽諾菲集團有個為期兩周的暑期子女交換項目,這個交換項目規(guī)則是:只要是賽諾菲員工,子女年齡在12至18周歲,都可以通過官網(wǎng)報名,輸入孩子年齡,性別和選擇交換的國家。交換周期為兩周。
2013年3月,韓獻偉給孩子在官網(wǎng)報了名,兩周后集團負責交換項目的主管Annie發(fā)郵件給他,提供了法國賽諾菲一位愿意來中國參加暑期項目的孩子的信息,通過郵件溝通,雙方父母達成了交換意向。
韓獻偉后來的法國“女兒”叫Ellisa,12周歲。去年7月6日Ellisa乘飛機來到中國,到中國父母家后,Ellisa對一切非常好奇,吃慣了西餐的她對中國菜更是贊不絕口。
中國“爸爸”帶著Ellisa游遍了西湖、運河,還帶她去博物館了解中國燦爛的歷史文化。
游完杭州不算,中國“好爸爸”還特意安排兩個孩子到北京旅游,把故宮,長城看了個遍,兩周后,Ellisa要分別了,韓獻偉為Ellisa一家人精挑細選了絲綢、茶葉、工藝傘等紀念品,登機的時候,Ellisa緊緊抱住韓獻偉,流著淚戀戀不舍。
八月,韓獻偉也把女兒送上了去往法國的飛機,在法國,法國“父母”也領著她游覽了世界最浪漫的都市,女兒在電話里大聲說:爸爸,我爬上埃菲爾鐵塔了,我還看到凱旋門,好高好大啊,我還去了盧浮宮,里面的油畫真漂亮。爸爸,法國的天好藍好藍啊,河水也特別特別清。Ellisa一家人還帶我去吃了法國奶酪,吃了法國大餐,爸爸,我好幸福啊……
電話這頭,韓獻偉聽著聽著都醉了,兩個12歲的孩子,在她們最純真的年代,種下了兩顆美好而快樂的友誼種子。而這一切,都受益于賽諾菲全球大家庭。
這是一個人人都可以成為師傅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師傅口語化的時代,假如在菜場,假如在馬路上,假如有人大聲在你背后喊你一聲“師傅”的時候,千萬別激動,這時候,師傅,只是代表了一個隨意的稱呼符號。
歷史像一駕信手由韁奔馳的快馬,載著我們飛快地前行,一些手工行業(yè)早早被我們拋棄在歷史的煙云里,而與那些時代相生的稱謂,比如師傅,已經(jīng)不再具有原來的內(nèi)涵。
但在工廠里,在企業(yè)里,師傅,這個稱呼,永遠都會帶著他們從心底里流出的尊重。
那是真的師傅。
責任編輯 孫 卓
山哈 (畬族)
“人有三尊,君、父、師。”
——《白虎通·封公侯》
引 子
從地圖上看,杭州是一只美麗的蝴蝶,而東面的余杭區(qū),則是那只漂亮的左翅。余杭區(qū)是一個古老又年輕的城區(qū)。說它古老,是因早在6000年前的馬家浜文化時期,已經(jīng)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了,后來,余杭之名,又多見春秋史籍。當時,余杭屬于吳、越的領地,比鄰富庶天下的杭州,小安偏居。說余杭年輕,則是它2001年方撤市設區(qū),融入主城,成為杭州的一翼。現(xiàn)在看來,1993年創(chuàng)設的余杭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可以說是余杭發(fā)展的一個縮影,原本江南水鄉(xiāng)的一片田野,如今有了成片的高樓大夏,有了花園式的廠房,有了筆直寬闊的東西大道。都說栽得梧桐樹,引得金鳳凰,我所走訪的“三只”藥業(yè)界的“金鳳凰”,都是設區(qū)后良禽擇木而居。
隨著采訪的深入,一個話題在腦海里跳了出來:尋找?guī)煾怠?/p>
自古以來,中國人對“師傅”和“師父”懷著深深的敬意,常言道:“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寫一個企業(yè),不能不寫傳承,不能不寫師傅和徒弟的關(guān)系,正是師徒關(guān)系構(gòu)成了企業(yè)的文化核心,這里既有技術(shù)層面的傳承,更有人文方面的潛移默化。
如今,“師父”早已褪去了宗親的印痕,傳道授業(yè)者早已成為令人敬重的“師傅”。
小時候,我母親常常會指著醫(yī)師對我說:叫藥師傅。
師傅王貴忠
每天清晨六點半,家住翠苑一區(qū)的王貴忠就早早起了床。今年58歲的老王麻利地收拾好家,輕輕帶上門,大步趕往翠苑公交站臺,風雨無阻,他要趕這趟七點鐘始發(fā)的廠車。這輛和杭州馬路上行駛的公交車外觀一致的廠車,屬于民生藥業(yè)集團全城九部班車中的一輛,這九輛班車每天就像九條金魚,從杭州城區(qū)的四面八方出發(fā),在城市的車水馬龍中游動,最后穿城而過,總能在八點前游到一個共同的目的地:余杭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民生藥業(yè)集團。
上了車,王貴忠找到自己的位置,一年坐下來,大家?guī)缀跽J可了自己的座位。每天這個時候,是王師傅每天睡一小時回籠覺的美好時光。自從2014年初從市區(qū)的余杭塘路搬到余杭區(qū)后,王師傅已經(jīng)適應了現(xiàn)在這樣的日子,現(xiàn)在,他頭一落靠背,眼睛就如拉上了簾子。
初冬的江南晨光明媚,光影穿過樓群和樹葉,斑斑駁駁落進車廂,落在王師傅關(guān)上了雙眼的臉上,汽車走走停停,輕柔如搖籃一般晃動著,周圍響起了起起伏伏的鼾聲。
師傅王貴忠是1976年進的民生藥廠。
那年我正好20歲,高中畢業(yè),當時街道通知我:民生藥廠要招工了。民生藥廠屬于地方國營,當時叫杭州第一制藥廠,那個時候的杭州伢兒都相信進工廠吃勞保。當時招工還要政審、考試,我這一批,有六十多個一起招進來的。
那時候,我住下城區(qū),家四周絲綢廠比較多,天天路過這些廠區(qū),總能聽到里廂邊機器咣當當,咣當當,很是羨慕。民生藥廠離城區(qū)比較遠,廠區(qū)四周當時還是農(nóng)村,有田,有桑樹,接到錄取通知后,我報到前一天悄悄遛進廠區(qū)考察了一下。記得偌大的廠區(qū)靜靜的,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藥水味,說不上好聞不好聞,廠區(qū)里走的人不多,偶爾遇到的,大多穿著白大褂,神情嚴肅,倒像是做藥廠的樣子。廠里的樹都很高大,馬路也很寬暢,環(huán)境干凈清爽,心里一下子就喜歡上了。
一進廠,我被分到大輸液的蒸氣車間,面對的是數(shù)不清的500毫升大瓶,工作就是蒸氣消毒、配料灌裝。
從76年到現(xiàn)在快退休了,我這輩子都在民生藥廠,前前后后跟過五個師傅。當然,印象最深的還是第一個師傅沈秀清,她是我的第一個師傅,我是她的最后一個徒弟,帶出我后,沒半年,她就退休了。
那天,廠辦領導把我送到調(diào)配車間,指著瘦瘦小小的沈秀清說:這是你的組長,也是你的師傅,以后你就跟她了。那時候的人關(guān)系挺簡單的,就連拜師這樣的大事也沒啥花式,就這樣,簡簡單單的開場白,我平生有了第一個師傅。
沈秀清是民生藥廠的老人了,算起來她應該是公私合營那一撥的職工。那時候,大輸液車間沒什么現(xiàn)代化的設備,就是幾只不銹鋼大桶,放進蒸餾水后,按處方比例添加原液,比如,加5%、10%的葡萄糖,這些全靠手工操作,經(jīng)常是沈師傅看著我調(diào)配方,指出這里那里的關(guān)節(jié)點,做藥的人來不得半點馬虎,那可是人命關(guān)天的事。三個月后,她認為我可以上崗了,才放手。
沈師傅走的時候,廠里舉行了老職工退休歡送會。那辰光,退休是件很光榮的事,好的單位要敲鑼打鼓,送“光榮退休”鏡框、送大紅熱水瓶、臉盆,離開廠時,胸口還要別一朵大紅花。
沈師傅走的時候,最后一次到車間來轉(zhuǎn)了轉(zhuǎn),她拿了塊抹布,東擦擦西擦擦,也不講話,看得我們一幫徒弟心里酸酸的。
在大輸液車間我做了兩年,后來聽說廠里要辦個制藥中專班,憑著高中生的底子,我大著膽子報名,全廠一千多個人,最后有17個人通過文化考試,錄取脫產(chǎn)讀書。我讀的是藥劑學,這個中專班是自己廠里辦的,當時廠里有個教育科,有自己的教師,外聘的也有。經(jīng)過兩年集中學習,專業(yè)知識提高不少,兩年后,回到針劑車間,到了小針部門做實驗,專門做新產(chǎn)品試制,老產(chǎn)品工藝改制。記得民生暢銷很多年的門冬氨酸鉀鎂就是我們這些中專生做出來的,門冬氨酸鉀鎂是電解質(zhì)平衡藥,后來一直生產(chǎn)了二十多年,成為民生藥廠的拳頭產(chǎn)品。
想想老底子的廠,一千多人,開個運動會,搞個籃球比賽都熱乎乎的。廠部還每半個月停工開一次全廠大會,開會的時候,禮堂里黑壓壓一片,書記廠長的聲音透過喇叭洪亮有力。
其實,那時候物質(zhì)生活并不富裕,剛進廠時,我領15塊工資,還有兩塊錢的米貼,印象最深的是年底評先進,上臺領個臉盆,拿張獎狀就開心得不得了。除了工資,平時也沒啥福利,后來,在余杭辦了個養(yǎng)雞場,從那以后,逢年過節(jié),一車車雞拉來,你一只我一只,鬧忙得像集市。別的廠職工看了都眼紅:還是你們民生靠得牢。
你看,一眨眼,當年的青工王貴忠,已經(jīng)快成為退休老頭兒了,再過兩年,我就六十了,民生經(jīng)過幾次改制,已經(jīng)由國營企業(yè)改制成股份制企業(yè)了。像我,退休工資也由社保發(fā),退休后同廠里實際關(guān)系不再像原先國營廠那辰光密切了。
你問我,帶過幾個徒弟?說實在的真的數(shù)不過來,不過我想想,正正式式拜師認徒的有過五個。
2004年后,廠里每年都要舉行“拜師帶徒”儀式,每次開會的時候,也是風風光光的,大紅會標墻上一掛,師傅和徒弟一對一簽字畫押。“拜師帶徒”年年搞,十年下來,有288對師傅徒弟結(jié)了對子,我因為徒弟帶得好,又超過三次以上,被評為內(nèi)部培訓師。
我手里有一張“杭州民生藥業(yè)集團有限公司2008年第五批‘拜師帶徒考核表”。考核表師傅欄里填著“王貴忠”,徒弟欄里填著“黃雙英”,有一段專家評語是這樣說的:“此次拜師帶徒的目標是徒弟掌握小容量針劑產(chǎn)品的配制、過濾、手灌封,封口等技能,以便于對各種產(chǎn)品進行生產(chǎn)前小試,判斷分析小試方案可行性及結(jié)果。師徒間有良好的互動,師傅身兼組長工作繁忙,但仍能細心教導,徒弟也能虛心學習,推陳出新,基本達到了預定的拜師帶徒效果。”
我沒有采訪到黃雙英,聽說她已經(jīng)離開民生了,但她是這樣評價王師傅的:“08年度的拜師帶徒活動已近一年。08年對于師傅王貴忠來說是很繁忙的一年。調(diào)配小組處于缺員狀態(tài),身為調(diào)配分析組的組長,不僅要管理好整個小組,很多工作都要他親力親為。這么繁忙的情況下他還是抽出了時間來教我小試技能。通過一年的學習,經(jīng)過師徒雙方的共同努力,我已熟練地掌握了小容量注射劑的配制、過濾和手工灌封、封口等技能。同時,對小試的目的、方案和結(jié)果能作出分析和判斷。基本達到了拜師帶徒協(xié)議中所規(guī)定的要求,使自己的專業(yè)技能水平又上了一個臺階。應用所學知識,相信在我今后的工作中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第五屆“拜師帶徒”活動結(jié)束的時候,王貴忠又一次拿到了“合格獎”:“……一年來,王貴忠等20名同志,積極履行‘拜師帶徒簽約的師傅職責,悉心傳授,徒弟認真學習,師徒雙方在教學中,知識、技能等都有了長足的進步,為提高企業(yè)各項工作的質(zhì)量奠定了基礎。經(jīng)考核,全部合格。根據(jù)‘拜師帶徒約定,給予王貴忠等20位師傅,每人720元獎勵,給予徒弟適當?shù)奈镔|(zhì)獎勵……”
2014年4月,民生藥業(yè)集團工會在綜合樓大會議室舉行了第十一批“拜師帶徒”簽約儀式,又有26對員工簽訂合約結(jié)拜為師徒,同時,第十批21對師徒受到了表彰獎勵。
民生藥業(yè)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王自強在儀式上說:今年是民生“十二五”發(fā)展戰(zhàn)略的第二年,也是民生“二次創(chuàng)業(yè)”的關(guān)鍵之年,這項“拜師帶徒”活動,既是提高員工素質(zhì)和勞動技能的一種載體,又能培養(yǎng)造就愛崗敬業(yè)和專研的員工隊伍,促進公司的不斷發(fā)展。王副書記要求師傅發(fā)揚傳、幫、帶作用,徒弟要虛心地把師傅的寶貴經(jīng)驗學到手,成為公司發(fā)展的重要人才。
在民生藥業(yè)集團,傳統(tǒng)的師徒關(guān)系被賦予了新的形式,新的內(nèi)容,在這家現(xiàn)代化的著名制藥企業(yè),“拜師帶徒”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血脈得已保留延續(xù)、開花結(jié)果,那種植根人心的師徒關(guān)系沒有因為市場經(jīng)濟而凋謝,沒有因為現(xiàn)代化而疏遠,人際關(guān)系因為師徒的存在而多了一份溫情,因為師徒的存在而多了一份責任與擔當,多了一份尊敬和關(guān)懷。
祖師傅周師洛
1977年2月,當民生藥廠新員工王貴忠喜氣洋洋開始規(guī)劃自己人生的時候,遠在寧波的鄉(xiāng)村,有一個80歲的老人悄無聲息溘然長逝,老人的去世在周圍并沒有引來多少關(guān)注,尤其是他的身世,更不被別人所知曉。直到1984年,當這位老人沉冤昭雪時,人們忽然才發(fā)現(xiàn),哦,原來那個清瘦的周師傅,是一生吃苦無數(shù),赫赫有名的民生藥廠創(chuàng)始人周師洛。
如今,走進民生藥業(yè)集團公司,第一眼看到的,便是這位老人。
我去的時候,周師洛便坐在那里,穿著西裝,大耳大腦門,臉頰清瘦,目光炯炯,不拘言笑。這座半身雕像的底座上,一段介紹非常簡單:周師洛,1897年生于浙江諸暨,1977年病逝于浙江寧波。1926年6月,周師洛等7人籌資創(chuàng)辦了杭州民生藥廠的前身——同春藥房。百年身后事,評說任由人,站在周師洛面前,我想越是簡單的背后越不簡單。
我對周師洛感興趣的倒不是因為他是民生藥廠的創(chuàng)始人,我最感興趣的是:在上個世紀初,在西藥被東洋人、德意志人、美利堅人瓜分的中國,是什么原因成就了民生藥廠的前身——同春藥房?
民國的時候,民族西藥工業(yè)相當落后,只有杭州的“民生”與上海的“海普”、“新亞”、“信誼”,號稱我國“四大藥廠”。正是這四家藥廠,支撐了整個中國的民族西藥工業(yè)。若按創(chuàng)辦時間順序,民生制藥位居第二位;但民生一開始就生產(chǎn)制劑和針劑,是名副其實的西藥廠,應該是國內(nèi)第一家西藥企業(yè)。
現(xiàn)在,我手里握著一份泛黃的珍貴資料,這份行楷印刷的33頁資料的作者不是別人,正是周師洛。這份《經(jīng)營民生藥廠26年回憶錄》,為我們勾畫出一幅近代民族醫(yī)藥工業(yè)的創(chuàng)業(yè)史卷。讓我們隨著周師洛的目光,回到那個動蕩不安的歲月吧。
恍惚中,我看見一個老人,坐在低瓦度昏暗的白熾燈下,正一筆一劃認真地回憶自己和民生走過的非凡道路。
我出生于浙江省諸暨縣吾家塢山村,世代業(yè)農(nóng)。我于1897年(光緒23年)出生,六歲時,大哥進取清朝末科秀才在家辦私塾,我七歲上學于大哥處,1912年畢業(yè)于翊忠高小,1915年畢業(yè)于諸暨縣立中學。那時二哥要我進師范或法政,因家中常遭地主惡霸的欺侮,倘我進師范法政后可以結(jié)交一些官僚豪紳,家中可以免受別人欺侮。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因師范畢業(yè)只能做個教員,法政畢業(yè)只能做個律師,還不如學醫(yī)藥和工業(yè),可以自力更生發(fā)展生產(chǎn)。遂于1917年考入浙江公立醫(yī)藥專門學校藥科,1919年與連瑞琦等參加過五四運動,至1920年夏畢業(yè)。畢業(yè)后與同學湯伯熊、姚典、馮繼芳等到諸暨開設諸暨病院,我負責藥局,至1922年因族侄周恩溥醫(yī)專畢業(yè)后,留日回國,開設同春醫(yī)院,邀我去主持藥局,我就到杭州同春醫(yī)院,七月浙江公立醫(yī)藥專門學校成立附設診察所,我由老師周冠三介紹擔任該所藥局調(diào)劑員。1923年春杭州第一師范發(fā)生中毒案,街頭巷尾傳說紛紜,謂系狐仙作祟,我未信之,去該校視察,情況非常嚴重,系頭天晚膳中毒,全校六七百人,幾無幸免,當即建議校長何炳松,化驗飯食,結(jié)果證實為砒霜中毒。當即用砒石解毒急救,因毒太重,定量結(jié)果,每碗內(nèi)砒霜含量達到致死量的六至七倍,雖經(jīng)急救,而死者竟達二十八人。事后確認,砒霜系該校會計貪污事發(fā),懷恨下毒。
從回憶錄上看,當年杭州第一師范中毒案對周師洛走上制藥道路起著不同尋常的作用,他意識到:沒有好藥化解,只能眼睜睜看著28人死于非難。
后來,周師洛經(jīng)朋友介紹,進入杭州中英藥房擔任藥師,除配方外,同時試制針藥,供應醫(yī)師和部隊的需要。所用設備因陋就簡,沒有煤氣燈,安瓿封口就用酒精燈裝上吹管和二連球送氣,試制成功后,周師洛建議老板擴大生產(chǎn),屢遭拒絕,萌生了辭職自辦藥廠的念頭。
一個窮孩子要辦藥廠幾無可能,好在周師洛有幾個鐵哥們。1926年6月,周師洛和當年藥科同學范文蔚、沈仲謀、周思溥、馮繼芳、陳樹周、田曼稱等七人決定籌資一萬銀元,創(chuàng)辦“同春藥房股份有限公司”,囊中羞澀的周師洛回老家向大哥借田二畝六分,抵押得現(xiàn)款250元,再向股東韓士芳借得250元入股。因股東大多是醫(yī)藥界和醫(yī)專同學,所以業(yè)務發(fā)展迅速,起家時主要販賣國外的醫(yī)藥原料和化學藥品,同時開始制造針藥和各種成藥丸散膏丹等,以民生制造廠化學藥品部名義出售。獲得資金后逐漸轉(zhuǎn)向制造,以國貨抵制外貨,滿足國內(nèi)需要。
1927年,一筆軍隊的采購大單給民生制藥提供了發(fā)展機遇。那年,國共合作后,北伐軍來到浙江,由白崇禧為東路前敵總指揮的部隊先到杭州,他的軍醫(yī)處長李鏡湖是醫(yī)專同學,就向同春藥房采購衛(wèi)生材料三萬元。
周師洛冒險接下了這一大單,派人轉(zhuǎn)道寧波、上海采購,貨到款清在醫(yī)藥圈內(nèi)樹立了良好口碑。后來,上海的中英、五洲、華美、中西、中法、萬國、科發(fā)、濟華堂等藥企都紛紛委托同春藥房代銷,代銷的好處就是銷售款項可以有三四個月的沉淀期,資金一活,民生的生產(chǎn)有了資本,慢慢有了自己的廠房,有了自己的品牌。
從同春到民生,周師洛是怎么想的?
民生藥業(yè)集團公司總部的一樓有一個企業(yè)展覽廳,里面收藏著一些民生藥廠珍貴的史料,其中就有一份當年《民生醫(yī)藥》的創(chuàng)刊詞,周師洛在其中闡發(fā)了自己關(guān)注民生、醫(yī)藥救國的思想。
“民生”為三民主義之一,意義的重大,事實的需要,先總理“三民主義”一書中,早已經(jīng)昭示我們了。
“醫(yī)藥”直接關(guān)系到每個人生命,常言道,好死不如惡活,沒有劇烈的刺激,誰也不愿自尋死路。可是英雄只怕病來磨,于此而需求救濟,便不得不乞靈于醫(yī)藥。
“東亞病夫”是我們中華民族最不名譽的一個綽號。醫(yī)藥的不深求,不進取,影響于民生極大,這個綽號,便成了世襲似的,而永遠地無法卸除。
是的,事實告訴我們,天災人禍,民不聊生,醫(yī)藥學術(shù),淪落人后,民窮財盡,更無力于求醫(yī)藥,有心人都興著其亡之嘆,然而處于驚濤駭浪之中,豈是一嘆可了的么?必也人盡其職,分工合作,奮力前進,殊途而同歸,“醫(yī)藥”“民生”也許可獲最后的成功!
……
但激情澎湃的周師洛怎么也沒想到,醫(yī)藥救國的道路竟是如此的曲折艱辛。
1926年6月,民生藥廠初創(chuàng)時期經(jīng)歷了軍閥戰(zhàn)亂幸存;1928年2月,一萬七現(xiàn)大洋在上海采購藥物時被盜,幾乎置民生于死地;1933年淞滬大戰(zhàn)爆發(fā),局勢動蕩,民生又一次面臨經(jīng)濟危機;1937年12月,杭州淪陷,為了避免日偽政權(quán)的控制和利用,周師洛響應省政府令,把民生藥廠分批撤出杭州,輾轉(zhuǎn)于蘇浙皖閩贛五省,八年抗戰(zhàn)經(jīng)歷了無數(shù)磨難,直到抗戰(zhàn)勝利回遷。
1949年,民族大義在周師洛身上再一次閃光,當時,國軍潰敗逃臺,董事長羅霞天極力主張把工廠遷往臺灣,周師洛嚴詞拒絕。由于他的反對,“民生”得以在大陸幸存。
解放以后,民生藥廠和大多數(shù)舊社會過來的企業(yè)一樣,經(jīng)歷了“公私合營”、“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地方國營工廠。周師洛的人生也因為“三反五反”于1952年墜入谷底,蒙冤32年,那是后話。
后來的民生藥廠,假如周師洛還能活著見證,一定會開心釋懷。1985年,他一手創(chuàng)辦的民生藥廠,經(jīng)歷了無數(shù)風雨后,又從杭州第一制藥廠更名為民生藥廠,那些日子,舉國上下,誰人不知“21金維他”?一家心系“民生”的企業(yè),以赤誠之心,把抗腫瘤類藥、抗心血管病類藥、治療肝病用藥、大輸液等源源不斷交給急需的患者手里。
2013年12月16日,臨平大道36號的民生新廠彩旗飄揚,鞭炮齊鳴。這座總體投資7億多,占地11.4萬平方米,建筑面積12萬平方米的新廠,嚴格執(zhí)行了國家新版GMP要求,建立了現(xiàn)代化的各類針劑、輸液、片劑、膠囊等制劑和眼藥外用藥等生產(chǎn)廠房及其他各輔助設施,設計產(chǎn)能比老廠區(qū)提升兩至三倍,設計年產(chǎn)值近20億元。
董事長竺福江站在新廠房的土地上對員工們揮臂感言:功崇惟志,業(yè)廣惟勤。民生人要將搬遷新址作為一個新的歷史起點,面對新機遇與挑戰(zhàn),堅守“發(fā)展企業(yè),貢獻社會,造福員工”的宗旨,堅守盡心盡力盡責的精神,把企業(yè)做好做強。繼續(xù)發(fā)揚堅韌不拔、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努力實現(xiàn)民生人的“三個夢想”,為人類的健康事業(yè)和地方經(jīng)濟做出新的貢獻。
歷史常常和我們開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比如民生藥廠,這家流淌著中國企業(yè)家實業(yè)興國,西藥中興夢想的藥企,在創(chuàng)設之初以股份制企業(yè)走入市場,在歲月更替中經(jīng)歷了公私合營、地方國營、廠長負責制等等體制改革后,最后又回歸到原點,成為一家現(xiàn)代股份制企業(yè)。當然,如今的民生藥業(yè),不再是周師洛他們的私人股份,如今的民生,更多寄托了民生人再次創(chuàng)業(yè),走出國門的理想。
離開民生的時候,我又站在周師洛面前默默對視,西下的陽光正透過巨大的玻璃門溫暖地灑在他的身上,有了陽光,周師洛的嘴角仿佛多了一絲笑意。
我想,如果在民生藥業(yè),想找一位“最老的師傅”聊聊,那便一定是他了,周師洛,一位有著民族工業(yè)振興夢想的中國藥師傅。
臺灣師傅王昭日
世上的藥,傳說都是“神農(nóng)鞭草”而得。
中藥服務華夏數(shù)千年至今仍深得國人信賴,只是在現(xiàn)代制藥面前,“神農(nóng)鞭草”早已過時,中藥西制,擺脫陶罐煎取的束縛也早已成現(xiàn)實,提煉、粹取中藥主要藥用成分,便是現(xiàn)代“神農(nóng)”們的工作。
在臺灣獨資的杏輝天力藥業(yè)公司,我意外發(fā)現(xiàn)了一味傳奇的中藥,同時也結(jié)識了臺灣師傅王昭日。
說起這味藥的獨特,是因為這味藥是江湖上傳聞很神奇的壯陽神藥:管花肉蓯蓉。也有一種說法它是“沙漠人參”,傳說成吉思汗就是吃了它,轉(zhuǎn)敗為勝,神勇殺敵,最后統(tǒng)一了蒙古,開創(chuàng)了新時代。
在大陸拓疆十多年的杏輝天力總經(jīng)理游能盈先生是個白面書生,說起肉蓯蓉,他更是如數(shù)家珍:肉蓯蓉只寄生在沙漠的梭梭林根系上。杏輝天力或許是第一家在大陸從事肉蓯蓉制藥的廠,早在2002月,他們就在新疆于田縣創(chuàng)辦了“和田天力沙生藥物開發(fā)有限責任公司”,現(xiàn)在有500畝科研基地和5.7萬畝GAP生產(chǎn)基地。
但從管花肉蓯蓉中提取有效成分卻不是件簡單的事。
在遠離新疆萬里之遙的杭州,杏輝天力藥業(yè)集團有著體量巨大的廠房,那些方方正正的巨大“盒子”被掩藏在高大、修剪得精精神神的柏樹后面,在這里,我沒有聽到機器轟鳴的聲音,也沒看到工廠慣有的高矗煙囪,當然,也沒看到肉蓯蓉如何從植物成為齏粉的過程,因為工廠有著極嚴格的防菌要求,不便參觀。
其實,我內(nèi)心對臺資企業(yè)的經(jīng)營模式更感興趣:這里的師傅又是怎么帶徒弟的呢?
王昭日博士就坐在我跟前,他是臺灣來的師傅,是杭州杏輝天力研究所的所長,奔五的人,長得白凈、壯實,顯然,因為是初次見面,有點局促。
我們公司也有師傅帶徒弟啊,只是說法不一樣,臺灣人叫技傳,而且有一套嚴格的制度規(guī)定。
在杭州杏輝天力最核心的部門要數(shù)我們這個研究所了,全所25人,三個博士,兩個是本地的。
我到大陸才一年,原來在臺灣總部做研發(fā),總部搞研發(fā)的人比較多,有一百多人。我的課題主要就是中草藥這一塊。杏輝天力是一家跨國公司,除臺灣總部外,加拿大有一家,大陸有杭州和新疆和田兩家。
說到技傳,我們大多是老師和學生一對多,每個學生也是同仁,他們專長不一樣,個性也不一樣,必須用實際行動去幫帶。醫(yī)藥研發(fā)和傳統(tǒng)技能不一樣的地方是:科技上的東西更適合以老師帶學生的方式傳授。在杏輝,我建立了一套技術(shù)標準、體系,遇到問題,不是先告訴他們怎么做,而是首先讓他們?nèi)ゲ檎屹Y料,自己討論尋求解決的方式。比如在植物有效成分提取上,我會先要求功效做一個報告,提取做一個報告,專利可行性再做一個報告,在完成報告評估后,請同仁再往下做,做的時候就開始做分工了,提取的專門做提取,分析的專門做分析。
王昭日是三個孩子的父親,也是臺灣醫(yī)學界的資深博士,但從他身上卻看不到絲毫權(quán)威的傲氣,用新員工黃佳慧的話說,他更像一個大哥哥。
這位“大哥哥”討人喜歡的一面是總能和80后玩到一處,附近的黃山、塘棲、周莊、西湖景區(qū)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特別是當課題遇到瓶頸時,王昭日會帶著他的團隊出去“放松放松”。那次,ST02項目又卡住了脖子,大伙想盡了辦法,提純度依然達不到生產(chǎn)所需要的標準。第二天是雙休日,王昭日建議去不遠的上海金山“放松放松”。
和往常一樣,大家聚在一處喝茶,聊天,忽然,不知誰高高舉起茶杯說:假如把溫度提高十度二十度,再改進一下過濾回流的辦法,ST02會不會提高提純度呢?大伙一聽興奮不已,你一言我一語,“放松”活動又成了學術(shù)研討會,于是急急結(jié)束了“放松”趕回實驗室。
果然,這一實驗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連師傅王昭日都直拍腦袋:我怎么就沒想到呢,我怎么就沒想到呢。
杏輝天力研究所里,大多數(shù)是70、80后,這些獨生子女出生的員工身上,有著與他們父輩不一樣的獨立性,少數(shù)人還缺少團隊精神。一次,王昭日從臺灣回來,除了帶回臺灣特產(chǎn)外,還帶了一包書名叫《執(zhí)行力》的書,這是一本在臺灣企業(yè)很有影響的書,他覺得企業(yè)目前最缺的就是執(zhí)行力。他像發(fā)臺灣特產(chǎn)一樣把《執(zhí)行力》發(fā)到每位中層干部手上,又按照全書九個章節(jié),讓他們?nèi)芜x一個章節(jié),做一次讀書分享報告。同時,他讓員工投票打分,評分高的,獎勵購書券一張。這件事,前后花了九個禮拜,最后得到的效果喜人:大家都愛看書了,企業(yè)執(zhí)行力文化也無形中得到了加強。
走進現(xiàn)代化的杏輝天力,依然能感受到濃濃的儒家文化細節(jié),比如高大門樓的兩側(cè),置放著一人多高的花瓶,寓意“進出平安”;而門廳里,最顯眼處還供著一尊觀音像,觀音前電子蠟燭長明著,因為不是特別的日子,香爐里剩著燃盡了的香尾巴,三只酒杯是空的。這些,總讓人聯(lián)想到這些擺弄高科技設備的人,心里存續(xù)的對神靈的敬畏。
我對總經(jīng)理打趣說:您的名字很好啊,姓游,名能盈,就是說走到哪里都能贏啊,大伙聽得哄堂大笑。
杭州杏輝天力就是游總?cè)谈M落地的項目,杏輝與杭州結(jié)緣已久。1999年臺灣大地震的時候,他們收到一份特殊的問候。原來,先前他們在考察杭州時,與老余杭一家叫天力的醫(yī)藥企業(yè)有過接觸,沒想到,當臺灣遭災時,天力老總專門發(fā)來郵件表示慰問。
隔年西博會的時候,游能盈和總經(jīng)理受邀來到杭州,有點時間,就一起去老余杭拜訪天力,應了那句無心插柳柳成蔭的老話,聊著聊著,僅一個星期,雙方就談妥了杏輝出資1700萬收購天力的方案。這家由國企轉(zhuǎn)制而陷入困境的企業(yè),迎來了新東家,游能盈對一百多名員工說,新廠房在余杭新區(qū)建成后,有職工宿室,我們熱烈歡迎老員工過來。結(jié)果,天力80%老員工都穿過整個杭州城市跟了過來。
“杏輝”是“心靈光輝”的別稱,早在1977年臺灣起家的時候,杏輝人便在企業(yè)文化高地確立了兩個字:誠與靜,誠以待人,處事以靜。
游能盈說,在杏輝,企業(yè)文化最重要的底色,就是最最簡單的三句話:請,謝謝,對不起。簡單的禮貌用語正是構(gòu)建人與人之間和諧關(guān)系的基礎。這家只有163名員工的企業(yè),2014年的產(chǎn)值達到1.1億元。
杭州是個宜居的城市,從2010年開始,每年十一月都要舉辦國際馬拉松賽,這已成為國內(nèi)最重要的馬拉松賽事之一。
自從杭州有了馬拉松賽事以來,杏輝天力總會第一時間報名參加,他們把它當作一年一度的企業(yè)文化來經(jīng)營。
2013年11月3日,西子湖畔拉起了警戒線,人們在道路兩側(cè)為奮力奔跑的參賽者加油,前頭跑得快的,有人已經(jīng)穿過湖濱步行街跑到了南山路了,跑得慢的,還落尾巴掉在北山路一帶。
師傅王昭日穿著短衫短褲,跑在杏輝天力隊的最前頭,他不時回頭,大聲喊著:保持節(jié)奏,調(diào)整呼吸,不要搶快,慢一點,堅持就是勝利。
這一天,杭州的天格外藍,碧空如洗,陽光溫暖,秋天的金黃把素顏西湖裝點得色彩斑瀾。
采訪結(jié)束的時候,王昭日笑著說:馬拉松最考驗人的意志力,只要還能跑,杏輝人永遠都不會放棄奔跑的機會。
法國師傅衛(wèi)平
印象中法蘭西是一個浪漫多情的民族,但法國雜志《Esprit》編輯Paul Thibaud自豪地說:“我們有多么視自由和平等為權(quán)利,就多么有義務以博愛去尊重他人。”
醫(yī)者仁心,制藥的人也應該有一顆博愛的心。
走進杭州賽諾菲民生,我被大門前一座黑色的大理石紀念碑所吸引,這座紀念碑上用金字鐫刻著中法英三國文字:深切緬懷賽諾菲亞洲區(qū)高級副總裁衛(wèi)平(1968-2011)。
長得小巧優(yōu)雅的代萍萍總監(jiān)告訴我:賽諾菲在中國有六家生產(chǎn)基地,六家基地的大門前,無一例外都安放著這塊統(tǒng)一制作的紀念碑。
衛(wèi)平是誰?衛(wèi)平怎么啦?
在代萍萍眼里,衛(wèi)平(Thomas Kelly)是個地地道道的中國通,他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更不容易的是他的骨子里,早已融入了中國文化。從1993年入職西安楊森,到后來的諾和諾德,再從先靈葆雅到賽諾菲-安萬特,衛(wèi)平深耕中國藥業(yè)幾十年,從藥企市場拓展一直做到中國區(qū)賽諾菲副總裁。
衛(wèi)平在中國高速拓疆擴土,他領銜賽諾菲后,每一天都在中國的天空上飛翔。衛(wèi)平堅信中國代表著未來,中國的發(fā)展只有一個方向,那就是前進,前進。更好的醫(yī)療服務,更好的藥品會給富裕后的中國人帶去最重要的東西:健康。
拼命三郎法國人衛(wèi)平把整個中國市場拓展計劃細化到具體的幾百個城市,如果不是因為太過勞累英年早逝,他所領導的賽諾菲會如他的夢想,讓法國和中國的聯(lián)系從未有過的緊密。
從1982年進入中國市場以來,賽諾菲這家在全球有11萬員工,業(yè)務遍及全球100個國家,112個生產(chǎn)廠家的跨國醫(yī)藥企業(yè),僅2012年度凈銷售額就達349億歐元。
一直堅持“超高超快增長”發(fā)展思路的賽諾菲,在中國大肆招兵買馬,并購企業(yè)、建立工廠。2010年,賽諾菲與杭州民生藥業(yè)組建了合資公司,核心資產(chǎn)包括民生藥業(yè)的拳頭產(chǎn)品“21金維他”。接著,又在2011年以5.206億美元收購了藥品生產(chǎn)商兼分銷商太陽石集團,并借此擁有了國內(nèi)最大的小兒感冒咳嗽藥品牌“好娃娃”,同時也擁有了太陽石集團在感冒咳嗽和女性健康領域的強大平臺。
這兩項交易使賽諾菲獲得了渴望已久的品牌和渠道。2012年,賽諾菲在華銷售額超過10億歐元,成為中國第三大處方藥物公司和第一大跨國疫苗公司。
被賽諾菲CEO魏巴赫稱為“賽諾菲的核心市場”的中國,正在逐漸成長成為這家法國醫(yī)藥企業(yè)可靠而巨大的盈利支柱。
2011年11月3日,在山東忙于收購太陽石的賽諾菲中國副總裁衛(wèi)平因心臟病不幸謝世。
這位法國師傅的離去,并沒有影響賽諾菲在中國的布局腳步,截至2012年底,賽諾菲在中國擁有7000名員工。并在上海建立了研發(fā)中心,北京、成都配備了研發(fā)團隊,具備了從藥物靶點發(fā)現(xiàn)到后期臨床研究的整體研發(fā)隊伍。
如今,我還能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讀到衛(wèi)平在中國各地與政府官員見面、商談的新聞,還能看到他和媒體互動的鏡頭,可惜,那位充滿活力的法國人現(xiàn)在只活在賽諾菲人的記憶里。
與浪漫主義不同的是,在賽諾菲民生,我只看到兩個字:嚴謹。
總監(jiān)代萍萍的辦公室墻上,我被密密麻麻的中英文提示所吸引,那塊叫做QC管理看板的黑板上,標注著賽諾菲民生的生產(chǎn)計劃,存在問題,各項進度。可以說企業(yè)各條線匯聚的所有問題、目標管理都集中在這里,可以說,總監(jiān)辦更像是一場戰(zhàn)役的指揮中心,而代萍萍墻上的QC板,無疑是作戰(zhàn)地圖了。
這是我在其他藥企所不見的,如果你以為這只是總監(jiān)才有的QC板,那就錯了,在后來的走訪中,從科室到最基層的操作間,墻上無處不有QC看板,法國企業(yè)文化中的嚴謹,在這里被發(fā)揮到了極致。
賽諾菲和民生藥業(yè)好比一對模范夫妻,早在1995年,賽諾菲安萬特就曾牽手民生制藥有限公司,到了2010年,民生藥業(yè)以拳頭產(chǎn)品“21金維他”作為嫁妝,按4:6比例共同成立了“賽諾菲民生”合資公司,現(xiàn)如今,民生藥業(yè)和賽諾菲民生共伴共生,卻因為文化基因的不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企業(yè)文化。
和“21金維他”一起嫁到法資控股 “賽諾菲民生”的,還有當時幾十位民生藥業(yè)的“老人”。
我叫孫華強,57出生,全家兩代都是民生藥廠職工,我父親今年84歲了,叫孫壽炎,解放前就在民生制藥廠工作,說起來還是民生的中層干部。我是77年進入民生藥廠的,實際上,74年就算民生藥廠的人了,為啥呢?因為當年城市青年都要上山下鄉(xiāng),為了不讓子女到邊疆吃苦,也算是規(guī)避政策吧,民生藥廠和富陽萬仕那邊一個公社簽訂了協(xié)議,租了一塊土地,搞廠社掛勾,把我們十個民生職工的子女下放到萬仕接受貧下中農(nóng)再教育。
“文革”結(jié)束后,我就作為知青回到了民生藥廠,眨眼就是一輩子。兩年前,我從賽諾菲民生退休了,退休后又返聘回賽諾菲工作,你問我為啥愿意返聘?其實想聘我的杭州藥廠很多,有的開的條件也很高,但我還是愿意每天來來去去坐二三個鐘頭到賽諾菲來做,為啥?一是我對賽諾菲有感情,二是賽諾菲能給我除了鈔票以外的東西,比如尊嚴。
我這一輩子跟過兩個師傅,一個是李海龍,現(xiàn)在還在民生藥廠做采購物流經(jīng)理,另外一個是張志良。在民生藥廠跟師傅還是老傳統(tǒng),多少帶著點師徒感情,而在法國企業(yè)里,一切都是有量化標準的,哪一道工序怎么做,程序怎么樣,標準怎樣都非常具體,上崗前都會集中培訓,每個崗位墻上也都有QC板,細化到每個人都清楚自己做什么,怎么做。可以這樣說,只要識字,只要嚴格按標準化程序操作就不會出錯。
在賽諾菲我也當過師傅,但我們這一輩人文化不高,外語也看不懂,主要是講具體操作的經(jīng)驗,一般都是集體上課,賽諾菲這點讓我很佩服,他們有個分級制度,每個辦公、工廠區(qū)域都是用指紋開門的,你沒有這個區(qū)域的權(quán)限,就進不了這個區(qū)塊,同樣,每個區(qū)塊的員工只要做好做精本職工作就可以了,不需要額外學習更多的生產(chǎn)技能。講得通俗一點,賽諾菲民生好比一架精密的機器,每個員工就是機器上固定的一個零件,只有每個零件良好,才能保證機器優(yōu)質(zhì)高效運轉(zhuǎn)。
70后韓獻偉是浙江金華人,大學畢業(yè)后,他一直在杭州幾家外資企業(yè)的設備動力部門工作,來到賽諾菲民生后,他分管著整個生產(chǎn)基地的設備管理。說起賽諾菲,他認為賽諾菲全球就像一個大家庭,你在這里生活,工作,成長,只要努力,你是有空間的。去年,印度賽諾菲一個小伙交流到杭州工作了一年,回去擔任了更好的職位,而他,也因為賽諾菲,有了一個法國女兒。
原來,賽諾菲集團有個為期兩周的暑期子女交換項目,這個交換項目規(guī)則是:只要是賽諾菲員工,子女年齡在12至18周歲,都可以通過官網(wǎng)報名,輸入孩子年齡,性別和選擇交換的國家。交換周期為兩周。
2013年3月,韓獻偉給孩子在官網(wǎng)報了名,兩周后集團負責交換項目的主管Annie發(fā)郵件給他,提供了法國賽諾菲一位愿意來中國參加暑期項目的孩子的信息,通過郵件溝通,雙方父母達成了交換意向。
韓獻偉后來的法國“女兒”叫Ellisa,12周歲。去年7月6日Ellisa乘飛機來到中國,到中國父母家后,Ellisa對一切非常好奇,吃慣了西餐的她對中國菜更是贊不絕口。
中國“爸爸”帶著Ellisa游遍了西湖、運河,還帶她去博物館了解中國燦爛的歷史文化。
游完杭州不算,中國“好爸爸”還特意安排兩個孩子到北京旅游,把故宮,長城看了個遍,兩周后,Ellisa要分別了,韓獻偉為Ellisa一家人精挑細選了絲綢、茶葉、工藝傘等紀念品,登機的時候,Ellisa緊緊抱住韓獻偉,流著淚戀戀不舍。
八月,韓獻偉也把女兒送上了去往法國的飛機,在法國,法國“父母”也領著她游覽了世界最浪漫的都市,女兒在電話里大聲說:爸爸,我爬上埃菲爾鐵塔了,我還看到凱旋門,好高好大啊,我還去了盧浮宮,里面的油畫真漂亮。爸爸,法國的天好藍好藍啊,河水也特別特別清。Ellisa一家人還帶我去吃了法國奶酪,吃了法國大餐,爸爸,我好幸福啊……
電話這頭,韓獻偉聽著聽著都醉了,兩個12歲的孩子,在她們最純真的年代,種下了兩顆美好而快樂的友誼種子。而這一切,都受益于賽諾菲全球大家庭。
這是一個人人都可以成為師傅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師傅口語化的時代,假如在菜場,假如在馬路上,假如有人大聲在你背后喊你一聲“師傅”的時候,千萬別激動,這時候,師傅,只是代表了一個隨意的稱呼符號。
歷史像一駕信手由韁奔馳的快馬,載著我們飛快地前行,一些手工行業(yè)早早被我們拋棄在歷史的煙云里,而與那些時代相生的稱謂,比如師傅,已經(jīng)不再具有原來的內(nèi)涵。
但在工廠里,在企業(yè)里,師傅,這個稱呼,永遠都會帶著他們從心底里流出的尊重。
那是真的師傅。
責任編輯 孫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