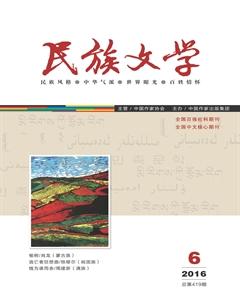逃亡者狂想曲
鐵穆爾
“我們從塞吉哈吉①逃亡到祁連山后不知過去了多少年?究竟有多少年了?”雙眼發紅的車凌敦多布一邊問我一邊緊盯著面前那張已經破舊的《亞歐大草原》地圖。不知道多少次了,今天他還是和從前一樣,眼睛從興安嶺掃到黑海、多瑙河和伏爾加河。又從西伯利亞凍土帶看到吐蕃特高原和萬里長城。那目光好像要點燃整個亞歐大草原。
車凌敦多布和我一樣都是祁連山中這個逃亡族群的一員。在夢中,我們就像騎著傳說中的宇宙之馬——乃曼塊勒圖乃日拉合②縱橫世界。遼闊的大地讓我們心醉神迷,但傳說中的那個善良溫情的人道世界卻又是那么遙不可及。
我和車凌敦多布的這個小小族群,在吐蕃特高原東北邊緣的群山中,具體說就是祁連山的群山草原以及山下的戈壁沙漠。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小小的族群就是亞歐大草原游牧民族的一個縮影。草原游牧民族的包容多元從這個小小族群復雜的族源譜系中一目了然——它濃縮了突厥系和蒙古系的幾大主要氏族。從歷史中了解到,鐵猴年③(公元840)的回鶻汗國,戰場上一敗涂地,接著又是大雪災,很多人都從蒙古高原絕命逃亡。數百年之后,又在無人知曉的塞吉哈吉九死一生,到祁連山下的三個巴彥巴斯圖④山川之間絕處逢生……
水猴年(1992)春天,堯熬爾⑤人乃曼部落安江氏族的洛布桑的老人,在紅灣寺小鎮那個紅色山崖下的小磚房里,坐在沙發上給車凌敦多布誦說了堯熬爾創世史詩《沙特》。
在久遠的往昔
天地還沒有形成
后來在一個茫茫大海中形成了天地
最初天地在一個金蛙身上
金蛙降臨宇宙
……
這是史詩《沙特》的開頭幾段,《沙特》說到了天地宇宙的形成,人類的起源,對文明和信仰的追求。同樣內容的史詩,在藥羅葛和呼朗格部落的堯熬爾人中,史詩名字叫做《尤達覺克》。《沙特》和《尤達覺克》是兩部堯熬爾人的精神瑰寶。住在夏日塔拉草原的林木措奶奶,她家的冬窩子在斡爾朵河東岸。她給車凌敦多布講述的是另一個版本的《沙特》片斷。
當天地一片混沌時,人們生活在一只巨大的金蛙頭頂。
金蛙眨眨眼便要大地震動翻江倒海。
汗騰格里向大地灑下黃金白銀和鐵,但禁止人們因挖這些金屬而讓大地母親于都斤·額客受傷。
但是人們仍然挖金屬,這樣傷害了大地母親于都斤·額客的身體。
于是在一片洪水的懲罰中人類滅亡了,天地間只剩下了一匹白馬,一個孤兒和一只白鳥。
孤兒吃著白馬的奶和白鳥銜來的食物長大了。
白馬后來老死了,孤兒用白馬的骨頭、馬尾和木頭制作了茂日英胡爾琴,琴聲就是模仿白馬的嘶鳴聲……
林木措奶奶說大洪水后,天地在大海中形成,人類從南瞻部洲形成后就在逃亡,為了逃出災難逃出死亡。大洪水之后,人類只剩下一個善良的男孩。這個善良的男孩逃亡到一個四周都是汪洋大海的小島上,從此又繁衍了人類……
我和車凌敦多布認為,人類在大洪水中逃亡的歷史說得很清楚,人類的毀滅不是因為技術和知識,而是因為精神生活的缺位和道德的淪喪,所以人類在宇宙生存競爭中遠不僅僅需要技術和知識,更為重要的是精神和思想。
車凌敦多布的書信、日記和筆記中也常說到大洪水和逃亡等。下面是他的書信摘錄:
從傳說中的大洪水時代的逃亡,到堯熬爾人的祖先匈奴人從南西伯利亞的泰加林中逃亡到了蒙古草原上,然后在神圣的鄂爾渾河和于都斤山麓發祥,建立了匈奴、突厥、柔然和堯熬爾兀魯斯——回鶻汗國,鐵猴年(公元840)汗國崩潰,堯熬爾人從蒙古高原逃亡,幾百年后,他們和內亞所有的游牧人一樣經歷了游牧人達到頂峰時的歷史——“蒙古和平”時代(13世紀)。又過了幾百年,一支堯熬爾人又從賽吉哈吉逃亡到了眼前的祁連山……
逃亡的路上共同的命運讓這些使用不同語言的人們都自稱為堯熬爾。逃亡者們說“堯熬爾”一詞的意義就是“天下一家”,就是“大地上的逃亡者聯合起來”。
逃亡的確會讓人們在精神上聯合起來嗎?我不知道。
堯熬爾人逃亡了多少年?生存和死亡,尊嚴和自由,希望不滅,逃亡不止。自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我就在牦牛毛織成的黑帳篷里,在牦牛奶做成的酥油和酸奶美妙的味道中,品咂到了一種逃亡者令人心碎的哀傷,同時更有無限的幻想、希望和憧憬。這種哀傷和憧憬也在歌謠《阿爾泰杭蓋》和史詩《沙特》中彌漫著……我在逃亡者的這種凄迷的憧憬和幻想中長大,伴隨著我的還有逃亡者的孤獨、身份認同的困惑,和逃亡者喪失習俗禮儀和歷史記憶的悲哀。
當年我們的祖先匈奴人,那些失敗的英雄在逃亡時有一個絕唱,就是后來有人譯成漢文留傳下來的《匈奴歌》:“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這真是我們的祖先匈奴人的歌嗎?翻譯的準確嗎?這些都是無法破解的謎。但在我內心里覺得這首歌確實是典型的游牧人思維,我相信這首歌是匈奴人或是月氏人烏孫人的歌。歌里說的仍然是那個永恒的問題——生存還是死亡。那么在歌里面沒有說的還有什么呢?那是離開祁連山或焉支山的逃亡者們不滅的希望,他們要逃亡到遙遠的地方,去尋找讓六畜(堯熬爾人認為是五畜)能蕃息,讓女人們更加美麗的草原。沒有時間猶豫彷徨和流淚哭泣,一聲長嘯絕塵而去。逃亡就是這個苦難大地上的生存狀態或策略,逃亡就是戰略轉移。只有逃亡才能讓人類產生無窮無盡的能量源。
在亞歐大草原上,從神圣的鄂爾渾河和于都斤山麓一直向西或向南的有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堯熬爾人(回鶻人)、蒙古人。在歐洲有自詡為文明人的羅馬人所說的“蠻族大逃亡”,就是從東方來的匈奴人導致了日耳曼游牧部落的西遷或者說逃亡。在非洲和西亞,還有偉大的摩西帶領希伯來人從埃及進行的那場偉大的逃亡,為了尊嚴和自由,劈開紅海越過沙漠,摩西充滿了無限的希望。逃亡就是希望。逃亡就是地球深處的呼喚。
逃亡讓我聯想到了撤退、轉移、妥協,這一切都和進攻、占領是一樣偉大的生存方式,為了最終取得勝利或變得強大。游牧人的逃亡或撤退不是消失或滅亡,而是抓住稍縱即逝的機會再次攻擊,取得最終的勝利。這是游牧文化的精髓之一。在逃亡、毀滅和妥協中重新復活。當然那是另一種方式的復活,復活之后也許和從前的面貌迥然相異。但那是一個新的生命。匈奴人在東方失敗后,又在歐洲的土地上崛起,在西方失敗后,過了一個漫長的時間他們又成為偉大的匈牙利民族……
人在逃亡中那些渺小而猥瑣的東西往往會消失的干干凈凈,多余的想法和多余的語言只會讓人們倒霉甚至帶來噩運,而自私自利、斤斤計較和互相傾軋會毀掉整個逃亡者們。逃亡者們需要最好的內心素質,就是勇敢、智慧和善良,就是遠大的眼光、開闊的胸襟和堅定果斷,逃亡路上如果沒有這些必不可少的品質就去等待死亡吧。
人類歷史因美妙而凄慘的逃亡而風生水起,滿懷憧憬的逃亡使人類的精神強大和美麗。逃亡令人懂得,生存不僅需要技術和知識,精神更為重要。逃亡是對于未知世界的探索,只有無盡的未知,才能讓人類更新已有的知識,更換舊的精神結構,逃亡是為了對抗毀滅。逃亡是不甘心于子孫被毀滅,不甘心于平庸和死亡。
人類在精神上也在不停地逃亡,沒有人能擺脫這份永恒的漂泊。世界像一條大路,世人都在那里逃亡,步行、騎馬、汽車、火車、輪船或飛機,匆匆又匆匆。迎面走過,擦肩而過,點頭招手,擁抱親吻,盛宴聚會,死亡出生,殺戮壓迫……不知道逃向哪里?所有活著的人都在逃亡,直到末日之后,重建那個人道或愛的大宇宙。宇宙最大的能量是愛。宇宙從愛生,最終也將歸入愛。
堯熬爾人曾經使用過自己的先輩創造的古代突厥文、古代回鶻文,后來又使用過八思巴文和吐蕃特文,在不斷游牧、遷徙或逃亡的歷史中,他們漸漸成為一個小小的邊緣族群,隨著逃亡的歷史不斷轉換著自己使用的文字。自從他們逃亡到了吐蕃特高原的東北邊緣——祁連山的陰坡和陽坡,那一度與世隔絕的深山老林和山下的戈壁沙漠上,他們仿佛又返回了遠古時代,對世界的認知甚至縮小或模糊了。大游牧民族英雄時代那些考究完美的禮節和華麗浪漫的語言已經淡忘了太多,他們又像在泰加原始森林中的遠古祖輩一樣,靠著慢慢變成俚俗方言的突厥語和蒙古語,靠著直白簡單的歌唱、頌詞和神話與這個世界交流,而遠離了他們先輩們的那些文字和文獻。我認為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了土狗年(1958)的斗爭和運動,在有些人中甚至延續到了今天。
刻在巖石上的文字大多都沒有能保持下來,如今呵!只有祁連山之巔才是見證,只有貝加爾湖,只有阿爾泰山,只有昆侖山脈,只有內亞地區形形色色的牧人兄弟姐妹們是見證……
在鄂金尼部落里,不少人是我的親屬,我有機會和時間聽他們慢慢回憶,不斷地詢問、補充和質疑。逃亡部落的歷史沒有太多識字者制造的文獻,憑借車凌敦多布的部落筆記,對照其他人的一些回憶以及部分檔案和史料,已經湮沒的幽暗的部落歷史脈絡在我面前又漸漸清晰了起來,我依稀看到了這個族群從前的文化和精神的結構。從過去模糊而離奇的歷史中,那些逃亡者們不時地進入我們現在的生活中。
在我去過的堯熬爾人中間,在我的部落里,人們是用自己族群的語言給我講述那些往事,而我又用漢文來轉述出來。漢語不是我的母語,美妙的漢語對我來說仍然是他者的語言,嚴格地說我自己使用漢語的程度仍然只能算是粗通。
那天晚上睡下后我做了一個夢,夢里有一個怪異的人邊走邊彈著一把吉他,看不出他是年輕人還是老人。當他走到我身邊時掉頭朝我笑著說:“喂……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車凌敦多布這個人……那些傳說和那些歌,還有……那一切都是因為你的心中積累了太多太多沒有能消解的東西……那一切都是動蕩歲月中產生的神話……你們是二元一體……”
接下來又是一個夢,夢中風雨大作,我看見鄂金尼部落最后一個頭目那奄喬治,他身材高大魁梧穿著紫紅色氆氌長袍和黑色高筒靴子,他從自己的那匹漂亮的紅色棗騮馬上跳了下來。只見他牽著馬朝我走了幾步,一只手提著韁繩,一只手遮在前額上微彎著腰朝我喊著:
“孩子……我們……部落的一部分人已經逃亡到了天堂,但是沒有找到扎帳篷和放牧牲畜的草原……”
我說:“什么?呵!您說的是天堂?是天——堂——嗎?您是在開玩笑吧?”
我詫異好半天又大聲說:“您不是還給西北局的負責人寫信反映草原日益縮小的事嗎?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是水蛇年的冬天,也就是公歷的1953年11月6日,是您和瓦科,還有昂什克,你們用吐蕃特文字寫了信,信是寫給當時西北局領導的,您忘了嗎?后來他們回復了沒有?”
我又迫不及待地大聲說:“現在,我們在這里也沒有多少草原,近幾十年里草原上到處都拉上了鐵絲圍欄,我們也沒有辦法騎馬馳騁,那些黑帳篷也很快就沒有了,人們基本上是定居放牧,草原上還有很多礦山和水電站……我們鄂金尼部落里沒有多少人說堯熬爾話了……”
那奄喬治擦掉額頭上的雨水和汗水后,奇怪地看著我一言不發。正在下的大雨漸漸變成了大雪。我忽然想起他早在土狗年秋天被捕后就沒有能活著回來。到現在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多世紀。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稀奇古怪的夢接連不斷。它們讓我想到了如今祁連山下縱橫的鐵絲圍欄,圈在鐵絲圍欄里的畜群。牧人們的確是有空閑時間了,但一系列頭痛的問題接踵而來。他們貸款買了樓房,牲畜價格下跌,難以還貸,貸款利息一年年增加,牧民們只能拼命掙錢。黃羊和獐子已經絕跡了,在人跡罕至的地方也開始有旅游者丟下的各種垃圾……
在夏日塔拉草原的小屋里,我翻看著車凌敦多布的信件、筆記和日記。
如今,在這個亞歐大草原的三個亞區之一——吐蕃特高原,時間又過去了許多年,這個察汗薩日節我再一次回到自己的鄂金尼部落時,我一次又一次目瞪口呆。在一次同部落的人們的宴席中,當有一位通曉堯熬爾語的牧女唱起自己族群的古歌時,我看見宴席上的年輕人和中年人都是一臉的麻木和冷漠……后來我已經司空見慣。
難道他們的智慧和靈魂被魔鬼搶走了嗎?是什么桎梏了他們的頭腦嗎?是什么強大的力量摧毀了他們的記憶和根基嗎?如果一個人對美好、善良和高貴麻木,那么丑陋和庸俗就會應運而生。
我的足跡遍及亞歐大草原,在蒙古高原,在南西伯利亞,在中亞細亞腹地,在東歐伏爾加河畔……回憶著大草原腹地的人們那近乎完美的禮儀,美奐美侖的歌舞和大海般深厚的詩文,再看看我的逃亡小族群在亞歐大草原的邊緣地區禮崩樂壞的狀況。我并不傷感,但這一切逼著我思考諸多嚴峻的命題,逼著我冷靜理性,逼著我擠出心中殘存的狂熱和偏執。
如今,我看見當年那個古老語詞彌漫的鄂金尼部落的的確確已經面目全非,不僅僅是會說自己語言的人已經寥若晨星,不僅僅是人們不再談論部落、阿魯骨駿馬、那個失敗的英雄,不僅僅是沒有人在乎史詩和古歌的含義。而是他們在變成另一種人,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和他們對話。
我想到甚至整個祁連山地區的堯熬爾,他們也可能已經和我曾經看到的完全不同時,我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
我是這個非凡族群和部落改頭換面或曰“轉型”時期的見證者,目睹著他們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線。我是傳說中的艾勒奇。我是鄂金尼。我是部落的墓志銘。我是最后的問候和致意。
我明白逃亡的族群從來就是這樣。戰爭與和平,聯合與分裂,破壞與建設,毀滅與新生,失憶和記憶……
我的眼前不時地晃動著車凌敦多布的身影,背景仍然是吐蕃特高原的秋天,在祁連山的群山草原,他在長滿了金色哈日嘎納花的原野上踽踽獨行,風吹入他長袍的前襟,羽毛草拂著他的黑色靴筒。
傍晚,太陽在西邊的巴彥哈喇山頂鄂博那邊消失了,山頂上空是漸漸淡下去的暗紅色。我坐在山崗上,在長久的寂靜中,那熟悉的“嗡……嗡……”聲又在我的耳畔響起,有時候那個聲音由遠及近,滾滾而來,浩浩蕩蕩。接著又漸漸遠去了,不知消失在什么地方。有時候那聲音若有若無,虛無縹緲,又像牧羊女手中紡錘捻出的纖細潔白的羊毛線,牽牽絆絆,纏纏繞繞,永不停歇,也沒有盡頭。起初我以為那是風的聲音,但用心聽又不像是風。我詢問過許多牧民,他們大多都很熟悉這種聲音。許多年后,車凌敦多布的父親告訴我那就是極強悍的神靈“贊”的呼嘯聲。
我整理車凌敦多布筆記的工作將告一段落了。他的筆記、日記和書信都令我感到不安,他那奇崛的語詞背后隱約閃現著某種令人驚訝的東西,那是顛狂、異端或是別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越來越覺得車凌敦多布的筆記對我來說是性命攸關的。有時候我感覺我和車凌敦多布,還有這本沒有寫完的手記融合成為一體,成了一個長翅膀的人,在幽暗的天地間飛翔,在逃亡……
太陽落山,靜悄悄的山崗下是那條泥濘的路,對面是草甸上的灌木叢和沼澤地。秋夜幽藍的天空已經繁星閃爍,接著夜幕降臨了。夜空中不時傳來南飛大雁的鳴叫聲。吐蕃特高原的東北屏障祁連山,仿佛是世界的盡頭。阿米岡克爾神峰像是一個巨大的藍色篝火在燃燒,山下長滿哈日嘎納的群山和原野凝重而幽暗。
注釋:
①塞吉哈吉:堯熬爾語,傳說中堯熬爾人東遷祁連山地區之前的原鄉地名,專家考證在今昆侖山、阿爾金山和柴達木一帶。
②乃曼塊勒圖乃日拉合:堯熬爾語,意為八條腿的宇宙神驥;裕固族傳說中的神馬。
③本文采用的紀年法系堯熬爾人的十二生肖紀年法。基本相同于藏族歷法紀年法。
④巴彥巴斯圖:堯熬爾語,意為富饒的懸崖之地。位于祁連山南麓黑河上游,也寫為八字墩,今名野牛溝。
⑤堯熬爾:突厥蒙古語,意為黏合,聯合之意。裕固人自稱堯熬爾。
選自作者即將出版的長篇非虛構作品《逃亡者手記》的最后一章。
責任編輯 孫 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