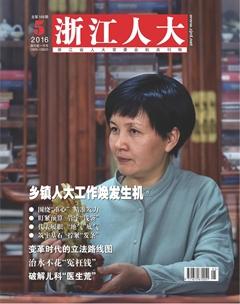破解兒科“醫生荒”
李紅梅 魏哲哲
每1000名兒童僅0.53名兒科醫生,每名兒科醫生日均門診17人次,我國兒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人手短缺”。破解這道難題,既需要政策層面的精準發力,也需要全社會共同營造良好的兒科醫患氛圍。
2015年底以來,一些大醫院兒科停診引起人們關注。隨著“全面兩孩”政策的落地,兒科醫療保健的“供需矛盾”更加凸顯。今年全國“兩會”上,“兒科醫生荒”問題被代表、委員熱議。有數字顯示,目前執業的兒科助理醫師為11.8萬名,至少還缺10萬名,缺口之大令人驚訝。
為什么出現了兒科醫生“職業荒”?如何讓這一職業重獲吸引力?記者進行了采訪。
醫生超負荷工作,兒童看病依然難
“我們工作強度很大,沒有午休,午飯在診室吃,吃過之后繼續看病。為了節約上廁所的時間,有時候選擇不喝水。”2016年2月3日,在接受采訪時,浙大兒院門診部主任汪天林表示。汪天林說,一般情況下,一名普通的主治兒科醫生一天接診近百位病人,2015年底的呼吸道疾病“旺季”中,浙大兒院門診量突破9700人次,創下新高。
前幾天,北京張先生的孩子高燒一直不退。“孩子還不滿一周歲,想去大點的兒童醫院,卻發現根本掛不上號。”無奈之下,張先生只得去普通的綜合醫院兒科就診。綜合醫院看病的患兒也不少,張先生夫妻兩人只能抱著孩子,在醫院的樓道里焦急地等待。
兒科看病有多難?以北京為例,北京市屬的兒童醫院只有兩所,不僅要接待北京本地患兒,還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的患兒,兩家兒童醫院的接診量驚人。2015年全年,首都兒研所附屬兒童醫院門急診人次達到217萬,日均接診量約6000人次,冬季高峰時期每天達到七八千人次。北京兒童醫院就診人次全年達到317萬。兩所醫院每名醫師門診日均接診人次達到三四十,比北京繁忙的大醫院醫師還要多50%的工作量。
“超載”運行是兒科醫院普遍存在的問題。這與兒科醫院的設計有關。我國大城市兒童專科醫院的接診能力是按照成人醫院的一半設計規劃的,床位一般只有四五百張。編制有限,就診人次不斷增多,造成兒科醫院門急診量急速膨脹,遠遠超過原定的設計量。
國家衛計生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的兒科執業助理醫師為11.8萬名,每千名0—14歲兒童兒科執業助理醫師數為0.53人,而美國、加拿大、日本三國每千名兒童兒科醫生數為0.85—1.3人。我國兒科執業助理醫師日均承擔的門診人次數約為17人次,是普通醫療機構執業助理醫師的2.4倍。
大城市兒科醫生工作忙,二三線城市也一樣忙。“河南省平均每5000名兒童才有一個醫生,兒科‘醫生荒最為嚴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0醫院原院長高春芳今年的提案就是解決兒科醫生短缺問題。
高春芳介紹,目前全國兒童專科醫院僅有68家,為醫院總數的0.52%,兒科床位258224 張,僅占全國總床位數的6.4%。截至2014年底,我國兒科床位缺口約9萬張,兒科執業助理醫師缺口至少為10萬人,本科以上學歷僅占33%,遠低于綜合科室臨床執業助理醫師中本科以上學歷比例為49.1%的水平。“兒科醫生的整體缺編,以及內部人才層次結構的不合理,導致兒科醫生超負荷工作,而兒童看病依然難。”高春芳說。
“我們醫院的兒科主任今年已經60多歲了,30多年從沒有休過假,過年也不敢離開。他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仍然奮戰在臨床一線。”高春芳所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0醫院兒科共3名醫生,每年需要診治1萬名兒童,其中住院兒童就達到4000多名。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國有2.3億14歲以下的兒童,這比世界第五人口大國巴西的總人口還多,醫療保健的需求是巨大的,兒科服務的資源總量還是遠遠不夠的。
醫學畢業生遠離兒科,醫院沒動力開辦兒科
“兒科專業醫生緊缺,原因無非有兩個——來源少、走的多。”蘇州大學校長熊思東分析:“人才的來源有兩類,一類是專業定向培養,另一類是相關專業的補充調劑。醫學人才的來源相對單一,兒科人才更為特殊,受學術興趣、社會認可度、生存壓力、發展空間的影響,選擇成為兒科醫生的人就很少。”
一名兒科醫生告訴記者,當年畢業的時候,同屆180名同學中,只有她一人選擇當兒科醫生。“不去參加同學聚會,自己的發展境況比同學差太多,除了受刺激沒別的,再說也沒有時間。”
高春芳認為,兒科專業的特殊性以及壓力大、風險高、待遇低等是兒科醫生短缺的主要原因。“兒科患者病情復雜、變化快,一旦病情加重就會危及生命,而患者年齡小、無法清楚表達使得醫生需憑借經驗診療,被稱為‘啞醫,造成醫生身心壓力很大。”孩子身體不適時,父母第一選擇往往是送醫,直接增加了兒科的工作量。而且,我國兒童多為獨生子女,送醫時陪護人員多,兒科診室內經常人滿為患,醫務人員在接診過程中,經常會被家長抱怨,做出不信任的舉動。遭誤解、受委屈,甚至成了兒科醫生的“家常便飯”。
一名兒科心內科醫生告訴記者:“心內科的技術含量是非常高的,而小兒心內科對醫生的要求更高。美國要求小兒心內科醫師比其他兒科多修兩年才能執業,很多人因此退縮。”這主要是因為兒童個體小,器官精細,經不起創傷打擊,相對成人來說,治療難度更大。兒童用的藥品、耗材又非常少,手術也只能修修補補,更考驗醫生技術水平,風險更大。
然而,與如此高難度工作相對的,卻不是高水平的薪酬。調查顯示,兒科醫生的薪酬不到成人同類科室的一半。原因很簡單,在以藥養醫機制下,醫院靠賣藥獲取收入。兒童用藥量少,有好技術卻“賣”不出好價。記者查看了一下,很多技術服務收費項目的價格只是成人的50%左右,兒科醫生的收入水平自然就低。
收入偏低,造成兒科人才流失嚴重。兒科醫生自嘲:就業首選綜合醫院,再選社區醫院,最后考慮兒科醫院,去了兒科醫院的想改行。
1998年,教育部將兒科并入臨床科室,兒科從本科專業中消失,更加劇了短缺情況。這幾年,醫學畢業生不從醫的現象明顯,大約30%—40%不當醫生,留下來從醫的人中當兒科醫生的更是少之又少。
在北京大學第一醫院院長劉玉村看來,醫院缺乏辦兒科的動力。他說,2015年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收治的兒科病人達到13700多例,平均一個病人的出院費用大概6000元,而成人出院費用一般平均接近2萬元,顯而易見辦兒科是不劃算的。
政策傾斜培養人才,提高待遇留住人才
“兒科醫生緊缺,反映出醫療體制改革中的深層次問題:一方面,我國現有的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在配置醫療衛生資源上還存在問題;另一方面,需要政府考慮兒科醫生這一職業的特點,對壯大兒科醫生隊伍、提高兒科醫療水平,給予政策扶持。”北京市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方來英指出。
2016年2月,教育部將兒科專業化教育前移,力爭到2020年每省(區、市)至少有1所高校舉辦兒科學本科層次專業教育,同時要求38所高水平的醫學院校增加研究生兒科專業招生數量。自2016年7月起,中國醫科大學、重慶醫科大學等8所高校招收兒科學專業本科生,到2020年力爭招生兒科住院醫師3萬名以上。
這無疑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方來英認為人才培養還有一個過程,當務之急需要考慮的是如何進一步釋放兒科醫生的活力,加強兒科基本常識的普及,讓家長學會預防疾病、處理小病等問題。“比如,兒科患者多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疾病,大多數時候是沒有必要去兒科醫院的,增加家長的醫療常識,能夠有效減輕醫院和醫生的壓力。”另外,還可以探索兒科醫生在社區開門診,更好地滿足患兒需求。
高春芳建議提高兒科待遇,對兒科醫生在工資、晉升、深造上進行政策傾斜,同時,提高兒科服務價格。
從學校人才培養的角度,熊思東建議,根據需求,確定大學專業的設置情況,一些有條件的院校,要恢復專業的設置。人才培養要更加貼近兒科的發展,設定科學的課程體系,讓學生有意愿、有興趣學習兒科專業。同時,學校要加強兒科醫生實習基地建設和臨床工作。
“不培養,兒科就是無源之水,但是培養出來的兒科人才,是否會選擇兒科專業工作,還是要看績效考核制度、晉升制度、社會認可程度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熊思東說。
“其實干兒科有干兒科的好,也正是因為孩子病情變化快,治愈率高,兒科醫生相比較其他科室醫生容易獲得成就感,沒有必要唱衰兒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浙大兒院黨委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鄒朝春說。鄒朝春介紹,為了應對“兒科醫護荒”,浙大兒院聯合浙大醫學院已設立了一個30人的小班,名為“臨床醫學(兒科方向)”,又稱“卓越兒科班”。學生自愿報名加入,通過篩選,第一年小班人數為27人。
“卓越兒科班的學生,能獲得比其他學生更多的學習、交流、實踐機會,比如早期接觸兒科臨床實踐,獲得海外交流的機會,以及能參加更多的學術活動。此外,通過與浙大兒院‘導師雙向選擇,獲得一對一帶教。”鄒朝春表示,小班施行一年以來效果不錯。
李斌介紹,國家衛計委正會同有關部門,采取綜合措施解決兒科資源短缺的問題。
“‘十三五時期,國家把增加兒科醫療資源的供給繼續作為體系建設的重點,力爭實現每個省區市都能有一所兒童醫院,常住人口超過300萬的地級市設置一所兒童醫院。同時,合理確定兒科醫務人員的薪酬待遇,確保兒科醫務人員的收入不低于或者高于其他專業同年資醫務人員收入的平均水平。”李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