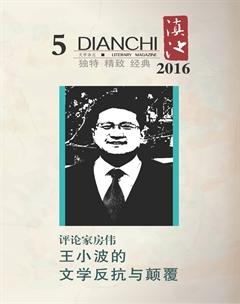我的家史(之三)
黃堯
銀魚時代和牛蛙時代
有的事不提也罷。只稍微留意過的事很容易忘記。河蚌的時代很快就過去了。間或還有,在深
而濁的河溝里,大多不值得如混江龍一般去搏戰一番。我的藍色珍珠珍藏了很久,早先擱置在一個小小的盒子里,不時拿出來確認是否變化,仍是“不怎么圓”,但那乳突其實很像一個佛頭,這樣便有了令自己信服的解釋,你把佛(至少是沙彌)請到家里,已屬圓滿,怎么能把它的“肉”給吃了呢?唐僧肉是吃得的么?當然有報應!且“緣”化為“孽”,是一個很糟糕的輪轉。隨后,幾次搬家,那珠子兀自消失,也不去找,大約隱歸叢林了吧。
滇池的筵席如電影的蒙太奇,沒了河蚌,隨即就有了銀魚,據說是從太湖“引種”的。怎么又是“引種”呢?不明白。滇池只是一個大食槽,盡由人們去攪和。人們望著這一池水討吃,滇池也就順從,一再恩賜。
銀魚很快繁衍,漁家開始編織目孔最小的網來捕撈這種身體梭長,有著尖嘴的小魚。孩子無此功力,但能看到拖網成兜成兜地將這些銀光閃閃的小魚打撈上來。銀魚出水就死,這令孩子傷心,畢竟,它可愛極了,一種永遠是“魚秧子”的梭形身體,腹則有一條細長的銀線,萬丈光芒就是從那里放射出來的,照亮它通體透明的魚身。死去的銀魚眼睛濕潤,一個簍子就可以陳放上萬的尸身,就有一萬只眼睛從垂直方向仰望天空。那是慘烈和悲愴的群殉。據說,這些最鮮美的東西將出口日本,人家專吃中國最好的東西,當然!出水即死,是不愿意被刀俎屠殺!可惜,透明、無染、自尊、美麗,卻是數以億計,群群總總的弱類!
是否“大宗出口”?以滇池的水域條件言,是不可能的。據說,在滇池的姊妹湖澄江撫仙湖銀魚也繁衍開來了。總之,“出口”是出了,日本人是“進口”了。但有“出”不了的殘渣,即很小,“不合規格”的,市場上就能見。兩三塊錢買一撮,打個雞蛋一合,炸了吃,味道果然甜美,你看人家!
不過幾年,滇池的銀魚時代結束。原因是網目越來越小,魚子魚孫一網打盡——這是可目擊的原因。至于水體本身,孩子們并不清楚。
“吃”的欲望大過滇池。“錢”的欲望大過“銀”的“魚”。
這是一個宿命的歸結。怎么會有一種魚叫“銀魚”,當然還有“金魚”。只管值錢,不管吃,所以然能生生不息,百態演化取媚人類。而既能吃又管賺錢的,當然就是犧牲的楷模。
可憐大地魚蝦盡,惟有什么?東岸萬頃濕地。
于是,有一種可怕可憎的東西出現了,就是“牛蛙”。牛如何與“蛙”匹配呢?是牛大的蛙么?還是蛙似的牛?這對多少有些遲悟的昆明人來說,是一個可怖的消息。在我們家解放當年疏散地的庾家花園一帶,最早聽到了這異類的叫聲,從水草茂密的濕地向夜空彈射,“空空空”!有如敵炮!于是聲震蘆蕩,四野怵然。
這對孩子們來說顯然是又一樁有關外族入侵的事件。于是,我們潛伏在葦叢和池塘邊,等待敵軍向“臺兒莊”發起攻擊。萬籟俱寂,月暈渾渾,突然地,“空——空空”,平野雷鳴,剎時,東西水域呼應:“空空空——空空空”,四面殺聲,滇池遭遇重圍。
用自制的弩子(竹篾制的弓箭)射殺這種身大如缽的蛙類巨無霸,是一件十分快意的事。但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經潛伏偵察,池塘周邊張有一米高的網。說明牛蛙是經營此類營生的人圈養的,可笑的是,圈養的笨蛋是更笨的蛋,那牛蛙怎么就接受投降了呢?看守所成了暴動的敵營,牛蛙伸張四肢,長過一尺,一個跳躍,就飛出網來,于是“侵略者”還原“帝國主義”,越過海峽,染指四海,滅殺諸如田蛙類的弱小,突然地在滇池周邊水域擴張起來。
滇池土種田蛙,又叫田雞,是孩子的伙伴,他們知道青蛙和田雞對莊稼是有益的。只有一回,1959年,我們的同學餓得要死,又在離昆明四十里遠的小墨雨村“秋收秋種”(現在叫“支農”),每餐只發一小碗蠶豆和兩個辣椒。于是“二王頭”自作主張抓了十幾個田雞,為此事,大王訓斥不已。但晾在房頭上的田雞轉眼就被貓偷走了。貓更餓。因為老鼠的更更餓,逃亡了。多數時候,孩子抓一兩只田雞,是作游泳教練,放在水盆里,仔細琢磨“蛙泳”的姿勢。
據說這種原產自非洲的牛蛙食量極大,專食田蛙、蛤蟆。早先聽岔了,以為蛤蟆是河馬。接著開始想象非洲。野牛、獅子和非洲象,混亂,難于組合。
事態卻愈加嚴重了,田蛙少了,不見了。
酒店、飯館很快就有了“牛蛙”上席——似乎這無形的策劃是一種深度的陰謀。為構陷者趨從的牛蛙后來被捕了,在被捕獲的牛蛙蹼掌上剔一口子,將受死者倒提起來,唰一下,就將那牛蛙整張綠蔭蔭的皮撕了下來,居然不死,登腿伸腳作泳狀,接著剖肚開膛,隨即就是陳放在某種容器里的平伸四肢的半透明肉身,血淋淋,其狀不忍目接。
因這酷虐,我們不吃牛蛙。但射殺牛蛙仍在進行之中。潛伏、循聲而去,突然撳亮電筒,即刻,反照過來的是蹲伏在地的灼灼一對熒眼,這家伙一個愣怔,正好發弩,竹箭能輕易穿透牛蛙的軔皮,將它牢牢釘在泥淖里——我們寧愿回到古代,倘若非對決不可,就用刀箭,那時我們強大無比,有“四大發明”。
大約兩年過去,有專家警告:慎食牛蛙。因為在牛蛙身上發現了寄生蟲!
當然!入侵者不是使用過細菌戰么?你們哪,愚!
這下,我們樂了。對不食族,是一種賞識和鼓勵。伙伴見面,問:你吃了沒有?沒有,就是智識型上等人。換了今日,應當說,你“牛蛙”了沒有。但那時,漢語沒有“寄生蟲”。
牛蛙時代悄然結束,間或還見餐館里有儲養在玻璃缸里的牛蛙,身型只原來的一半不到,蔫蔫的蹲伏狀,也不作牛吼,抑或羊咩也不聞,一打聽,是水泥池里養殖的。
“寬片魚”時代
與牛蛙的戰爭滋長著一種仇見。
我們的小小雨蛙、青蛙、田蛙和蛤蟆呢?
它們自春至秋的酬唱,是響徹滇池和昆明郊野最美的夜之曲。
一個慣于孤獨的孩子站在田野里,太陽落下了,在最后一線紅光里,裸頭赤身的孩子成了一個黑色的剪影。天空一翻,幾乎在轉瞬間,湛藍色的大幕在啟明星牽動下合攏四野。他等待著什么?第一聲蛙鳴。
它們自春至秋的酬唱,是響徹滇池和昆明郊野最美的夜之曲。
一個慣于孤獨的孩子站在田野里,太陽落下了,在最后一線紅光里,裸頭赤身的孩子成了一個黑色的剪影。天空一翻,幾乎在轉瞬間,湛藍色的大幕在啟明星牽動下合攏四野。他等待著什么?第一聲蛙鳴。
來了,第一聲,是顫顫的,向著水中,卻反彈向空中,“呱——”,A大調!昨日 C大調!雨中,則是 B大調。當第一聲落下,第一組的“呱呱”從組合陣容的前列起聲,延續幾個四分之一拍,仍是顫顫的,忐忑的,裝飾性的,一個休止符!突然,合聲從大幕背景處起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瞬時,大镲、軍鼓——那是蛤蟆樂隊加入,星光揮指!四野合聲!
孩子枕著蛙聲入眠。
如果這交響猝斷,孩子會在噩夢中哽咽、死去。
我們還是趕在交響走完序曲、進入高潮之前長大了。
長大的孩子知道僅僅是夢,他們只是不愿只有一種聲音,絕非對某一物類的憎惡。
一天,和前一天同樣平常的一天。
一個孩子在滇池邊垂下釣鉤,一件奇異的事情發生了,咬鉤細碎,卻總是不上鉤。仔細觀察用蚯蚓做的釣餌,竟然被碎斷數截,這種從側面咬鉤的行為,要么是狡獪的馬魚,要么就是更小的魚類——類似游擊戰中的襲擾戰術。孩子是嫻熟的釣手,換了一個最小的魚鉤,并試著在水漂震動時就迅速起竿,咬鉤更加劇烈,大有發起“圍點”進攻的態勢。這樣的較量持續一個小時,幾乎耗盡魚餌。孩子有些煩惱且疲憊了,最后的決戰,使用的是“爆破鉤”,這是用三兩個小鉤組合成的,如果其中一個鉤被咬,則邊的兩個鉤會在瞬時“炸開”,在魚的前后上下形成一個“鉤叢”,這原本是為最兇狠的魚類的非規則戰術設計的——結果可想而知,噗啦一聲,起竿了,卻出乎意料的輕巧,幾乎感覺不到分量,但確乎是魚。它是被爆破鉤鉤住了腹鰭才未脫逃的。孩子傻眼了!這是
什么魚?它只有一張紙片菲薄,卻是元寶的形狀,有五彩光暈,畸小的眼和口。在河邊草地上蹦騰幾下,死了。一副寧肯自絕,也誓不供述的樣子。
接著,在滇池各個水域都有這樣的魚出現,再過一年,無所不在,即便在翠湖這樣封閉的水域里,它們也開始迅速繁衍。與土種的馬魚、石頭魚爭搶地盤,并決定性地戰勝它們。
沒有人出來宣布對這一事件負責。
就人類分工而言,似乎孩子們屬于注視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態,搜索探察,最好以原初本能將其結果“吃掉”的一類。也負責對某一異種物類的命名。自然界事件的爆發,無論從它的中心引爆,還是悄然釀成,總要像波浪一樣推至邊緣。孩子浪跡在這死水微波的邊緣,拾取屬于他們被分配的份額。
最初叫“元寶魚”,但這有著寶光的東西不好吃,瘠薄少肉,又有濃重泥腥味,與華貴的命名不適,改叫“貓魚”,只饞貓才配;末了又覺有些不敬且損毀的意思,改叫“寬片魚”。取其形似薄片的樣子。再未易名。注入了滇池的名冊。
時間:1964年。
滇池已經沒有象樣的魚類,廣闊的水面甚至少見湛藍,正蒸騰一種霧靄般的煩惱。
篆塘、大觀河大約有幾十個扳罾的漁人。這是一種類似固定漁網的捕撈工具。它有一個岸上或船頭的支架,往水里沉下一個“X”型骨架上懸吊的大網,交叉點上系有可操控的纜繩,起落隨意,也有在網中投放少許誘餌的,隔一段時間,漁夫扯動吊繩將漁網升起來,來不及逃走的小魚小蝦即落入網中。
這是滇池最古老的一道風景。孩子們喜歡,是一個罾架下,必有一個體格強健的漁夫,把水中的大罾拽出水面,類似古代勇士張弓的姿勢,應用的是杠桿原理。如果是水中行船在船頭扳罾,大罾起時,水花蓬起又落下,網中魚兒陡然失陷,飛起跳躍,竟然有在邊緣上的脫逃者,驚險至極……于是,一陣枉嘆,一陣喝彩,漁家用
一個長竿上的網兜探入網底,一抖網綱,收了獲。葦塘、河岔、岸磯,青山隱約,碧水瀲滟,煙村裊然,罾船影疊又疏離,且行且停……
因為扳罾不可能扳到大魚,只能撈到小魚小蝦,屬于欲望窗外,頗帶娛樂休閑性的風景,是很耐看的。
如今,只有“寬片魚”,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在是與否間,漁家便徒有枉嘆。不久,扳罾的少了,夕陽多好,只是沒了風景……
1967年,“文革”武斗,城市武裝割據,我在翠湖漁釣,大約延續整個夏季,那是多么寂寞無聊的歲月,無聊的魚、無聊的斜陽、無聊的垂線、無聊的上鉤、無聊的穿餌——大約“寬片魚”由寡而極眾,到了自相殘殺、難民涌動的地步,沒有空鉤的,每垂必得,棄之還來,出水即歿,來呈干白的死像——險怪!瘋狂!——無以解讀的寓言!
“斷河”漂游
1959年前,以盤龍江為首的匯入滇池的六條河流,都可以游泳。
“發大水”的季節,可以看見孩子們從護國橋頭縱身跳入水中,穿橋而過,或爭搶上游,在金牛街的小碼頭上岸,再回頭演示一次,如此反復,樂而不疲。整條的盤龍江、寶象河、西壩河、南壩河穿城河段,每間隔一里,用石頭支砌的河岸兩側都有“小碼頭”,即一個豁口,十數級臺階折沖而下,直入水面,以供間或清理河道的小船泊靠,更多的用意,則是滿足居民取水、浣洗。于是,沿岸風景,一如水鄉。
那時,“機器水”(自來水)已經在昆明城市的中心普遍使用,但河邊的居民,仍愿意用川流不息,明澈清冽的河水,那是永不枯竭的水源,不花錢。一分錢一大桶的“機器水”最初獲得的名聲是“有股子藥味”,事實上是水廠用漂白粉類的氯制劑消毒的少許殘留,于人體并無大礙。但嬌弱的昆明人頗多詬病,雖不致聲討,但排斥是顯見的。
一條大河,姑娘媳婦頗樂將衣裳、被單、細的粗的、夾的棉的,都挽個籃筐帶到河邊來漂洗,連同淘米洗菜,閑話家長里短,夾雜棒槌嘣嘣聲,煞是熱鬧。用河水也是有民約的,諸如漂染廠、米線廠、面粉廠、豆粉廠、毛巾廠等有規定的取水口。盤龍江北護國橋段有幾家小廠子,是漂染漿洗土布的,依法約,必須在北岸人口較少的河段用水,于是,這里漿青洗白,將數丈長的藍靛、生白土布順流拋入河中,一擺一抖,漫江藍靛入翠,皎漿沉碧,蛟騰龍戲,看呆了對岸的姑娘媳婦,有對歌的,唱:“隔岸柳芽綠如珠,樹下站個馬大粗,漿青洗白近三冬,咯有沿口布(去聲)——丟來!”,“布”是去聲,仿白族聲腔調式。“沿口布”是窄不過一寸的布條,拿來“滾”布鞋口沿或袢扣子的。那邊“馬大粗”唱過來:“盤是龍來水是云,你要沿口要探云,粘潮繡鞋不劃算,逗過嘴來親——吧咋!”——類似西式的“飛吻”。
打情罵俏。騷性十足。
河流是城市的血脈。
昆明在這里長大,孩子也一樣。
1958年“大躍進”,1959年建國 10周年。
這個時段對每一個城市似乎都很重要。
讓人感覺這個城市就要“蟬蛻”了。
先是拆了城墻——大約全中國都在拆毀護衛一個城市,或作為城市象征的城墻。昆明的城墻有明城墻和清城墻,東門城墻拆了就有了“青年路”。因為是以青年義務勞動的方式來完成的;大南城和南城墻拆了就有了“北京路”。新的路就在老城墻的地基上,把歷史的故跡踩在腳下,合乎“破舊立新”的時代精神。如果不拆,大約沒有誰有勇氣去修一修這些確實已經殘破的城墻,這是實話。古代叫“城池”,城與水,其實有共生關系,即城墻都有護城河,而昆明的護城河大多是天然的,如南城的順城河。東城的盤龍江。“水利”不僅是農業灌溉之需,還是城市環境與居民取用之需。這時的入滇河流成為可憎惡的多余之物,入城河段大凡是城市建設需要的,要么填了,要么“蓋”了——“蓋”的工程是個偉大的創造,既不便“堵”與“疏”,最簡便的辦法就是將它給“蓋”了“帽”。結果,盤龍江、金汁河、銀汁河、西壩河、明通河、寶象河、梁家河碎斷無數,兀自成了“地下河”與“地上河”,何處隱沒,何處出露,全然不清楚。如今的昆明地圖,仍看不到完整的河流標線。至于大觀河與篆塘連接的河口,造就了城中水運碼頭,干脆就堵了,大觀河遂成死河,篆塘成了污池。
為什么要消滅河流?為什么要與河流爭地,甚至用窒死河流的辦法來建造樓房?一個孩子是回答不了這些個問題的。他們睜大眼睛看著這些河流一條條消失。有的隱沒或去向不明。全然不明白它準確的表義,是該用新生活的內容來填充記憶,還是為丟失巨大的玩具而悲傷。
滇池突然從它的天然存在一夜間顯現了它的另一種存在。
這天,接到通知,要我帶領四十個泳技最好的同學,一早趕往海埂參加一項重要活動。我們早晨六點跑步出發,八點半準時到達指定地點,那里卻空空如野。事前,聽說海埂新公路已經開通,是閻紅彥政委命令搶通的。這下,從紅廟村西口有了一條六米寬的柏油路,直抵海埂沙岸。那簡直就是羅馬大道,我們愜意至極,一切都表明,我們與時代同步,進行偉大的航程。路兩邊插滿了彩色旗幟,嘩嘩飄揚,步履那樣輕快,你不想跑也由不得地要跑。
十點鐘,來了幾輛車,黑色轎車上走下來閻紅彥政委。上將與我們一一握手,說:“以后你們來海埂玩兒,方便了是吧?”我說,“這可以省了一個小時時間。”他說:“這么說來你們比我忙,那咱們就下水?哪里可以下水啊?”我說:“隨處可以,兩個長堤間水深不超過兩米五。”他呵呵一笑:“看來,你們是健將嘍!末將打頭陣如何?”大家都笑了。
上將的泳技不錯。至少比我們想象的好。他身邊有警衛員,看來不如將軍,顯得緊張吃力,我們則在他周圍,游成一個大圈。不過二十分鐘,他開始仰泳,停息在水面漂浮。我們也換成同樣泳姿。一片水域翻成魚肚白,他突然一轉騰,在水面上大笑:“是我發命令了嗎?沒有吧?你們盡管玩就是了。”他上岸了,就要告別,遠遠招手說:“你們什么時候再來,別忘了約上我。”
云南軍政第一首長的這一活動,是對毛澤東“暢游”的遙相響應。但我們只隱約知道這個含義。大多“選手”還沉浸在滇池有了一條好路的興奮中。還有,學校備下的兩個饅頭也是白面的,那時,這很奢侈,學校食堂還吃玉米面摻飯。金黃的粒子粗喇喇的,要合湯才能下咽。
“軍事化”與“掃泳盲”
1964——1965年,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越南戰爭似乎就要擴展到我國的“家門口”——云南、廣西邊境。毛澤東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口號。學校往“準軍事化”方向轉變。民兵營、機槍連成立。課堂里經常有三分之一的同學缺課——他們正接受軍事訓練。同班同學有的參軍,有的進入軍事體育俱樂部長期培訓,我的同桌尚進終于達成心愿,成了一名“準飛行員”。他在滑翔俱樂部兩年,已經具備教練資格。他還活潑好動,富于創造力,又會畫畫,他自制“卡通”小書,解析“小人”的動作,一上課就翻來讓我看。紙頁快速翻動,“小人”就打斗,翻筋斗——他要么成為一名畫家,但“飛行員”對他并非好的職業——他患有嚴重的鼻竇炎,這是在滇池上空飛行,長期受冷濕空氣侵襲落下的。他走了,我深為惋惜。
毛澤東“暢游”的經典效應還在擴大。
我已經學會“典型化”的工作方法。高 66
(4)班在文理分科后只有 35名學生。女生 18名。男生 17名。我們開始嚴酷訓練,第一課程自然是“全部人都要會游泳,一年后達到千米成績”。究竟有多少同學是自愿的,不清楚,也不理會。因為這是“政治”。
回到了滇池。在初夏季節,滇池仿佛遲寐,波浪不興。
如果在午后四點鐘下課,跑步到達的最短距離是大觀河口。如果是星期天,至少有大半天來強化訓練。還好,多數情況下,風和日麗。同學們到達河口,清點人數,分組“強渡”江河。而我,多半最后一個下水,這有監督的作用。全然沒有考慮危險,因為這也是恥辱,我們的越南兄弟正在犧牲,同學中已經有人從軍,一切顯得悲壯而豪邁。
由泳技較好的男同學在楔型隊伍的前端和兩側保護,全班分組泅渡。而大半女生根本不會游泳,如同“趕鴨子下水”,但沒有誰表現“畏水”。因為這遠不及毛澤東說的“大風大浪”。這樣下來一兩月,都會了。我頗有成就感,這可以示范,沒有哪個班級能像“文史班”那樣,“整建制”地投入大江大河,還能全數出沒風波又盡數活著回來。
但有一次,差點出事。
那是一個星期天下午,班里照計劃進行訓練,地點選在庾家花園西邊河口。與滇池廣闊的水面相接,是“喇叭口”的最上部。水面寬約一百五十米,離庾家花園最近的東岸有一個平緩的草坡,還有一張擱淺在岸上的蓬船——風景十分優美。大家編隊下水,先抵達對面河岸,再沿河岸水域向滇池草海前游數百米后返回。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一距離已經不成問題。
在編隊下水抵近中游后,突然從蓬船里出來一位女同學,大約她們輪流在蓬船里換泳衣,她落在了最后,只見她匆匆忙忙就下了水,要去趕拉開了大約一百米距離的隊伍……
依往常的習慣,我這時在岸上,懶懶地曬太陽,也多少注視水面的情況。突然我視角里出現了異常,那個最后下水的女同學不知什么原因,劃泳的動作慌亂起來,接著沉沒,又出水,只有一只手在水面上攪動……我看情勢不妙,那一瞬的判斷是她沒來得及做準備活動,
大約是腳抽筋了——她對付不了這種情況,我即刻呼喊隊伍末端的同學回來營救,自己跳下水,飛快向她游去——但岸上的判斷與在入水后的判斷截然不同——我估計已經到達“出事”水面,但不見人,周圍沒有浪花和水窩。我即刻潛下水,往四周摸索,忽地,我感到搭上了她的手,但這位嗆水的同學完全慌亂了,她的腳一下絞纏在我的脖子上,我在水下迅速擺脫,再次抓住她時,控制了她的腰部,但前胸接連被她猛力揣蹬,我不能松手,只能在水下拼命將她斜斜托起向我預計的岸邊靠攏——我在水下憋得太久,已經將氣吐完,是無氧狀態,但堅持一秒就一秒……
后面回身趕來的同學終于將她拖向岸邊。過后,這些同學復述當時情況:我在水下托起她時,事實上,她半身在水面以上,仍緊閉眼睛,胡亂揮舞雙手,她根本不知道她已經脫離險境景,她嚇壞了——當然,幸好無事。
我在水下憋氣太久,口涎里有血絲,胸口疼痛一周。
訓練沒有受到影響,但我想,水上救護是個大問題。不久,我們請來市體委教練,由班上泳技最好的四個男同學接受“溺水營救”的訓練。幾乎同時就奏效,在志舟體育場跳水訓練時,班里一個楊姓同學(他泳技差,還根本就不會跳水)從七米高臺上往下跳——不知是因為我負有責任,還是天生如此,我變得極其敏感,似乎渾身每個毛孔都長滿觸發開關——當發現他站在高臺上有傾身動作時已經來不及制止——果然,浪花拍得太大,入水后,我數秒,亂糟糟滿是人頭的水面不見他出來,兩秒、三秒、五秒……我即刻讓教練吹響哨音(哨音急促,表示泳池發生狀況),池中的人迅速上岸,水面浪涌平息,依然不見這個楊同學——我和救護隊下水,往深水區迅速探索施救——他被直挺挺地抬上來,已經停止呼吸——接下來,教練緊急實施“背掛式”控水,人工呼吸……
老黑、家晨、嘉林、振東(歸國華僑同學)在泳池底部發現了他,“跟個死魚一樣,直挺挺地,漂咚漂咚……怪嚇人的。”
他活過來了,在不斷嘔水后,他喘了過來,即刻恢復血色。
教練十分惱火,大罵這個剛剛轉陽依然耷拉個腦袋綿綿軟軟需要四個救護隊員架持著的人:“你這王八蛋!揍死你還不夠,四仰八叉地你跳什么水?你被水拍暈了知不知道?你來試老子的膽量?”回頭對我說,“幸好快。要遲一點,你打火化場電話吧。”他指指四個隊員:“你們還可以,畢業了。”
我感激這四位同學。其中,老黑水性最好,常以水底撈硬幣來炫耀自己。以后,我知道,他們多次在昆明各水域,包括城區翠湖公園,多次營救落水婦女兒童。這里還要加上一個名字:崇杞。那次翠糊救人也很危險,聽見呼救,他們中的三個人來不及脫衣就下水,那個被抬上來的中年婦女體重至少在 200來斤,近岸了,又往水里竄,大呼:“你們救我干什么?我要死、死、死……”折騰半個小時。直到警察被圍觀群眾喊來接手“案子”。
可憐大冬天的,是昆明最冷的天氣,他們身上的棉衣全成了泥水泡子,三個人脫下來擰了又擰,卻不能再上身,只得半赤著身瑟瑟索索往學校走,不知誰憤憤地唾了一口:“爛婆娘,救她干什么!”有人說:“喂,我身上只有一毛錢,誰還有?我們去福照街喝碗糊辣湯!”
那年月,救人,根本不算回事。
被救,似乎也不是事。
“舢板隊·滇池海難”
昆明航海俱樂部舢板隊就沒有那么幸運。沒有幾天,消息傳來,他們死了一個人,是個女孩子,昆明八中初中部初三班的女孩。
我周圍沒有人說得清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她遇難的情況,也沒有通報。一般說來,高中部與初中部有很強的隔離感,在我們眼里,他們是些小孩子。但聽說這個女孩很優秀,五項全能,她身材高挑,是女籃中鋒,策應能力很強,也很活潑,留兩條特別長的辮子,打球時就盤在頭頂,這使她的身量顯得更加高大,中投時“發炮”,那“炮彈”就是從這個小磨盤似的黑發圈里射出去的,每發必中,全場得分她獨占一半——當然大多數男生是為她去喝彩的,那時只欠缺一個名詞:“美女”及“粉絲”。
全校籠罩在陰云中,連上課鐘聲也是嘶啞的。
一個星期過去,消息漸漸明朗。其實,昆明第八中學參加昆明航海俱樂部在滇池集訓的還有五六個學生。為什么偏偏挑中她,不清楚。抑或是她自己愿意去——她泳技原本不錯。同樣是個陰天,但教練和學員都愿意盡快完成課程。據說舢板在離開出發碼頭不遠,即遭遇側風,六個槳手并沒有慌亂,但他們沒有及時調正船頭,教練員用喇叭在岸上喊,發口令指示,但嗆著風,指令也許根本沒有傳達到那里,這時,擔任第一槳手的肯定有些驚慌,側風卷著一米高的浪花打來,船開始進水,接著,一陣驚亂,船翻了。
這原本是最尋常的事故,平時訓練也不少遇到,況且隊員個個都是游泳能手,還按規定穿著救生衣——他們很快自行游回岸邊,甚至沒有丟棄纜繩,把舢板牽引著向碼頭靠攏,隨即,重新整隊——這時——也許過去了五六分鐘,教練發現只有五個隊員!
一切顯得不可思議!教練大叫一聲:“把船翻過來!”
沒有人明白他的意思,“把船翻過來”蘊含著的絕命呼叫把這些孩子嚇壞了,教練第一個跳下水,接著,有更多的人下水,將六米長的舢板在水中翻了身——她就在扣船底,她最后的動作是使勁地拽住自己的長辮子——她的發辯在舢板傾覆的一刻纏在了槳勾上,那是一個拇指粗,只有很小開口的銅環……
她的黑辮子,長長的辮子,最后的裝飾是滇池的海菜花,白的,星狀……
還有海菜修長的,長滿小勾的細莖,披挎在她的肩上,比過,與辮子一樣長……
沒有追悼會,因為“要革命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
但能感受到那條黑辮子緊緊纏繞每個人的心。
我突發奇想:如果她是一條魚呢?“人的進化”是罪惡之始。
以后,但凡教人游泳,我只有一句話:“把你想象成一條魚,去吧……”
尚進,那個飛行員回來了,他能準確說出各種飛行器的名稱,也能說出各種艦船,包括軍體訓練科目中船艇、舢板的型號,最重要的是他與這個女孩認識,他們是一個大院里長大的,但女孩父母只是普通工人……
“應當學會打水手結。”他悶悶地道。我不知道“水手結”與這個女孩的死有什么關系,她是被自己的辮子纏死的。
“她如果知道打水手結,就會解開任何一種結子。”他手里有一根繩子,他打了一個結,解開,又打一個結,再解開。他是來收拾他的“玩具”的,這根特制的繩子是他的愛物,他用它在課間跳繩,練習彈跳,保持體能,他能在空中讓繩子在腳下過三次,無人能及,“不過,她要是慌張了,就遭了……”
滇池的上空和水面——憑氣流上舉,隨濁浪沉沒,只在一線……
沒有人說,她為什么被允許在水上運動訓練時還保有她的長辮子,教練居然熟視無睹?這是生死大忌!這是規則!也沒有人出來證實“她是舍不得(那條令所有人側目的黝黑閃亮的長辮子)”,我們都盼望有人說出來。但,沒有。那時,沒有“愛美”這個詞匯。也許有,屬于她,深藏在水底,必須與身而殉……
軍體訓練照常熱動。
運寬參加了體委的游泳培訓,他原本體格不錯,通過遴選能進入專業培訓,大家一律刮目相看。“出爐”后,他們成為某種示范標準,如果“蛙泳”泳姿不對,看他的表演就行。
“滇池海難”如波遠去,軍體運動狂熱地開展,幾乎沒有受類似事件的影響,隨時準備打仗的氣氛越來越濃郁。
責任編輯 張慶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