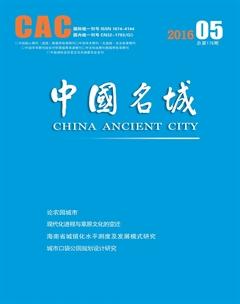授人以花,手有余香
徐雁
摘 要:中國花文化是植物在中國歷史和人類文明進程中所起作用的總和,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圖文并茂的《中國花文化史》,不僅是一部系統地探尋中國花史的發展歷程及花文化內涵和外延軌跡的專著,也是一部從文化價值系統層面引導和提升讀者認知中國花文化史價值的隨筆性讀物,填補了中國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史上一個學術空白。
關鍵詞:花文化;歷史研究;中國花文化;書評
Abstract:The Chinese flower culture encompasses all the roles that the plants can play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becoming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constructing the urb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fully illustrated page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lower Culture not only explores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China's flowers, the connotation and denotation of Chinese flower culture in a systematical way, bu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raise its readers' awareness about the value in Chinese flower history from the cultural value perspective, meanwhile, it fills a gap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n material and non-material culture in China.
Key words:flower culture ; historical study ; Chinese flower culture ; book review
中圖分類號: C9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6)-05-92(4)
百態千姿地呈現于大自然界的花兒,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不僅是四時八節、良辰嘉會的植物美景,更是色、香、味、形可品可賞的精神樂事,早已在文化層面深度浸淫了人們的精神家園。晚唐詩人魚玄機詩云:“春花秋月入詩篇,白日清宵是散仙。空卷珠簾不曾下,長移一榻對山眠。”原來腦海中有了花朝月夕乃至花前月下的美好記憶,即使清冷山居,也不會感到心靈上有甚孤寂了。
其實“花朝月夕”,在中國原非一句虛語和套話,其中都有著特定的寓意。所謂“花朝”,指的是農歷二月十五日清晨,而“月夕”則是八月十五日的中秋之夜。陽春花開早,仲秋月夜圓,所指皆一年一遇的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寄托著人生美好的文化寓意。在中國文化傳統上,宮中和民間每遇“花朝節”,都會有祭拜花神、賞玩花燈、踏青游園、撲蝶游藝、蒔花植木、種瓜挑菜、占卜年成、簪花戴草、乞巧發愿、對歌求偶、賞紅掛彩、香市廟會乃至飲百花酒、勸農勉桑等豐富多彩的活動內容。“百花風雨淚難銷,偶逐晴光撲蝶遙。一半春隨殘夜醉,卻言明日是花朝。”正是明代戲劇家湯顯祖所詠嘆的“花朝節”七絕詩。至于“花前月下”,古往今來,隱喻的都是男戀女愛的纏綿故事。
遺憾的是,隨著百余年來農業社會在中國的不斷解體,在西方工業化和都市化的強勢影響下,中國民間的花文化傳統卻越來越有被邊緣化的傾向。為改變這一積弱之勢,上海交通大學設計系教授兼中國花文化研究會會長周武忠先生,借鑒并拓展《廣群芳譜》(汪灝編撰,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和《中國花經》(陳俊愉主編,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的著述傳統,以沉潛專注二十年的工夫,寫作了《中國花文化史》(海天出版社2015年12月版)一書。該書以七十五萬字,凡十三章、共五十六節的圖文體量,另加《中國花卉發展大事記》、《中國花卉典籍》、《中國名人與花卉》、《中國傳統花卉食品》等五個附錄,集中展現中國古今花文化發生發展史的全貌,填補了中國物質文化與非物質文化史上一個學術空白(圖1)。
作者指出:“花文化并非‘花卉和‘文化的簡單組合,而是人與植物關系的自然流露。中國花文化是植物在中國歷史和人類文明進程中所起作用的總和,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引言》),而賞花的前提是知花,首先要懂得花之“道”,尤其是作為“一個愛花的民族”的子民,更要學會并善于從色、香、姿、韻四方面來品味和欣賞,因為“任何一種花木所能產生的美感,都是基于其自然特性之上的,因此,認識花卉是欣賞花卉美的前提。”而“結合花卉本身的自然美和人文之善的意識形態,以花的形、色、香、德隱喻人的品性或人生追求,主導了中國近3000年的花藝文化觀。”(第三章《四時幽賞》)這一認知和發現,正是本書立論的重要基礎。
為此,在以題為《花·華·花文化》的本書引言開篇后,作者別具匠心地規劃了十三個主題內容,依次是:《千載流芳:中國花文化概覽》、《滋蘭樹蕙:中國的花卉資源》、《四時幽賞:中國的用花藝術》、《蒔花藝卉:花卉與中國園林》、《花朝月夕:花卉與中國民俗》、《含英咀華:花卉與民眾健康》、《筆下生花:花卉與中國文學》、《水墨丹青:花卉與中國藝術》、《拈花微笑:花卉與儒釋道》、《群芳會聚:花卉與中國典籍》、《名花傾城:中國國花與市花》、《屐痕處處:花文化與中國旅游》、《繼往開來:中國花卉文化產業》,從而系統地探尋了中國花史的發展歷程及花文化內涵和外延的軌跡,充分地展示了中國花與中國文化之間的相互關系。
圖文并茂的《中國花文化史》,不是一部旨在講解植物科技內涵的花史專著,而是一部從文化價值系統層面,引導和提升讀者認知中國花文化史價值的隨筆性讀物,因此,作者在對各章標題作仔細推敲和精心設計之后,其著述的重點,自然集中在如何融會貫通中國花文化內容的方方面面,以充分凸現“花與人”和“人與花”之間的精神關系發展史。
瀏覽本書后不難發現,作者機巧地運用了先總敘、后分述的學術寫作手法,從而在時間上從古及今地串聯起了有關的花人花事,把在普通的觀賞價值之外,花與中國人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關系,分主題地解析于世。如前三章,基本上是對中國花卉資源、中國人用花藝術及其文化背景的概述,然后從第四章《蒔花藝卉》開始,以九章分論中國花與古典園林與古書典籍,與文學、藝術,與儒、釋、道教,與民俗、養生、旅游,與中國國花和市花,直至與花卉文化產業之間的關系。有一些篇章,則以數百千字的導言來概述主題,引領全篇。如: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擁有花卉種類最豐富的國度之一,亦為世界花卉栽培的發源地。中國人馴化、培育、利用花卉的歷史極其悠久。而且,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由于花卉與中國人生活的關系日益密切,也就不斷地被注入人們的思想和情感,不斷地被融進文化與生活的內容,從而形成了一種與花(包括花卉和花木)相關的文化現象和以花為中心的文化體系,這就是中國花文化。(第一章《千載流芳》)
民俗,就是世代相傳的民間生活習俗……中國人素有愛花的習慣。我們的祖先在大自然中悠游了數千年,始終以一種虔誠的心態來看待自然,甚至賦予自然花草以人類的靈魂,期許個人的造化能與心目中的花草相映照、互比美。人們心目中的種種花草意象,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符號。又由于本身具有的美化環境、凈化空氣、入藥治病等實際功用,花卉很自然地與人們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歲時節日、游藝娛樂等發生了密切的關系,久而久之,積淀成為民俗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五章《花朝月夕》)
在專題論述方面,作者力求在客觀陳述現象、總結史實的基礎上,能夠突出提煉其所包含的中華文化意象。如通過對宋代男子在良辰佳節簪花習俗的考察,指出這是中國先民“辟邪求吉”的一種愿望體現,“自遠古起,人們就認為某些植物有著禳災避禍、祛除不潔、帶來吉祥的特別功能。那些顏色鮮艷高潔、芬芳馥郁的花朵,往往被人們視為能帶來吉祥的祥瑞之物。”(第五章《花朝月夕》)通過對有關花卉入藥療病、入饌養生和窨茶、護膚現象的考察,指出這是以中華傳統醫藥原理為基礎的一種生活態度和生命哲學,“始終與儒、釋、道的精神世界相呼應,最終形成養生與怡情并舉的特點。”(第六章《含英咀華》)
在本書中,作者還隨機引據了《詩經》《離騷》中有關先民秉蘭佩花的記載,及屈原、陶淵明、李白、周敦頤、李漁、林語堂等古今歷史文化名人的鑒賞案例,以證說中國古代文人學士常常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而庭院和書室中的花卉,則往往成為其情志趣尚的重要載體。如松、竹、梅被古人稱為“歲寒三友”,表示歷經磨難仍忠貞不渝的友誼和不畏艱苦環境的堅貞情操;而梅、蘭、竹、菊被稱為“四君子”,則是以梅之高潔、蘭之清幽、竹之亮節、菊之傲霜來表白人格和情操,這是以其植物品性來比德、言志和祈愿,使這四種植物實現了人文性的升華,被賦予了豐富的文化內涵、特定的象征意義和復雜的情感因素。“園林花木的精神內涵和吉祥寓意,是中華民族文化所獨有的藝術特質,也使中國古典園林中的植物語素變得更加豐滿。”(圖2)
作者通過對歷代文人學士以花卉為題材的詩歌、詞賦、小說、戲劇等的考察,指出這些豐富而精彩的文學作品,“使自然的花花草草呈現出特有的情趣和藝術魅力,溫暖、潤澤著中國每一個文化的心,融入了中華文化的血脈,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國花卉文學的傳統。”(第七章《筆下生花》)通過對中國花鳥畫的考察,則指出“無論是錯彩鏤金的工筆重彩,還是講究筆墨韻味、自然清新的的水墨花卉,均取得了極高的藝術成就,名家輩出,技法獨特,成為中國乃至世界畫苑中的一枝奇葩。”(第八章《水墨丹青》)
西諺云:“授人以花,手有余香。”在文化交流史上,奇花異卉還是不同民族、不同宗教背景和不同文化底蘊的人,實現溝通、交流和理解的最佳載體之一。日本植物學者中尾佐助教授(なかおさすけ,1916—1993年)在《花與民族文化》一書中說,早在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江戶時代(1603—1867年),“花文化已成為一種非常有特色的文化,而鄰近的中國作為日本花文化的前輩,其當時的花文化已十分輝煌”。至于線裝百卷本的《廣群芳譜》,在清嘉慶、道光年間,日本商船更曾多次將之捎帶入境。另有史料表明,自光緒二十五年(1899)開始到公元1918年,接受英國維奇花木公司的派遣,英國園藝學者威爾遜(E.H.Wilson,1876—1930年)曾不遠萬里,在二十年間五次來華搜集中國野生觀賞植物,達千余個品種之多。他在1929年出版的專著《中國,花園之母》中表示,“歐美的花園、公園中,不可能沒有中國產的觀賞植物。或者說,沒有中國產的觀賞植物的種植,就不能成為優美的花園、公園了。”
為此周武忠先生行文所及,有時還能夠在空間上將南北方、中西部乃至中國與海外的花人花事有機地整合到一起,以拓展中國花文化史的人文視野。例如:
中國古代的私家園林,同時也是一個生活起居的空間,要求它有供應飲食的職能……采摘、品嘗時鮮美果,是園居生活的一種樂趣;釀制花果食品,是又一番田園風土情趣的活動。這都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中國古典園林中這種“花園自供”現象,與當今歐美一些發達國家提倡的“自給性園藝”(self sufficiency),不正好是古今中西園林藝術相互映照、殊途同歸的一個佳例嗎?(第四章《蒔花藝卉》)
中國是花的故鄉,遠古人類敬畏變化莫測的大自然,而花卉以其春華秋實、草枯木榮的生活輪回與流逝,顯示出其頑強的生命力,得到人類的敬畏與崇拜。隨著這種崇拜的發展,花卉被人格化并神化,從而有了“花神”。中國傳說中最早的“花神”是女夷……楊貴妃(杏花花神)、西施(荷花花神)、李白(牡丹花神)、陶淵明(菊花花神)等,是在民間深受尊敬、同情和喜愛的人物,成為特定花卉的象征,并被奉為“花神”,其美好的形象或高尚的道德,也隨著花神文化的流傳而得到傳承。(第五章《花朝月夕》)
至于本書第九章《拈花微笑》中,作者以“儒學與花卉”、“佛教與花卉”、“道教與花卉”三節,縱談儒、釋、道學與花卉之間的關系,雖然較諸其他各章篇幅不大,但可謂匠心獨運,別具只眼。他通過比較研究后指出:“與道教、佛教濃厚的宗教思想氛圍不同,儒學花木思想與精神似乎與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結合得更為緊密,也因而更具有普適性,得以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從而潛移默化影響著幾乎所有的中國人。”
《中國花文化史》是周先生早年專著《中國花卉文化》(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的主題拓展和內容深化版。當年《中國花卉文化》問世時,就被稱為“我國花卉文化項目研究的第一本書”。當代著名園藝、園林家汪菊洲先生(1913—1996年)在序言中敏銳地發現,該書從“花是大自然的精華”開始,進入到屬于精神文化深層的花卉審美;從“中國,迷人的花卉王國”,深入到中國花卉文化的物化形態,尤其是“中國名花古今談”一章,“更著力于歷史上形成‘十大名花審美的精神文化方面。”如今,在《中國花文化史》中,這一文化視角和學術方法,被作者作了比較充分的發揚和光大。
在《中國花文化史》后記中,周先生概略地回顧了他于1994年應邀出席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24屆國際園藝科學大會,并在回國后呼吁成立中國花文化研究會的種種心路歷程,然后總結陳說道:“健全的花文化體系可以引領花卉文化消費,促進花卉市場健康發展。創意設計新穎、優質的花文化產品,發展花文化旅游,可以豐富人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提升生活品質,讓花卉在人類文明和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從而把其著述本書的學術原旨表白無遺。相信通過閱讀本書,人們一定會在精神層面上,更富有知識性和學理性地認同花的人文價值和中國花的文化傳統,并積極參與以“人與花,花與人”為主題的花文化事業和產業,讓“美的花,花的美”在生活中發揮出更好的效用和更美的魅力來。
責任編輯:王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