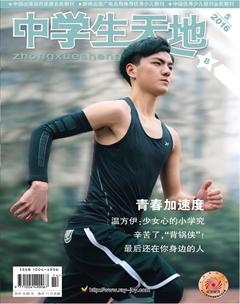“背鍋俠”與“甩鍋俠”
大神說說
作者:倪一寧,上海交通大學中文系學生,新銳作者,著有《賜我理由再披甲上陣》。
很多人都感慨,年紀越大,越傾向于做“獨行俠”。比如,一節選修課可以自由選擇交作業的方式:做小組辯論,或者交一篇課程論文。如果是大一,我們說不定會選擇聽起來比較容易的小組辯論。但作為大四的“老人”,我們幾乎都是不假思索地選擇了寫課程論文。
因為寫論文只要一個人趴在圖書館的自習室里吭哧吭哧寫就行了。然而你知道做小組辯論有多煩嗎?要微信組群,寒暄過后敲定哪個時間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討論,然后有人早到,有人遲到,還有人放鴿子。好了,終于大家都到了,心平氣和地坐下來分派任務,這時候難免有矛盾:有人說自己一講話,大家就走神,不適合當一辯;有人說討厭總結,不想當四辯;還有人壓根沒有摸透辯論規則,自以為只要舉例子、抖機靈、咆哮兩聲就萬事大吉了。最后,當場發揮好壞,只有一小部分取決于你,還有很多的可能性,是決定于別人。輸了,你也不能怪罪;贏了,嘿,誰說要把功勞記在忙里忙外的你頭上了?
小學的時候,老師給小朋友寫評語,比較消極的一句是“某某同學不太合群”。對于一個孩子來說,不合群確實是個巨大的劣勢,他可能是孤僻,可能是霸道,也有可能僅僅是跟別人的興趣不一樣。長大后我們反倒害怕合群,因為都知道那又有另外一個說法,叫作“浪費時間”。所以人其實是越來越朝自我的方向走,不想有無效的溝通,不想做重復的勞動,不想浪費自身的價值,這些都是正常的。
我自己在團隊協作的時候,也從來不是組織者或者是積極參與者,我是個討厭“統治”與“被統治”的人。所有的回憶都是在不遲到的前提下,能多晚到就多晚到,過程中有時發呆有時玩手機,真正走心的瞬間也是寥寥的。
不過,我很快發現了一個規律:在一個團隊中,真正能被歸類為“有用”或者“沒用”的人其實很少。大多數人,有自己的閃光點,也有沒法隱藏的惰性。人的優缺點往往是共存的,相互依賴,共生共長。視野很開闊的人,可能就很抗拒做一些細節性的工作;而一些做細節工作很靠譜的人,或許就提不出什么奇特的點子。我們當然希望,一個人集全部閃光點于一身,但常常不能。
所以這個問題不妨以另一個視角來看,人當然是會傾向于記得自己的“勞苦功高”,也會希望整個團隊和諧、高效,每個人的每一句話都在點子上,讓事情速速解決,早早完工。但或許,你所以為的“卓越功勛”,并不是整個團隊工作里最重要的部分。人往往高估自己的價值,也常常低估了他人的能量。
當然,也不排除那種極端情況,就是你的隊友看起來不靠譜,實質上也真的搞砸了事情,那么你要不要“拔刀相助”呢?
我覺得是要的。小學時代,老師特別喜歡搞大掃除,而我,真的是個很討厭勞動的人。尤其是拿著抹布擦一塊積灰的玻璃,我內心真的很抗拒。當時,跟我一個小組搭檔擦窗戶玻璃的同學,她是真的很講義氣,怕老師過來檢查的時候發現我在“磨洋工”而批評我,就大包大攬,讓我假裝去上廁所,她幫我承擔了任務。
我回來的時候有點心虛,怕她會忍不住跟老師說:“這些其實都是我擦的,那個誰誰偷偷去上廁所了呢!”
但沒有哦,她很義氣地說:“這些是我倆一起干的。”
那個女生很容易寫錯別字,直到小學畢業,她的語文作業都是我幫她檢查了一遍再上交的。在“擦玻璃事件”之前,我們并沒有什么交集,但是在她擦窗戶的時候,也把我的內心一點點“擦亮”了。
真的,人世間的事情計較起來,哪有盡頭呢?對一個人付出的時間和金錢假使能計算的話,那么對一個人所付出的心力呢?那個用什么來衡量才精準?你老想著不吃虧的話,光是為了躲避吃虧,你所花的時間,其實已經可以創造很高的成就了。
我不是說,每件搞砸的事情后面,都要有個偉大的你在兜底。而是說,當一些事情需要你挺身而出的時候,先別急著計較性價比,而是問自己一聲:這個忙,我幫得起嗎?如果是超出你能力范疇之外的,那就直接搖頭拒絕,如果恰好是你力所能及的,為什么不試試看呢?
我們都追求效率和公平,但總也希望在緊張嚴肅之外,遇見猝不及防的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