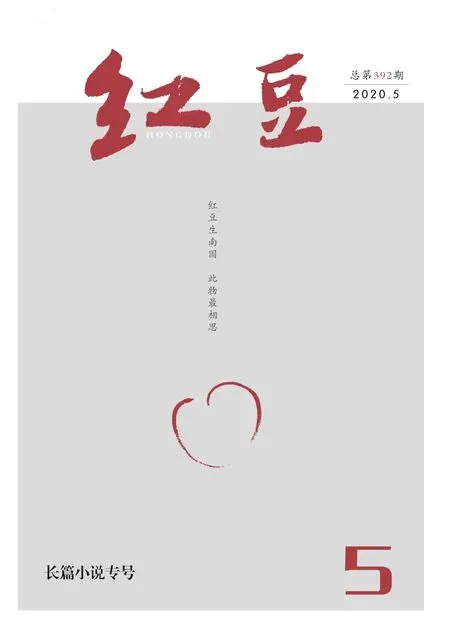文與畫的內在關系
陳傳席,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美協理論委員會副主任。曾任美國堪薩斯大學研究員,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大學教授。2014年榮獲“巴黎榮譽市民”徽章。已出版學術著作《六朝畫論研究》《中國山水畫史》《畫壇點將錄》《悔晚齋臆語》《弘仁》《中國紫砂藝術》《陳傳席文集》等50余部,部分著作被譯為外文在國外出版。發表學術文章近千篇。
陳傳席提倡“陽剛大氣”,以振奮民族精神;提出“正大氣象”,改變畫壇小巧邪怪現象。這些觀點廣被眾多書畫家贊同和實踐,形成一股風氣。他較早提出反對殖民文化,在題材上提倡民族精神,糾正很多畫家錯誤的創作傾向。近年來,他又提出書畫作品要有“秀骨”,這對書畫家有重大的啟導作用。
陳傳席教授史論兼備,旁涉文學詩詞,在書畫造詣上亦是超塵脫俗,自成一家。繪畫作品被收入《中國繪畫年鑒》。散文作品收入《二十世紀中國散文大系》等多種重要散文集中。現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繪畫創作。
文有文脈,畫有畫脈。但文脈對于一個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來說是靈魂,是國家精神的集中體現,畫不是。從大的方面講,“文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畫可能是不朽之事,但不是經國之大業。思想、學術、歷史可以通過文永久、準確、完整地傳播下去,用畫來傳播其效果就微乎其微了。自從文字產生以來,各種學說、思想及歷史都是靠文字傳流下來的,不可能靠畫傳流下來。
“半部《論語》治天下。”直到現在,我們都靠一種主義。一種理論或某種思想治理天下,這都是文脈的一部分,不可能靠畫去治理天下。一篇文章可以治天下,一篇文章亦可以亂天下。畫的功用不會有如此之大。有很多人是因為讀了一本書或一篇文章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或走上了獻身民族事業的大道,畫的力量不會有這么大。
讀書不獨能改變人的氣質,而且能養人的精神,長久讀書(優秀的書、高雅的書),人的心胸開闊,氣質非凡。“腹有詩書氣自華”,內在充實的是文雅之氣,表現在外的“華”也絕不同于凡俗。畫家畫人物重在畫出人物的內在氣質,工人、農民、士兵、商人(奸商、儒商)、賣菜的、挑擔的、文人學者、教授,各有各的內在氣質,這氣質正是內在蘊藏的外現。人們經常說“學者氣質”而不說“畫家氣質”,也不說“作家氣質”,更不說“農民氣質”(其實各有各的氣質),就因為學者以讀書為職業,讀的書多了,這氣質必然非同一般。作家、畫家也必須讀書,但較學者讀書為少,氣質也無法和學者相比。而且學者讀的書非淺薄之物,多高深之理,義理融通,文精詞妙,境界非凡,人的精神在讀書中得到涵養,精神變了,氣質也變了。孔子說:“古之學者也為己,今之學者也為人。”“為己”就是充實自己,豐富自己,改變自己,自己好了,為政自然公正有方,作文自然高雅有理,繪畫自然格調不俗。
藝術是自我代表,繪畫更是自我表現,你的氣質不凡,格調高雅,學問精深,人品不俗,自然會在畫面上有所表現,心手不可相欺。當然需要一定技巧。藝術的表現方式是技巧,沒有技巧無法表現,有了技巧,表現了你自己。你沒有學問,在畫上怎能顯示出學問?你沒有不凡的氣質,畫面上怎能顯示出不凡的氣質?多讀書,多為文,改變你的氣質、精神,才能改變你的畫。技巧是表現的手段,人才是主體。人的改變靠文,不能靠畫,畫的改變也靠文。
明李日華有一句名言:“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非塵襟俗韻所能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充拓心胸為主。”正是這個道理。
中國歷史上是文官治政的國度,唐人“以詩取士”,詩寫的好才能中進士,才能做官。而西方一直是貴族和教會把持政權,貴族和教會需要藝術,全由匠人去創作,匠人的審美觀決定藝術的品質。而中國的文官需要藝術,一方面以文人的審美左右藝術,一方面文人自己參與創造藝術。所以世界上只有中國有文人畫,而且其他畫種和藝術也都借鑒中國畫,文人畫又以書法為基礎,書法更是文人的專利和文人必備的基礎。
文官治政,一切都要以文為基礎。中醫、園林、繪畫等等,都有很強的文化性。畫上要題詩,還屬于文在畫上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內涵。董其昌題畫詩云:“一一毫端百卷書”,每一筆上都蘊藏有百卷書的基礎,好的文人畫上一筆一墨中都有百卷書、千卷萬卷書的底子,否則不可稱為文人畫,也不會有文人畫的內涵。明代的周臣曾指導過唐寅繪畫,但后來畫的名氣趕不上唐寅。人問他,老師不如學生,應作何感想,周臣回答:“但少唐生三千卷書耳。”周臣在繪畫技法上可以作唐寅的老師,但畫境和畫的內涵都趕不上唐寅,還是讀書少了。不讀書,不學文,豈能作好畫?
前面說過,文的功能大于畫,孔子、莊子的思想,黑格爾、達爾文、馬克思的思想都是靠文傳播,不可能靠畫傳播。孔子說:“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藝”只可游之而已。儒家又認為藝術是“小道”(“雖小道,必有可觀焉”),“小道”的作用趕不上“經國之大業”的文,但這個“小道”又必須建在“大道”的基礎上,沒有文的修養,文的內涵,這“小道”決不能成功。所以,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繪畫又不是小道。
鄧椿在《畫繼》中說“畫者,文之極也。”又說:“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表示了他對文與畫的關系之重視,畫成為文的最高表現了。
前面說到文脈與畫脈,文脈至為重要,但中國的畫脈中又一直有文脈的內涵和基礎。所以,畫和文是不可分的。否則便是畫匠之畫,便是庸俗的畫,格調不可能高。至于在畫上題詩文,乃是文人畫的另一形式。尚不在此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