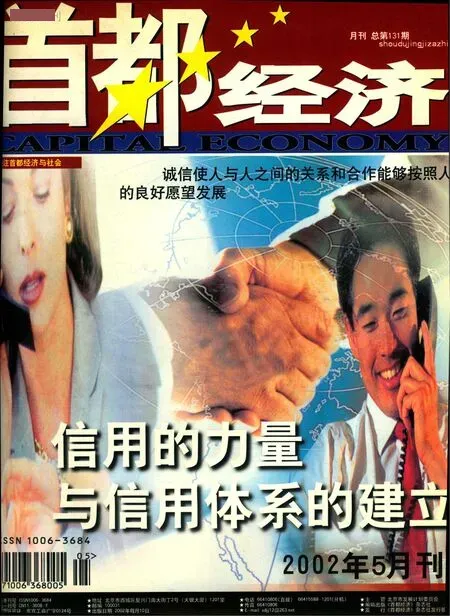北京人口與就業(yè)環(huán)境之我見
胡彭輝
在全國人口紅利消退的大背景下,北京市持續(xù)推進(jìn)地下空間綜合整治、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改造、拆違打非等專項(xiàng)行動,常住人口增量和增速延續(xù)下降態(tài)勢。
今年,伴隨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的落實(shí),全市人口規(guī)模將受到嚴(yán)控,增速保持低位。在非首都功能疏解進(jìn)度和力度加大背景下,全市就業(yè)面臨一定壓力,就業(yè)總量矛盾突出,但總體形勢仍有望保持平穩(wěn)。
以近年來0.3的平均就業(yè)彈性估算,按照2016年GDP增長6.5%,考慮非首都功能疏解因素影響,預(yù)計(jì)2016年北京市從業(yè)人口達(dá)到1200萬人,同比增長1.7%,增速略有回落。
人口與就業(yè)壓力仍然較大
當(dāng)前,全國城鎮(zhèn)化仍處于加速階段,首都面臨的人口增長壓力仍然較大。2000年以來,我國城鎮(zhèn)化率幾乎成直線上升趨勢,到2014年已經(jīng)達(dá)到54.8%。到2020年,我國城鎮(zhèn)化率有望突破60%。新型城鎮(zhèn)化過程中,有上億規(guī)模的人口要從農(nóng)村向城鎮(zhèn)轉(zhuǎn)移,以及大量人口在不同城市間流動,勢必會導(dǎo)致各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普遍面臨人口膨脹的壓力。未來一段時間,我國還面臨著解決好現(xiàn)有“三個1億人”問題的任務(wù),即促進(jìn)約1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落戶城鎮(zhèn),改造約1億人居住的城鎮(zhèn)棚戶區(qū)和城中村,引導(dǎo)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qū)就近城鎮(zhèn)化。北京作為首都,是人口城鎮(zhèn)化最高端的吸附點(diǎn),具有強(qiáng)大的磁吸效應(yīng),必然成為人口流動和人口聚集的重要節(jié)點(diǎn),未來北京仍將面臨較大的人口增長壓力。
與此同時,全國就業(yè)壓力加大。世界經(jīng)濟(jì)復(fù)蘇進(jìn)程緩慢,發(fā)達(dá)國家及新興經(jīng)濟(jì)體的外貿(mào)需求疲弱影響國內(nèi)企業(yè)出口增長,這些因素都將對國內(nèi)就業(yè)構(gòu)成威脅。我國經(jīng)濟(jì)仍處在調(diào)結(jié)構(gòu)、轉(zhuǎn)方式的關(guān)鍵階段,新舊動力的轉(zhuǎn)換也在進(jìn)行之中,新動力還難以對沖傳統(tǒng)動力下降的影響,經(jīng)濟(jì)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對就業(yè)的滯后影響將逐步顯現(xiàn)。多家機(jī)構(gòu)預(yù)計(jì)2016年經(jīng)濟(jì)增速可能繼續(xù)放緩至6.5%左右,城鎮(zhèn)新增就業(yè)人數(shù)可能保持穩(wěn)中略降。同時,受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動,國企改革重組啟動,將釋放一定數(shù)量的勞動力,可能進(jìn)一步加大就業(yè)壓力。上述國內(nèi)外宏觀環(huán)境均將通過對北京經(jīng)濟(jì)增長施加影響,進(jìn)而影響就業(yè)增長。
此外,北京不斷加快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進(jìn)度和力度將對人口流動和就業(yè)產(chǎn)生一定影響。京津冀協(xié)同發(fā)展背景下,北京市將持續(xù)加強(qiáng)人口規(guī)模調(diào)控,重點(diǎn)疏解一般性產(chǎn)業(yè)特別是高消耗產(chǎn)業(yè),區(qū)域性物流基地、區(qū)域性專業(yè)市場等部分第三產(chǎn)業(yè),部分教育、醫(yī)療、培訓(xùn)機(jī)構(gòu)等社會公共服務(wù)功能,部分行政性、事業(yè)性服務(wù)機(jī)構(gòu)和企業(yè)總部等四類非首都功能,伴隨此類產(chǎn)業(yè)和功能向北京郊區(qū)、天津和河北省市疏解轉(zhuǎn)移,伴隨就業(yè)崗位的減少,各區(qū)域之間的人口遷移規(guī)模和步伐均將加大加快,對就業(yè)規(guī)模、就業(yè)布局、就業(yè)的行業(yè)結(jié)構(gòu)也均會產(chǎn)生影響。
戶籍制度改革雙重影響
2014年發(fā)布的《國務(wù)院關(guān)于進(jìn)一步推進(jìn)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要落實(shí)放寬戶口遷移政策,全面放開建制鎮(zhèn)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yán)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guī)模。目前北京市已經(jīng)審議了《北京市居住證管理辦法(草案)》、居住證公共服務(wù)配套政策及積分落戶管理辦法,戶籍制度改革對北京人口規(guī)模調(diào)控將產(chǎn)生雙重影響。
一方面,戶籍制度改革將加大戶籍遷移人口增長壓力。北京已沉淀大量外來常住人口,未來無論積分落戶制度如何設(shè)計(jì),都將有部分常住外來人口符合積分落戶條件,成為戶籍人口,加之這部分人群的配偶、子女、父母也將隨之落戶,必然會使戶籍遷移人口較改革前增長更快;居住證制度和積分落戶制度的建立將讓常住人口產(chǎn)生穩(wěn)定預(yù)期,導(dǎo)致其定居北京的可能性進(jìn)一步增大。
另一方面,全國戶改加快背景下,其他城市落戶政策的放寬,可能會分流部分本市常住外來人口或潛在來京人口。北京相對嚴(yán)格的人口積分落戶條件,可能促使部分人群去往落戶條件相對較為寬松的城市落戶,從而減輕北京市人口規(guī)模調(diào)控的壓力。影響大小將取決于北京和各地的具體實(shí)施細(xì)則。
目前,人口向超大城市集聚的態(tài)勢仍將持續(xù),外來人口增長壓力仍然明顯。在人口規(guī)模調(diào)控背景下,考慮全面二孩政策落實(shí)因素,戶籍自然增長人口規(guī)模擴(kuò)張壓力日益凸顯,加上戶籍人口機(jī)械增長主要由人才引進(jìn)、親屬投靠等人口遷入帶動,難以在短期內(nèi)明顯減少,戶籍人口年均增量將超過20萬的規(guī)模。
北京市戶籍人口與常住外來人口在全市不同區(qū)縣間尤其是城六區(qū)與十個遠(yuǎn)郊區(qū)縣間、全市與津冀省市間的遷移現(xiàn)象將增多,存量人口與增量人口相互替代的數(shù)量和頻率均將日益突出,往年全市人口進(jìn)多出少的現(xiàn)象有望改變,人口進(jìn)出平衡的苗頭逐步顯現(xiàn)。綜合上述因素,預(yù)計(jì)2016年全市常住人口較上年增長1%左右。
就業(yè)新增長區(qū)域逐步形成
近年來,由于不斷壓縮中央和全市留京戶籍指標(biāo)引導(dǎo)全市高校畢業(yè)生更多流向京外就業(y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高素質(zhì)勞動力供給。同時,非首都功能疏解中可能存在的“業(yè)走人留”現(xiàn)象將進(jìn)一步釋放低端勞動力,促使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總量矛盾較為突出。高素質(zhì)勞動力供給減少與非首都功能疏解后產(chǎn)生的“業(yè)走人留”加劇就業(yè)總量矛盾和結(jié)構(gòu)性矛盾。如城六區(qū)動物園、大紅門等批發(fā)市場搬遷過程中,在就業(yè)崗位壓縮外遷的同時,從業(yè)人員并未隨產(chǎn)業(yè)的外遷而明顯向外疏解,部分人員仍然滯留城六區(qū)或郊區(qū),可能加大就業(yè)總量矛盾。此外,全市用人單位的勞動力需求與求職者的知識結(jié)構(gòu)和技能結(jié)構(gòu)存在偏差等就業(yè)結(jié)構(gòu)性矛盾仍然突出。
“雙創(chuàng)”背景下,服務(wù)性行業(yè)新業(yè)態(tài)置換傳統(tǒng)行業(yè)就業(yè)的特征日益明顯,就業(yè)新增長點(diǎn)逐步顯現(xiàn)。一方面,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逐步拓展就業(yè)空間,服務(wù)業(yè)、新興產(chǎn)業(yè)加快發(fā)展擴(kuò)大就業(yè)容量。科技服務(wù)業(yè)、信息服務(wù)業(yè)等領(lǐng)域“雙創(chuàng)”將保持持續(xù)活躍,教育、健康醫(yī)療、文體等公共服務(wù)領(lǐng)域政策約束將進(jìn)一步放松,新技術(shù)與產(chǎn)業(yè)將加速融合,有望保持向好走勢,帶動勞動力需求穩(wěn)定增加。另一方面,近年隨著網(wǎng)購、互聯(lián)網(wǎng)生活服務(wù)、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等網(wǎng)絡(luò)創(chuàng)業(yè)就業(yè)新業(yè)態(tài)的不斷涌現(xiàn),由此帶來的新增就業(yè)不斷置換傳統(tǒng)商業(yè)和服務(wù)業(yè)就業(yè),促使服務(wù)業(yè)內(nèi)部的就業(yè)結(jié)構(gòu)發(fā)生明顯變化,既增強(qiáng)了服務(wù)業(yè)吸納就業(yè)的能力,也提升了服務(wù)業(yè)就業(yè)質(zhì)量,有助于保障整體就業(yè)的平穩(wěn)。
功能調(diào)整疏解背景下,就業(yè)新增長區(qū)域逐步形成。市級行政事業(yè)單位明確向通州搬遷,城六區(qū)功能向郊區(qū)轉(zhuǎn)移等,進(jìn)一步推動就業(yè)布局加快調(diào)整。市行政副中心、新機(jī)場等建設(shè)本身將創(chuàng)造一定的就業(yè)崗位,搬遷后行政事業(yè)單位、新機(jī)場臨空經(jīng)濟(jì)等配套服務(wù)需求旺盛,均需提前規(guī)劃建設(shè),將促使通州、大興等成為新的就業(yè)增長區(qū)域。
(作者單位:北京市經(jīng)濟(jì)信息中心經(jīng)濟(jì)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