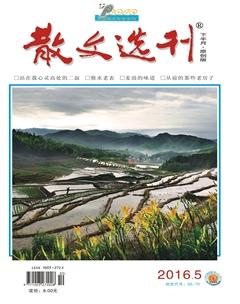站在我心靈高處的二叔
李光彪

人到中年,懷舊的心情就越來越重,常常想起老家那些枯萎的老樹、去世的老人……尤其是二叔。
在我曾經裝訂的記憶檔案里,二叔個頭不高,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愛憎分明,做事風風火火,說話擲地有聲,急性子,是鄉村方寸土地上讀過高小、識字最多的人。解放后,他當過生產隊記分員、會計、隊長,算是祖輩最大的“官”。因而,村里不論紅白喜事、贍養父母、家庭不和、鄰里糾紛、牛吃莊稼、馬踏地等,好事請他主持,壞事請他擺平,矛盾請他化解,是個響當當的人物。
二叔經常用“人有三窮三富,馬有九瘦九肥”這兩句話敘述家史:在我爺爺輩上,家里養著幾匹大騾子,煮著一灶酒,馱到狗街、貓街、馬街、黑井賣,在村里是數一數二的人家。由于家境的寬裕,爺爺奶奶從小就對長子的父親嬌生慣養,百般寵愛放縱,使得父親十多歲就染上鴉片,成天不干活,搖骰子賭博,養成了好吃懶做的惡習,還經常偷家里的東西變賣,換鴉片吸。結婚以后,娶進門的婆娘管不住父親,還經常挨父親打罵,不到一年,身懷有孕的婆娘就吊脖子死了。后來,出身貧寒的母親,由于父母包辦,被“二婚”的父親娶進了家。
母親來到我家,幾年后,相繼有了大哥、大姐。可已為人父的父親還是惡習不改,不務正業,偷偷摸摸吸鴉片,搖骰子賭博。解放以后,我家被劃為貧下中農,要養家糊口,必須靠苦工分,分糧、分紅。由于國家禁止吸鴉片,父親黃皮寡瘦,像個病人,干不了重活,掙不到高工分,只能當飼養員——放牛。于是,本來只能做椽棒的母親,如孩子過早地挑起大人的擔子,不得不當頂梁柱用,支撐起了全家人生存的大廈。
母親畢竟是個女人,整天起早貪黑地干活,腳不著地的奔波,始終很難扭轉家境的困窘,還常常挨父親罵,遭父親打,便提出要和父親離婚。母親越這樣要求,父親罵聲越大,拳頭越重。二叔看不過意,跑過來先是臭罵父親:“大哥你吃糧不管事,還打人罵人,你手摸良心想想,像大嫂這樣點著火把都找不到的婆娘哪里有,狠就來罵我、打我嘛……”二叔對父親的“批評教育”過一段時間又不管用了,父親又借酒發瘋,開始打罵母親,還胡說母親與二叔私通,要殺了母親。母親的婚姻是悲哀的,與父親陰差陽錯的結合,根本就沒有享受過什么叫愛情,如關在同一廄里的驢和馬,牛和羊,雞和豬,雄性不管怎樣可恨,總是能夠用強悍占有懦弱的雌性,讓雌性被迫無奈地懷孕、產子、下蛋、哺育。二哥、三哥、二姐和我,就是這樣來到人間,像群跟著母雞刨食的小雞,風里來、雨里去,在母親呵護的翅膀下長大的。
我九歲那年,頭上的哥哥姐姐們,娶的娶、嫁的嫁,都有了兒女,婆媳妯娌之間的摩擦越來越多。在二叔的主持下,原來的大家庭分成幾家,各立門戶,我和母親擁有幾樣破舊的家具什物,一間低矮昏暗的小屋,構成了人生的第一個“家”。父親沒人要,單人獨戶一家,時不時來騷擾我和母親。二叔依然會跑來像個長輩似的教訓父親:“大嫂的筷子又沒擔在你碗邊上,腳都伸進棺材半支的人了,還死不悔改……”依然不停地安慰母親:“俗話說樹大分枝,人大分家,大嫂你把他們拉扯成人,不簡單了,就剩小六這老兒子,只要有我在,兄弟會幫你呢……”母親依然抹著眼淚,不折不撓地領著貌似奶孫輩的我苦苦地生活著。
年幼無知的我,因為不懂事,肚子餓,有時偷吃人家的水果、苞谷、紅薯、番茄、青筍,或是撈魚摸蝦、捉雀打鳥;或是跟別家的孩子頂嘴打架,常有人跑上門來論理討說法,索要賠償,惹得母親用吆雞棍、掃把追著教訓我。二叔總會來勸母親:“大嫂,娃娃不懂事,偷點東西吃不犯法,打傷了,出個三長兩短不好,以后我來教育他,莫打了、莫打了……”好幾次,二叔的出現,總是讓我免受皮肉之苦。
最難忘的是那年夏天,我們一群娃娃在去找豬草的路上,路過一個小水壩,看見泡田栽秧的水已接近壩底,并有魚不時浮出水面,在我這個“娃娃頭子”指揮下,一群娃娃赤裸裸的像些鴨子,撲進水里,追逐戲水,用籃撮魚。因水淺,幾個回合,就被我們攪成泥漿,一條大魚被追得筋疲力盡,撮到了手,爬上岸,我們貓玩老鼠似的在草坪上你摸我捏,驚喜了半天,正商量著把死去的魚偷偷拿回家打牙祭。此刻,生產隊的放水員不知從哪兒冒出來,肩上的鋤頭往我們面前“哐”的一放,便罵:“你幾個小短命的,誰叫你們來偷大集體的魚,曉得嗎?這是破壞社會主義,斗死你們……”
一陣刑訊逼供似的審問,駭得我滿褲襠尿,只好低頭認錯,我們一個個比麂子跑得還快,溜回了家。我惶恐地躲進了二叔家的牛廄樓上,像只被獵狗追攆的兔子,蜷縮在草堆里,不敢動彈。
傍晚,我“領導”的“偷魚事件”如決堤的水,在村里傳開。透過草樓的窗戶,我看見放水員正在舉著那條大魚,站在曬場上,開會似的圍著很多人,議論紛紛,斥責我們的罪過,有的說要批判家長,教育娃娃,有的說要加倍罰款,矛頭都指向我。身為生產隊長的二叔卻從人群中站了出來,對著眾人說:“娃娃不懂事,既然已經犯了,該罰就罰,集體的財產不能破壞,確實該教育的要教育。”說話聽音,鄉親們看在二叔的分上,同意罰我家八角錢。只見母親哭著下跪,向鄉親們認了錯,為我交了罰款,便羞愧地跑回家,拿著棍子遍村遍巷喚著我的乳名找我。我只有哭泣,不敢答應,不敢露面。
透過草樓的窗戶,我看見那條大魚,被鄉親們摸來摸去,個個都想吃,卻出不上隊委會打躉估的價,最后還是二叔出了兩塊錢買回了家。
透過草樓的窗戶,我聽到二叔刮魚鱗殼、洗魚、破肚、宰魚的聲音,魚的香味也由遠而近朝草樓飄來。
透過草樓的窗戶,我又看見二叔端著牛料從牛廄走來,喂完料,二叔上樓拿牛草,無意中發現了哭哭啼啼的我,便說:“小六啊,小六,你媽到處找你呢,下來、下來。”
聽到二叔喊我,母親也知道了,拿著棍子,喊著我的乳名,罵著跑來。我急中生智,一閃抱住了二叔的腿,躲到了二叔背后。二叔一邊勸母親,一邊叫我認錯,我哭哭啼啼講了事情發生的經過,又軟口軟舌地認了錯,才逃過一難,平息了“偷魚風波”,二叔把我和母親叫去吃飯,讓我嘗到了一口魚湯、一坨魚肉。那魚肉、魚湯一直在我腹中,多少年沒有被消化似的,香到現在。
二叔家和我家僅一墻之隔,聽得見兩家人說話,聞得見兩家的飯菜香,有好吃的,二叔家總會勻出一點叫我去拿。所以,我最喜歡去二叔家玩。二叔還是重復著那句老話:“人有三窮三富,馬有九瘦九肥,腌菜罐總會有發水的時候,……”并不斷地鼓勵我:“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你一定要好好讀書,將來像我一樣當大官……”
二叔愛看書,看的都是煙盒大的《毛主席語錄》,磚頭厚的《毛澤東著作》的“紅色書”。時不時領著我念幾段,或叫我們背幾句,教育我也幾乎是引用《毛主席語錄》里的話。二叔“當官”也關照過我家不少,比如讓父親放牛,讓母親上曬場打糧,讓我家享受貧困戶的救濟,使我有衣穿、有飯吃,一直像頭二叔手下飼養的小豬、小牛,得以順利成長。我工作以后,父親已經離世,每年上墳,二叔總要帶著我去父親的墳前祭奠,跪在父親的墳前祈禱:“大哥、大哥,起來吃飯嘍,今天小六和我來看你,你在陰間一定要好好保舉小六,將功補過……”
每次回去,二叔總忘不了問我母親的情況,再三叮囑我,要好好善待母親:“你媽一生命苦,沒過上好日子,現在熬出頭了,你要好好照顧她,讓她多享幾年福。”
當我把幾件衣服,或是幾樣水果、糖果、幾塊錢送給二叔時,他總是拒絕:“你在外面緊,要買房子,要供娃娃讀書,還要養你媽,小六啊小六,我們空腳白手沒東西給你,全家都享你的福,以后莫拿回來了、莫拿回來了……”
令我遺憾的是,自己還來不及報答二叔,他就走向了另一個世界。那天,我在國外出差,接到二叔不幸去世的電話,恨不能包機返程。結果,那一次歐美之行,原設想是很愉快的事,卻成了我揪心的苦旅。回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為生前沒有帶二叔到楚雄、昆明轉轉,或是來城里和我生活一段時間,讓他也沾沾我的光,聽他講講《毛主席語錄》,而深感內疚。
總想著要為二叔做點什么,想來想去,我只好按照鄉俗,把二叔的墳筑得比祖輩的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