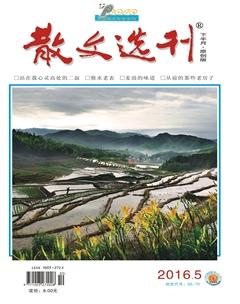如煙雪事
吳華
去年秋季的一天,剛吃完飯,固定電話響了:“你是王立群嗎?”“是,你是哪位?”“我是你的老同學修國成。”我一時有點發愣,驀地,想起來了,這是我中專時的同學。時光已逝去近50個春秋,我們之間并沒有過聯系。他是怎么想起了我,怎么知道了我家的電話?于是,我問道:“你是怎么知道我家的電話號的?”他說:“通過公安啊。我不光知道了你家的電話,還知道了你的手機號。”他說出的11位數,完全對……
1965年秋,我考上了中央冶金工業部在長春創辦的冶金地質學校。報到后才知道,我們班37名同學分別來自江蘇、山東、吉林三省。4年多的時間,我們在同一間教室上課,在同一個食堂就餐。1966年夏,爆發了“文化大革命”。雖然我們分成了兩派,但后期的“革命大聯合”使我們又走到了一起。一起去鄉下參加秋收勞動;一起到遼寧丹東的一座金礦勞動鍛煉,在那里度過了近半年的時光,并在那里過了春節。
1969年11月下旬,我們終于畢業了。37名同學分別被派往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屈指數來,47年近半個世紀的光陰如白駒過隙般的過去了。
電話中,他很惋惜地說:“我們的同學有的已經走了,離開了人世。”他說到了A,還說到了B,還有……
A是江蘇考來的一位同學,我清晰地記著他的容貌、聲音和舉手投足的樣子。我和他有過一次不愉快的事。我們學校食堂中午的飯菜比較好,都是細糧,菜中有時還有幾片肉。我不太喜歡吃肉,只能吃一點瘦的。一天中午,菜中有肉,我菜里的肉還不少,三四片吧,但都帶白的,有的還帶肉皮。我用勺子把白的和皮割下,扔了。這樣的做法讓他看見了。他說你不吃肥肉和肉皮,怎么能扔掉,這是浪費。我說,不扔,你吃呀。他說,我吃,你給我。忘記我還說什么了,可能我的話說得重了,他竟掉了眼淚。后來,他把此事告訴了輔導員老師。老師批評了我。
B是吉林農安考來的一位同學,他上邊的門牙有兩顆下半部有黃紅色的斑點。開始時我想他怎么不刷牙,后來知道那是生長在鹽堿地域的緣故。“文化大革命”中,他和班上不多的幾位同學是另一派,和我們的“觀點”不一致。“武斗”升級后,我做了“逍遙派”,離開學校回家了。在家待了一個多月以后,又有點想學校、想同學。還想,“武斗”厲害了,學校一定更亂了。離開學校回家時把行李捆起來放在宿舍樓里,還能在嗎?于是,決定回學校一趟。回到學校,看到學校滿目瘡痍,一派占據教學樓,一派占據宿舍主樓,樓頂上都架設著兩排數個高音喇叭。不少窗戶都沒了玻璃,有的門也沒了,用磚壘起來堵著。我住的那幢二層宿舍樓的窗玻璃基本上都沒了,門也不知道跑向哪里,室內到處都是磚瓦,哪里還有行李?我漫無目的地在校園內徘徊。后來,有人告訴我,我的行李讓B給拿到教學樓里去了。我到教學樓找到了他,對他表示了感謝。
如今,他倆卻走了,離開了家人、離開了同學、離開了人世。
“聚散皆是緣,離合總關情”。當年,我們從三省來到同一所學校、同一間教室,真的是緣分。4年多以后,我們分別了,又走向了三省的各個地方。46年過去了,沒想到有的人卻沒了,過早地離開了。
4年多的同學情誼,40多年的離情別緒,怎么也不能在電話中一一訴說。放下電話,我忽然想到李谷一演唱的《那溪那山》:“想起那年,有我有你的時候……難得相聚,痛快喝酒……只要你常懷念,兄弟姐妹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