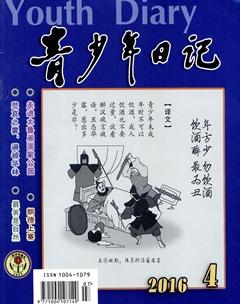朗德上寨
王穎銀
6月20日 雨
此次去朗德上寨純屬在計劃之外的。
下了一夜暴雨,直到早上九點多才轉(zhuǎn)為淅淅瀝瀝。趕到車站卻聽得售票員說西江街上被水淹了去不了。大呼“上天果然薄我”,忽又聽說朗德寨就在附近,比西江還近。朗德上寨,這個地方我是知道的。曾在喜馬拉雅聽書的一個旅行電臺上聽過一篇關(guān)于朗德上寨的游記,這個寨名便深深地刻在了腦海里。未曾想它就在附近。于是立刻出發(fā)去朗德。
坐的是很老式的班車,連巴士都稱不上。車上共十來個乘客,看上去大部分都是如我們這般去游玩的。出了凱里市區(qū),車子在還算平坦的縣道上行駛。左側(cè)有一條河,水流湍急,泥黃色的河水翻滾著,估計是昨晚的暴雨從山上沖刷下來的。再往前,已經(jīng)看得出河邊的好些地方被淹沒,有輛面包車只露出個頂來。車上的人開始騷動起來,拿著手機對著窗外拍照。雨還在下,窗外一片朦朧景象。有一座吊橋橫亙在河上,已然是被河水沖跨了的,橋面垂直掛在河上,在風(fēng)雨中晃蕩。馬路旁有一排藍(lán)色帳篷,上面寫著“救災(zāi)”大字。
我微微興奮起來。想起三毛去瑪丘畢丘那次,回去的途中河水暴漲,火車停走,命懸一線,她卻依舊處之泰然,沉著冷靜。當(dāng)時想自己是如何都做不到像三毛那般灑脫淡然的,如今是不是也能向三毛靠近一點了呢?或許所謂的處之泰然不過是走過萬水千山后的自然而然罷了。
約摸四十來分鐘,班車在寨門前停下。一車人一起往前走,有一個看上去不足二十歲的姑娘,小小的個子,背上卻背了一個一歲左右的嬰兒。這里的女子大都早婚。她是本地人,帶領(lǐng)著我們往前走。不寬的馬路,左側(cè)是高山,偶爾有被大雨沖下來的泥土堆在路旁,右側(cè)垂直下去十來米還是那條沸騰著的河,偶有部分馬路也塌陷下去,看得人有點后怕。河那邊是高山,古樹參天,郁郁蔥蔥,一棟棟3層吊腳樓巍然屹立于斜坡陡坎上。煙雨在山間繚繞,翻滾,沸騰,似乎要迎接一場盛宴。
前面走過來一位大爺,跟我們說,前面危險,分開走,快點過去。背著孩子的女子告訴我們,現(xiàn)在是雨季,滑坡泥石流是常有的事。“那你們要出去買菜什么的了該怎么辦?”朋友問。她笑了,明明還是張娃娃臉,“我們不需要買,我們自己都有。”
走過滑坡的地方便已經(jīng)看得到村子了,有一座木橋橫在河面上。這不像普通的木橋,形如牌樓,狀如涼亭。女子說,這叫風(fēng)雨橋。大概是為村里的人遮風(fēng)避雨而得名吧。橋上人影綽綽,似乎很是熱鬧。待我們走過去,見橋上擠滿了人,大都是躲雨的游客。其他的就是當(dāng)?shù)氐睦先耍┲绶^上簡單地綁了個假發(fā)髻,簪一朵大大的假花。用竹籃裝了各種銀飾、首飾、繡品向游客兜售。不似有些旅行景點當(dāng)?shù)厝死p著你買這買那,她們只是很熱情地介紹她們的作品,讓我們戴上看看,我由衷地說她們做得真好,她們很自豪得笑,臉上的笑容淳樸得不摻一絲雜質(zhì)。
已是中午,我和朋友決定先吃飯再到處轉(zhuǎn)轉(zhuǎn)。這里沒有餐館飯店,只有一些民居在門口掛個“農(nóng)家樂”的木牌子。我們隨便走進一家,穿過左側(cè)長廊便是客廳,即是堂屋。這里家家戶戶都是三層的穿斗式木結(jié)構(gòu)吊腳樓,懸虛構(gòu)屋,架空而立,正中堂屋外側(cè)安有苗語稱為“階息”的“美人靠”。所謂美人靠,就是姑娘們閑時坐著閑聊、刺繡或做其他手工的長椅,獨特的S形曲欄,和堂屋融為一體。坐在美人靠上可以看到對面的山,層巒疊嶂,云霧在山間嬉戲,河水在山腳下狂奔。堂屋的墻上貼滿了照片,都是這家人的孩子穿了苗族服飾的樣子,墻上還掛了幾套苗族服飾。有客人穿了來拍照,主人家也不介意。
雨還在下。有游客在嘟囔這里的落后與不便。朋友原是本地人,于是很不滿地小聲說:“你嫌棄就不要來啊!”我安慰性地朝她笑笑,其實很多人都一樣。想起去年在六盤水紅果的時候,遇到過一次當(dāng)?shù)氐脑岫Y。有喪事的人家都用白布裹著頭,用竹棍挑著棉被床單,上面貼上白紙黑字的挽聯(lián)。有花圈也有扎好的栩栩如生的紙馬、紙牛。有人牽著一頭羊,羊在抵死反抗。朋友的家人請我們一起去吃飯,我們被讓挑著被單跟著走,進退兩難。這與我家鄉(xiāng)的葬禮都不同,我們就是完全陌生的外來客,無意中闖入一場祭禮,生怕一不小心觸犯了人家的忌諱。儀式尚未開始我們已千方百計逃離了那里。事后想來,我總說想尋原生態(tài)的民族風(fēng)俗,可是當(dāng)真正遇見的時候我又唯恐避之不及。便如這些人一樣,可能是我們終究還沒有理解真正的旅行罷。
吃過飯,我們往村里走。這里的道路都是用鵝卵石或青石鑲砌鋪就,蜿蜒著四處延伸。路不寬,兩邊是高高矮矮的房屋,青瓦鋪成的屋檐上長滿了青苔,似是為這古老的村落向世人展示它的生機與活力。檐角掛著老式的馬燈,燈罩上布滿了灰塵和蜘蛛網(wǎng)。房梁上整整齊齊地掛著金黃的玉米棒。轉(zhuǎn)過幾座木樓,便到了一個比較寬闊的場子。場子被稱作“銅鼓坪”,模仿古代銅鼓面太陽紋的圖案,以青褐色鵝卵石和料石鋪砌成十二道光芒,朝著十二個方向伸展。聽說若是不下雨,穿著盛裝的苗族男女便匯聚在這里舉行銅鼓舞、蘆笙舞的表演。
再轉(zhuǎn)過幾座吊腳樓,便到了這里不多的景點之一——楊大六故居。所謂的故居其實和周圍的木樓沒什么區(qū)別,只因楊大六這個人。楊大六苗名陳臘略,咸同農(nóng)民起義首領(lǐng)之一。相傳他跨上戰(zhàn)馬,勇猛異常,嚇得清兵驚問“他是誰?”但聽苗民贊譽道:“羊打羅!”苗話“羊打羅”即“兇死了”、“勇敢極了”之意。清兵不懂苗話,誤以為這位身先士卒的悍將叫“楊大六”,于是便上了書,以至外人不知其真實姓名。從此楊大六作為苗寨英雄被這里歷代苗家人緬懷。
楊大六故居旁的一個木樓里兩位阿婆正坐著聊天,看到我們過去,忙停下來招呼我們過去,又是介紹她們的飾品。盛情難卻,我拿起一只銀手鐲問:“這是真銀嗎?”阿婆用著蹩腳的普通話說:“百分之六十。”另一位阿婆從自己籃子里拿起一件顏色稍暗的,“這是真銀。苗銀做的。”一聽是苗銀我來了興趣,拿起來細(xì)細(xì)看,上面雕刻著不知名的圖案,不是很精致卻有著明顯的民族特色。她又解釋:“都是我請人打的。”剛才的阿婆也笑著附和:“都是請人打的,這些手鏈也是自己編的。很好看的。”我心想,在景區(qū)這樣毫無商業(yè)心機地做生意的人恐怕不多了,剛才在風(fēng)雨橋上那些村民也是這樣,或許只是純粹地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外人認(rèn)可,錢多錢少倒在其次。
雨還在下,拿著一條銀質(zhì)項鏈站在來時的路口,回頭看,這座小小的村寨在風(fēng)雨中越發(fā)寧靜,越發(fā)古老起來。
湖南隆回一中
推薦教師:胡德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