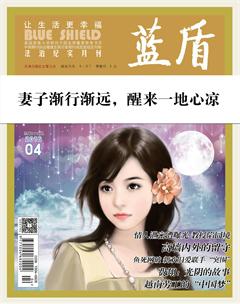靜默是一種教養
徐賁
許多中國人有愛熱鬧,在公共場所大聲喧嘩的習慣。如果有在場者加以規勸或批評,則會堅持說是他們的“權利”。其實,作為自由言論的權利并不等于隨時隨地大聲發言。言論遭禁的被迫“沉默”與說話交流中自我克制的“靜默”并不是同一個概念。
美國社會學家澤魯巴維爾在《房間里的大象:生活中的沉默和否認》一書中,提到了三種可以加以區分的“無聲”機制,它們分別是禮儀性靜默(教養)、社會習慣的不語(禁忌)和政治性的沉默(政治正確),它們是在不同“壓力”下形成的。
靜默是一種自我節制,這種“禮節性的壓抑”是社會交際習俗性的規范,是民間生活傳統的一部分,并不是由政府權力或其他公共權威體制來規范的。作為交談禮儀的一部分,禮節性的沉默一直受到人類學、語言學、社會文化學等的關注。美國人類學家巴索研究了美國西部阿帕奇部落文化的沉默,他指出,阿帕奇人認為,在許多場合都應該保持靜默,而在西方人看來,這些應該是說話的場合。解決沖突,西方人用交談,阿帕奇人會用沉默不語。
奧·斯特貝格在 對冰島人的研究中也得出類似的結論,“冰島人會在可能有危險的時候保持沉默,而說話幾乎總是危險的。”這類似中國人經常說的“禍從口出”。她認為,在沖突時保持沉默是一種“拖延策略”,而且,“說出口的話就再難收回。”這也類似于中國人說的“覆水難收”。不隨便表態,不一定因為是“君子一言、駟馬難追”,而是話一出口,便難以收回。與其說了之后麻煩,還不如干脆別說。說話和花錢一樣,雖然一時痛快,但一出去,就回不來了。
靜默本身可以是一種交流的形式。英國19世紀詩人勃特勒說,“適時的沉默比說話更雄辯。”當然,這不一定是指文學創作中所運用的那種盡在不言之中的沉默。美國社會學家高夫曼說,交談的禮儀是“一種公共的安排,讓人知道什么時候必須說話,什么時候應該沉默”。語言學家稱此為“社會體制性不語”或群體決定的沉默。
交際中的沉默經常會伴隨不同手勢和面部表情,因此具有足夠的表意作用,表達的是熱情、冷淡、親密、疏遠、客氣或敵意等等。不同人士對交際中的沉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中世紀法國神學家和詩人德·里爾稱沉默寡言為傲慢無禮,蕭伯納則稱沉默是“最完美的鄙夷表現”。法國作家德·梅內說,沉默不語是“一個大毛病”,另一位法國作家德·拉羅什富科則主張,“人要知道什么時候該沉默”。
禮儀性靜默需要知道什么場合不該出聲(如廟宇、博物館、劇院、圖書館),對誰不要作聲(如皇帝或逝者),如何用靜默表示敬畏(對神、統治者,為官員出行開道的“肅靜”“回避”),誰應該少言寡語(公婆面前的媳婦、主人面前的奴仆)。
有時候,個人之間的禮儀性沉默(合宜或得體)與群體和社會的習俗沉默(禁忌、規矩)的區別會變得模糊,于是形成某種集體性沉默。法國社會學家孔德稱此為“沉默的合謀”。例如,西西里島上的“緘默”規則要求族群內部的事情不對外人談起。黑幫和黨派也有類似的規矩,稱為“紀律”或“黨性”,懲處破規者比對敵人還要兇狠,是一種靠恐懼和合謀來維持的沉默。
沉默經常是一種令對手害怕的威脅方式和壓制對手的震懾手段。美國人類學家吉色南曾記下一位械斗者的話:“他什么都不說,沉默真叫人害怕。”什么都不說往往比大聲謾罵、肆意宣泄更為可怕,即所謂的“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具有攻擊性的集體(如軍隊、秘密警察)為了保護震懾和威嚇的勢能,都一定會有嚴格的噤聲保密紀律。
麥克康夫萊指出,“沉默是宗教最本質的因素之一。”與其他形式的禮儀性沉默一樣,宗教沉默經常不是負面的,而是有正面的意義。宗教沉默是一種對神的敬畏和虔誠,是在內心傾聽神旨的方式,由于說話無法表達心靈和精神的至深感受,所以緘默不語。《道德經》的“大音希聲”,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說的“凡不能說的,必須保持沉默”,也都可以作宗教的理解。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