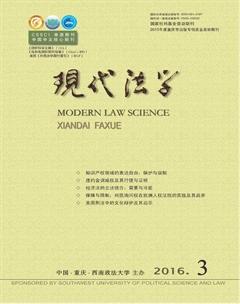美國刑法中的文化辯護及其啟示
摘要:文化辯護是隨著美國移民增加和文化多元凸顯而出現的一種新型刑事辯護。二十多年來,美國法律學者中贊成者與反對者對文化辯護各執一詞。從美國司法實踐來看,贊成者的觀點逐漸被部分法院接受,一些州法院甚至聯邦法院在刑事案件中采納了文化證據。文化辯護現在還不是一種獨立、正式的辯護類型,往往是與傳統類型的辯護結合使用。文化證據既可以在審前程序和庭審程序中起作用,也可能在執行程序中發揮作用。文化辯護可以在辯訴交易中降低控方指控或在審判中使被告人獲得輕罪甚至無罪判決,還可能導致被執行人提前假釋。文化辯護的案件處理過程中,關于文化的專家證言起著關鍵作用。美國刑法中的文化辯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對完善我國相關的辯護制度不乏啟示意義。
關鍵詞:文化辯護;文化多元;社會危害性;文化證據;專家證人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志碼: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3.11
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的移民國家。這種人種上的聚合帶來的是文化上的多元化。而文化的多元又會與法律規則一致性的要求發生矛盾。在刑事領域中也會出現文化沖突:一些少數族裔根據他的文化標準、價值觀念實施的行為卻可能因為體現占主體地位群體的文化標準、價值觀念的法律禁止這種行為而構成犯罪[1]。根據不同文化標準評價行為人是否具有犯意、行為是否構成犯罪、刑事責任的大小,其結論可能相差甚遠。文化差異能否在刑事審判中得到認可,文化證據能否在刑事案件中得到采納,美國法學界對此爭議很大,正如有學者所言:“在過去的二十年中,文化辯護在美國(但不限于美國)法律學者中引發了極大的爭議。”[2]“最大的爭議在于被告人在辯護中是否能夠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依靠他的文化背景。”[3]
一、文化辯護的由來及解讀
(一)文化辯護的由來
美國是實行對抗制(Adversarial process)刑事訴訟的國家。由控方指控被告人涉嫌構成犯罪,并將案件證明到表面成立(Prima facie)的程度。被告方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通常會基于事實和法律,對自己無罪或罪輕提出辯護意見。辯護方在刑事訴訟中與控方直接對抗,在發現刑事案件的法律真實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美國刑事辯護制度極為發達,刑事辯護的種類也多種多樣。在美國傳統的刑事辯護中,有無罪辯護和輕罪辯護,有實體辯護和程序辯護,有基于正當化事由的辯護、可寬恕事由的辯護與法律政策的辯護事由的辯護等。刑事辯護中的具體辯護事由包括正當化事由,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意外事實、警察圈套、執行職務、體育競技、醫療行為、機械故障、被害人同意等;可寬恕事由,包括未成年、精神病或缺陷、夢游癥、自動癥、失憶癥、醉態、認識錯誤、受脅迫、受挑釁等;基于法律政策的辯護事由,如外交豁免、司法(或行政)赦免、超過訴訟時效等。因此,無論是從辯護類型還是辯護事由來看,美國傳統刑事辯護中都沒有文化辯護的提法與地位。
歷史上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法院并不承認被告人的文化與社會主流文化的分野,也不接受文化差異作為一種獨立的、實體辯護事由[4]。例如在1836年英國的Rex v. Esop參見:7 Car.& P.456,173 Eng.Rep.203(1836).案中,一個巴格達人被指控犯有獸奸罪,但被告人聲稱在他的國家中這種行為不構成犯罪。盡管辯護人向法庭提供了關于被告人的文化信息,但法庭并沒有因此而減輕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與英國刑法有著淵源聯系的美國刑法曾經也不考慮移民的文化因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871年Carlisle v. United States
參見:Carlisle v.United States,83U.S.147(1872).案的裁判中,曾引用美國前國務卿Daniel Webster在1851年所說的話:“每個在外國出生但生活在本國的人都應當服從于這個國家,只要他仍然居住在這個國家。僅僅是因為他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事實,他獲得了臨時的保護,也有義務像本國公民一樣遵守居住地的法律。”[5]直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法院才開始采納基于文化差異的辯護。美國之所以從否認到承認文化差異在刑事案件中的影響,是因為移民越來越多,基于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理念,文化多元化(Cultural pluralism)表現日益突出。這種文化差異導致了文化的受眾在行為心理上的不同,以至刑事案件中文化沖突也日益凸顯。有人統計,在20世紀80年代的法律案件中,有2%的案件在處理中存在文化沖突的事實[4]。文化差異導致的刑事案件在處理上的困難也越來越受到法學界的關注。在1985年的一個亞洲移民的刑事案件——People v. Kimura參見:Record of Court Proceedings,People v.Kimura,No.A-09113(Super.Ct.L.A.County Nov.21,1985).案中,檢察官使用了一個叫作“文化辯護”的新理論[6]。1986年發表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評論》上的一篇文章新造了 “文化辯護”這個詞匯當然,文化因素在刑事案件中影響案件的判決,在美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期。例如,188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Exparte Crow Dog(109 U.S.556,570-72(1883).)案中認為,一個印第安人被指控在保留區內謀殺另一個印第安人不適用聯邦刑法,而適用當地部落法。但兩年后,法律規定進行了修訂,認為印第安人與其他人同樣適用聯邦法律。(參見:John Alan Cohan. HONOR KILLINGS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l.W.Int’l L.J.2010(2):224.=。自此,實務人員和理論學者對這一辯護的優、缺點進行了長期的辯論[7]。
(二)文化辯護解讀
由于文化辯護出現的時間尚短,在“文化辯護”的把握上學者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學者就明確指出:“文化辯護”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容易使人誤解的[8]。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學者嘗試對其進行界定。有學者認為,文化辯護是一種運用于移民的被告人解釋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主張減輕處罰的法律策略[9]。有學者認為,文化辯護是指任何在刑事案件中運用文化證據證明被告人行為正當、證明被告人行為不具有刑事可罰性或減輕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情況[10]。還有人認為,“文化辯護”通常是指被告人可以提出文化證據以表明他在行為實施時的心理狀態或意圖[7]。
從這些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化辯護首先是基于文化因素提出的。“文化辯護將兩個獨立存在的概念——文化和法律標準的最重要方面聯系在一起。”[11]文化是一種包括在一個社會中占主體地位的知識、道德和美學標準的觀念系統,它也是一種交際行為的方式[12]67。文化是人內在的道德標準和是非尺度。“無論個人以什么樣的方式接受他所在社會的典型文化元素,他一定會將其內化,這個過程叫作同化(Enculturation)。甚至最不依習俗而行的人都無法逃離他們文化的影響。文化的影響是如此之深,以至甚至精神病人的行為都強烈地反映出文化的特征。”[13]39一個在本國法律文化中遵守法律的被告人在其他法律文化下可能會實施犯罪行為,因為他的價值觀迫使他這么做。當法律背后的道德價值內化為個人行為準則時,法律更為有效。一個公正的法律制度應當考慮各個被告人的道德維度[14]。人類的行為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受其社會和文化背景決定。“不同的社會階層、種族群體、宗教群體、國家,其信仰、觀念、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極為明顯。”[15]67因此,文化的差異導致行為人對行為價值標準的理解差異,但行為人根據本屬于自己的文化實施的行為卻可能會被其他的文化所禁止。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認為,少數族裔中支配行為人行為的文化應當能在主流文化范圍內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據使用,以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意圖和心態,從而證明行為人罪的有無或輕重。
其次,文化辯護的適用對象主要是外國移民或新來到美國的人(以下統稱為外國移民)。即使是外來族裔,如果其本身就是出生在美國、成長在美國,在學校、社區等接觸的都是美國的文化,也就不會因為文化的差異而出現價值觀念上的不同,行為標準也就不會有差異。因此,文化辯護主要適用于不是出生在美國的外國移民。在解讀文化辯護時,有人甚至強調文化辯護適用的主體是新移民的被告人。例如有學者認為:文化辯護中新來者(New comer)的行為是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所塑造,他們沒有美國刑法中規定的構成犯罪所需的必要的心理狀態[16]。
再次,文化辯護只適用于特定刑事案件中。隨著國家間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相互的文化滲透、借鑒使文化不斷出現趨同與融合的趨勢。從法律文化上看,法律觀念、價值、規則也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中相互影響,法律文化的趨同日益凸顯。因此,就法律規則而言,各國法律規定在眾多領域都大同小異,也就不存在國家間刑事法律文化的全面、根本性沖突。這種情況下,從國外來到美國的移民就不會在美國刑事法前無所適從。因而并不是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這些被告人都會提出文化辯護。當然,這種文化的融合只是大體融合,不是整體同一,因此,不同文化圈中文化的內容還是會有差異。只有在存在文化沖突的刑事案件中才可以適用文化辯護。實證研究表明,文化沖突主要存在于一些與家庭榮譽(Family honor)、重婚、離婚、血親復仇、傳統醫療、巫術、禮射(Celebration shooting)等有關聯的案件中[1]。
二、學界關于文化辯護的爭議
有學者說,一旦提到文化辯護,人們便會立即提出四個突出的問題:一是確定什么樣的被告人群體可以提出這一辯護;二是如何保持刑法對移民的一般預防功能;三是如何保持刑法對大多數人的公平;四是如何維護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le of legality)[6]。從美國法學界對文化辯護的態度看,反對者與贊同者之間的爭議主要圍繞這些問題展開,但并不限于這幾個方面。
(一)文化辯護反對論
1.不知道法律不是寬恕的理由
新移民美國的人提出文化辯護最有力的理由在于,他們是從國外新移民來美國的,不在美國出生、成長,自己原來國家的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和行為規則影響和決定著自己的行為,不熟悉體現美國價值觀念、道德準則的法律規定。反對者認為,法律格言早已闡明“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的理由”(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這一格言經常用來警告那些身處法庭的人,不要主張自己不知道特定法律的存在或對法律規定了解不充分,因為法庭不贊同公民不知法律的主張。”[17]而且,如果承認文化辯護則會使“不知法律”成為罪刑法定原則的例外而與該原則相矛盾[6]。有學者聲稱:大多數人第一次聽到文化辯護時,因擔心它會導致無政府主義而拒絕它。如果每個人都能主張法律的例外,那么法律將無力把社會個體緊緊聯系在一起。少數族裔應當改變他們的行為以使其行為與所在地的法律相一致[18]5。拒絕文化辯護將鼓勵移民對歸化地的法律進行了解[14]。
2.文化辯護違反了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是美國的一個憲法性原則。一方面,平等保護不能考慮被保護人的種族、性別或來自什么國家。如果被告人基于自己主觀的信念實施的違法行為受到寬恕,那么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和對自己行為后果的預測性將受到損害。因此,文化辯護通過給予移民被告人特殊優惠的處遇會歧視社會上的其他民眾。而且,“文化辯護給予移民被告人以免予定罪或從寬處罰的機會,那么這些行為的被害人就無法得到平等的保護”
文化辯護經常受到女權主義者的反對,因為這些犯罪的受害人經常是婦女和兒童。(參見:Nancy S. Kim. BLAMEWORTHINESS, INTENT, AND CULTURAL DISSONANCE: THE UNEQUAL TREATMENT OF CULTURAL DEFENSE DEFENDANTS[J]. U.Fla.J.L.& Pub.Pol’y,2006(2):199.)事實上,女性和兒童往往是文化辯護案件中被指控行為的受害人。以女性的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為例,2005年11月25日聯合國發表的《改變具有傷害性的社會習俗——婦女生殖器摧殘》報告中稱,全球每年仍有300萬女童遭受生殖器切割。美國于1996年成文法禁止對女性實施割禮,并將其列為犯罪行為。但移民到美國的人中仍然有人保持原有習俗,對女性實施割禮的行為。例如,2003年,一個名叫Khalid Adem的被告人因為毀損女性生殖器而被捕;2004年住在南加州的一對夫婦也因為毀損女性生殖器而被捕。在這兩個案件中,被告人均提出了文化辯護。。“考慮某人的文化背景根本上與法官考慮諸如性別、年齡、心理狀態等其他的社會特征沒有區別。”[19]另一方面,平等原則要求平等遵守法律規定。居住在美國的移民應當遵守美國的法律和習慣。“行為地法律(Lex loci)必須適用。不能允許他們躲在他們文化傳統的背后。如果一個美國人去新加坡并違反了當地的法律,他將會根據當地的法律受到懲罰。同樣的標準應當適用于在美國的新加坡人。”[20]“盡管不承認文化辯護對移民的被告人而言可能會不公正,但承認文化辯護對大多數被告人而言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們無法適用這一辯護。”[14]
3.文化辯護可能被濫用
文化辯護的存在通常適用于行為受到國外文化影響的群體,但這一群體難以確定。首先,文化本身并不是如磐石一樣固定不動地、靜態地存在。“文化”和“傳統”的定義和意義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并取決于其背景情況[20]。“哪些群體的人能夠說他們具有可以適用文化辯護的‘文化’?為什么?”“如何在時間、空間和人群方面確定文化的邊界?”[21]例如,有學者擔心,移民到美國的兒童受到父母的虐待后,作為責任人的父母在面臨虐待兒童的指控時可能用文化辯護來逃脫被定罪或獲得從輕懲罰[22]。因此,基于文化而進行的辯護也就處于一個完全不確定的狀態。其次,如何明確界定可以提出文化辯護的被告人的范圍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14]。如果說新移民或剛到美國的人行為受到原文化的影響而可以提出文化辯護的話,那么在美國居住多久就可以說了解美國文化,自己原有文化不影響其價值觀念和行為規則了?在People v.KimuraKimura案(No.A-091133 (Santa Monica Super.Ct.Nov.21,1985).)發生于1985年。一名生活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日本裔婦女發現她的丈夫有外遇后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孩子并試圖自殺。辯護人提出被告人自殺是因為在日本傳統文化中,孩子是母親身體的一部分,而且婦女可以處理自身以免被丈夫不忠行為羞辱。案中,被告人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4年,辯護人仍然提出了文化辯護。為了社會秩序的目的,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的區分標準應當是客觀的。社會應當建立在法律的權威之上。應當對刑法進行客觀解釋,而不能像允許文化辯護一樣主觀地加以解釋。“當前并沒有被告人提出文化辯護的指南或程序保障,文化證據的提出在每個案件中都不相同。這會導致官員們在文化沖突案件中自由裁量權的任意適用。”[14]
4.文化辯護不利于實現刑法目的
一般預防是刑法的重要目的。反對者認為文化辯護的出現成了實現刑法目的的障礙。例如有學者認為:基于移民被告人的文化而寬恕這些被告人,會給移民傳遞這樣一種信息,即他們無須遵守所在地的刑法,刑事司法制度會寬恕他們的錯誤行為。這樣,文化辯護對刑法預防犯罪的功能會有消極影響,這對社會安全也不利[23]。特別是這類案例通常由媒體過度宣傳,無疑會增加移民對文化辯護寬恕危害行為的了解。同時,“那些因為文化的原因而被迫實施某種犯罪行為的人無論是否給予文化辯護的機會,刑法的預防犯罪功能對他們都不起作用”[5]。
(二)文化辯護贊成論
1.“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的理由”并不是一個絕對規則
“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理由”的法律格言并不是絕對的。“該格言有時與刑法的基本原則是沖突的,因為刑法認為道德上不具有過錯的行為不應當受到懲罰。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理由這一規則應當進行重構,即合理的不知法律不能作為不相關的刑法事實而排除。”[24]“當不知法律否定了指控的犯罪所必需的心理狀態的存在時”,不知法律就可以成為辯護事由[25]356。美國《模范刑法典》2.04(3)也對這一格言做了例外性的規定。《模范刑法典》的評述者也認為,當某人既不知道其行為的犯罪性也沒有合理的途徑知道相關信息,那么就不得懲罰這個人。在美國刑法中,危害行為與犯意是兩個不可或缺的表面成立條件美國刑法中的犯罪成立條件包括表面成立條件和實質成立條件兩個方面。(參見:賴早興. 美國犯罪成立要件與證明責任分配[J].法學家,2007(3):153-155.)。正如有的學者所言:“一般說來,犯罪包括兩方面的要素:危害行為(Actus reus),即犯罪的物理或外部特征;犯意(Mens rea),即犯罪的心理或內在特征”[26]85。在證明犯意時,雖然控方并不要證明被告人意圖違法,但一些成文法要求控方證明被告人在實施行為時具有特定的心理狀態(即特定的犯罪意圖),沒有這種心理狀態就不能認定構成犯罪。實際上,行為人行為時的心態往往受到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影響,某一種文化所禁止的行為在另一種文化中卻是被許可、包容甚至鼓勵的。新移民美國的人往往受原來文化的支配很難短時間內適應美國文化的要求。因此,按美國刑法規定的具有犯意的行為人完全可能事實上不存在成立某種犯罪所要求的犯意。有學者主張:“文化辯護通常是被當作一個可寬恕事由來運用。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違法的,但因為行為人缺乏構成某罪所需的可責性的心理要素而被寬恕。”[14]而且,在文化辯護的案件中,“文化辯護要求被告人基于他們自己文化背景中確定的、慣常的規則進行辯護,而不是僅僅依據對主流文化不了解。”[27]
2.文化辯護是實質平等的要求
法律平等包括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28]94-96。刑法中的實質平等就是在遵守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行刑事司法個別化原則(Principle of individualized justice),在刑事案件的處理中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做出合理的判決。對于文化辯護的贊同者來說,平等對待僅僅意味著:法律制度并非統一地適用,而是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不同地適用[29]。“為了達到每個被告人的個別正義,對其懲罰的尺度應當與其可罰性的程度相一致。在法律的限度內懲罰一個對特定法律不了解的人是不公正的。當被告人沒有與他人有同樣的機會在文化環境中成長以了解或學習法律,那么歸罪于一個不了解法律的人就是不公正的。法律中應當考慮這一因素,以達到對被告人的個別公正。”[14]
在美國長大的人,有一系列的社會力量(如學校、社區、教會等)傳授法律知識、培養價值觀念,美國本土的價值觀念、法律意識在他們腦海中逐漸根深蒂固。但新近移民來美國的人卻沒有得到相應社會化力量的幫助,因而缺乏同樣的法律知識、價值觀念的積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們腦海中根深蒂固的是他們原來所在國家的價值觀念和法律準則。“對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人和新近移民美國的人采取同樣的標準而對其差異視而不見,顯然是不公平的。”[8]在刑事指控中不讓新近移民提出文化證據對他們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吸收和理解本地的刑事法律[7]。
3.文化辯護是保持文化多元的需要
文化多元是國際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鑒的結果。文化多元化的前提是承認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相對主義認為道德原則是相對的,因而不存在一體適用(One-size-fits-all)的道德[5]。它“要求承認多元社會道德體系的存在”[30]。文化多元化“意味著每一個少數群體都有權保持某種文化價值,因而維持自己的認同感”[4]。從法律文化的角度看,當移民和難民到達一個新國家,他們帶來的是原有的法律文化與法律傳統。這些法律傳統與新國家已經存在的法律也存在匯合的過程,這必然會導致法律的多元化。“多數群體不能僅僅因為存在的差異而懲罰少數族裔。如果一個法律制度因為被告人遵守自己的文化而懲罰他,那么這個法律制度發出了這樣一個信息:被告人的文化是低下的。”[14]只有將文化辯護作為一種獨立、正式的辯護才能有效地防止主流社會用刑事司法制度損害文化的多樣性[31]。承認文化辯護是美國保持文化多元必不可少的,通過保持少數民族的重要價值,文化辯護有助于維護文化的多元性[7]。
在國際人權法中,所有的國家都有義務保護公民的文化權利。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規定:在那些存在著人種的、宗教的或語言的少數人的國家中,不得否認這種少數人同他們的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實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就享受文化權利而言,至少移民到其他國家的人有機會告訴法庭促使他實施了行為的文化與新國家的文化明顯是沖突的。因此,為了文化權利的實現,應當構建文化辯護制度[19]。
4.文化辯護的濫用可以防止
文化辯護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提出。什么情況下可以提出文化辯護呢?有學者認為:在文化為被告人的行為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非犯罪的解釋時,或當文化性的要求將被告人置于特別壓力之下而無法做出選擇時,法庭應當考慮文化證據。相反,如果被告人主要意圖是傷害其他的人,他僅僅宣稱文化認可他的這種暴力行為時,法庭應當拒絕寬恕他[32]。這只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或理念,具體制度上應當考慮得更為細致。有學者提出,為防止文化辯護的濫用,法庭應當考慮三個基本問題:“一是訴訟當事人是少數族裔的成員嗎?二是這個群體是否存在這樣的傳統?三是訴訟當事人行為時受到了這一傳統的影響嗎?”[19]基于此,一個提出文化辯護的案件應當具備三方面的條件:一是這里面存在文化原因。二是自己的文化認可這種行為。在文化認可理論下,被告人承認自己實施了違法行為,但他主張不應當承擔美國刑法所規定的刑事責任,因為他本國的文化認可或寬恕這種行為。三是文化要求,即自己國家的文化迫使或要求他有義務做出某些行為。
5.文化辯護不會妨礙刑法目的的實現
文化辯護與傳統的其他辯護類型不同,它只能在少數、特定的案件中提出。“能夠適用文化辯護的犯罪非常少,所以文化辯護的適用不會損害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7]而且,刑法的另一個目的在于懲罰犯罪,懲罰的尺度就是罪刑均衡。“正是罪刑均衡的觀念為文化辯護提供了正當化理由。如果被告人的行為受到文化因素的激勵,那么其應當受譴責性就小,因此其應受的懲罰就要輕。”[18]11因此,從這個方面看,文化辯護不是妨礙了刑法目的的實現,而是有助于刑法目的實現。
三、司法實踐中的文化辯護
曾經有學者斷言:“文化辯護作為非法行為的一種正式的寬恕理由當前只存在于法學理論界中,將來在美國任何司法區都不可能獲得承認。”[8]事實情況如何呢?從美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法院對于文化辯護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有的法院完全不采納文化證據。“在法庭中提出文化證據最大的障礙在于法官的這樣一種觀念:從其他文化中而來的人應當遵守居住地國家的標準。這個我稱之為‘同化推定’(Presumption of assimilation)。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法官經常基于這種與案件無關的理由拒絕考慮關于文化背景的證據”。[18]6有的法院則允許被告人在謀殺罪、強奸罪、兒童或配偶的虐待等犯罪的刑事審判中提出文化證據,而這種文化證據對案件的審理結果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采納文化辯護的法院大多數是州法院,但也有聯邦法院。例如1991年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在Mak v. Blodgett參見:754 F Supp. 1490(W.D.Wash.1991).案的判決中認為:“辯護律師沒有提出文化辯護可以認定為辯護人的不盡責。”總體上,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法院允許被告人在刑事訴訟的各階段提出文化背景的證據已經成為一種增長的態勢[7]。
(一)文化辯護在刑事辯護中的地位
在刑事案件中采納文化證據的法院現在并沒有承認文化辯護是一種獨立的辯護類型。“在指控犯罪或量刑時,被告人的責任能力應當被考慮。檢察官或陪審團應當考慮被告人犯罪行為背后的文化因素,但不是作為正式、獨立的文化辯護。”[14]通常情況下,文化辯護與傳統刑事辯護共同使用。“‘文化辯護’在美國法學界還不是一個得到正式確認的積極辯護(Affirmative defense),相反,‘文化辯護’通常是指被告人可以提出文化因素以表明他在行為實施時的心理狀態或犯意。實踐中,文化辯護通常不是僅僅依據文化因素這一孤立的事實因素,相反,文化因素通常與一個或多個得到確認的刑事辯護(如精神病、受挑釁、法律錯誤等)相聯系。”[7]將文化因素在已經存在的辯護中運用比將其作為一般的、獨立的辯護更具有策略性[33]。有學者將其形象地概括為“文化+”(Culture-plus)模式,即在傳統刑事辯護內使用文化因素[7]。一般認為,司法實踐中將文化辯護與傳統辯護結合,體現了刑事司法制度已經在法律秩序與文化多元、司法個別化之間實現了協調。“移民被告人聘請的辯護人同樣是其他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可以聘請的。任何被告人可以基于精神病辯護、能力減弱辯護、法律錯誤辯護和激情辯護而主張自己不具有實施某犯罪所需的犯意。因此,當刑事司法制度尊重文化多元和司法個別化中采納了文化辯護,那么它就能維持當前法律秩序的標準。”[23]
司法實踐中的一些案例證實了這種情況。例如People v. Chen參見:No. 87-7774 (N.Y.Sup.Ct.Mar.21,1989).案中,一個生活在紐約的中國男子知道他的妻子有婚外情后用棍棒將妻子打死。在法庭審理中專家證言表明,根據傳統的中國文化,一個妻子的淫亂行為給婚姻帶來羞辱,也是丈夫個性懦弱的表現。審理法官認為:“陳的行為是文化的產物……文化不是一個可寬恕事由,但它是使被告人更容易爆發的因素。這個文化因素正是暴發的因素。”[34]法官認為被告人因挫折而心理失常,“這沒有達到法定精神病的程度,但基于文化的因素,他妻子的行為對于一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人產生了影響。”本案最初的指控是二級謀殺,刑期從最低十五年監禁刑至終身監禁,后來實際指控的是二級過失殺人,刑期為最高十五年有期徒刑,最后法院判決的是緩刑五年。又如,在People v.Wu參見:235 Cal.App.3d 614 (Cal.Ct.App.1991).案中,一位中國籍女子在得知其丈夫有外遇后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并試圖自殺。辯護方提出了自動癥(Automatism)辯護和文化辯護。精神科專家證明被告人行為時意識處于朦朧狀態。跨文化的心理學專家證言表明,被告人的感情沮喪只能根據其文化背景進行理解,她的行為有文化動機,她希望把她自己和兒子從羞辱和虐待中拯救出來,并在死后再相聚。但法官拒絕指示陪審團可以考慮被告人的文化背景證據,被告人被裁定構成二級謀殺罪。但在上訴審中被告人的文化辯護主張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最后,被告人被裁定犯故意殺人罪,但獲得了較輕的刑罰。
對于司法實踐中將文化辯護與其他傳統辯護結合而不給予其獨立、正式的辯護地位,有學者提出了異議。“支持將文化辯護作為獨立、正式的辯護的人認為,在一個所謂文化多元和司法個別化的國家,將文化辯護與傳統的其他辯護結合的做法無法為移民被告人提供足夠的保護。”[4]“在文化辯護還不是一個獨立正式辯護的情況下,被告人可能主張他在實施錯誤行為時患有精神病。他的文化因素導致的對當時情況的理解將被當作精神病,他因此也會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簽。即使精神病辯護成功,被告人也會因為患有精神病而被長期關押。”[23]“獨立、正式的文化辯護的一個主要的好處在于,它將確保法庭考慮文化證據,而不是將關于采納證據的適合與否的決定權留于個別法官,正式的政策將確保法院的門是對文化資料敞開的。”[19]
(二)文化辯護起作用的階段
一般認為,文化信息和專家證據可以在審判前或審判中作為與訴訟的爭點相關問題被提出來。例如,文化證據可以在辯訴交易中或在定罪、量刑階段作為與犯意、激怒的原因、理性、減輕罪責等相關的問題提出來[8]。文化證據能影響審前程序中所做的決定,如是否需要逮捕,是否要進行辯訴交易。在審判階段,被告人可以尋求提出文化證據以否定存在成立犯罪所需的要素,從而得到無罪判決;文化辯護也可以用以支持精神病辯護或受挑釁的辯護。在上訴審中,文化主張也可以以下幾種形式作為上訴理由:法官認為不相關而不當地排除了文化證據;法官拒絕給陪審團關于文化證據恰當分量的指示;在量刑階段辯護律師沒有提出文化因素作為考慮因素[18]7。
司法實踐中的案例也表明,文化辯護在庭審前和庭審中均對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認定起著重要作用。我們首先來看一個文化辯護在辯訴交易中起作用的案例——People v.MouaNo. 315972-0 (Fresno County Super.Ct.Feb.7,1985).案。本案中,一名居住在美國的名叫Moua的老撾洪族男子被指控強奸和綁架一位老撾婦女。被告人聲稱他的行為不是犯罪,因為他實行的是老撾洪族傳統的搶婚儀式(抓到婦女,將其帶到自己家中發生性關系,成立婚姻)。辯護人提出了洪族這一文化儀式的證據。在辯訴交易中,被告人承認犯有非法拘禁罪,檢察官將原來的綁架和強奸指控降低為非法拘禁罪的指控。
我們再來看一個文化辯護在庭審中起作用的案例——Krasniqi案Hugh Downs & Barbara Walters, “WE WANT OUR CHILDREN BACK”, 20 /20 (18 August 1995) (Nexis)[Krasniqi].。在本案中,被告人Sam Krasniqi是一個定居在美國的阿爾巴尼亞人,他在公共體育館撫摸了他四歲女兒的生殖器。檢察官認為這種撫摸行為是為了性滿足,被告人構成性虐待犯罪。性虐待是一種特定意圖的犯罪,即為了性滿足,因此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人有這樣一個意圖。當被告人在德克薩斯州刑事法院被起訴時,一個阿爾巴尼亞文化研究的專家證明這種撫摸在該文化中表達的是愛的情感,而不是為了性滿足。在庭審中,法院考慮了辯護人提出的文化辯護,被告人隨后被裁定無罪。
其實,文化辯護并不僅僅在庭審前或庭審中起作用,在案件判決后的刑事執行過程中,文化因素仍然會起作用。我們來看一個案例——State v. Chong Sun France379.E.2d 701 (N.C.App.1989).案。本案中一個名叫Chong Sun France的韓國婦女被指控故意將她的兒子關在衣柜中致其死亡,但被告人聲稱他兒子的死是意外。在審理的過程中,被告方沒有向陪審團提交文化證據,陪審團裁定被告人構成二級謀殺和虐待兒童罪,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在該案判決后,由在美國的韓國婦女組織的群體運動指出,在刑事程序中應當考慮被告人的文化證據;韓國文化的專家證言證明對韓國人而言將自己的孩子獨自留在家里沒有人照看是通常的習慣做法,被告人沒有殺害自己孩子的故意。假釋France的申請人認為:“France女士將她的孩子獨自留在家里是錯誤的,這違反了法律的規定,但考慮到文化差異,我相信她沒有殺害她的孩子。” France于1992年12月31日提前獲得假釋。這一提前假釋就是因為法院沒有允許陪審團考慮France文化背景證據而致政府受到了極大壓力的結果[23]。
(三)文化證據的運用
文化辯護作為一種新型的辯護或新的辯護事由,涉及抽象的文化因素,這對從事法律工作的檢察官、律師、法官甚至假釋官等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文化辯護的刑事案件中,“專家證據在文化辯護的案件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它證明文化傳統的存在,并有助于表明是否文化傳統事實上在特定情形下對個人產生影響。沒有專家證據的幫助,法庭很難在案件審理中理解提出的文化主張。”[18]11同時,辯護方通常會收集一些與被告人有同樣文化背景的人的證言,以文化受眾的身份說明自己對文化的親身感受。例如,在State v. Kargar
679 A.2d 81,1996 Me.162,68 A.L.R.5th 751.案中,被告人是一個阿富汗的難民,住在緬因州,幫助鄰居照顧小孩。一天鄰居發現被告人親他自己18個月大孩子的陰莖,而且在被告人家里還發現了一張他親孩子陰莖的照片,于是便報了警。被告人面對警察的調查承認自己親了小孩陰莖的事實,但他辯稱親小孩的陰莖在他們的文化中是可以接受的通常做法。在法庭審理中,辯護方提供了一些了解阿富汗人的證言,證明在阿富汗親自己小孩身體的任何部位都是一種習俗和通常做法,這是為了表達對孩子的愛憐;而且,親一下自己小孩的陰莖或將其整個放入口中都一樣,并不是為了性的感受。辯護人還提供了包括亞利桑那大學近東研究中心Ludwig Adamec教授和紐約阿富汗圣戰情報中心Saifur Halimi主任(同時也是一位宗教學教師)在內的一些書面專家證言[26]719。在量刑階段,一個當地牧師作證,證實被告人被定罪的行為在當地文化中是無罪的、適合的,并非性行為。所有這些證言都證明在當地法律中,被告人的行為既不是錯誤的行為,也不是性侵犯行為,被告人不知道他的行為在緬因州的法律中是非法的本案并沒有在一審法院得到無罪判決。在上訴審中,緬因州最高法院基于文化辯護撤銷了被告人的有罪判決。(參見:John Alan Cohan. HONOR KILLINGS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l. W.Int’l L.J.2010(2):233.)。
除專家證言外,其他一些人的證詞或呼吁都會對文化辯護的案件產生影響。在People v. Kimura一案中,數千日本人簽名呼吁,在日本對為免于家人的羞辱而與孩子一同自殺行為的指控不會超過過失殺人罪,通常判處的刑罰也非常輕,一般是暫緩量刑、緩刑等。在State v. Chong Sun France案判決后,在美國的一些韓國婦女組織了群眾運動,呼吁在刑事程序中應當考慮被告人的文化證據。這些都對案件的處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四、啟示
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我國也是外國人入境人數眾多的國家。根據國家旅游局的統計,2014年1月至12月入境旅游外國人人數為2636.08萬人。另外,國際移民組織發布的《2013世界移民報告》顯示,到2011年,在中國居住著68萬多名外國人。這些人受其文化的影響,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和方式等也會與我國公民不同。,最新進行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漢族人口約為12.259億人,占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約為1.1379億人,占8.49%。我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從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著各自的發展歷史文化心理倫理道德和審美意識”[35]。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必然會導致行為人價值判斷、思維習慣、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因而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上出現不同,在刑法處遇上就應當有區別對待的措施。如有的少數民族男女一旦有了婚約,男方不管女方是否同意就硬行搶親、強行同居;有些民族如拉祜族、哈尼族、傣族等廣泛延續早婚傳統,女孩13歲就舉行成人禮(如藏族幼女的“戴天頭”習俗),此后男子與其發生性行為或結婚都是習俗所允許的,不會受到社會的譴責和干預[36]。如果這些行為均按我國刑法的規定作為犯罪處理,顯然在刑法適用上會遇到很大的阻力。正因為如此,《刑法》第90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刑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這說明在我國刑事立法上承認了文化因素對行為人的影響。據統計,目前我國共建立了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在55個少數民族中,有44個建立了自治地方,實行區域自治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71%。如果這些地方根據《刑法》的規定結合本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變通或補充規定,文化因素對行為人的影響就會體現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但事實上,我國民族自治地方并沒有充分運用《刑法》第90條的授權根據陳興良教授的說法,“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據我所知,還沒有這種變通或補充的規定出臺。”(參見:陳興良.刑法疏議[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198.)。從司法實踐中看,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司法機關開始關注民俗對行為人的影響,如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發布了《關于進一步發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年發布了《關于在審判工作中運用善良民俗習慣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指導意見》,但它們關注的是“善良風俗”、“善良民俗習慣”,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影響,因為文化并非都是善良風俗或民俗習慣。
如何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充分考慮不同民族、種族的文化對行為人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影響,是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雖然美國是多種族的國家,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但兩者共同的文化多元性特征決定了我們在法律制度的構建中可以相互借鑒。就刑法領域而言,美國刑事法中的文化辯護為我們重視刑事訴訟中的文化因素、構建完善的相關制度提供了思考的方向。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一是確立文化辯護事由在我國《刑法》中的地位。我國《刑法》規定的辯護事由主要是刑事責任年齡、精神病、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犯罪停止形態、坦白、自首和立功等,尚無文化辯護的位置,甚至連學界都沒有充分重視這一辯護事由。從美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有的司法區將文化辯護與其他傳統辯護結合而不給予其獨立、正式的辯護地位,有的做法與此相反。筆者認為,如果文化因素是與精神病、受挑釁、法律錯誤等傳統辯護事由共同作用,那么將其作為傳統刑事辯護內的因素也無不可;但如果是文化因素單獨起了作用,也應當允許辯護方單獨提出文化辯護。
二是明確文化辯護證據可以適用的階段。刑事訴訟(公訴)分為偵查、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法庭審理、執行等階段。在美國刑事訴訟中,文化信息和專家證據一般在審判前或審判中作為與訴訟的爭點相關問題被提出來,如果這一過程中遺漏了這些信息或證據,在刑罰執行階段仍然可以提出。筆者認為,這一做法是可取的,我們雖然強調被告方應當在審判前或審判中提出文化辯護的信息或證據,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其在刑罰執行中提出。
三是重視專家證人的作用。文化辯護的提出使檢察官、律師、法官甚至假釋官等面臨新的挑戰,因為被告方提出的文化證據的相關性、合法性、真實性判斷與傳統證據存在極大的差異。尤其是這種文化證據的判斷中還存在價值判斷與作用程度判斷的問題,這不是一般法律人可以勝任的,這就要充分重視專家證人的作用。從美國刑事訴訟中文化辯護適用案例看,專家證人在幫助陪審團或法官等理解特定文化因素對行為人的影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機關可以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勘驗、檢查或鑒定,“專門知識的人”還可以出庭就鑒定人做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這說明我國還沒有構建起通常性的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現有制度下,文化辯護提出后被告方很難請求法庭讓熟知其文化習俗的專家證人出庭為其作證,因為這類案件并不存在鑒定的問題。因此,在文化辯護案件處理過程中為了使檢察官、律師、法官、假釋官等得到專家的幫助,有必要建立起通常性的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參考文獻:
[1] Tamar Tomer-Fishman. “Cultural Defense,” “Cultural Offense,” Or No Culture At All?: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sraeli Judicial Decisions In Cultural Conflict Criminal Cases And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m[J].J.Crim.L.& Criminology,2010(2):476,496.
[2] Sigurd D’Hondt. The Cultural Defense As Courtroom Drama: The Enactment Of Identity,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In Criminal Trial Discourse[J]. Law & Soc. Inquiry,2010 (1):67.
[3]James C.Fisher. Role Of Morality In Cultural Defense Cases: Insights From A Dworkinian Analysis[J].Birkbeck L.Rev.,2013(2):281.
[4] Note. The Cultural Defense In The Criminal Law[J]. Harv.L.Rev.1986 (6):1293,1293,1293,1295.
[5] John Alan Cohan. Honor Killings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l.W.Int’l L.J.,2010(2):223,248,225.
[6] Julia P. Sams.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Cultural Defense”As An Excuse For Criminal Behavior[J].Ga.J.Int’l & Comp.L.,1986(2):335,345,351-352.
[7] Naomi Mendelsohn. At The Crossroads: 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A Cultural Defense To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J].Rutgers L.Rev.,2004(4):1019,1020,1020,1021, 1023,1016-1019,1020,1031.
[8] Kristen L. Holmquist. Cultural Defense Or False Stereotype?[J]. Berkeley Women’s L.J.,1997(1):61,63-64,61,63-64.
[9] Alice J. Gallin. The Cultural Defense: Undermining The Policies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J]. B.C.L.Rev.,1994(3):735.
[10] Nancy S. Kim. Blameworthiness,Intent,And Cultural Dissonance:The Unequal Treatment Of Cultural Defense Defendants[J]. U.Fla.J.L.& Pub.Pol’y.,2006(2):200.
[11] Maria Beatrice Berna. Cultural Defense:Possible Correlations And Applicatiot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omen’S Rights[J]. J.L.& Admin. Sci.,2015(4):191.
[12] Levine,R..Roperties Of Culture: An Ethnographic View. In Schweder,R.And Levine, R.,Cultre Theory: Essays On Mind,Self,And Emo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3] Ralph Linton. Tree Of Culture[M].New York:Alfred A. Knoff Inc.,1955.
[14] Carolyn Choi. Application Of A Cultural Defens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J]. Ucla Pac. Basin L.J.,1990(8):86,89,87,89,86,86,86,88-89.
[15] Marshall H.Segall,Et Al.Human Behavior In Global Perspective:An Introduction To CrossCultural Sychology[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1990.
[16] Sherman. Legal Clash Of Cultures[J].Nat’l L.J.,1985(8):1.
[17] Jennifer L.LairSmith. 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 Distinguishing Subjective Intent From Mistake Of Law In State V.Barnard[J]. 1 Charlotte L.Rev.,2009(2):335.
[18] Alison Dundes Renteln. The Cultural Defense[M].New York:Oxford,2004.
[19] Alison Dundes Renteln.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n.J.L. & Soc.,2005(1):48,48-49,48-49.
[20] J.Tom Morgan, Laurel Parker. The Dangers Of The Cultural Defense[J]. Judicature,2009(5):206,206.
[21] Valerie L. Sacks. An Indefensible Defense: On The Misuse Of Culture In Criminal Law[J]. Ariz.J.Int’l & Comp.L.,1996(2):534.
[22] R. Lee Strasburger.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The Cultural Defense As Justification For Child Abuse[J].Pace Int’l L. Rev., 2013 (1):162.
[23] Sharon M.Tomao. The Cultural Defense: Traditional Or Formal?[J]. Geo.Immigr. L.J.,1996(2):253,253,253,242.
[24] Kumaralingam Amirthalingam. Ignorance Of Law, Criminal Culpability And Moral Innocence: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Blame And Excuse[J]. Sing.J.Legal Stud. 2002(1):302.
[25] W. Lafave, A.Scott. Handbook On Criminal Law[M].St.Paul,Mn:West Publishing Co.1972.
[26]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M].New York: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2009.
[27] James M. Donovan, John Stuart Garth. Delimiting The Culture Defense[J]. Quinnipiac L.Rev.,2007(1):112.
[28] 賴早興.刑法平等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9] Sam Beyea. Cultural Pluralism In Criminal Defense: An Inner Conflict Of The Liberal Paradigm[J]. Cardozo Pub. L. Pol’y & Ethics J., 2014(3):719.
[30] Alison Dundes Renteln.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Law & Contemp.Probs.,2010(2):256.
[31] Anh T. Lam. Culture As A Defense: Preventing Judicial Bias Against 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J]. 1 Asian Am.Pac.Is.L.J.,1993(1):49.
[32] Kay L.Levine. 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Of Crime And Culture:A Sociolegal Perspective On Culture Defense Strategies[J]. Law & Soc.Inquiry,2003(1):80.
[33] Kent Greenawalt. The Cultural Defense: Reflections In Light Of 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J]. Ohio St.J.Crim.L,2008 (1):321.
[34] Diana C.Chiu. The Cultural Defense: Beyond Exclusion, Assimilation,And Guilty Liberalism[J]. Cal.L.Rev.,1994(4):1053.
[35] 田聯剛,趙 鵬.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關于少數民族文化在中華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思考[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2.
[36]鄭鶴瑜.論我國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刑法的沖突及其解決[J].中州學刊,2007(2):82.
歷史上英美法系國家的刑事法院并不承認被告人的文化與社會主流文化的分野,也不接受文化差異作為一種獨立的、實體辯護事由[4]。例如在1836年英國的Rex v. Esop
參見:7 Car.& P.456,173 Eng.Rep.203(1836).案中,一個巴格達人被指控犯有獸奸罪,但被告人聲稱在他的國家中這種行為不構成犯罪。盡管辯護人向法庭提供了關于被告人的文化信息,但法庭并沒有因此而減輕被告人的刑事責任。與英國刑法有著淵源聯系的美國刑法曾經也不考慮移民的文化因素。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871年Carlisle v. United States
參見:Carlisle v.United States,83U.S.147(1872).案的裁判中,曾引用美國前國務卿Daniel Webster在1851年所說的話:“每個在外國出生但生活在本國的人都應當服從于這個國家,只要他仍然居住在這個國家。僅僅是因為他居住在這個國家的事實,他獲得了臨時的保護,也有義務像本國公民一樣遵守居住地的法律。”[5]直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法院才開始采納基于文化差異的辯護。美國之所以從否認到承認文化差異在刑事案件中的影響,是因為移民越來越多,基于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的理念,文化多元化(Cultural pluralism)表現日益突出。這種文化差異導致了文化的受眾在行為心理上的不同,以至刑事案件中文化沖突也日益凸顯。有人統計,在20世紀80年代的法律案件中,有2%的案件在處理中存在文化沖突的事實[4]。文化差異導致的刑事案件在處理上的困難也越來越受到法學界的關注。在1985年的一個亞洲移民的刑事案件——People v. Kimura
參見:Record of Court Proceedings,People v.Kimura,No.A-09113(Super.Ct.L.A.County Nov.21,1985).案中,檢察官使用了一個叫作“文化辯護”的新理論[6]。1986年發表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評論》上的一篇文章新造了 “文化辯護”這個詞匯
當然,文化因素在刑事案件中影響案件的判決,在美國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期。例如,1883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Exparte Crow Dog(109 U.S.556,570-72(1883).)案中認為,一個印第安人被指控在保留區內謀殺另一個印第安人不適用聯邦刑法,而適用當地部落法。但兩年后,法律規定進行了修訂,認為印第安人與其他人同樣適用聯邦法律。(參見:John Alan Cohan. HONOR KILLINGS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l.W.Int’l L.J.2010(2):224.=。自此,實務人員和理論學者對這一辯護的優、缺點進行了長期的辯論[7]。
(二)文化辯護解讀
由于文化辯護出現的時間尚短,在“文化辯護”的把握上學者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學者就明確指出:“文化辯護”這一概念本身就是容易使人誤解的[8]。但即使如此,仍然有一部分學者嘗試對其進行界定。有學者認為,文化辯護是一種運用于移民的被告人解釋自己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或主張減輕處罰的法律策略[9]。有學者認為,文化辯護是指任何在刑事案件中運用文化證據證明被告人行為正當、證明被告人行為不具有刑事可罰性或減輕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情況[10]。還有人認為,“文化辯護”通常是指被告人可以提出文化證據以表明他在行為實施時的心理狀態或意圖[7]。
從這些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文化辯護首先是基于文化因素提出的。“文化辯護將兩個獨立存在的概念——文化和法律標準的最重要方面聯系在一起。”[11]文化是一種包括在一個社會中占主體地位的知識、道德和美學標準的觀念系統,它也是一種交際行為的方式[12]67。文化是人內在的道德標準和是非尺度。“無論個人以什么樣的方式接受他所在社會的典型文化元素,他一定會將其內化,這個過程叫作同化(Enculturation)。甚至最不依習俗而行的人都無法逃離他們文化的影響。文化的影響是如此之深,以至甚至精神病人的行為都強烈地反映出文化的特征。”[13]39一個在本國法律文化中遵守法律的被告人在其他法律文化下可能會實施犯罪行為,因為他的價值觀迫使他這么做。當法律背后的道德價值內化為個人行為準則時,法律更為有效。一個公正的法律制度應當考慮各個被告人的道德維度[14]。人類的行為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受其社會和文化背景決定。“不同的社會階層、種族群體、宗教群體、國家,其信仰、觀念、價值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極為明顯。”[15]67因此,文化的差異導致行為人對行為價值標準的理解差異,但行為人根據本屬于自己的文化實施的行為卻可能會被其他的文化所禁止。這種情況下,許多學者認為,少數族裔中支配行為人行為的文化應當能在主流文化范圍內作為刑事訴訟的證據使用,以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意圖和心態,從而證明行為人罪的有無或輕重。
其次,文化辯護的適用對象主要是外國移民或新來到美國的人(以下統稱為外國移民)。即使是外來族裔,如果其本身就是出生在美國、成長在美國,在學校、社區等接觸的都是美國的文化,也就不會因為文化的差異而出現價值觀念上的不同,行為標準也就不會有差異。因此,文化辯護主要適用于不是出生在美國的外國移民。在解讀文化辯護時,有人甚至強調文化辯護適用的主體是新移民的被告人。例如有學者認為:文化辯護中新來者(New comer)的行為是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所塑造,他們沒有美國刑法中規定的構成犯罪所需的必要的心理狀態[16]。
再次,文化辯護只適用于特定刑事案件中。隨著國家間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相互的文化滲透、借鑒使文化不斷出現趨同與融合的趨勢。從法律文化上看,法律觀念、價值、規則也在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中相互影響,法律文化的趨同日益凸顯。因此,就法律規則而言,各國法律規定在眾多領域都大同小異,也就不存在國家間刑事法律文化的全面、根本性沖突。這種情況下,從國外來到美國的移民就不會在美國刑事法前無所適從。因而并不是在所有的刑事案件中這些被告人都會提出文化辯護。當然,這種文化的融合只是大體融合,不是整體同一,因此,不同文化圈中文化的內容還是會有差異。只有在存在文化沖突的刑事案件中才可以適用文化辯護。實證研究表明,文化沖突主要存在于一些與家庭榮譽(Family honor)、重婚、離婚、血親復仇、傳統醫療、巫術、禮射(Celebration shooting)等有關聯的案件中[1]。
二、學界關于文化辯護的爭議
有學者說,一旦提到文化辯護,人們便會立即提出四個突出的問題:一是確定什么樣的被告人群體可以提出這一辯護;二是如何保持刑法對移民的一般預防功能;三是如何保持刑法對大多數人的公平;四是如何維護罪刑法定原則(Principle of legality)[6]。從美國法學界對文化辯護的態度看,反對者與贊同者之間的爭議主要圍繞這些問題展開,但并不限于這幾個方面。
(一)文化辯護反對論
1.不知道法律不是寬恕的理由
新移民美國的人提出文化辯護最有力的理由在于,他們是從國外新移民來美國的,不在美國出生、成長,自己原來國家的價值觀念、道德準則和行為規則影響和決定著自己的行為,不熟悉體現美國價值觀念、道德準則的法律規定。反對者認為,法律格言早已闡明“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的理由”(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這一格言經常用來警告那些身處法庭的人,不要主張自己不知道特定法律的存在或對法律規定了解不充分,因為法庭不贊同公民不知法律的主張。”[17]而且,如果承認文化辯護則會使“不知法律”成為罪刑法定原則的例外而與該原則相矛盾[6]。有學者聲稱:大多數人第一次聽到文化辯護時,因擔心它會導致無政府主義而拒絕它。如果每個人都能主張法律的例外,那么法律將無力把社會個體緊緊聯系在一起。少數族裔應當改變他們的行為以使其行為與所在地的法律相一致[18]5。拒絕文化辯護將鼓勵移民對歸化地的法律進行了解[14]。
2.文化辯護違反了平等原則
平等原則是美國的一個憲法性原則。一方面,平等保護不能考慮被保護人的種族、性別或來自什么國家。如果被告人基于自己主觀的信念實施的違法行為受到寬恕,那么社會上其他人的權利和對自己行為后果的預測性將受到損害。因此,文化辯護通過給予移民被告人特殊優惠的處遇會歧視社會上的其他民眾。而且,“文化辯護給予移民被告人以免予定罪或從寬處罰的機會,那么這些行為的被害人就無法得到平等的保護”
文化辯護經常受到女權主義者的反對,因為這些犯罪的受害人經常是婦女和兒童。(參見:Nancy S. Kim. BLAMEWORTHINESS, INTENT, AND CULTURAL DISSONANCE: THE UNEQUAL TREATMENT OF CULTURAL DEFENSE DEFENDANTS[J]. U.Fla.J.L.& Pub.Pol’y,2006(2):199.)事實上,女性和兒童往往是文化辯護案件中被指控行為的受害人。以女性的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為例,2005年11月25日聯合國發表的《改變具有傷害性的社會習俗——婦女生殖器摧殘》報告中稱,全球每年仍有300萬女童遭受生殖器切割。美國于1996年成文法禁止對女性實施割禮,并將其列為犯罪行為。但移民到美國的人中仍然有人保持原有習俗,對女性實施割禮的行為。例如,2003年,一個名叫Khalid Adem的被告人因為毀損女性生殖器而被捕;2004年住在南加州的一對夫婦也因為毀損女性生殖器而被捕。在這兩個案件中,被告人均提出了文化辯護。。“考慮某人的文化背景根本上與法官考慮諸如性別、年齡、心理狀態等其他的社會特征沒有區別。”[19]另一方面,平等原則要求平等遵守法律規定。居住在美國的移民應當遵守美國的法律和習慣。“行為地法律(Lex loci)必須適用。不能允許他們躲在他們文化傳統的背后。如果一個美國人去新加坡并違反了當地的法律,他將會根據當地的法律受到懲罰。同樣的標準應當適用于在美國的新加坡人。”[20]“盡管不承認文化辯護對移民的被告人而言可能會不公正,但承認文化辯護對大多數被告人而言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們無法適用這一辯護。”[14]
3.文化辯護可能被濫用
文化辯護的存在通常適用于行為受到國外文化影響的群體,但這一群體難以確定。首先,文化本身并不是如磐石一樣固定不動地、靜態地存在。“文化”和“傳統”的定義和意義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并取決于其背景情況[20]。“哪些群體的人能夠說他們具有可以適用文化辯護的‘文化’?為什么?”“如何在時間、空間和人群方面確定文化的邊界?”[21]例如,有學者擔心,移民到美國的兒童受到父母的虐待后,作為責任人的父母在面臨虐待兒童的指控時可能用文化辯護來逃脫被定罪或獲得從輕懲罰[22]。因此,基于文化而進行的辯護也就處于一個完全不確定的狀態。其次,如何明確界定可以提出文化辯護的被告人的范圍將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14]。如果說新移民或剛到美國的人行為受到原文化的影響而可以提出文化辯護的話,那么在美國居住多久就可以說了解美國文化,自己原有文化不影響其價值觀念和行為規則了?在People v.Kimura
Kimura案(No.A-091133 (Santa Monica Super.Ct.Nov.21,1985).)發生于1985年。一名生活在加利福尼亞州的日本裔婦女發現她的丈夫有外遇后殺死了自己的兩個孩子并試圖自殺。辯護人提出被告人自殺是因為在日本傳統文化中,孩子是母親身體的一部分,而且婦女可以處理自身以免被丈夫不忠行為羞辱。案中,被告人在美國已經生活了14年,辯護人仍然提出了文化辯護。為了社會秩序的目的,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的區分標準應當是客觀的。社會應當建立在法律的權威之上。應當對刑法進行客觀解釋,而不能像允許文化辯護一樣主觀地加以解釋。“當前并沒有被告人提出文化辯護的指南或程序保障,文化證據的提出在每個案件中都不相同。這會導致官員們在文化沖突案件中自由裁量權的任意適用。”[14]
4.文化辯護不利于實現刑法目的
一般預防是刑法的重要目的。反對者認為文化辯護的出現成了實現刑法目的的障礙。例如有學者認為:基于移民被告人的文化而寬恕這些被告人,會給移民傳遞這樣一種信息,即他們無須遵守所在地的刑法,刑事司法制度會寬恕他們的錯誤行為。這樣,文化辯護對刑法預防犯罪的功能會有消極影響,這對社會安全也不利[23]。特別是這類案例通常由媒體過度宣傳,無疑會增加移民對文化辯護寬恕危害行為的了解。同時,“那些因為文化的原因而被迫實施某種犯罪行為的人無論是否給予文化辯護的機會,刑法的預防犯罪功能對他們都不起作用”[5]。
(二)文化辯護贊成論
1.“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的理由”并不是一個絕對規則
“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理由”的法律格言并不是絕對的。“該格言有時與刑法的基本原則是沖突的,因為刑法認為道德上不具有過錯的行為不應當受到懲罰。不知法律不是寬恕理由這一規則應當進行重構,即合理的不知法律不能作為不相關的刑法事實而排除。”[24]“當不知法律否定了指控的犯罪所必需的心理狀態的存在時”,不知法律就可以成為辯護事由[25]356。美國《模范刑法典》2.04(3)也對這一格言做了例外性的規定。《模范刑法典》的評述者也認為,當某人既不知道其行為的犯罪性也沒有合理的途徑知道相關信息,那么就不得懲罰這個人。在美國刑法中,危害行為與犯意是兩個不可或缺的表面成立條件
美國刑法中的犯罪成立條件包括表面成立條件和實質成立條件兩個方面。(參見:賴早興. 美國犯罪成立要件與證明責任分配[J].法學家,2007(3):153-155.)。正如有的學者所言:“一般說來,犯罪包括兩方面的要素:危害行為(Actus reus),即犯罪的物理或外部特征;犯意(Mens rea),即犯罪的心理或內在特征”[26]85。在證明犯意時,雖然控方并不要證明被告人意圖違法,但一些成文法要求控方證明被告人在實施行為時具有特定的心理狀態(即特定的犯罪意圖),沒有這種心理狀態就不能認定構成犯罪。實際上,行為人行為時的心態往往受到價值觀念、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文化因素的影響,某一種文化所禁止的行為在另一種文化中卻是被許可、包容甚至鼓勵的。新移民美國的人往往受原來文化的支配很難短時間內適應美國文化的要求。因此,按美國刑法規定的具有犯意的行為人完全可能事實上不存在成立某種犯罪所要求的犯意。有學者主張:“文化辯護通常是被當作一個可寬恕事由來運用。行為人實施的行為是違法的,但因為行為人缺乏構成某罪所需的可責性的心理要素而被寬恕。”[14]而且,在文化辯護的案件中,“文化辯護要求被告人基于他們自己文化背景中確定的、慣常的規則進行辯護,而不是僅僅依據對主流文化不了解。”[27]
2.文化辯護是實質平等的要求
法律平等包括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28]94-96。刑法中的實質平等就是在遵守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行刑事司法個別化原則(Principle of individualized justice),在刑事案件的處理中考慮案件的具體情況做出合理的判決。對于文化辯護的贊同者來說,平等對待僅僅意味著:法律制度并非統一地適用,而是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不同地適用[29]。“為了達到每個被告人的個別正義,對其懲罰的尺度應當與其可罰性的程度相一致。在法律的限度內懲罰一個對特定法律不了解的人是不公正的。當被告人沒有與他人有同樣的機會在文化環境中成長以了解或學習法律,那么歸罪于一個不了解法律的人就是不公正的。法律中應當考慮這一因素,以達到對被告人的個別公正。”[14]
在美國長大的人,有一系列的社會力量(如學校、社區、教會等)傳授法律知識、培養價值觀念,美國本土的價值觀念、法律意識在他們腦海中逐漸根深蒂固。但新近移民來美國的人卻沒有得到相應社會化力量的幫助,因而缺乏同樣的法律知識、價值觀念的積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們腦海中根深蒂固的是他們原來所在國家的價值觀念和法律準則。“對長期生活在美國的人和新近移民美國的人采取同樣的標準而對其差異視而不見,顯然是不公平的。”[8]在刑事指控中不讓新近移民提出文化證據對他們是不公正的,因為他們沒有充分的時間吸收和理解本地的刑事法律[7]。
3.文化辯護是保持文化多元的需要
文化多元是國際文化相互交流和借鑒的結果。文化多元化的前提是承認文化相對主義。文化相對主義認為道德原則是相對的,因而不存在一體適用(One-size-fits-all)的道德[5]。它“要求承認多元社會道德體系的存在”[30]。文化多元化“意味著每一個少數群體都有權保持某種文化價值,因而維持自己的認同感”[4]。從法律文化的角度看,當移民和難民到達一個新國家,他們帶來的是原有的法律文化與法律傳統。這些法律傳統與新國家已經存在的法律也存在匯合的過程,這必然會導致法律的多元化。“多數群體不能僅僅因為存在的差異而懲罰少數族裔。如果一個法律制度因為被告人遵守自己的文化而懲罰他,那么這個法律制度發出了這樣一個信息:被告人的文化是低下的。”[14]只有將文化辯護作為一種獨立、正式的辯護才能有效地防止主流社會用刑事司法制度損害文化的多樣性[31]。承認文化辯護是美國保持文化多元必不可少的,通過保持少數民族的重要價值,文化辯護有助于維護文化的多元性[7]。
在國際人權法中,所有的國家都有義務保護公民的文化權利。聯合國《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7條規定:在那些存在著人種的、宗教的或語言的少數人的國家中,不得否認這種少數人同他們的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實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的語言的權利。“就享受文化權利而言,至少移民到其他國家的人有機會告訴法庭促使他實施了行為的文化與新國家的文化明顯是沖突的。因此,為了文化權利的實現,應當構建文化辯護制度[19]。
4.文化辯護的濫用可以防止
文化辯護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案件中都可以提出。什么情況下可以提出文化辯護呢?有學者認為:在文化為被告人的行為提供了可供選擇的、非犯罪的解釋時,或當文化性的要求將被告人置于特別壓力之下而無法做出選擇時,法庭應當考慮文化證據。相反,如果被告人主要意圖是傷害其他的人,他僅僅宣稱文化認可他的這種暴力行為時,法庭應當拒絕寬恕他[32]。這只是一個基本的原則或理念,具體制度上應當考慮得更為細致。有學者提出,為防止文化辯護的濫用,法庭應當考慮三個基本問題:“一是訴訟當事人是少數族裔的成員嗎?二是這個群體是否存在這樣的傳統?三是訴訟當事人行為時受到了這一傳統的影響嗎?”[19]基于此,一個提出文化辯護的案件應當具備三方面的條件:一是這里面存在文化原因。二是自己的文化認可這種行為。在文化認可理論下,被告人承認自己實施了違法行為,但他主張不應當承擔美國刑法所規定的刑事責任,因為他本國的文化認可或寬恕這種行為。三是文化要求,即自己國家的文化迫使或要求他有義務做出某些行為。
5.文化辯護不會妨礙刑法目的的實現
文化辯護與傳統的其他辯護類型不同,它只能在少數、特定的案件中提出。“能夠適用文化辯護的犯罪非常少,所以文化辯護的適用不會損害刑法的一般預防功能。”[7]而且,刑法的另一個目的在于懲罰犯罪,懲罰的尺度就是罪刑均衡。“正是罪刑均衡的觀念為文化辯護提供了正當化理由。如果被告人的行為受到文化因素的激勵,那么其應當受譴責性就小,因此其應受的懲罰就要輕。”[18]11因此,從這個方面看,文化辯護不是妨礙了刑法目的的實現,而是有助于刑法目的實現。
三、司法實踐中的文化辯護
曾經有學者斷言:“文化辯護作為非法行為的一種正式的寬恕理由當前只存在于法學理論界中,將來在美國任何司法區都不可能獲得承認。”[8]事實情況如何呢?從美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法院對于文化辯護有著完全不同的態度。有的法院完全不采納文化證據。“在法庭中提出文化證據最大的障礙在于法官的這樣一種觀念:從其他文化中而來的人應當遵守居住地國家的標準。這個我稱之為‘同化推定’(Presumption of assimilation)。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法官經常基于這種與案件無關的理由拒絕考慮關于文化背景的證據”。[18]6有的法院則允許被告人在謀殺罪、強奸罪、兒童或配偶的虐待等犯罪的刑事審判中提出文化證據,而這種文化證據對案件的審理結果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采納文化辯護的法院大多數是州法院,但也有聯邦法院。例如1991年一個聯邦上訴法院在Mak v. Blodgett
參見:754 F Supp. 1490(W.D.Wash.1991).案的判決中認為:“辯護律師沒有提出文化辯護可以認定為辯護人的不盡責。”總體上,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美國法院允許被告人在刑事訴訟的各階段提出文化背景的證據已經成為一種增長的態勢[7]。
(一)文化辯護在刑事辯護中的地位
在刑事案件中采納文化證據的法院現在并沒有承認文化辯護是一種獨立的辯護類型。“在指控犯罪或量刑時,被告人的責任能力應當被考慮。檢察官或陪審團應當考慮被告人犯罪行為背后的文化因素,但不是作為正式、獨立的文化辯護。”[14]通常情況下,文化辯護與傳統刑事辯護共同使用。“‘文化辯護’在美國法學界還不是一個得到正式確認的積極辯護(Affirmative defense),相反,‘文化辯護’通常是指被告人可以提出文化因素以表明他在行為實施時的心理狀態或犯意。實踐中,文化辯護通常不是僅僅依據文化因素這一孤立的事實因素,相反,文化因素通常與一個或多個得到確認的刑事辯護(如精神病、受挑釁、法律錯誤等)相聯系。”[7]將文化因素在已經存在的辯護中運用比將其作為一般的、獨立的辯護更具有策略性[33]。有學者將其形象地概括為“文化+”(Culture-plus)模式,即在傳統刑事辯護內使用文化因素[7]。一般認為,司法實踐中將文化辯護與傳統辯護結合,體現了刑事司法制度已經在法律秩序與文化多元、司法個別化之間實現了協調。“移民被告人聘請的辯護人同樣是其他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可以聘請的。任何被告人可以基于精神病辯護、能力減弱辯護、法律錯誤辯護和激情辯護而主張自己不具有實施某犯罪所需的犯意。因此,當刑事司法制度尊重文化多元和司法個別化中采納了文化辯護,那么它就能維持當前法律秩序的標準。”[23]
司法實踐中的一些案例證實了這種情況。例如People v. Chen
參見:No. 87-7774 (N.Y.Sup.Ct.Mar.21,1989).案中,一個生活在紐約的中國男子知道他的妻子有婚外情后用棍棒將妻子打死。在法庭審理中專家證言表明,根據傳統的中國文化,一個妻子的淫亂行為給婚姻帶來羞辱,也是丈夫個性懦弱的表現。審理法官認為:“陳的行為是文化的產物……文化不是一個可寬恕事由,但它是使被告人更容易爆發的因素。這個文化因素正是暴發的因素。”[34]法官認為被告人因挫折而心理失常,“這沒有達到法定精神病的程度,但基于文化的因素,他妻子的行為對于一個生在中國、長在中國的人產生了影響。”本案最初的指控是二級謀殺,刑期從最低十五年監禁刑至終身監禁,后來實際指控的是二級過失殺人,刑期為最高十五年有期徒刑,最后法院判決的是緩刑五年。又如,在People v.Wu參見:235 Cal.App.3d 614 (Cal.Ct.App.1991).案中,一位中國籍女子在得知其丈夫有外遇后殺死了自己的兒子,并試圖自殺。辯護方提出了自動癥(Automatism)辯護和文化辯護。精神科專家證明被告人行為時意識處于朦朧狀態。跨文化的心理學專家證言表明,被告人的感情沮喪只能根據其文化背景進行理解,她的行為有文化動機,她希望把她自己和兒子從羞辱和虐待中拯救出來,并在死后再相聚。但法官拒絕指示陪審團可以考慮被告人的文化背景證據,被告人被裁定構成二級謀殺罪。但在上訴審中被告人的文化辯護主張得到了法庭的支持。最后,被告人被裁定犯故意殺人罪,但獲得了較輕的刑罰。
對于司法實踐中將文化辯護與其他傳統辯護結合而不給予其獨立、正式的辯護地位,有學者提出了異議。“支持將文化辯護作為獨立、正式的辯護的人認為,在一個所謂文化多元和司法個別化的國家,將文化辯護與傳統的其他辯護結合的做法無法為移民被告人提供足夠的保護。”[4]“在文化辯護還不是一個獨立正式辯護的情況下,被告人可能主張他在實施錯誤行為時患有精神病。他的文化因素導致的對當時情況的理解將被當作精神病,他因此也會被貼上精神病人的標簽。即使精神病辯護成功,被告人也會因為患有精神病而被長期關押。”[23]“獨立、正式的文化辯護的一個主要的好處在于,它將確保法庭考慮文化證據,而不是將關于采納證據的適合與否的決定權留于個別法官,正式的政策將確保法院的門是對文化資料敞開的。”[19]
(二)文化辯護起作用的階段
一般認為,文化信息和專家證據可以在審判前或審判中作為與訴訟的爭點相關問題被提出來。例如,文化證據可以在辯訴交易中或在定罪、量刑階段作為與犯意、激怒的原因、理性、減輕罪責等相關的問題提出來[8]。文化證據能影響審前程序中所做的決定,如是否需要逮捕,是否要進行辯訴交易。在審判階段,被告人可以尋求提出文化證據以否定存在成立犯罪所需的要素,從而得到無罪判決;文化辯護也可以用以支持精神病辯護或受挑釁的辯護。在上訴審中,文化主張也可以以下幾種形式作為上訴理由:法官認為不相關而不當地排除了文化證據;法官拒絕給陪審團關于文化證據恰當分量的指示;在量刑階段辯護律師沒有提出文化因素作為考慮因素[18]7。
司法實踐中的案例也表明,文化辯護在庭審前和庭審中均對行為人刑事責任的認定起著重要作用。我們首先來看一個文化辯護在辯訴交易中起作用的案例——People v.Moua
No. 315972-0 (Fresno County Super.Ct.Feb.7,1985).案。本案中,一名居住在美國的名叫Moua的老撾洪族男子被指控強奸和綁架一位老撾婦女。被告人聲稱他的行為不是犯罪,因為他實行的是老撾洪族傳統的搶婚儀式(抓到婦女,將其帶到自己家中發生性關系,成立婚姻)。辯護人提出了洪族這一文化儀式的證據。在辯訴交易中,被告人承認犯有非法拘禁罪,檢察官將原來的綁架和強奸指控降低為非法拘禁罪的指控。
我們再來看一個文化辯護在庭審中起作用的案例——Krasniqi案
Hugh Downs & Barbara Walters, “WE WANT OUR CHILDREN BACK”, 20 /20 (18 August 1995) (Nexis)[Krasniqi].。在本案中,被告人Sam Krasniqi是一個定居在美國的阿爾巴尼亞人,他在公共體育館撫摸了他四歲女兒的生殖器。檢察官認為這種撫摸行為是為了性滿足,被告人構成性虐待犯罪。性虐待是一種特定意圖的犯罪,即為了性滿足,因此檢察官必須證明被告人有這樣一個意圖。當被告人在德克薩斯州刑事法院被起訴時,一個阿爾巴尼亞文化研究的專家證明這種撫摸在該文化中表達的是愛的情感,而不是為了性滿足。在庭審中,法院考慮了辯護人提出的文化辯護,被告人隨后被裁定無罪。
其實,文化辯護并不僅僅在庭審前或庭審中起作用,在案件判決后的刑事執行過程中,文化因素仍然會起作用。我們來看一個案例——State v. Chong Sun France
379.E.2d 701 (N.C.App.1989).案。本案中一個名叫Chong Sun France的韓國婦女被指控故意將她的兒子關在衣柜中致其死亡,但被告人聲稱他兒子的死是意外。在審理的過程中,被告方沒有向陪審團提交文化證據,陪審團裁定被告人構成二級謀殺和虐待兒童罪,被判處二十年監禁。在該案判決后,由在美國的韓國婦女組織的群體運動指出,在刑事程序中應當考慮被告人的文化證據;韓國文化的專家證言證明對韓國人而言將自己的孩子獨自留在家里沒有人照看是通常的習慣做法,被告人沒有殺害自己孩子的故意。假釋France的申請人認為:“France女士將她的孩子獨自留在家里是錯誤的,這違反了法律的規定,但考慮到文化差異,我相信她沒有殺害她的孩子。” France于1992年12月31日提前獲得假釋。這一提前假釋就是因為法院沒有允許陪審團考慮France文化背景證據而致政府受到了極大壓力的結果[23]。
(三)文化證據的運用
文化辯護作為一種新型的辯護或新的辯護事由,涉及抽象的文化因素,這對從事法律工作的檢察官、律師、法官甚至假釋官等提出了新的挑戰。在文化辯護的刑事案件中,“專家證據在文化辯護的案件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它證明文化傳統的存在,并有助于表明是否文化傳統事實上在特定情形下對個人產生影響。沒有專家證據的幫助,法庭很難在案件審理中理解提出的文化主張。”[18]11同時,辯護方通常會收集一些與被告人有同樣文化背景的人的證言,以文化受眾的身份說明自己對文化的親身感受。例如,在State v. Kargar
679 A.2d 81,1996 Me.162,68 A.L.R.5th 751.案中,被告人是一個阿富汗的難民,住在緬因州,幫助鄰居照顧小孩。一天鄰居發現被告人親他自己18個月大孩子的陰莖,而且在被告人家里還發現了一張他親孩子陰莖的照片,于是便報了警。被告人面對警察的調查承認自己親了小孩陰莖的事實,但他辯稱親小孩的陰莖在他們的文化中是可以接受的通常做法。在法庭審理中,辯護方提供了一些了解阿富汗人的證言,證明在阿富汗親自己小孩身體的任何部位都是一種習俗和通常做法,這是為了表達對孩子的愛憐;而且,親一下自己小孩的陰莖或將其整個放入口中都一樣,并不是為了性的感受。辯護人還提供了包括亞利桑那大學近東研究中心Ludwig Adamec教授和紐約阿富汗圣戰情報中心Saifur Halimi主任(同時也是一位宗教學教師)在內的一些書面專家證言[26]719。在量刑階段,一個當地牧師作證,證實被告人被定罪的行為在當地文化中是無罪的、適合的,并非性行為。所有這些證言都證明在當地法律中,被告人的行為既不是錯誤的行為,也不是性侵犯行為,被告人不知道他的行為在緬因州的法律中是非法的
本案并沒有在一審法院得到無罪判決。在上訴審中,緬因州最高法院基于文化辯護撤銷了被告人的有罪判決。(參見:John Alan Cohan. HONOR KILLINGS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l. W.Int’l L.J.2010(2):233.)。
除專家證言外,其他一些人的證詞或呼吁都會對文化辯護的案件產生影響。在People v. Kimura一案中,數千日本人簽名呼吁,在日本對為免于家人的羞辱而與孩子一同自殺行為的指控不會超過過失殺人罪,通常判處的刑罰也非常輕,一般是暫緩量刑、緩刑等。在State v. Chong Sun France案判決后,在美國的一些韓國婦女組織了群眾運動,呼吁在刑事程序中應當考慮被告人的文化證據。這些都對案件的處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四、啟示
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十六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
我國也是外國人入境人數眾多的國家。根據國家旅游局的統計,2014年1月至12月入境旅游外國人人數為2636.08萬人。另外,國際移民組織發布的《2013世界移民報告》顯示,到2011年,在中國居住著68萬多名外國人。這些人受其文化的影響,價值觀念、行為習慣和方式等也會與我國公民不同。,最新進行的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大陸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現役軍人的人口中,漢族人口約為12.259億人,占91.51%;各少數民族人口約為1.1379億人,占8.49%。我國各民族都有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從不同角度向世人展示著各自的發展歷史文化心理倫理道德和審美意識”[35]。這種文化上的差異,必然會導致行為人價值判斷、思維習慣、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差異,因而在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認識上出現不同,在刑法處遇上就應當有區別對待的措施。如有的少數民族男女一旦有了婚約,男方不管女方是否同意就硬行搶親、強行同居;有些民族如拉祜族、哈尼族、傣族等廣泛延續早婚傳統,女孩13歲就舉行成人禮(如藏族幼女的“戴天頭”習俗),此后男子與其發生性行為或結婚都是習俗所允許的,不會受到社會的譴責和干預[36]。如果這些行為均按我國刑法的規定作為犯罪處理,顯然在刑法適用上會遇到很大的阻力。正因為如此,《刑法》第90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可以由自治區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會根據當地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特點和刑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制定變通或者補充的規定。這說明在我國刑事立法上承認了文化因素對行為人的影響。據統計,目前我國共建立了155個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包括5個自治區、30個自治州、120個自治縣(旗)。在55個少數民族中,有44個建立了自治地方,實行區域自治的少數民族人口占少數民族總人口的71%。如果這些地方根據《刑法》的規定結合本地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變通或補充規定,文化因素對行為人的影響就會體現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但事實上,我國民族自治地方并沒有充分運用《刑法》第90條的授權
根據陳興良教授的說法,“但從目前情況來看,據我所知,還沒有這種變通或補充的規定出臺。”(參見:陳興良.刑法疏議[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198.)。從司法實踐中看,我國最高司法機關和地方司法機關開始關注民俗對行為人的影響,如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發布了《關于進一步發揮訴訟調解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積極作用的若干意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年發布了《關于在審判工作中運用善良民俗習慣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的指導意見》,但它們關注的是“善良風俗”、“善良民俗習慣”,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影響,因為文化并非都是善良風俗或民俗習慣。
如何在刑事訴訟的過程中充分考慮不同民族、種族的文化對行為人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等方面的影響,是我們必須深思的問題。雖然美國是多種族的國家,我國是多民族的國家,但兩者共同的文化多元性特征決定了我們在法律制度的構建中可以相互借鑒。就刑法領域而言,美國刑事法中的文化辯護為我們重視刑事訴訟中的文化因素、構建完善的相關制度提供了思考的方向。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
一是確立文化辯護事由在我國《刑法》中的地位。我國《刑法》規定的辯護事由主要是刑事責任年齡、精神病、正當防衛、緊急避險、犯罪停止形態、坦白、自首和立功等,尚無文化辯護的位置,甚至連學界都沒有充分重視這一辯護事由。從美國的司法實踐來看有的司法區將文化辯護與其他傳統辯護結合而不給予其獨立、正式的辯護地位,有的做法與此相反。筆者認為,如果文化因素是與精神病、受挑釁、法律錯誤等傳統辯護事由共同作用,那么將其作為傳統刑事辯護內的因素也無不可;但如果是文化因素單獨起了作用,也應當允許辯護方單獨提出文化辯護。
二是明確文化辯護證據可以適用的階段。刑事訴訟(公訴)分為偵查、審查起訴、提起公訴、法庭審理、執行等階段。在美國刑事訴訟中,文化信息和專家證據一般在審判前或審判中作為與訴訟的爭點相關問題被提出來,如果這一過程中遺漏了這些信息或證據,在刑罰執行階段仍然可以提出。筆者認為,這一做法是可取的,我們雖然強調被告方應當在審判前或審判中提出文化辯護的信息或證據,但亦不能完全排除其在刑罰執行中提出。
三是重視專家證人的作用。文化辯護的提出使檢察官、律師、法官甚至假釋官等面臨新的挑戰,因為被告方提出的文化證據的相關性、合法性、真實性判斷與傳統證據存在極大的差異。尤其是這種文化證據的判斷中還存在價值判斷與作用程度判斷的問題,這不是一般法律人可以勝任的,這就要充分重視專家證人的作用。從美國刑事訴訟中文化辯護適用案例看,專家證人在幫助陪審團或法官等理解特定文化因素對行為人的影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司法機關可以聘請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參與勘驗、檢查或鑒定,“專門知識的人”還可以出庭就鑒定人做出的鑒定意見提出意見。這說明我國還沒有構建起通常性的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在現有制度下,文化辯護提出后被告方很難請求法庭讓熟知其文化習俗的專家證人出庭為其作證,因為這類案件并不存在鑒定的問題。因此,在文化辯護案件處理過程中為了使檢察官、律師、法官、假釋官等得到專家的幫助,有必要建立起通常性的專家證人出庭作證制度。
ML
參考文獻:
[1] Tamar Tomer-Fishman. “Cultural Defense,” “Cultural Offense,” Or No Culture At All?: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sraeli Judicial Decisions In Cultural Conflict Criminal Cases And Of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m[J].J.Crim.L.& Criminology,2010(2):476,496.
[2] Sigurd D’Hondt. The Cultural Defense As Courtroom Drama: The Enactment Of Identity,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In Criminal Trial Discourse[J]. Law & Soc. Inquiry,2010 (1):67.
[3]James C.Fisher. Role Of Morality In Cultural Defense Cases: Insights From A Dworkinian Analysis[J].Birkbeck L.Rev.,2013(2):281.
[4] Note. The Cultural Defense In The Criminal Law[J]. Harv.L.Rev.1986 (6):1293,1293,1293,1295.
[5] John Alan Cohan. Honor Killings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l.W.Int’l L.J.,2010(2):223,248,225.
[6] Julia P. Sams.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Cultural Defense”As An Excuse For Criminal Behavior[J].Ga.J.Int’l & Comp.L.,1986(2):335,345,351-352.
[7] Naomi Mendelsohn. At The Crossroads: 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A Cultural Defense To 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J].Rutgers L.Rev.,2004(4):1019,1020,1020,1021, 1023,1016-1019,1020,1031.
[8] Kristen L. Holmquist. Cultural Defense Or False Stereotype?[J]. Berkeley Women’s L.J.,1997(1):61,63-64,61,63-64.
[9] Alice J. Gallin. The Cultural Defense: Undermining The Policies Against Domestic Violence[J]. B.C.L.Rev.,1994(3):735.
[10] Nancy S. Kim. Blameworthiness,Intent,And Cultural Dissonance:The Unequal Treatment Of Cultural Defense Defendants[J]. U.Fla.J.L.& Pub.Pol’y.,2006(2):200.
[11] Maria Beatrice Berna. Cultural Defense:Possible Correlations And Applicatiot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Women’S Rights[J]. J.L.& Admin. Sci.,2015(4):191.
[12] Levine,R..Roperties Of Culture: An Ethnographic View. In Schweder,R.And Levine, R.,Cultre Theory: Essays On Mind,Self,And Emoti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13] Ralph Linton. Tree Of Culture[M].New York:Alfred A. Knoff Inc.,1955.
[14] Carolyn Choi. Application Of A Cultural Defens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J]. Ucla Pac. Basin L.J.,1990(8):86,89,87,89,86,86,86,88-89.
[15] Marshall H.Segall,Et Al.Human Behavior In Global Perspective:An Introduction To CrossCultural Sychology[M]. New York: Pergamon Press,1990.
[16] Sherman. Legal Clash Of Cultures[J].Nat’l L.J.,1985(8):1.
[17] Jennifer L.LairSmith. Ignorance Of The Law Is No Excuse: Distinguishing Subjective Intent From Mistake Of Law In State V.Barnard[J]. 1 Charlotte L.Rev.,2009(2):335.
[18] Alison Dundes Renteln. The Cultural Defense[M].New York:Oxford,2004.
[19] Alison Dundes Renteln.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Cultural Defense[J]. Can.J.L. & Soc.,2005(1):48,48-49,48-49.
[20] J.Tom Morgan, Laurel Parker. The Dangers Of The Cultural Defense[J]. Judicature,2009(5):206,206.
[21] Valerie L. Sacks. An Indefensible Defense: On The Misuse Of Culture In Criminal Law[J]. Ariz.J.Int’l & Comp.L.,1996(2):534.
[22] R. Lee Strasburger.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The Cultural Defense As Justification For Child Abuse[J].Pace Int’l L. Rev., 2013 (1):162.
[23] Sharon M.Tomao. The Cultural Defense: Traditional Or Formal?[J]. Geo.Immigr. L.J.,1996(2):253,253,253,242.
[24] Kumaralingam Amirthalingam. Ignorance Of Law, Criminal Culpability And Moral Innocence: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Blame And Excuse[J]. Sing.J.Legal Stud. 2002(1):302.
[25] W. Lafave, A.Scott. Handbook On Criminal Law[M].St.Paul,Mn:West Publishing Co.1972.
[26] Joshua Dressler. Understanding Criminal Law[M].New York: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2009.
[27] James M. Donovan, John Stuart Garth. Delimiting The Culture Defense[J]. Quinnipiac L.Rev.,2007(1):112.
[28] 賴早興.刑法平等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9] Sam Beyea. Cultural Pluralism In Criminal Defense: An Inner Conflict Of The Liberal Paradigm[J]. Cardozo Pub. L. Pol’y & Ethics J., 2014(3):719.
[30] Alison Dundes Renteln.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The Cultural Defense[J]. Law & Contemp.Probs.,2010(2):256.
[31] Anh T. Lam. Culture As A Defense: Preventing Judicial Bias Against Asi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J]. 1 Asian Am.Pac.Is.L.J.,1993(1):49.
[32] Kay L.Levine. Negotiating The Boundaries Of Crime And Culture:A Sociolegal Perspective On Culture Defense Strategies[J]. Law & Soc.Inquiry,2003(1):80.
[33] Kent Greenawalt. The Cultural Defense: Reflections In Light Of The Model Penal Code And The Religious Freedom Restoration Act[J]. Ohio St.J.Crim.L,2008 (1):321.
[34] Diana C.Chiu. The Cultural Defense: Beyond Exclusion, Assimilation,And Guilty Liberalism[J]. Cal.L.Rev.,1994(4):1053.
[35] 田聯剛,趙 鵬.多元共生 和而不同——關于少數民族文化在中華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思考[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1):2.[36]鄭鶴瑜.論我國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刑法的沖突及其解決[J].中州學刊,2007(2):82.
本文責任編輯: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