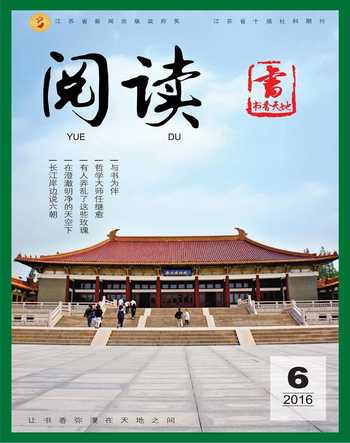哲學大師任繼愈
嚴青?郭改雲



任繼愈是我國哲學宗教學界的一代宗師,他在佛教方面的研究成就被毛澤東譽為“鳳毛麟角”。他精于學問,不攀龍附鳳,不趨炎附勢,始終保持實事求是正直謙虛的節操。他一輩子以國家社會需要為己任,無論在治學、教學,還是執掌國家圖書館的各個領域,均有重要貢獻。
大智將啟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出生在山東省平原縣一個中等家庭。其實,任家祖上曾經也屬殷實富裕之家,但任繼愈祖父在和幾個兄弟分家之后,因生意失敗,而致家道中落。任繼愈的父親任簫亭出于經濟考慮,報考了費用較低的保定軍官學校,與國民黨高級將領劉峙、顧祝同等是同班或同級。任簫亭后來官至少將,但由于生性耿直,不屑彎腰折桂,一直被國民黨嫡系部隊視為“異己”。1945年4月,他被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派到張自忠的部隊,參加了抵御日軍的“老河口戰役”,之后轉任參議閑職。
任繼愈自己則認為,父親報考軍校,其實還有沖出封建家庭樊籬的另一層意思。任家是一個大家族,四代同堂,有那種“像巴金筆下《家》的味道,北方傳統的封建主義大家庭”。封建家庭的特點就是封建家長制,子女要絕對服從家長,不能違逆,婚姻不能自主,諸如此類。任繼愈認為,父親在那個環境下很受束縛,于是沒有受限于任家的世代書香門第,選擇離開家庭,考上了保定軍官學校,成為任家第一位行伍之士。
不過任簫亭仍然喜歡讀書,屬于文武兼修的“儒將”。他迎娶的夫人、任繼愈的母親宋國芳,出自平原縣一戶鄉紳家庭,她在50歲時開始學識字,后來竟能與遠在他鄉的兒子們往來書信。在父母的影響下,任繼愈和幾個兄弟自小就懂得學習和做人的很多道理。
后來,任繼愈一家人在魯南一帶自立門戶。任父遠在外地從軍,任母獨自擔起家庭重擔。這位堅強的女性,用她深沉博大的母愛,呵護著小繼愈兄弟幾個。有一次,尚在吃奶的小繼愈得了重病,醫生開了湯藥。母親給他喂藥時,小繼愈的腳不小心把藥碗踢翻了,湯藥潑了一地。母親連忙趴到地上吮吸湯藥,再變成乳汁喂給他。這件事任繼愈終生銘記在心,直到他90多歲高齡時,還常常回憶,每每講起,眼淚盈眶,他說:“人的本性天生是善良的。”
無論生活怎樣艱辛,平日非常嚴格、節儉的母親,卻十分重視孩子們的文化教育。任繼愈4歲入私塾,每每遇到連父母都不能解答的問題時,小繼愈知道,書本里有個神奇的世界,那里會有他想揭示的一切事物的答案。有人說,任繼愈從小養成的那種刨根問底的習慣,正是他日后成為一代哲學大家的基礎。宋代理學家朱熹小時候也是如此,當他父親用手指著天,告訴他上面是天時,朱熹馬上問:“天上面有什么?”這就是哲學家的思維方式。他不僅想知道事物的表面,還想知道事物的本質和背后。自由寬松的家庭環境、專注思考的學習態度、熱烈執著的求知欲望,讓小繼愈日益養成了哲學家所需的素質和思維方式。
蕓竹之緣
還在1941年,已經在西南聯大擔任講師的任繼愈,有一個北大哲學系的同學名叫王維澄,此時正在師范學院當副教授,其妻在聯大附中教書。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請假,王維澄便請任繼愈代為授課。當時,任繼愈覺得有些為難:依理說,老朋友出言求助,理應責無旁貸,但他認為自己是學哲學、教哲學的,而王維澄的愛人卻是教語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勝任朋友之托嗎?任繼愈真的有些躊躇。但他畢竟架不住老同學多番懇請,便硬著頭皮答應了。好在,王維澄的愛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試試看。
不想,這一助人為樂,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緣。
原來,其時在聯大附中還有一位語文老師,叫馮鐘蕓。她出生于一個顯赫的學術家族:父親馮景蘭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中國礦床學的重要奠基人;大伯馮友蘭,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當時是聯大文學院院長;姑姑馮沅君是文學史家和作家,魯迅曾稱贊她是與廬隱、凌叔華、冰心齊名的“五四”才女,后來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一級女教授;堂姑父張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學家,曾任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堂妹馮鐘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紅豆》《三生三石》等。據不完全統計,馮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級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鄉河南的唐河,馮友蘭和他的弟弟妹妹則被稱為“馮家三兄妹”,名聞遐邇。唐河乃至整個南陽地區不但因馮家而感到驕傲,還因之形成了一種好學求知的良好風氣。
馮鐘蕓就出于這樣一個書香門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來也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史家、語文教育家。
任繼愈幫人帶的這個班,正好在馮鐘蕓所帶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語文,這樣難免有些接觸,一來二去,兩人就熟識起來。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這段姻緣,1943年,馮鐘蕓又被聘到聯大中文系當了助教,成為西南聯大第一位女教師,與任繼愈的接觸愈加頻繁起來。
當時,聯大中文系不僅有聞一多、朱自清、羅常培這樣著名的學者,中文系還有一部《四部叢刊》。任繼愈研究中國哲學史,覺得《四部叢刊》很有用,便經常去借書,正巧馮鐘蕓也到那里借書。兩個年輕人因為有了前面的基礎,此時相見,便多了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感覺。更為巧合的是,任繼愈還經常去馮鐘蕓的伯父馮友蘭先生那里探討哲學問題,也常常與馮鐘蕓不期而遇。
這以后,兩個年輕人的心越來越近。
可是,看上去,這兩個年輕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談婚論嫁。這讓任繼愈的導師湯用彤先生很是著急。于是,湯先生親自跑到馮家,代表任繼愈的家長(當時任繼愈的家人都在山東或武漢)去談這件大事。湯先生提親很鄭重,那時人們大多穿長衫,湯先生還特別加了一件馬褂,登門到馮家去提親。實際上,1943年春天,任繼愈的母親剛剛去世,一是他甚為懷念母親,二是為母親服孝期間,因此任繼愈絕口不提婚姻之事。
聯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羅常培先生,對任繼愈的印象甚好。而馮鐘蕓就在羅常培的系里當助教。很快,湯、羅兩位先生便心照不宣、不約而同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了。湯用彤有時家里請客,便同時邀請任繼愈和馮鐘蕓兩人去吃飯;羅先生則請他們逛逛昆明滇池公園,這當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人都心知肚明。這么一來,他們的來往就更多了起來。于是,在先生們的主持之下,任繼愈和馮鐘蕓舉行了一個訂婚儀式,證婚人就是羅常培先生。此后,任繼愈和馮鐘蕓一生相濡以沫,一起度過了六十年歲月。
其實,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是流行早婚,甚至娃娃親的。任繼愈小的時候,家里也給他定過親,但他稍長后,堅持要自己尋找愛情,頂著家庭壓力,硬是把婚退了。他也從未見過父母給他定的那個女子。
馮鐘蕓后來擔任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助教、講師、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導師,全國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民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全國婦聯執委會委員。除卻工作之外,馮鐘蕓還筆耕不輟,并于1948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評論集《杜甫研究論文集》,人物傳記《莊周》《屈原評傳》《杜甫評傳》《貫云石》,以及散文自選集《蕓葉集》等。
授業北大
1948年12月15日夜,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南苑機場,專程接胡適等一批高等學府文化學者。偌大的總統號,只接走了胡適夫婦和陳寅恪等幾位學者及家眷。任繼愈與眾多教師——馮友蘭、湯用彤、熊十力、鄭天挺、沈鈞儒、張岱年等等,均毫不動搖,滿懷希望,留在了北平,他們和歡欣鼓舞的人們共同迎來了北平解放。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學府的雕梁畫棟和遠處西山的夕陽剪影,成為他們一生魂牽夢縈的精神家園。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馬寅初先生為北大校長。當時的北大教師上課,還保留著西南聯大的傳統:沒有統一的教材,而是依照各自所長盡情發揮,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僅以語言課程而言,王力教古文,魏建功講音韻學,朱德熙講授語法修辭。文學課則更豐富多彩,游國恩講先秦兩漢、詩經楚辭,林庚講魏晉南北朝、唐詩,浦江清講宋詞元曲,吳祖緗講明清小說和《紅樓夢》。外國文學更是不得了,曹靖華講蘇俄文學,季羨林講東方文學,李賦寧講英國文學,馮至講德國文學,聞一多的弟弟聞家駟講法國文學。名家云集,各有所長。
當時的學術教學環境,正如風光旖旎的燕園一樣,令人賞心悅目,沉醉其間。知識分子如同迎來了姹紫嫣紅的春天,任繼愈感覺一下子去掉了臃腫的冬衣,換上了輕薄的春裝一樣,覺得渾身有使不完的勁兒。也是從這一年起,任繼愈兼任了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此時,任繼愈和馮鐘蕓有了兩個孩子,兒女雙全。女兒叫任遠,兒子取名任重,“任重而道遠”,任繼愈不僅將自己的一生追求時刻銘記,而且也在下一代身上寄托了希望和祝愿。
這段時期,國家政治清明,生活穩定,任繼愈又有機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對社會歷史和思想的關系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了,對任繼愈來說,這是個讀書和研究的好時機。此時的任繼愈年富力強,白天和晚上都要上課、開會、學習,往往是家人都睡了,他還沒有回來。孩子們好不容易看到任繼愈回來,吃過晚飯后他又埋頭去看書、寫文章。當時住的是平房,冬天各家都靠小煤爐取暖,一開門,僅存的一點熱氣都跑光了,深夜里更是寒氣逼人。為了熬夜工作,任繼愈設計了一張小炕桌,他坐在床上,蓋上被子,腿伸到小桌子下邊,頭頂上方再拉過來一個燈泡,看書寫字就不冷了。在這樣的條件下,他撰寫了不少課堂講義,也完成了許多學術專著。
任繼愈的教學和治學一樣嚴謹。一個學生交給他一篇研究伊斯蘭教的論文,任繼愈連夜看完,不僅寫了批注意見,而且改正了標點。學生找他為自己的書作序,他一絲不茍,一定要把書稿先拿來看一遍,能寫就寫,絕不隨便吹捧人。而在教學時,他采取平等的態度來研討,跟學生在一起也特別隨便,從來不會用自己的身份,強迫學生接受他的觀點。任繼愈經常對學生說,他非常佩服司馬遷,讓大家都學習司馬遷。他說,司馬遷被漢朝統治者迫害,很慘,應該說漢朝對不起他,但司馬遷寫史尊重史實,寫了漢代的繁榮、升平,并沒有借機報復,歪曲、篡改歷史。“這就是科學的精神,尊重歷史”。
任繼愈培養學生,注重思想方法等根本問題,曾有學生問任繼愈,他應該學習佛教的哪個派別。任繼愈說:“我們去頤和園,都是先上萬壽山、佛香閣,看了頤和園的全景,再去諧趣園、十七孔橋,對不對?沒有一進門就往諧趣園跑的。學習、研究一門學問也是這樣,首先要掌握這一學科的全貌,整個的歷史,把基礎打好,再去研究某一派別或某一斷代。你現在不要忙著想什么宗派,把基礎的中國史、世界史、佛教史以及佛經都多讀幾遍,弄通如道教史、基督教史等,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再考慮具體的研究方向。”
現北大哲學系教授王博回憶說,“大家都有個重要印象:任先生為人十分謙和、低調。我覺得,任繼愈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學者,而且是有古風的學者。任繼愈生命中有剛毅、柔韌的氣質,說話言簡意賅,擲地有聲,做人有原則,很堅持。此外,任先生也是有現實關懷的學者,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整理都包含了現實的關懷。在做學問方面‘擇善而固執之,體現了北大哲學系的開放精神。”任繼愈門下弟子眾多,李澤厚、余敦康、張豈之等在上世紀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
鳳毛麟角
任繼愈是最早應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指導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之一。新中國成立之后,任繼愈主動學習、運用馬克思主義。他說:“學著用歷史唯物主義來觀察社會和分析歷史現象,回頭來再剖析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就有了下手處,過去看不清楚的,現在看得比較清楚了……”侯外廬先生的《中國思想通史》開此先河,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繼之,隨后又有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整個20世紀50年代,哲學界紛紛開始服膺馬克思主義。
任繼愈憑借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逐漸摸索出一條以釋、道、儒三教相互影響為切入點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道路。由此,他走出了一條與前輩學者不同的治學道路,使他的佛教史、中國哲學史研究別開生面,自成一家。任繼愈最大的學術貢獻是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辯證法來研究中國哲學史,并開辟了用馬克思主義視野觀察宗教問題的先河。
他思考,中國傳統文化大致可以舉出以下幾種特點和品格:不失自我的兼容性、與時俱進的應變性、取之有節的開發性、剛柔相濟的進取性、和而不同的自主性。但最突出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尤其善于吸收一切有價值的外來文化,融入固有文化主流,不斷發展,幾千年沿著既定的方向,走著自己的路。中華文化根深葉茂,源遠流長,從來都是以自己固有的思想體系、思維模式來迎接外來文化的。
佛教等幾個外來宗教傳入中國及其發展道路,也充分體現了這些特色。佛教最先傳入中國,并不是直接從天竺來,中國人所認識的佛教經典都是根據西域文字翻譯成漢文轉手引進的,一度佛教在中國被看作是黃老清靜無為的理論,而中國最早介紹佛教的著作《四十二章經》及《牟子理惑論》,都以中國傳統忠孝觀念來理解這一外來宗教。景教(西方基督教的一支)在唐代最初傳入中國,中國人認為這個教派“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窅然靈虛,后后而妙有”,“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這完全是當時唐人的新解。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中國學者也著《天方性理》,以迎接這一外來教義,結合中國傳統文化來理解。與此同時,中國傳統宗教的忠孝觀念得到一切外來宗教的認同。后來的儒佛道三教會同,無不體現了中華文化圓融無礙、海納百川的特點。研究佛教不知不覺與儒、道兩家會合;研究儒教又必然與佛、道兩家貫通;研究道教又必然與儒、佛兩家相會。
正是在唯物辯證地看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任繼愈從新中國建國之初開始,就試圖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來重新建立中國哲學史的論述體系。20世紀50年代,任繼愈把對佛教哲學思想的研究作為研究中國哲學的組成部分。從那時起,他連續發表了幾篇研究佛教哲學的文章,受到學術界的關注。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任繼愈和他的文章,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和重視,后來便有了在中南海與任繼愈一席長談的佳話。任繼愈是最早為毛澤東所注意到的哲學史家,他的這些論文后來以《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出版,成為新中國用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其實,毛澤東對宗教問題始終是關注的,但這一點任繼愈先前并不知曉。后來,受邀與毛澤東談話,對此體會漸深。任繼愈過去寫的一些關于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澤東基本都了解,且都認真看過。毛澤東對任繼愈一直評價很高,在《毛澤東文集》中留有這么一段話:“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伊斯蘭教的沒有見過。”
這就是毛澤東說任繼愈是“鳳毛麟角”的由來。
1964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眾多研究所里,增加了世界宗教研究所。這個研究所是中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任繼愈主持籌備并一直擔任領導工作。研究所當時設在北大,參加者有中宣部的理論專家于光遠、北京大學校長陸平、國務院宗教局局長肖賢法等。時年48歲的任繼愈出任所長。工作開展以后,研究所又辦了一個刊物,叫《世界宗教研究》,在國內外影響很大。
群體哲學
任繼愈在研究宗教的同時,也沒有停下研究哲學的腳步。在談到宗教與哲學的關系時,他說,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動物吃飽喝足后就安靜了,人的好多問題卻是在吃飽喝足之后產生的。人需要關心自身最終的結果,渴望了解死后的生活等等。解決這些問題有兩個途徑:一是宗教,另一個是哲學。宗教向人保證:你一定能得到幸福,沒有任何懷疑;而哲學是理性思維的上升,也指出人生解脫的道路,但不保證人人都可能最后解脫,得到最高真理,得到精神的自由。哲學關注生存群體的解脫,關心集體,關注弱勢群體,品位高尚,不自私,充滿了人道主義的情懷。
很多人認為,任繼愈的哲學研究是一種“精英哲學”,而中國社會更需要的是一種“平民哲學”的研究,所以,雖然有很多人知道任繼愈,卻不知道任繼愈的哲學思想。任繼愈曾經在接受采訪時說:“我研究的不是所謂的‘精英哲學,也不是什么‘平民哲學,而應該是群體哲學。我不想離開群體去標新立異,一個人不可能獨立做好一件事。”
其實,正是在“七七事變”后1938年的那次西南大遷徙中,任繼愈看到了中國的現實,才更加堅定了終身從事哲學研究和思考的方向。而且,他也一直以結合中國國情為原則,以探索國家和社會的出路為己任。任繼愈的群體哲學還體現在,他將研究的觸覺伸到了影響中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瑣碎問題。比如他在1956年便開始提醒政府注重中國本土醫學的開發和科學利用,并為此寫了一篇名為《正確對待中醫》的文章。更有趣的是,他還提醒政府要注重人才的選拔與流動,并在文章《創業人才與守業人才》里利用古今事例進行對比,以示警惕。怪不得很多與他打交道的人都評論他是一個“瘋狂工作,并忘記自己存在的可愛小老頭”。
任繼愈說,哲學的起源也說明哲學家不能只停留在書齋。有一次,任繼愈在回答記者關于哲學的現實意義的問題時,他談到,人類自從認識了自身的存在和它的獨特價值,就開始了對社會、個人的作用進行探索。人類與自然界打交道已有200萬年以上的歷史。而人類認識自己、探索社會成因、如何在群體中生活、建立人際關系的規范,最多不過幾千年。這說明,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漫長歲月中,哲學萌發得很遲,但它又是人類文化中最精華的部分,最有價值的部分。迄今為止,世界上許多民族有文化、有藝術而沒有哲學。沒有文字就沒有哲學,因為哲學是高度抽象思維的產物。至于人類發現歷史唯物主義的時間就更短了,那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明創造,使人們找到了一個有效的工具,用它來觀察歷史現象,分析社會現象,研究社會發展規律和歷史進程方向,從此不再陷于盲目。而在研究哲學的方式方法上,任繼愈也有自己的特色。從步入學術界那一天起,任繼愈就懷著一種沉重的心情,一種巨大的歷史責任感,這可能與他所處的時代有緊密的聯系。作為一位與新中國歷史同步的人,任繼愈經歷得太多,他的心,始終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任繼愈的學術態度是治學要獨立,效果要為公。
他曾說:“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不可能成為真正獨立和自由的人。”然而,任繼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兩個人。一是魯迅,一是居里夫人,因為他們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前者不平則鳴,毫無畏懼、永不妥協;后者淡泊名利,榮辱不驚、天然本色。如前者不易,如后者亦然。“我佩服魯迅不是因為他的才華,而是因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現象敢于指出,不妥協,不和稀泥,這是一般的知識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難得的可以克服困難,又可以經受成功考驗的人。成功、名譽都絲毫沒有影響她的內心,她是卓越的科學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親。她時刻不忘祖國,將自己發明的元素命名為钚,以紀念自己的祖國波蘭。這是一位偉大的女性。”
任繼愈的學術研究明顯帶著“為人民服務”的傾向。比如中國是一個宗教大國,每一名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受“儒、道、釋”三家的影響。改革開放前他受毛澤東所托研究“佛學”,可以說任繼愈的學術是為人民為國家服務的學術。難能可貴的是:任繼愈精于學問,不攀龍附鳳,不趨炎附勢,始終保持節操。
有記者問任繼愈:哲學對于您自身的意義何在?任繼愈是這樣回答的:“多想想別人,少想想自己,多幫助別人。我的一些成果,一半靠自己的努力,一半靠機遇和外部環境條件。我在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成績不是最拔尖的,不過也不是最差,算個中等。但是我有上學的機會而別人沒有,這是我的機遇。后來我考上大學,這也是我的機遇。別人求學的機會讓給了我,我應該回報社會。好比一桶水,你不能光是從里面舀水,你還得往里面加水,這桶水才不會枯竭。”
平日與朋友交談,除了學術交流,任繼愈說得最多的都是國家大事。朋友問:“一輩子研究宗教,您信教嗎?”他慨然一笑:“就是要不信仰才能研究,我是無神論者。馬克思說過,如果跪著看誰,誰就一定比你高了!”若讓他談談自己,真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每到關鍵處,任繼愈總是輕巧地把話題岔開。他強調得最多的是,與他人相比,自己并非最出類拔萃,都是機遇。他說:“如果沒有社會的培養,就沒有個人的成材。我從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勞記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歲的時候編了《中國哲學史》,當時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別人,也一樣能編出來。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學家了,這和我的實際情況不符。”任繼愈不認同別人認為他是頗具影響的哲學家的說法,他認為,中國將來一定會誕生偉大的哲學家,但那需要一定的條件。他說,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哲學家,應該說他要能夠涵蓋世界上的根本問題,要有說服力、有征服力,能使人信服。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也沒有這個條件。哪一個宗教也做不到這一點,更不用說哲學家了。中國難出哲學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關系。借鑒西方本來是好事,但把握不好,就成了依樣畫葫蘆,生搬硬套,先是搬西方資產階級的,后來又生搬蘇聯的。實際證明,這種方法無助于弄清哲學的本來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亂。當然,還有很多因素制約哲學家的出現及對哲學思想的認同。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他們也是后來才影響世界的,當時他們也影響不了,后人才拿他們作旗幟,馬克思也是如此。文化是一種積累,思想有超前性和滯后性,不是亦步亦趨,于中國更是如此,需要一個過程,相信以后中國一定會有人成為影響世界的哲學家。
國圖歲月
歲月如梭,轉眼之間到了1987年。從1964年受命組建宗教研究所,屈指算來,任繼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已經工作了20多年。是年,任繼愈從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調任當時被稱為“北京圖書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從此坐擁書城,傳播知識和文明——他視之為一位嚴肅知識分子的最高使命。
這一年,任繼愈71歲。
任繼愈愛書,愛藏書,是出了名的。走進任繼愈先生的家,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貼墻而立的一排書柜。任繼愈告訴造訪的人,這是清末一個藏書家的書柜。其弟子變賣了柜子里的藏書,最后連柜子也要賣掉,他便買了下來。任繼愈愛書,對藏書家的柜子也格外珍惜,柜子里放的都是他最珍愛的圖書。然而,在任繼愈晚年,書柜里的書卻漸漸少了,每年都有一些書被他運走了。原來,這些書的新去處是任繼愈的家鄉——山東省平原縣圖書館。他說:“我從念高中開始到北京,就沒怎么回過山東,把它奉獻給養育我的土地,心里踏實一點。”任繼愈還說,讓書本給更多的人翻閱,能更有效地發揮它的價值。
現在的圖書館學界和圖書館界,有一種圖書館存在悲觀論,這種理論和聲音認為,隨著現代技術的迅猛發展,人們對信息和文獻的需求,不再似過去那樣依賴圖書館,人們可以不利用圖書館或不到圖書館就可獲取所需要的文獻和信息,并且最終有一天會不再需要圖書館,圖書館將在人類社會中消失。對此,任先生有他個人的深刻思考,在2009年接受《中國圖書館學報》專訪時,任老說:“圖書館是一個長壽的機構,即使國家消亡了,政府沒有了,但圖書館會存在。方式可以不一樣。因為知識總是有的,求知總是有的。”任繼愈說,圖書館是一個國家文明的重要載體之一。中國國家圖書館記載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發展軌跡,是中國乃至世界文明的寶庫。他說:“圖書館作為收集、加工、存儲各種圖書、資料和信息的公益性文化設施,在知識和信息的傳播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同時也是全民終身學習和教育的基地。圖書館可以不受年齡、學科的限制,為讀者提供所需資料,起到解決知識匱乏的作用;圖書館雖然不直接創造財富,卻間接培養創造財富的人,這就是我們對社會的貢獻。我們的教育職能不同于大學,責任要比大學大,服務的范圍要比大學廣,服務的層次要比大學深。”
國家圖書館的定位,一直是圖書館界關注的重點。作為館長,此一問題是任老一直思考的重要問題。在任繼愈眼里,圖書館是一項公益性文化事業,對國家、對民族、對人類的貢獻是長期的、與時俱進的。因此,國家應當加大投入,不求直接回報,不應該把圖書館等同產業去經營。當然,公益服務不等于免費服務。圖書館可以根據不同的職責,秉承公平的原則,向公民提供一定層面上的免費服務。對有些超常成本的服務,收取一定的成本費用是合理的,也是世界各國共同采用的方式,這仍屬于公益性服務的范疇。在2009年《中國圖書館學報》訪談中,任老在談到他任館長以來國圖的發展變化時說:“其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過去我們館偏重文獻資源的收藏和整理,流通考慮得少。我來之后,在努力扭轉,越是希見的東西,越要跟社會見面,不要鎖起來。重藏輕用的局面現在已經得到了改善。”
他還身體力行領導了空前的古籍文獻整理工程,依托國圖的館藏,整理古代文獻。他歷時十余年,以國家圖書館館藏《趙城金藏》為底本,主持編纂107卷《中華大藏經》。就在去世前他還在主持規模達2億字的《中華大藏經續編》編纂工作。2004年,看到世界范圍內收藏的敦煌文獻都已陸續出版,而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獻卻由于經費原因不能面世,任先生心急如焚,致函有關部門:“今我國力日昌,倘若國家對此項目能有一定的投入,我愿意盡我九旬老人的綿薄之力,使這個項目在3年左右的時間全部完成,還敦煌學界能完整使用資料的一個愿望。”在任先生的主持下,如今150巨冊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已陸續出版。此外,他生前還主持著《中華大典》的編纂和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為了讓國家圖書館珍貴的館藏得到社會的廣泛使用,他說,他整理古代文獻,可以說是近水樓臺先得月,這也是他作為館長的一份工作和責任。他預測,中華民族文化的鼎盛期可能要在20年后到來,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就是做一些文獻的積累和整理工作,為文化高峰期的到來打基礎。這就是一個以文化建設為己任的老人的拳拳之心。
在清理傳統遺產的工作中,任繼愈是付出精力最多、成果最為豐碩的學者。從儒教,到佛教、道教;從哲學,到宗教,到自然科學,還有其他如文獻學、民俗學等等。傳統文化的每一個領域,任繼愈都有自己獨特的建樹、過人的視野和高屋建瓴的指導。23年前,任老剛剛上任時所擔心的設備一流、圖書館的實力未必一流的現狀已不復存在,國圖現在已經邁進了國內外一流圖書館的行列。
一個心愿
在一次與記者談話時,任繼愈透露:他想完成一部屬于自己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在他的構想中,這部哲學發展史與他在上世紀60年代主編的4卷本《中國哲學史》大不相同——不是教科書,全部是他個人研究心得。“不要太長,大約30萬字。”任繼愈計劃著。舉重若輕,不慕虛華,正是他的學者本色。要把幾十年對中國哲學的理解濃縮在30萬字的篇幅中,難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學者以“著作等身”為榮耀的時候,老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對此,老人的思量更為久遠:“歷史上有很多書,號稱學術著作,卻沒有學術性;號稱科學著作,卻沒有科學性。因緣時會,也曾時行過一陣子。時過境遷,便被人遺忘得干干凈凈。主持這個淘汰選擇的就是廣大讀者。天地間之大公無過于斯者。我自己寫書,希望它的‘壽命能長一點。”
但他最終未能完成這部只有30萬字卻令人充滿期待的大書。
枯燥浩繁的整理工作占據了他大部分時間,因為,在他的案頭,總有看不完的書稿。而與自己的著述相比,他永遠把這些書稿排在更加優先要處理的位置。《中華大藏經》《中華大藏經續編》《中華大典》、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訂……無一不是鴻篇巨制。的確,時間寶貴。任繼愈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他只得把自己的寫作計劃暫時擱下。正因為如此,任繼愈著述一部帶有自身學術總結性質的《中國哲學發展史》的計劃,被一拖再拖,一延再延,最終未能實現。
對于學界,這是一個永久的遺憾;但對于任繼愈,卻是無悔的選擇。早在十多年前,任繼愈在給女兒的家書中就曾這樣寫道:“要相信我們有能力,也有責任對中華文明有所貢獻。即使不為目前,也要為后世;即使今天用不上,只要看到日后對社會有用,就值得去干。”而縱觀任繼愈一生的學術研究,盡管跨越多個領域,但我們卻能真切地感到:傳承中華文化,把國家和民族的興衰系于心頭,始終是他學術研究的主線。
2009年7月11日,任繼愈在北京醫院離世。他的遺照兩邊寫著這樣的挽聯:“老子出關,哲人逝矣,蓬萊柱下五千精妙誰藏守;釋迦涅槃,宗師生焉,大藏大典四庫文明有傳人。”
(摘編自江蘇人民出版社《真理的思考——任繼愈傳》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