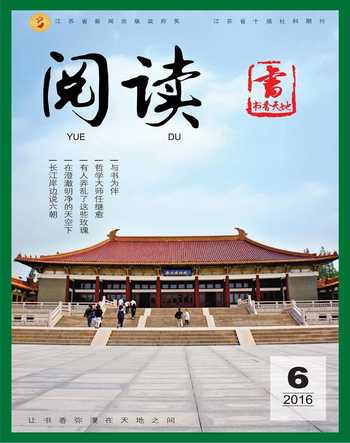慢燉的中國
李倩冉
黃梵的文字,向來包含著睿智的機警。理性的洞察,落于準確的表述,是他在閱讀中獲得的體悟,也一步步實現于他的創作,從短篇小說到近來的“物語詩”,莫不如是。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浮色》,更是恍然有了學術專著的面影——不僅僅是體例上的關鍵詞和參考文獻,抑或其中百科全書式的知識滲透。一個智性的敘事人,早已不滿足于講一個感性的故事,小說伸出多重觸角,要求讀者調用理智參與其中,并尤以歷史審思最具特色。
小說主體的時間外殼,不過只是2009年9月的最后一周:父親雷壯游被從天而降的隕石震暈后住院,不久于人世;兒子雷石接到父親病危的電報后駕車返鄉,一路坎坷,到達醫院時父親已去世幾個小時。然而,黃梵在一個中年大學教授返鄉路上的思緒萬千,和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的意識迷亂中,植入了整個二十世紀后半葉中國的歷史圖景。正如題記所言:“故鄉仿佛就是我自己”,宏闊的外部世界完全微縮于心靈的一滴,一個生命體攜帶了全部的歷史刻痕。
隱伏于雷壯游迷亂的神智中,有一個名為“未來城”的歷史瞭望點。盡管小說對未來城的構筑,足以引人想起近年來大陸如流感般席卷的科幻熱潮,盡管在文學遠不如現實離奇的當代中國,“想象力”是作家們亟需補上的一課,然而科幻或幻想本身,并不是黃梵的終極目的。未來城的存在,最大的意義在于為小說的歷史審視“調焦”。一方面,未來城充滿歷史的潛望鏡:雷壯游通過芯片讀到21世紀大學的鬧劇,并頗感驚訝;而他向未來城的居民解釋政治任務、積極分子等詞語,也讓彼時的人類困惑——當下習以為常的經驗,因在未來城獲得更長的歷史焦距而找回了自身的荒謬感。另一方面,盡管在未來城因果律發生了倒置,它本身卻是當下社會的一枚果實:由于人類的持續榨取,未來城環境惡劣,人類生命體征愈趨孱弱,遠離本真,只能龜縮在科技的外殼中“虛擬體驗”,在頻繁的甲烷雷爆中惶恐度日;但那時人類所懂得的敬畏、道德與文明,同樣也發端于20世紀的善念。未來城作為末世寓言,照鑒了當下的所有清澈與渾濁。同時,它只能反觀,不能更改過往,正如雷壯游眼看著李惠安的死去而別無他法,小說對歷史葆有了極大的尊重。
存在于記憶果核中的世界,被黃梵有意抹除了歷史時間節點,這讓《浮色》不再匍匐于中國當代小說線性的時間軸和歷史主義的枷鎖,而是開始一種“布朗運動”。一旦拭去時間的浮塵,你就能發現進步史觀的虛妄,從而更清晰地洞見人性的恒常,比如欲望。無論是石柳龍和美婦,還是雷壯游和瓊花、云霞,抑或雷石和李慧、耿莎、杜涓,甚至未來城的雷壯游和巖石……大半個世紀天翻地覆的歷史境遇中,當代中國人的欲望景觀竟如此相似:發自本能而稍顯猙獰,不知饜足又千篇一律,以至于這種欲望書寫讀到后來讓人疲憊。而這或許正與作者的意圖相關:因含有理性的審思,小說中的欲望從來不是靈魂的棲所,而是一種疾患,是壓力下的爆發物,是當代中國的心靈癥候,從而幾乎不是愛情。《浮色》中,愛情與欲望無關,并從來晚于毀滅。
盡管冷靜而理性,小說卻可貴地少有急切的判斷。語言謹慎地游走在事件與事件之間,只是勾連和展現,評判引而不發,充分讓人性在小說中博弈,頗耐人尋味。比如雷壯游堅持認為自己文革時參加武斗與李平陽燒安國寺有根本不同這一細節。不同于欲望書寫的類同,圍繞信仰,黃梵呈現了老住持、石柳龍、顯信和尚、唐師、雷壯游及其父母、伽德牧師、雷石、無瑕和尚、雷石的信徒朋友等一系列人物的信與不信,以及安國寺、高僧墓園、石家墩、百歲宮、教堂等宗教空間。小說并不鮮明地批判失去信仰的渾渾噩噩,也不一味推舉信仰的神性,而是細密地展開信仰的殮布,抖落其中包藏的眾生百態。同時,語言的節制使得小說多智慧的洞悉而較少詩思的漫衍,盡管音樂和意緒之間的疊映自有其獨到的節奏,小說的詩性不在語言中的情緒起落,而在于人類宏大場景的騰挪,即整個小說所呈現的“去勢”:安國寺的數次被毀,雷壯游、云霞的先后去世,耿莎自殺,未來城人類數量稀少并虛弱如《百年孤獨》家族最后被螞蟻吞噬的空皮囊……小說尾聲,一切落于白茫茫的大雪——盡力編織的浮華世界,都統統散去,浮生塵色,終歸于寂滅。這也正是標題“浮色”所暗示的:塵世的眾生萬相、光怪陸離的世事景觀,不過只是文明史的浮塵而已。
至此,《浮色》的歷史圖景在架構上已從當代小說疲沓的跋涉中飛升起來,足以與世界文學比一比了。我本想精益求精地期待小說于理性的洞察之外注入更多酒神的迷狂,將收攏的再散開,將清晰的重扯亂,把沉淀下去的又激揚起來。而當看到小說結尾歷時六年六易其稿的履痕時,卻因不能抑制的感動放下了苛求。這些年里,大陸長篇小說以令人驚駭的速度進行著“機械復制時代”的快速生產,文壇喧鬧而浮華,我們也被迫喝過太多勾兌的飲品與稀釋的糖漿。而今打開《浮色》,也終于可以嘗到用文火慢慢燉熟的中國,好像一碗濃郁的烏雞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