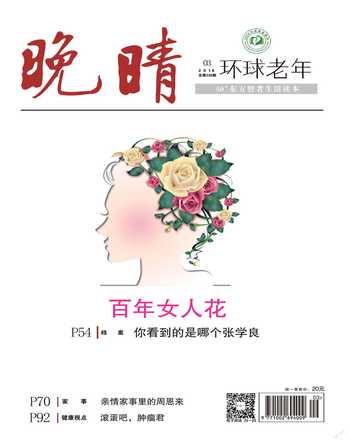曾益新:在思考中前行
田樹(shù)

與“老辣炮手”鐘南山相比,54歲的曾益新顯得低調(diào)。其實(shí),這位海歸院士一直是中國(guó)醫(yī)改的智囊。“一個(gè)有思想的人,才是一個(gè)真正有力量的人。”巴爾扎克的這句話,似乎在曾益新身上得到了印證。他善于思考,且不斷尋找可能的突破。
遵從于內(nèi)心的召喚
1990年,曾益新獲得中山醫(yī)科大學(xué)(現(xiàn)中山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博士學(xué)位。在那個(gè)出國(guó)潮涌動(dòng)的年代,他順理成章地跨出了國(guó)門:“那時(shí)候,一個(gè)普通的肝炎肝硬化患者,都會(huì)讓很多醫(yī)院束手無(wú)策。特別當(dāng)看到一些晚期癌癥病人痛苦地離去,我感到很難過(guò)。”
1992年至1997年,他先后來(lái)到東京都老人綜合研究所、日本東京大學(xué)醫(yī)科學(xué)研究所和美國(guó)賓夕法尼亞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留學(xué)經(jīng)歷豐富了他的視野:在日本體會(huì)到了什么是勤奮和認(rèn)真,在美國(guó)則感受到了真正的自主和創(chuàng)新。“科學(xué)研究是一場(chǎng)寂寞而艱苦的長(zhǎng)跑。在國(guó)外,我學(xué)到的不僅是書(shū)本上的醫(yī)學(xué)知識(shí),還有先進(jìn)的管理理念和求實(shí)的科學(xué)態(tài)度。”曾益新談起他的留學(xué)體驗(yàn)時(shí)說(shuō)。
1997年,當(dāng)時(shí)的中山醫(yī)科大學(xué)逆時(shí)而動(dòng),向海外學(xué)子拋出了橄欖枝,一舉召回10多名留學(xué)人員。曾益新就是其中之一。12年前的中國(guó),醫(yī)療科研條件都相對(duì)較差。曾益新的選擇頗令人“不解”。但是,曾益新堅(jiān)持自己的理想,他認(rèn)為“學(xué)了東西就是要報(bào)效祖國(guó)的”。
就像許多老一輩留學(xué)人員一樣,先回國(guó)安定下來(lái),再融合進(jìn)去,接著發(fā)揮優(yōu)勢(shì)。曾益新說(shuō),走過(guò)這“三部曲”之后,事實(shí)證明回國(guó)發(fā)展是一個(gè)明智的選擇。
“在自己的國(guó)家,每一個(gè)勤奮工作的人都能找到屬于自己的舞臺(tái)。更重要的是,我在這里找到了精神、文化上的認(rèn)同感,這個(gè)層面上的‘回歸讓我著迷。”
在思考中前行
找到了問(wèn)題,一步一步腳踏實(shí)地地解決問(wèn)題,這也是曾益新一貫風(fēng)格。既然已經(jīng)明確基層醫(yī)療水平是醫(yī)療體系的最短板,他本人和一些院士專家曾向國(guó)家建議設(shè)立10萬(wàn)個(gè)基層特聘全科醫(yī)師崗位,每個(gè)鄉(xiāng)鎮(zhèn)衛(wèi)生院和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wù)中心設(shè)2個(gè),其編制由國(guó)家特設(shè),放在縣區(qū)級(jí)醫(yī)院(即縣管鄉(xiāng)用);除了正常收入外,由國(guó)家每年給予10萬(wàn)元特殊津貼。這些經(jīng)過(guò)正規(guī)訓(xùn)練的全科醫(yī)師(或從二級(jí)以上醫(yī)院招聘的大內(nèi)科醫(yī)師再經(jīng)全科強(qiáng)化訓(xùn)練)將成為基層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學(xué)科帶頭人,提升基層醫(yī)療水平、提升對(duì)病人的吸引力、提升基層醫(yī)療機(jī)構(gòu)的業(yè)務(wù)量和業(yè)務(wù)收入,從而形成一個(gè)良性循環(huán),吸引更多合格的全科醫(yī)師去基層工作。特崗計(jì)劃可以說(shuō)是國(guó)家在特殊時(shí)期采取的一個(gè)特別手段,目的是通過(guò)強(qiáng)力的政府干預(yù)建立起一支活躍于基層的全科醫(yī)師“國(guó)家隊(duì)”和“種子隊(duì)”,帶動(dòng)整個(gè)基層醫(yī)療水平的提高,補(bǔ)齊醫(yī)療體系的最短板,是政府“該出手時(shí)就出手”的表現(xiàn)。可喜的是,目前已經(jīng)在四個(gè)省份開(kāi)展全科醫(yī)師特崗計(jì)劃的試點(diǎn)工作,可望在不久的將來(lái)總結(jié)、提高、不斷完善。
除了政府行為外,曾益新院士還提出應(yīng)該大力鼓勵(lì)社會(huì)資本進(jìn)入全科醫(yī)學(xué)領(lǐng)域。方法是在高端社區(qū)設(shè)立全科診所(健康會(huì)所),對(duì)社區(qū)人群以家庭為單位進(jìn)行健康管理,行使全科醫(yī)師的職能。這種高端診所的醫(yī)生待遇好,當(dāng)然收費(fèi)也高,需要居民購(gòu)買商業(yè)保險(xiǎn)或自費(fèi)來(lái)覆蓋。但只要真正能提供高質(zhì)量的服務(wù),高端社區(qū)的居民是有能力、也有意識(shí)購(gòu)買商業(yè)醫(yī)療保險(xiǎn)的。目前已經(jīng)有一些有遠(yuǎn)見(jiàn)的企業(yè)家在居住小區(qū)開(kāi)設(shè)全科診所,以提升其小區(qū)的品牌價(jià)值;也有名牌醫(yī)學(xué)院畢業(yè)生在大醫(yī)院工作數(shù)年后愿意去高端社區(qū)診所工作。這方面還需要國(guó)家給予政策支持,包括牌照發(fā)放、稅收優(yōu)惠等,以鼓勵(lì)和引導(dǎo)這個(gè)領(lǐng)域的發(fā)展。
當(dāng)全科醫(yī)生的來(lái)源解決后,下一步如何解決患者在初級(jí)、二級(jí)、三級(jí)診療機(jī)構(gòu)中的分流及轉(zhuǎn)診問(wèn)題?雖然目前醫(yī)改對(duì)此還沒(méi)有明確,但是,作為一個(gè)兼收并蓄的思索者和改革者,曾益新院士沒(méi)有停下思考和探索的腳步。
改革,但不越位,曾益新說(shuō):“我沒(méi)有想過(guò)要超越現(xiàn)有體制,而是在傳統(tǒng)的框架下,做些突破,比如讓沿襲已久的職工代表制度,改變了‘花瓶的被動(dòng)角色。”
“一個(gè)有思想的人,才是一個(gè)真正有力量的人。”巴爾扎克的這句話,似乎在曾益新身上得到了印證。他善于思考,在縝密的思考中,不斷尋找可能的突破。思考,也許是收獲正確答案的惟一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