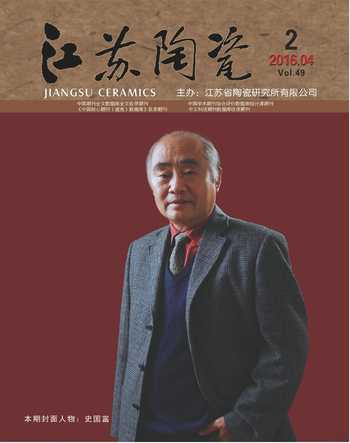淺析紫砂壺的自然韻味
宗媛
紫砂壺的誕生和發(fā)展始終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guān)。譬如它因茶而生;又常常被附加上豐富的人文情懷;同時(shí),它與自然亦有著天然的聯(lián)系。自古以來(lái),許多紫砂壺都保留著自然的韻味,并且給予人無(wú)限的藝術(shù)感懷。在表現(xiàn)自然韻味時(shí),恰到好處的搭配融合十分考驗(yàn)制壺藝人的功力。但凡一件優(yōu)秀的紫砂壺藝作品,定是渾然天成而不失美感創(chuàng)意,能夠使人從中獲取豐富的情感,體會(huì)到超越器皿本身作用的價(jià)值。
事實(shí)上,在紫砂壺中表現(xiàn)自然韻味的最佳方法便是在作品中植入自然元素,使之一目了然。紫砂壺以造型凸顯整體藝術(shù)形象,作為最主要的表現(xiàn)形式,造型素來(lái)十分豐富而變化萬(wàn)千,珠圓玉潤(rùn)的圓器、棱廓分明的方器、脈絡(luò)有致的筋紋器、趣味盎然的花器等,無(wú)不千姿百態(tài)。這其中,花器對(duì)于自然韻味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度無(wú)疑是最強(qiáng)的,它最主要的特征便是充分汲取自然元素精髓,并和造型創(chuàng)意融為一體,現(xiàn)所要賞析的這把“瓢蟲(chóng)瓜趣壺”(見(jiàn)圖1),便是花器典范之作,其自然韻味更是不言而喻。
紫砂花貨是用提煉取舍的藝術(shù)手法來(lái)表現(xiàn)自然形態(tài)中富有美學(xué)價(jià)值的部分,并符合功能合理、視覺(jué)美觀(guān)和使用安全等實(shí)用原則,或直接將壺的形狀塑成自然之物的樣貌,或在幾何形體上運(yùn)用鏤雕、捏塑等方法,將自然形態(tài)變化為造型的部件。現(xiàn)今所知的人類(lèi)歷史上最早的紫砂壺“供春樹(shù)癭壺”,據(jù)說(shuō)就是借鑒古老銀杏樹(shù)干上的癭結(jié)而捏塑成壺型的,并成為了文獻(xiàn)記載中的花器鼻祖。
“瓢蟲(chóng)瓜趣壺”采用花器造型的表現(xiàn)方式來(lái)傳遞其獨(dú)特的自然韻味,同時(shí)裝飾瓢蟲(chóng)、瓜葉,使整把壺透著空靈清秀的氣息,描繪出一幅意境唯美的深秋趣圖。壺身圓潤(rùn)飽滿(mǎn),形似一只蒂落的南瓜,整個(gè)壺身極富張力,占整件作品一大半的空間,這樣的設(shè)計(jì)將秋日豐收的喜悅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壺身上南瓜筋紋的線(xiàn)條清晰利落,表現(xiàn)力極強(qiáng),輕輕地一捺便刻畫(huà)出瓜果飽熟的姿態(tài),幾條筋紋便足以將豐碩寓意寫(xiě)盡,象征著瓜熟蒂落的成熟。壺蓋內(nèi)嵌,與壺身化為一體,一柄瓜蒂作壺鈕,整把壺完整而妙趣橫生。瓜葉卷成的壺嘴,含蓄而美麗,一根老瓜藤作壺把,瓜藤卷曲的姿態(tài),自然的紋痕,甚至其中空的特征,都進(jìn)行了栩栩如生的細(xì)致刻畫(huà)。
除了花器造型之外,這把“瓢蟲(chóng)瓜趣壺”也充分運(yùn)用塑器裝飾特征來(lái)豐富整體藝術(shù)內(nèi)容。壺身塑整片瓜葉脈絡(luò)清晰,葉莖向上自然伸展生機(jī)勃勃,瓜葉上暫歇的一只瓢蟲(chóng)形態(tài)逼真、比例協(xié)調(diào),頭、足、翅皆被雕刻得與現(xiàn)實(shí)中的瓢蟲(chóng)一模一樣,再用黑色顏料點(diǎn)綴頭和足,更是拍案叫絕,這只瓢蟲(chóng)是整把壺的畫(huà)龍點(diǎn)睛之筆,不僅完美呼應(yīng)了主題,更仿佛在寧?kù)o秋色中增添了生命的動(dòng)感色彩,達(dá)到靜中寓動(dòng)的藝術(shù)效果。
“瓢蟲(chóng)瓜趣壺”將一瓜、一葉、一蟲(chóng)組合成壺的形態(tài),傳遞出濃濃的秋意和自然韻味,給人以無(wú)限美的感受。宋代詩(shī)人秦觀(guān)有詩(shī)云:“我來(lái)仍值風(fēng)日好,十月未寒如晚秋。”而這把富有自然韻味的紫砂壺,則將秋韻濃縮,令人賞心悅目。除此之外,整把壺所流露出的生命力量和人文內(nèi)涵,進(jìn)一步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品位,壺如人生,使人們?cè)谄疯b這把壺的同時(shí)能夠反觀(guān)自身,領(lǐng)悟成熟與成長(zhǎng)的生命姿態(tài)。
日本漢學(xué)家、紫砂壺收藏家?jiàn)W玄寶在《茗壺圖錄》一書(shū)中對(duì)紫砂壺有這樣的評(píng)價(jià):“溫潤(rùn)如君子,豪邁如丈夫,風(fēng)流如詞客,麗嫻如佳人……飄逸如仙子,廉潔如高士,脫塵如衲子。”可以說(shuō),紫砂壺是美物的代表,更是富有價(jià)值的藝術(shù)形式。羅丹說(shuō)過(guò),“生活中從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fā)現(xiàn)美的眼睛。”,對(duì)于紫砂壺藝創(chuàng)作而言同樣如此。
以似水流動(dòng)的情懷去做一把壺,壺也會(huì)用感情來(lái)回應(yīng)。為創(chuàng)作出有自然氣息的生動(dòng)的花器作品,不僅需要作者親臨自然,用敞開(kāi)的心靈去感受自然的美麗和偉大,更需要在此之后撩動(dòng)內(nèi)心的創(chuàng)作情懷,提煉取舍把自然帶入方寸之間的一把壺上。只有這樣,才會(huì)賦予一把壺獨(dú)特的藝術(shù)個(gè)性,這應(yīng)是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