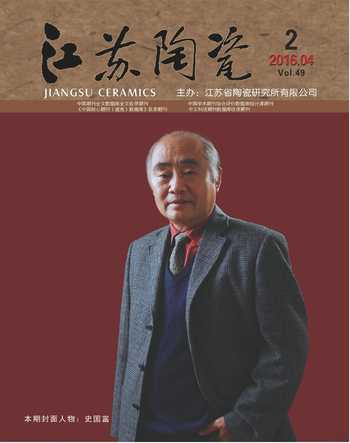漁歌晚唱 還道人間歡樂多
湯燕萍
漁,《辭海》解釋為捕魚。《史記·貨殖列傳》:“舜,漁于雷澤” 。這一記載說明,漁,即捕魚,是人類生存的一種手段,像舜這樣的圣人也曾以捕魚為業。關于漁的藝術形象可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時代。在新石器的彩陶盆、罐上,就出現彩繪的漁紋,有張口翹首互相追逐的大魚,有并排游動的小魚。藝術創作是從人們生活的勞動實踐中產生的,在半坡彩陶上繪制的人面紋的兩側繪有魚形,說明先人們已把捕魚作為人類生存的手段之一,是那時候人們漁獵生活的寫照。《史記·貨殖列傳》還記載有:“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
由于魚和人們生活的關系密切,引起歷代文人的廣為關注。唐代朱景玄《唐朝名畫錄》記載了詩人張志和與書法名家顏真卿的一段軼事:“張志和,或號煙波子,常漁釣于洞庭湖,初,顏魯公(真卿)典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為卷軸,隨句賦象,人物、舟船、鳥獸、煙波風月皆依其文,曲盡其妙。”可惜,顏真卿所贈的漁歌及張志和依其詩意所作的漁歌圖都沒有留傳下來。
在陶瓷裝飾上,魚紋是陶瓷裝飾常用的吉祥圖案之一。明代的“五彩魚藻紋蓋罐”上,有用紅色繪制的紅鯉魚,分布在罐身及罐蓋,大小不一,姿態各異,穿梭往來,造型生動。還有用黃、藍、綠、紫色繪成的水藻,分布在魚的周圍,五彩交相輝映,令人賞心悅目。
宜興紫砂關于魚題材的作品當首推清代邵大亨的“魚化龍壺”,《三秦記》記載有:“江海魚集龍門下,登者化龍。”“魚化龍壺”即是以此內容設計創作的,其壺用淺浮雕的方式在壺體的兩面各塑一魚一龍,并配以云水紋,形態生動而寓意深長,是對魚的形態的另一種藝術詮釋,比喻人生的平步青云。
“魚壺”(見圖1)的造型,其嘴、把、底、蓋皆借鑒了顧景舟的“笑罌壺”,不同之處一是壺體拉長,底足收小,頸肩部沒有云肩線的裝飾;二是改水滴形鈕為橋形鈕,為增加其把玩意趣,在橋形鈕上套一能活動的圓環,增添其靈動感。在造型特征上,“魚壺”這種上豐下斂的造型可追溯到東晉的“黑釉盤口壺”,以后這一優美的造型在瓷器器型上得到廣泛的應用,如宋代名窯耀州窯的“青釉剔花瓷瓶”。陶瓷器的造型美是直觀的,優美的造型給人以特有的視覺美感,人們在欣賞的過程中感到愉悅,得到精神上的享受。“魚壺”的上部連同其嘴、把,形成一種開拓、外展的態勢,它與下收的底足在對比中產生了轉化、節奏之美,而在總體上它們和諧共處,這種造型之美是在歷代傳承中不斷完善的。
“魚壺”是用“壓紋”的技法來描繪畫面的,它從民間工藝的刻紙中汲取藝術營養,民間刻紙有一種特殊的裝飾美,它把我們常見的動物、植物、生活用品等形象圖案化,在民間稱之為吉祥圖案。它的起源可上溯到商代,至宋代逐漸成熟,明、清為鼎盛期,達到“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境地。魚的塑飾在商代就在玉雕上得到應用,到清代,在民間的刺繡、織錦、磚刻、木雕、石雕、剪紙等工藝品中可經常見到它們的身形。
“魚”諧音“余”,它寓意年年有余、喜慶有余、富貴有余等,成為民間喜聞樂見的題材。“魚壺”的裝飾,壺體中部是一條豎向下凹的筋紋,在其上部有一條接近半圓的凹線,刻畫出魚的頭部,其中上部用特制的工具壓制出兩圈圓形的凹凸線,以刻畫出魚眼。在半圓的凹線下用竹制的特形工具壓出一個個魚鱗紋,自中部至兩側斜向排成三至四排,這是一種圖案化的魚形,是具有民間刻紙風格的圖案,它簡潔、明快、質樸、夸張、得意忘形,具有裝飾意趣。壺蓋上的橋形鈕則寓意江南的小橋流水人家,與描述魚的意境相融洽。
江南人稱魚米之鄉,人們把“魚”放在“米”之前是有它的歷史淵源的,因為我們的先人最早是以漁獵的手段生存下來的,這是大自然天然的恩賜,以后人們才學會了放牧、養魚、種稻,所以歷代的文人贊美漁樵耕讀,并把“漁者”作為精神生活的一種寄托。唐代文學家王勃的《滕王閣序》中有“漁歌唱晚,響窮彭蠡之濱”的名句,描述的是鄱陽湖的漁民在晚間歸來,魚滿艙、船成行,歡歌笑語,喜慶豐收的情景。“魚壺”的設計創作,是把古人的文學語言化為紫砂的雕塑藝術語言,在紫砂的造型與裝飾上表達我們對生活的熱愛,對生活的謳歌,也表達我們對紫砂藝術的熱愛,對紫砂藝術的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