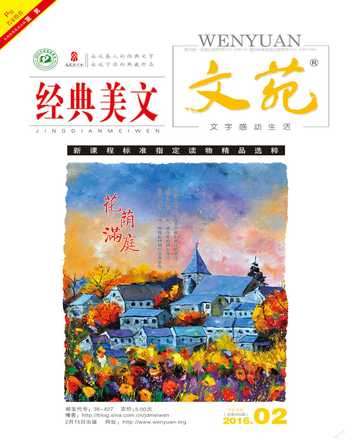荻花秋瑟瑟
項麗敏
這本書里收有他的《我與地壇》,有《命若琴弦》和《我的遙遠的清平灣》等名篇佳作。正如編者所說,凡是讀過史鐵生作品的人,沒有不被他作品中煥發出來的精神力量和藝術魅力打動的。他的博大和深邃不僅僅是因為他身體的殘疾,也是因為他的平實、寬厚、堅強和樂觀。
就此,閱讀本書,重拾那些歷經滄桑歲月磨煉依然煥發著耀眼的光芒的文字。相信這些文字會帶給我們彌足珍貴的美和藝術感染,在我們的心田,散發著花朵一樣的芬芳!
仲秋后的一天,我在微信里寫了一行字:即便行走在荒寂秋野,也要有涼風里看荻花的悠閑心情。
寫這行字的時候,正走在一條伸向湖邊的小道上,小道兩邊鋪滿碎石子和細草,不遠處,一片荻花逆光而立,令人出神。
荻花就是《詩經》里的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說的就是它。只是蒹葭這個詞過于古老,也過于書面化,不適合日常使用。日常生活中,人們大多習慣叫它芭茅、蒲葦花或芒草。
眾多的名號里,比較喜歡的還是荻花,可能是受幾位詩人朋友的影響,荻花開在她們的詩行間,自在,寧靜,脆弱又堅韌,如同詩的真諦,也如同生活的真諦。
荻花常見于曠野、溪畔與河邊,生性喜水,也喜荒僻,越是無人的地方它就越是恣意——寫到這里,突然想到張愛玲的一句話:在不與人交接的場合充滿生命的歡欣。這句話用在荻花身上也很妥帖。
若是依照植物學的嚴謹,細究起來,荻花、芭茅、蒲葦花,這些雖同為禾本科,但并非同一事物,之間還是有區別的。
荻花開在白露時節,花穗下垂,呈煙花狀四面分散,初開時為絳紫色,霜降后花穗轉白。荻花的白是花白,像暮靄降下之前微茫的天色,有些蒼涼,又有說不出來的溫暖與親切,猶如家中長者兩鬢的白發,讓人想伸出手去撫摸,想把臉輕輕貼上去。
芭茅揚穗的時間就早多了,在五月末,春夏交接之際。芭茅初開時也是絳紫色,慢慢地顏色褪去,轉為淺棕,再轉淡黃。若沒有人收割,芭茅會一直佇立在那里,扛著一面小小的黃旗,直到與秋天的荻花會合。此時芭茅的花絮早已飛盡,莖稈金黃,細長,在風里搖擺起伏,柔軟而謙卑,又有所堅持。
蒲葦花和荻花幾乎同時揚穗,它們是約好了在秋天會面的密友。蒲葦花的色澤銀亮,初開時花穗向上,銀矛般,插在路邊和山間,隱隱地透著兵戈氣,使秋之山野更為肅殺。河灘上的蒲葦花則要抒情得多,黃昏時分,夕陽從山巔投過來,似一束眷戀的目光,擁抱著蒲葦花,也擁抱著蒲葦花在水里微漾的倒影,蒲葦花此時看起來更像是銀色火焰,喧嘩又寂靜,也像牧神獻給仙女的情歌,繚繞在百鳥歸林的曠野。
芒草也叫五節芒,花穗棕黃,和荻花開在一處,難以分辨,然而知情者還是能將它們區分開來。它們最明顯的區別在于莖稈,荻花的莖稈是中空的,截短了可做吸管用,芒草的莖稈則是實心,柔韌結實,用來編草席最好。
“草花之中,不列入芒草怎么行?使得秋野遍饒情味者,莫非就是這些芒草嗎?其穗端泛紅,色甚濃郁,當朝露濡濕之際,試問還有比這更可賞的嗎?”
寫芒草的文字中,最愛《枕草子》里的這一節,三言兩語,便將芒草的情態勾勒出來。但我又總覺得,清少納言寫的芒草就是我眼前所見的荻花。和芒草比起來,荻花的名字確實更富情味,是暖色調的,而芒草呢,聽上去有如芒在背的不安感,色冷,甚至有些凄涼。
在秋風瑟瑟的山野漫行,眼前除了飄落的黃葉,已無甚可看的了,使人不免生出歲月荒蕪、人生寂寞清冷的感慨,然而只要有一片荻花開在那里,就會讓目光陡然亮起,心頭生出溫熱,就像一個游子,在無所著陸的荒寂中,突然看到了久違的親人,看到心之所系的、遙遠又親密的故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