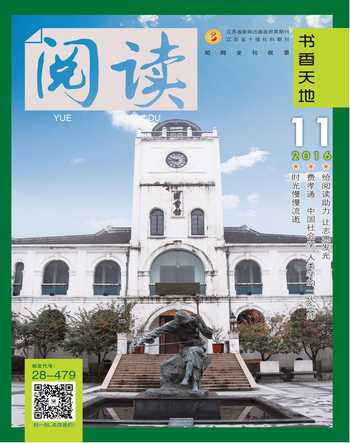西南聯(lián)大的“長(zhǎng)征”
李誠(chéng)

這是一所只存在了8年半時(shí)間的大學(xué)。 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馮友蘭、沈從文、錢穆、金岳霖……均曾執(zhí)教于這所大學(xué);楊振寧、李政道、黃昆、朱光亞、鄧稼先……都是它的學(xué)生。
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簡(jiǎn)稱“西南聯(lián)大”),一個(gè)讓很多人肅然起敬的名詞;而在它輝煌的背后,又包含著那個(gè)時(shí)代賦予它的苦難。1937年11月,南遷的北京大學(xué)、清華大學(xué)、南開(kāi)大學(xué)在長(zhǎng)沙聯(lián)合辦學(xué),學(xué)校初名“國(guó)立長(zhǎng)沙臨時(shí)大學(xué)”。這所誕生于抗戰(zhàn)烽煙中的大學(xué),注定了其顛沛流離的命運(yùn)。3個(gè)月后,戰(zhàn)火逼近湘江,學(xué)校再次遷移。國(guó)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68天里,300多名師生,穿越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多公里,徒步688公里,終于抵達(dá)遙遠(yuǎn)的云南昆明。這段艱苦卓絕的遷徙,被稱為“中國(guó)教育史上的長(zhǎng)征”。
西遷之爭(zhēng)
當(dāng)時(shí),要不要西遷昆明,在學(xué)生中有著激烈的爭(zhēng)論。
一個(gè)不容忽視的背景是—1937年11月,日機(jī)就開(kāi)始轟炸長(zhǎng)沙,所有人都明白,作為后方重鎮(zhèn)的長(zhǎng)沙,成為抗敵前線只是一個(gè)時(shí)間問(wèn)題。
空襲警報(bào)聲不時(shí)響徹城市,西南聯(lián)大的師生無(wú)法安心上課,人心浮動(dòng)。
事實(shí)上,西遷昆明早就被提上日程。北京大學(xué)校長(zhǎng)蔣夢(mèng)麟向剛剛出任教育部長(zhǎng)的陳立夫提出過(guò)該計(jì)劃。陳立夫說(shuō),蔣介石認(rèn)為大學(xué)搬來(lái)遷去會(huì)影響士氣,未予同意。
直到1938年1月上旬,形勢(shì)愈發(fā)嚴(yán)峻,陳立夫才同意學(xué)校搬遷。
但爭(zhēng)議依舊存在。
出于職責(zé)和個(gè)人前途考慮,多數(shù)教職員贊成西遷;與此相反的是,很多學(xué)生反對(duì)西遷。
學(xué)生反對(duì)的原因,大多出于年輕人的熱血精神。此前,已經(jīng)有部分學(xué)生選擇了投筆從戎,用最直接的行動(dòng)拯救苦難的祖國(guó),在這種情緒的影響下,逃難式的西遷行動(dòng)被學(xué)生視為“逃跑”,萬(wàn)不可行。
當(dāng)西遷的告示貼出后,教室走廊上隨即貼滿了反對(duì)西遷的壁報(bào)。一名學(xué)生撰寫了這樣的文字—“須知大觀樓不是排云殿,昆明湖不在頤和園”,要大家勿為四季如春的昆明所惑;有的學(xué)生更直接,在告示四周框起黑圈,寫上“放屁”兩字。
西南聯(lián)大的一舉一動(dòng),即使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也會(huì)引起各方關(guān)注。
為了說(shuō)服學(xué)生,蔣夢(mèng)麟邀請(qǐng)軍委會(huì)政治部部長(zhǎng)陳誠(chéng)來(lái)校演講。在演講中,陳誠(chéng)說(shuō):“你們是中國(guó)為數(shù)不多的文化精英,抗戰(zhàn)勝利后,擔(dān)負(fù)著國(guó)家復(fù)興的希望。”
據(jù)統(tǒng)計(jì),盡管在反對(duì)西遷聲明上簽名的同學(xué)超過(guò)了二分之一,但最后去了云南的仍占全校學(xué)生的三分之二。
事后來(lái)看,學(xué)校西遷是明智之舉。
最后一課
西遷之事,困難重重。
經(jīng)費(fèi)是首要問(wèn)題。1938年1月22日,學(xué)校貼出告示,公布了路費(fèi)津貼的規(guī)定—教職員每人65元,學(xué)生每人20元,沿途各辦事處人員外加食宿費(fèi)和每人每日辦公費(fèi)5元。
對(duì)學(xué)生而言,20元的路費(fèi)津貼遠(yuǎn)遠(yuǎn)不夠。
當(dāng)時(shí),從長(zhǎng)沙至昆明,乘車至少需要55元。一斤米約0.18元,55元相當(dāng)于每名學(xué)生一年的生活費(fèi)。
步行入滇的計(jì)劃,在此形勢(shì)下應(yīng)運(yùn)而生。
學(xué)校師生赴滇路線有3條:一是組織旅行團(tuán)步行,沿直線到昆明;一是乘車,經(jīng)桂林到越南河內(nèi),再轉(zhuǎn)往昆明;一是乘船,先下廣州,到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再到昆明。
大部分教職工和全體女學(xué)生選擇了乘車或坐船。但還有11位自愿步行的教師,他們組成了旅行團(tuán)的輔導(dǎo)團(tuán)隊(duì),以南開(kāi)大學(xué)教務(wù)長(zhǎng)黃鈺生教授為主席,聞一多、曾昭掄也是成員之一。
2月初,學(xué)校開(kāi)始組織男學(xué)生體檢,體檢結(jié)果分A、B、C三種:體檢表上有兩個(gè)“A”的,或一個(gè)“A”和一個(gè)“B”者,發(fā)“甲種赴滇就學(xué)許可證”,必須步行,沒(méi)有條件可講;體檢表上有兩個(gè)“B”者,可自愿選擇是否步行;體檢表上只要有一個(gè)“C”的,則乘車或坐船。
所有學(xué)生行前,須打預(yù)防針,防止感染疫病。
學(xué)校請(qǐng)張治中委派黃師岳中將,擔(dān)任湘黔滇旅行團(tuán)的團(tuán)長(zhǎng)。
為此,黃師岳來(lái)學(xué)校講話,稱:“此次搬家,步行意義甚為重大,為保存國(guó)粹,為保留文化。”他甚至將此次西遷定義為中國(guó)“第四次的文化大遷移”—前三次為張騫通西域、唐三藏取經(jīng)、鄭和下西洋。
他的講話,極為鼓舞士氣。
據(jù)記載,湘黔滇旅行團(tuán)從長(zhǎng)沙出發(fā)時(shí),加上醫(yī)生和雇工、伙夫,總計(jì)335人。
1938年2月18日,聞一多為文學(xué)院的學(xué)生上了最后一課。他高呼:“中國(guó)不是法蘭西,因?yàn)椋袊?guó)永遠(yuǎn)沒(méi)有最后一課!”
2月19日,旅行團(tuán)的師生們召開(kāi)誓師大會(huì)。在震天的口號(hào)聲中,他們踏上了征途。
長(zhǎng)征路上
旅行團(tuán)采用了軍事化管理,下設(shè)兩個(gè)大隊(duì),大隊(duì)長(zhǎng)由學(xué)校的軍訓(xùn)教官擔(dān)任;每大隊(duì)又設(shè)3個(gè)中隊(duì),每中隊(duì)有3個(gè)小隊(duì),中隊(duì)長(zhǎng)、小隊(duì)長(zhǎng)均從體格健壯、認(rèn)真負(fù)責(zé)的學(xué)生中遴選。
但這種長(zhǎng)途行軍,對(duì)師生們來(lái)說(shuō)都是第一次。
按黃師岳的想法,隊(duì)伍應(yīng)該采取正規(guī)行軍方式,兩隊(duì)分列路兩側(cè),保持一定距離,勻速前進(jìn),統(tǒng)一休息。幾天后,這種美好的愿望被現(xiàn)實(shí)擊得粉碎,生性自由的大學(xué)生紛紛抗議,最后竟自動(dòng)散開(kāi),攔也攔不住。
為此事,黃師岳感慨“帶丘九跟帶丘八就是不一樣”。他索性放手,每天早晨集合點(diǎn)名,然后大家一哄而散,團(tuán)長(zhǎng)負(fù)責(zé)殿后,只要當(dāng)天能到目的地,隨便你怎么走。
有人戲言,西南聯(lián)大的自由空氣就是從旅行團(tuán)開(kāi)始形成的。
開(kāi)始時(shí),黃師岳還擔(dān)心有人會(huì)“打游擊(掉隊(duì))”,但每到飯點(diǎn),一點(diǎn)名,一個(gè)不少,他便放心了。
當(dāng)然,學(xué)生們也有規(guī)矩的時(shí)候—每到一個(gè)城鎮(zhèn),學(xué)生們須集合列隊(duì),方可進(jìn)城。
各城鎮(zhèn)的歡迎儀式相當(dāng)隆重。一些縣城大開(kāi)城門、掃凈大路,路面撒上黃土,貴州玉屏縣政府還組織了小學(xué)生列隊(duì)歡迎。
但一出城,學(xué)生們又恢復(fù)了自由散漫的形象。
一位親歷者回憶:除了在較大的城市多停留一二天外,哪怕是下著傾盆大雨,當(dāng)集合的號(hào)音吹響之后,也只得撐開(kāi)雨傘,讓雨滴飄灑在衣服上出發(fā)了。
學(xué)生們睡農(nóng)舍、古廟,甚至睡在棺材蓋上。有時(shí)候,他們找不到住宿地,只能行軍至深夜,備嘗辛苦。
最痛苦的,是爬山。據(jù)說(shuō)每次一看到前方有大山阻隔,這群學(xué)生甚至?xí)诔雠K言,然后爭(zhēng)相“打游擊”。
行軍日子長(zhǎng)了,他們也總結(jié)出了一些經(jīng)驗(yàn):走路不能穿防滑的釘鞋,會(huì)刺破腳;應(yīng)穿草鞋,還要將草鞋用水浸濕,找鵝卵石敲打一遍,這樣穿著比較舒服;盤山公路曲折,可以找小路,順著電線桿走,一般十拿九穩(wěn)……
一些原本身體孱弱的學(xué)生,十幾天下來(lái),也慢慢能一天走上四五十里路。
一夜驚魂
湘西多土匪。
據(jù)親歷者回憶:旅行團(tuán)進(jìn)入湘西前,黃師岳在集合訓(xùn)話時(shí),特別說(shuō)明:他已給土匪頭目寫了信,但危險(xiǎn)仍是有的,故隊(duì)伍要整齊,不許爭(zhēng)先也不許落后。
上路前,當(dāng)?shù)乩习傩找矊?duì)學(xué)生們說(shuō):“前面多綠林朋友,你們要當(dāng)心些啊!”
湘西公路曲折,兩旁峭壁矗立,強(qiáng)人隨時(shí)出沒(méi)。
深夜,黃師岳召集各小隊(duì)長(zhǎng)開(kāi)會(huì):據(jù)聞?dòng)卸偻练碎_(kāi)來(lái),學(xué)生們須穿好衣服,吹熄燈火,等待命令。
一夜驚魂。
第二天,集合號(hào)正常吹響。
旅行團(tuán)始終沒(méi)有與湘西土匪正面接觸過(guò)。據(jù)說(shuō),這是湖南省政府事前給“湘西王”陳渠珍打了招呼,說(shuō)將有一批窮學(xué)生“借道”去云南讀書云云。還有一種說(shuō)法是,他們身穿軍裝,土匪誤以為是軍隊(duì)開(kāi)拔,未敢造次。
進(jìn)入云南境內(nèi)。第一天,身穿軍裝的學(xué)生們與一支滇軍部隊(duì)迎面而過(guò)。滇軍官兵看他們制服嶄新、隊(duì)容整齊,誤以為他們是航空部隊(duì),當(dāng)即開(kāi)罵:“我們正開(kāi)往前線去打仗,他們‘航空兵卻躲在后方享福!”
行萬(wàn)里路
在一些當(dāng)事人回憶的資料上,我們可以大致還原這支旅行團(tuán)的行軍場(chǎng)景。
身著草綠色軍裝,打著綁腿,帶著“湘黔滇旅行團(tuán)”的臂章,背著水壺、干糧袋、搪瓷飯碗和雨傘,穿草鞋,三三兩兩如天馬行空,隊(duì)伍拉得很長(zhǎng)。
隊(duì)伍的尾部,是聞一多、曾昭掄等教授,以及黃師岳,騎著自行車,來(lái)回巡視。
兩輛運(yùn)載行李、鍋碗炊具的卡車,不緊不慢地跟在最后。
所有人都被太陽(yáng)曬成了“黑人”,身強(qiáng)力壯,688公里磨礪的成果顯而易見(jiàn)。
4月27日,旅行團(tuán)到達(dá)大板橋,離目的地昆明不到20公里。
許多人興奮異常,希望一鼓作氣趕到城中。但黃師岳還是下令休息—他希望進(jìn)城的是一群干凈、整潔的學(xué)生。
值得一提的是,黃師岳是旅行團(tuán)中年齡最大的,學(xué)校為了照顧他,特給他準(zhǔn)備了一匹馬和一輛自行車。但他視學(xué)生如骨肉,時(shí)常將馬和自行車讓給一些身體不適的學(xué)生騎用。
4月28日,距昆明10多里處,先期到達(dá)的聯(lián)大同學(xué)前來(lái)迎接,學(xué)校還準(zhǔn)備了茶點(diǎn),由蔣夢(mèng)麟夫人陶曾谷女士帶著幾位教授夫人和女同學(xué)殷勤款待。
午后,旅行團(tuán)整隊(duì)出發(fā)。接近城區(qū)時(shí),街頭已有舉著橫幅、呼著口號(hào)歡迎的男女同學(xué)。蔣夢(mèng)麟和清華校長(zhǎng)梅貽琦也等候多時(shí)。
大隊(duì)人馬抵達(dá)市區(qū)的圓通公園后,黃師岳一一點(diǎn)名,將花名冊(cè)鄭重交給蔣夢(mèng)麟,并向他敬禮。
此行全程1663.6公里,號(hào)稱3500里,除去途中休息、天氣阻滯及以舟車代步外,實(shí)際步行40天,每天平均步行約65里,除了中途因病傷減員的,大部分按時(shí)到達(dá)。
當(dāng)日,昆明舉城傾動(dòng)。外國(guó)報(bào)刊評(píng)論:“中國(guó)文化已經(jīng)西移。”
聞一多的胡須已有近尺長(zhǎng),曾昭掄渾身爬滿了虱子,所有學(xué)生猶如黑炭、疲憊不堪……5月4日,西南聯(lián)大重新開(kāi)課,直到1946年5月4日復(fù)員北上。
1946年11月,胡適在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九周年校慶紀(jì)念會(huì)上,重提旅行團(tuán)的這段歷史:“這段光榮的歷史,不但在聯(lián)大值得紀(jì)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紀(jì)念。”
遷移的故事,被寫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xué)的校歌:
“萬(wàn)里長(zhǎng)征,辭卻了五朝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離別。千秋恥,終當(dāng)雪,中興業(yè),須人杰。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guó)運(yùn),動(dòng)心忍性希前哲。待驅(qū)除仇寇復(fù)神京,還燕碣。”
歌聲高昂。
(摘自《報(bào)刊薈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