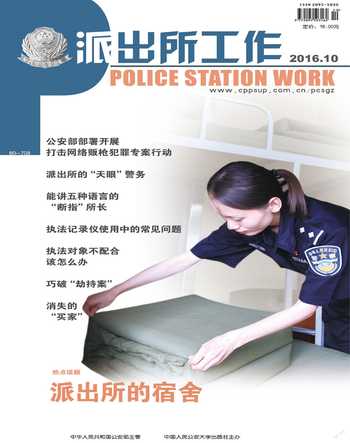西門警事之二十二敲打敲打
魏煒 北風翼

1.
事情其實很簡單,但卻把高副所長給難住了。
這天下午,寧先生從皇家園林游覽出來,剛上公交車,就被人擠了一下。他趕緊摸摸口袋,錢包不見了,于是報了警。
顧照他們駕車趕到現場,準備把寧先生帶回派出所先做筆錄。沒想到,寧先生指著一個看熱鬧的人說:“他就是小偷兒!”
那個小伙子就笑了:“這是誣陷啊!警察先生,你們可得給我作證,他說我是小偷兒,這是誣陷我,還侵犯了我的名譽權,我要他賠償我的精神損失費。”
顧照讓小伙子把隨身物品拿出來看一看。他很配合,把口袋里的錢包、手機、鑰匙都掏了出來。顧照又對寧先生說:“你是不是看錯了?”寧先生搖著頭,堅持說:“我不會看錯,就是他。”顧照又到周圍的垃圾桶里看了看,還真找到了寧先生的錢包,身份證和卡都在,但一千多元現金沒了。
要是遇到一般人,這會兒就會說算了,給小伙子賠個禮,各自走人。但寧先生還是堅持要懲治小偷兒。小伙子也較上了勁,堅持讓他賠償精神損失費。顧照看現場越聚人越多,七嘴八舌,沒辦法做工作,只得把他們都帶回所里,然后跟高副所長做了匯報。
高副所長讓顧照他們再去現場,看周圍是否有監控探頭,再問問是否有證人。顧照去了半個多小時,回來匯報說周圍沒有探頭,也沒有證人。高副所長說先按被盜案給寧先生做筆錄,著重問他為什么懷疑是那個叫魯青的小伙子行竊的。
寧先生的回答很簡單:他發現被盜后,回頭看了一眼,只有魯青在他身后。魯青的回答卻更簡單:我看那輛車人太多,根本就沒想上,在等下一趟車呢。兩個人都忽略了一個細節:是否有人偷走錢包快速離開了?寧先生說他沒看到,魯青說他沒注意。寧先生更擰了:“懲治不了小偷兒,就是你們無能,我得投訴你們!”
高副所長的腦袋都大了。一點兒證據都沒有,怎么懲治啊?真要讓寧先生給投訴了,他面子上過不去呀,而且這話傳出去,就真顯得他太無能了。
這時,值班員給他打來電話:“咱們旁邊撿破爛的那個老頭兒要見你,說是來給你當證人的!”
高副所長一邊往大廳走,一邊腦子里快速閃回。那個老頭兒他很熟悉,但卻不知道姓名,每天都要從這條街上走好幾趟,把垃圾箱里但凡能賣點兒錢的廢品都撿走。他個子不高,面色黝黑,穿著也很破舊,背后背一只蛇皮袋,微微有些駝背。見到他們,總是笑一笑。他看到了什么呢?
見到高副所長,老頭兒笑笑說:“我給你們作個證。那會兒我就想來,可我那袋子太臟,怕把你們的車弄臟了,就回家去放了袋子。沒耽誤事兒吧?”高副所長忙著說:“沒耽誤,沒耽誤,您來得正好。”然后,就領著他來到問詢室。
老頭兒名叫鄭月秋,今年六十八歲,無業,住在另一個派出所的轄區里。鄭月秋說,那個小偷兒顯然是個老手兒,偷完了錢包,馬上就把里面的現金掏出來揣進了自己的錢包里,然后把那個錢包甩進了垃圾箱里,他親眼看到了。最可氣的是小偷兒偷完以后,并沒逃走,還在那兒饒有興味地看熱鬧。他見小偷兒沒有要逃走的意思,他要是沖上去抓,沒準兒倒把小偷兒驚跑了,索性就讓他得意一會兒,先穩到派出所里來再說。于是,他就沒再說什么,回家去放廢品了,然后就趕了回來。
他指認的小偷兒正是魯青。這下高副所長心里就有了底。魯青沒想到有人看到他作案,還敢出來作證。高副所長說:“你不承認也沒關系,失主指認你,又有人證證實你甩包,證據確鑿,照樣拘留你。有話你就到拘留所里再說吧。”
魯青看再抵賴也沒用,就認了。
寧先生領回了自己被盜的物品和現金,馬上夸贊警察有本事。
高副所長回來對鄭月秋說:“大叔,謝謝您啊。您一出來作證,那小子就虛了,全承認了,這就送他進拘留所。”高副所長從口袋里掏出一百元現金,塞到鄭月秋手里:“錢不多,聊表謝意!”
鄭月秋看到那錢,卻像看到燒紅的烙鐵似的,臉色都變了,連連擺著手說:“不、不,你的謝意我心領了,但這錢不能要!事兒辦完了,我就趕緊走了。”說完,他就急急匆匆地走了。高副所長有些不明白了:他一個撿廢品的,按說是最缺錢的。辛辛苦苦撿一天,未必能賣一百元錢。自己掏腰包對他表示感謝,這錢可以說是來得光明正大,他怎么反倒不要呢?
2.
周六這天,高副所長趕去看他老爸。他老爸名叫高振遠,今年快七十歲了,原來也是分局的民警,還曾在幾個派出所當過所長,現在退休在家頤養天年。他住的房子,是公安局那會兒分的,戶型很小。高副所長后來要娶妻生子,就貸款另買了房子。城區的房子價高,他只好在遠離市區的偏僻地方買了,離著老爸這兒就遠了,平常難得來一趟,只有周末才能過來。
他遞給老爸兩瓶酒:“爸,您嘗嘗。這酒新鮮啊,市面上很少見到。”
高振遠好喝個酒,每天兩頓,好在他知道自律,每頓只喝二兩,絕不超量。貴酒他也舍不得喝,只喝二鍋頭。高副所長時常買些好酒過來,就算給他解解酒癮,也是聊表孝心。高振遠接過酒來看了看,嘆了口氣說:“這酒看著不錯,也挺貴的吧?可惜我沒那口福啊。我喝不了醬香的,一喝就頭暈,只能喝清香的。你拿回去自己喝吧。”高副所長說:“我喝不了這么高度數的。”高振遠想了想說:“有工夫送給你鄭叔叔吧,他能喝。”
高副所長還是頭一回聽到老爸提到鄭叔叔,不禁問道:“鄭叔叔是誰呀?”高振遠輕描淡寫地說:“我以前的一個同事。”高副所長說:“沒聽您說過。”高振遠說:“我們來往不多了。”高副所長又想問,來往不多,怎么想著把這么好的酒送給他呢。但還沒來得及問,女兒就跑過來,非要讓他帶著出去玩兒。高振遠就笑呵呵地說:“你們出去逛逛吧,我們在家里準備飯。”
傍晚,他們要走的時候,高振遠把那兩瓶酒遞給他,又遞給他一張寫著鄭叔叔家地址的紙條,讓他一定要把酒送過去。
第二天上午,高副所長到分局去開會,散會后,他就繞了個彎兒,循著地址去找鄭叔叔家。
那里是一片棚戶區,都是老舊的平房,街道很窄,進不去車。他拎著兩瓶酒走進了小街道,一路打聽著來到鄭叔叔的住處。住這里的窮人多,撿廢品的也不少,東西都堆在門口,又臟又亂,還散發著臭氣。但鄭叔叔家卻不一樣。他撿來的廢品,都分門別類地放好,擺得很整齊,也沒有臭味。鄭叔叔家只有一間房子,門兩側又擺滿了廢品,只剩窄窄的一道縫隙,進門都得側著身子。高副所長先叫了兩聲,沒人應。
旁邊有戶人家開了門,一個中年婦女站到門口,看到他先愣了一下,然后問他:“警察啊,你找誰呀?”高副所長問她:“鄭叔叔是住在這兒吧?他家沒人啊。”中年婦女說:“是老鄭。大白天的,他撿廢品去啦。你找他有事兒啊?”高副所長說:“我給他帶了兩瓶酒來。麻煩你轉交給他。”中年婦女說:“沒問題。你放我這兒吧。他一回來我就給他。”高副所長把酒交給了中年婦女,心里納悶,老爸的同事,怎么會撿上廢品了呢?
3.
傍晚,快下班的時候,高副所長忽然接到值班員的電話,說鄭月秋來了,要見他。
高副所長想,一定是那天沒要錢,后悔了。他掛了電話,從錢包里抽出一百元錢,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來到大廳,卻見鄭月秋正站在一個角落里望著他,手里赫然提著那兩瓶酒!
高副所長一時愣在那里。難道鄭月秋就是老爸的老同事?他這個拾荒老人,又怎么和退休老干部扯得上邊兒呢?就在他愣神兒的工夫,鄭月秋走到他跟前,問道:“高所,這酒是你送我的吧?”高副所長說:“是啊。”鄭月秋說:“你的酒我不能要。”說著,就把酒塞回到他手里。高副所長忙著說:“鄭叔叔,你想錯了。這酒是我老爸送給你的。我爸,高振遠,你記得吧?”鄭月秋卻冷然說道:“誰的酒我都不能要!”說完,轉身走了。
高副所長愣在那里。這是怎么回事兒啊?老爸說跟他是老同事,要送給他兩瓶酒,人家卻不肯要,給送回來了。他馬上給老爸打了電話,把事情說了。高振遠生氣地說:“你再給他送去!他就是不收,也得給你一個不收的理由!”高副所長點頭應了,心里暗笑。怪不得兩個人還算是朋友,原來都這么倔。要擱在別人,肯定不會這樣。
下了班,他再次趕往鄭叔叔家。看到鄭月秋正和收廢品的小販爭執著。高副所長一聽爭執的內容,更是驚得瞠目結舌。原來,鄭月秋撿到了一個很精美的酒瓶,當工藝品擺在屋里欣賞。剛才,他賣給小販一些廢品,小販拿出張整鈔來,他進屋去給小販找零錢,同時也邀請小販進屋去喝杯水。小販看到了那個酒瓶,要花三十元錢買下來,鄭月秋不肯賣。小販一路把價格抬到了五十元,鄭月秋還是不肯。這時,高副所長來了。鄭月秋就對小販說:“別爭了。你就是出一千塊,我也不賣這個酒瓶子。”小販瞟了他一眼說:“你這個老頭兒,真是怪啊,有錢都不賺。要擱在別人,巴不得呢!”說完,就氣哼哼地走了。
高副所長問他:“叔啊,你咋就不賣那個酒瓶?”鄭月秋說:“誰知道他買了這個酒瓶去干什么呢。要是裝了假酒去害人,我不就成了幫兇嗎?那錢不光咬手,還能咬人的心啊。”
鄭月秋把高副所長拉進屋,給他倒了一杯茶,然后就坐到他對面,看著他,緩緩地問道:“你知道鄭叔叔怎么犯的罪嗎?”高副所長驚問道:“鄭叔叔你犯過罪?”鄭月秋點了點頭,又抬眼望了望自己的屋子,重重地嘆了口氣說:“要是沒犯罪,我也該跟你爸一樣,享受著天倫之樂呢。可這一犯罪,就全毀了。”
鄭月秋說,早年他曾是高振遠的同事和要好的朋友,也是一名令人敬畏的警察,后來犯了罪,被抓起來判了刑,等他服完刑出來,已經一無所有了。老婆帶著孩子改嫁了,房子和家里的一切都被賣了給他還款。他也被“雙開”了,成了無業游民。還是政府救濟他,給他辦了低保,又給了他一間廉租房。他也沒啥本事,就是起早貪黑地撿廢品,賣幾個小錢,維持生計。
講完了這些,他又重復了剛才那句話:“你知道鄭叔叔是怎么犯的罪嗎?”高副所長搖了搖頭。他真不知道。老爸也從來沒跟他說過鄭月秋犯罪的事。鄭月秋重重地嘆了口氣,慢慢地說:“還不就是從一瓶酒開始的嘛!”
原來,鄭月秋那時正在拘留所里當看守。逢到他值班的時候,就負責看守一個通道,那里有十間拘留室,關押著百十名犯罪嫌疑人。親戚朋友們都知道他干著這個活兒。后來就有人托到朋友,請他給號兒里的親人一點關照,無非就是借機讓他出來一會兒,多放會兒風,抽根兒煙。這當然算不得什么大事兒。后來,有人就托朋友送給他一瓶好酒。好酒當然好喝,他也就開了這個口子。再有親戚朋友送酒來求他照顧照顧里面的人,他都來者不拒。也就是從這一瓶酒開始,他看到了來錢的門路,開始是來者不拒,后來就跟犯罪嫌疑人的家屬要,而且膽子也越來越大,早先還是要酒要煙,后來就要錢,直到東窗事發。
誰能相信,一瓶好酒毀了他的一生啊。他恨透了酒,也忌了酒,幾十年了,他滴酒不沾。當然了,不是自己的錢,他也躲得遠遠的,一分都不要。所以,高副所長給他一百元錢的時候,把他嚇得夠嗆,堅決不肯收。
講完了自己的故事,鄭月秋盯著高副所長,問道:“你說,我跟你爸的日子比起來,誰過得好?”問完他重重地嘆了口氣說:“我當拘留所副所長的時候,你爸還是個普通民警呢。我要是不犯罪,興許真能干出點兒名堂來。就是跟他一樣,也能踏踏實實地退休,老婆孩子都不走,我也能享受天倫之樂,又怎么會過得這么凄慘?我不怪他們,只怪我自己。人這一輩子啊,走錯了一步,就再也回不了頭了。”
高副所長無言以對。
他不知道該怎么安慰鄭叔叔,也無從安慰。他也知道,鄭叔叔是不肯收那兩瓶好酒的。這是鄭叔叔的人生底線。他默默地提起那兩瓶酒,跟鄭叔叔告辭。鄭叔叔只是點了點頭,還沉浸在悲傷里,都沒送他出來。
4.
周六,高副所長又帶著老婆孩子看老爸。高振遠見到他,目光竟先掃向他的鞋,問道:“唉,你怎么又穿上這雙舊鞋了?上次穿的那雙新鞋,你說特別舒服,我在網上查了一下,要四千多元呢。”高副所長不好意思地說:“我那會兒昏了頭了,花那么多錢買雙鞋,真后悔死了。可鞋子穿過了,又退不了,只好刷干凈,放著,留個紀念吧……”
高副所長又跟老爸說起他給鄭月秋送酒的事。高振遠臉色凝重地嘆了口氣說:“挺聰明的一個人,要不是被財迷了心竅,肯定比我有出息。他那賊心眼兒,可多了。那回聽我說起你穿這么貴的鞋,他嚇了一跳,說想辦法敲打敲打你,讓你別再走他的老路。”高振遠說到這兒,才發覺自己說走了嘴,忙著打住了話頭兒。
高副所長一愣,接著臉也紅了。兩個月前,他幫人家辦了件事兒,人家送了他一個購物卡。他覺得沒啥大事兒,就收下了。然后,就買了這雙名貴的鞋。聽了鄭叔叔的故事后,他害怕了,把錢退給了人家,也把鞋收起來了。他記得鄭叔叔說過的那句話:人這一輩子啊,走錯了一步,就再也回不了頭了……
(作者系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龍橋派出所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