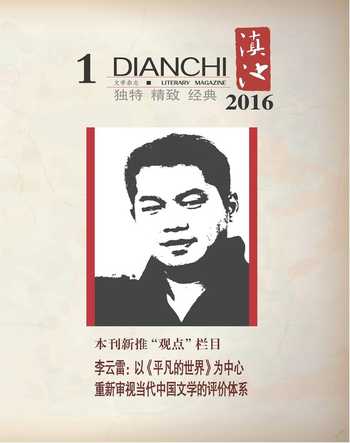重新審視當代中國文學的評價體系
電視劇《平凡的世界》熱播,又引起了關于路遙和現實主義的廣泛討論。路遙的長篇小說《平凡的世界》在 1988年完成,但這部現實主義長篇巨制在當時并沒有得到文學界的足夠重視,在文藝思潮風云變幻的 1980年代,現代主義、先鋒派等文藝思潮風頭正勁,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審美規范,在這一審美規范的視野中,“現實主義”是一種陳舊、落后、保守的寫作方式,而只有形式、技巧與敘述方式的探索,才是“創新”。在這樣的時代潮流中,路遙堅持自己的創作方式,他在小說《人生》獲得巨大成功之后,潛下心來,以 6年的艱苦勞動,最終完成了《平凡的世界》。在路遙的隨筆《早晨從中午開始》中,我們可以看到路遙創作這部作品的艱辛過程,而在厚夫新近出版的《路遙傳》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發表、出版的曲折故事。在以現代主義為新時尚的文學界,這部作品所遭到的冷遇可想而知,而路遙也為這部作品耗盡心力,于 1992年英年早逝,年僅 43歲。
《平凡的世界》雖然受到 1980年代主流文學界與評論界的忽視,但卻得到了讀者的廣泛歡迎,在幾項讀者調查中,都顯示《平凡的世界》是“當代大學生最喜歡的文學作品”,或者“20年內對被訪者影響最大的書”。我們可以看到,《平凡的世界》自問世以來,就在讀者中有著持久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是穩定的,而且在逐步上升。最近,《平凡的世界》“專家冷,讀者熱”的奇特接受現象,也引起了文學界的關注與反思,不少學者與評論家都認為,應該重新認識《平凡的世界》的文學與思想價值。在我看來,重新認識路遙與《平凡的世界》,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以趙樹理、柳青為代表的“人民文學”傳統,重新思考現實主義的精神,重新思考當代中國文學的發展方向與評價體系。
1.路遙與“人民文學”傳統
路遙在他的小說與隨筆中,多次表達了對柳青的尊重。柳青不僅以《創業史》等經典作品著稱于世,而且他長年扎根在長安縣皇甫村的經歷,也在文學與生活、文學與人民的關系等方面,對路遙這一代作家,產生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柳青對路遙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在我看來,至少有以下幾點:扎根生活與人民,在對生活的長期觀察與思考中構思與創作自己的作品;以典型人物與典型的社會關系為核心,敏感地捕捉一個時代及其精神的變化,并以史詩性的形式呈現普通民眾的生活與情感;鍥而不舍的文學追求,以及勇攀高峰的執著精神,柳青在病榻上仍在修改《創業史》第二卷,而路遙為創作《平凡的世界》,也幾乎累垮了身體。柳青只是“人民文學”傳統的一個突出代表,趙樹理、周立波等作家,在 1950年代也都回到故鄉,尋找到一塊根據地,長期深入地體驗生活,在與普通民眾的接觸了解和共同生活中,才創作出了《三里灣》、《山鄉巨變》等經典作品。
當然在 1980年代,“人民文學”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路遙和柳青也有所不同,如果我們將《平凡的世界》中的孫少平、孫少安,與《創業史》中的梁生寶相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和孫少平、孫少安相似,在梁生寶身上也有著積極的奮斗精神,但不同的是:(1)梁生寶不是“個人奮斗”,而是作為一個小集體的帶頭人,帶領村民“集體奮斗”;(2)梁生寶奮斗的方向不是離開農村,到城市里去,而是和鄉村融為一體,在大地上建功立業;(3)梁生寶的奮斗目標也不是個人的“發家致富”或“成功”,而是帶領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于孫少安、孫少平的“個人奮斗”,梁生寶這樣的“社會主義新人”及其“集體奮斗”,其實更典型地體現出“人民文學”的人民性,而《平凡的世界》在 1980年代的文學環境中繼承了“人民文學”的傳統,而又在某些方面做了變異。或者說,路遙小說中的人民性,處于一種歷史的過渡狀態,他小說中的“人民性”與柳青小說中不同,柳青小說中的人民性是扎根于鄉土的,而路遙則要從鄉土中走出,但他的小說中仍然是有人民性的,而在 1990年代新寫實小說之后,我們看不到“人民性”,看到更多的是“個人”及其“日常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人民性”要有一種歷史的理解,只有在歷史的視野中,我們對“人民”轉化為“個人”的過程才能有深刻的認識,而路遙正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上。
現在我們一般都說,1980年代對路遙與《平凡的世界》評價不高,但這只是一個方面,在1980年代也有一些評論家對之有較高的評價,否則《平凡的世界》也不可能獲得茅盾文學獎。對《平凡的世界》評價較高的就是秦兆陽、朱寨等老一代的批評家,而這些批評家恰恰在新時期延續了“人民文學”的傳統,他們與當時提倡現代主義的批評家構成了一種對立。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1980年在秦兆陽主持的《當代》雜志刊發,并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平凡的世界》最初如果先到秦兆陽手中,或許就不會經歷發表與出版的波折了。
當然秦兆陽這一代批評家也有他們的局限性。秦兆陽在 1990年代初有一個著名的事件,就是他把張煒的《九月寓言》退了稿,何啟治在他的文章中回憶了這一事件,并把他自己和周昌義、洪清波的稿簽都放在了文章中,也把秦兆陽的稿簽放上去了,我們比較一下可以看出,秦兆陽不能夠接受《九月寓言》這樣的現代主義作品,有他的局限,也有他的道理,這是他現實主義理論的“邊界”之外的作品,但在 1950年代秦兆陽受批判,是因為《現實主義——廣闊道路》,這篇文章批評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秦兆陽“現實主義——廣闊道路”的邊界,一個邊界是他不能接受現代主義,另一個邊界是他不能接受教條化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這兩個邊界之間,我們可以看到,秦兆陽的現實主義理念是比較寬泛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平凡的世界》被主流文學界忽視,秦兆陽將《九月寓言》退稿,這兩個事件可以讓我們看到 1980年代以來文學的復雜性,也可以讓我們看到“人民文學”傳統新時期以后復雜文學環境中的挫折與延續。這一復雜的問題還有另一個例子,比如《白鹿原》在 1997年獲得了茅盾文學獎,著名文藝理論家陳涌在他的評論文章中,以“真實性”與“傾向性”這樣的現實主義理論范疇,對《白鹿原》做出了肯定,這也讓我們看到老一代文藝理論家仍以“人民文學”的傳統與標準,對新的重要作品進行評價,這也可以說是“人民文學”在新時代的一種延續與發展。
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對 1980年代“純文學”的反思,以及“底層文學”等新的文藝思潮的興起,對“人民文學”傳統有了新的認識。我們可以看到,當下不少青年寫作者仍將《平凡的世界》作為重要的思想藝術資源,但當下的寫作者來說大多沉浸于“個人”與“日常生活”之中,對此之外的事情則喪失了表達的興趣、愿望與能力,這是我們今天重讀《平凡的世界》時,有必要反思的。我們應該意識到,“個人”及其“日常生活”都處于歷史之中,并且是歷史發展變化中的一部分,尤其在當代中國迅猛的發展與劇烈的變化之中,我們的“個人”與“日常生活”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也不是從來如此的,我們只有在歷史變遷與社會結構的對比中,才能認識到此時此刻的“個人”、“日常生活”的相對性與有限性,也就是說,我們的“個人”與“日常生活”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不同社會階層的“個人”與“日常生活”也是不同的,認識到“個人”與“日常生活”的相對性與有限性,我們才有可能走出這種觀念的限制,在一個更大的視野把握中國經驗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并將之作為自己寫作的動力。魯迅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我們只有打開封閉的視野,將整個歷史與當代經驗視為個人創作的對象、對話的目標,才能將他人的痛苦轉化為自己的痛苦,才能認為歷史的發展與“個人”有關,才能具有更為寬廣的胸懷與更為高遠的追求。今天重讀《平凡的世界》,可以讓我們從“人民性”看到“個人”的局限,也可以讓我們從“中國經驗”看到“日常生活”的不足。
2.“現實主義的勝利”
《平凡的世界》的成功,可以說是“人民文學”傳統的勝利,也是現實主義的勝利。現實主義在 20世紀初傳入中國,在中國文學界有著長久而深遠的影響。現實主義不是簡單的寫實,在現實主義背后有一整套現代性的思想與世界觀,以及科學的認識論與創作方法。現實主義要寫生活中的人物、故事與細節,但更重要的,是要寫出作者對生活的認識與理解。優秀的作家,總是能將對世界的整體理解融入到作品之中,在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狄更斯的筆下,我們看到的是不同的生活世界,也是作家對生活的不同理解與思考,在魯迅、茅盾、老舍等作家的作品中,也是如此。
所謂現實主義精神,就是作家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不過這種求真,既包括作家對生活細節的觀察與描摹,也包括作家對時代與世界的整體認識與判斷。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對時代做出清醒而深刻的分析,因為這超出了個人經驗的范疇,需要思想的穿透力與理論的抽象能力,以及整體性的藝術提煉能力。在這個意義上,現實主義并不只是與現實相關,也與歷史與未來相關,與我們對世界的整體理解相關。
在 20世紀文學史上,圍繞現實主義曾產生過無數爭論,如果粗略地概括一下,我們可以發現,在 1920—40年代,現實主義在與其他藝術流派的論爭與競爭中,逐漸成為了文學界的主流;在 1950—70年代,主要是現實主義尤其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內部的爭論;在新時期以后,在現代主義諸種思潮的沖擊下,現實主義逐漸被邊緣化。應該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在實踐中的僵化,是新時期現代主義興起的重要原因。但在今天,如果我們從一個更大的視野來看,在19世紀歐洲批判現實主義的高峰之后,20世紀歐美的現代主義與蘇聯、中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都是超越批判現實主義的努力,現代主義主要是以抽象的方式表達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絕望、頹廢與掙扎,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則以一種建構的、樂觀的方式,描繪當代生活,勾畫理想的未來。在 1980年代,我國主流文學界簡單地拋棄現實主義,熱情擁抱現代主義,雖然有可以理解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種態度與情緒,而缺乏理論上的分析與辨別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他們無法認識《平凡的世界》的價值,反而是秦兆陽、朱寨等老一代理論家對之做出了高度的評價,現在來看,無疑秦兆陽等人的分析與判斷更具說服力。
如果仔細思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路遙的《平凡的世界》是現實主義,但并不是一種批判現實主義,而是一種建構性的現實主義,是一種有方向、有理想的現實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它又與 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一樣,《平凡的世界》中所描繪的,不是一種比較明確或者堅固的理想,或者特別急迫的理想,而是在懸置了理想或將理想抽象化之后,仍朝那個方向努力。所以我覺得《平凡的世界》里面的這種有理想的現實主義,正是其樂觀的基調、理想的基調存在的根本,也是他獲得老一代評論家認可,包括能獲得茅盾文學獎重要的因素。現在還能不能再產生《平凡的世界》這樣的作品,或者說能不能再有一種有理想的、有方向的現實主義?這取決于現實及對現實的理解與總體感受。雖然路遙的小說也有悲劇感,但整體上是向前的,底色是溫暖的,是看得見希望的,在這個意義上,重建一種有理想的現實主義,《平凡的世界》可以給人以啟發。
在《平凡的世界》中,既有現實主義精神,也有浪漫主義情懷。為了創作《平凡的世界》,路遙翻閱了十年的《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及多種地方報紙,并親自到煤礦等地體驗生活,為此甚至勞累過度,充分顯示了一個作家的孜孜不倦的求真精神。但在小說中,也處處充溢著浪漫主義情懷,小說中對孫少平、孫少安在艱難生活中執著奮斗精神的描繪,對孫少安與田潤葉、孫少平與田曉霞浪漫愛情的描述,都深深地打動了讀者的心。不過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評論者認為,一個農家子弟與縣領導干部女兒的愛情不真實,但在小說所講述的 1975—1985年間,我國的貧富與階層分化并不巨大,這樣的故事還是可信的,并能讓人感到一種浪漫主義的美感,而這一問題的提出,則折射出了當代社會中所存在的問題,這同樣是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的。現實主義精神并不排斥浪漫主義情懷,在現實主義理論的結構內部,就包含著對作家主體性的尊重,包含著對未來的想象與召喚,包含著虛構與幻想的空間。如果我們不在所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的進化鏈條上理解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而將之作為把握世界的不同藝術方式,那么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的結合便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說現實主義更注重客體與客觀性,以科學的方法與精神追求真實,那么浪漫主義則更注重主體與主體性,強調以作家的思想、精神與情懷觀照這個世界,從中我們可以更多地看到作家的才情與想象力,只有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主義情懷相結合,才能在主客體的融合中呈現出一個完整的藝術世界。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現實主義應該汲取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探索的一些成果,比如在經歷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洗禮之后,我們不會再簡單地認為,一個“完整”的主體可以“透明”地反映現實,對于何謂真實、如何抵達真實等問題,現實主義可以在汲取新的探索之后,做出更深刻的表達。同時,現實主義要對時代的“新穎性”有充分的敏感,現實主義要有“發現”,要有獨特的視野、眼光和藝術敏感點,而不是一談現實主義,就陷入了千篇一律的故事及其講法。在我看來,當前中國文學界最需要的是“清醒的現實主義”,對于現實,我們需要的并不是現在的“批判”或直接將其視作“荒誕”,也不是某種單一的理念或方法,而是要以一種清醒、理性、冷靜的態度,對當代中國的現實做出自己的觀察與思考。“清醒的現實主義”是一種態度,也是一種方法。面對復雜的世界或未知的因素,重要的不是急切表明態度,而是以清醒的態度去探索,去思考,去把握;重要的也不是以個人的主觀想象將復雜的世界簡單化,而是在充分認識到世界的復雜性之后,以新的方式為之賦形。在這方面,重讀路遙及其《平凡的世界》,并將之歷史化與相對化,可以讓我們對現實主義理論有更深刻的認識。
3.當代中國文學的評價體系
在最近談到《平凡的世界》時,李陀指出它是對八十年代文學的全面挑戰,“無論路遙有意無意,《平凡的世界》的寫作在客觀上,實際上是對 80年代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一個全面的挑戰——說它全面,是因為這個挑戰首先是針對 80年代以‘朦朧詩、‘實驗小說、‘尋根文學為代表的新寫作傾向的挑戰,這是很明顯的;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路遙的寫作同時也是對這些新潮寫作之外的其他各種寫作傾向和潮流的挑戰,這既包括對那一時期也很火的‘改革文學的挑戰(比較一下《新星》和《平凡的世界》),也包括那一時期以‘寫實為特色的諸家小說寫作的挑戰(比較一下《綠化樹》和《平凡的世界》),甚至我以為他也是對‘陜軍作家群體的挑戰(比較一下陳忠實、賈平凹和路遙的寫作)。”注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 1980年代的美學標準,以及挑戰這一標準的《平凡的世界》所帶給我們的啟示。必須承認,我們現在的文學深受 1980年代文學的影響,1980年代構建的美學觀念與文學體制在今天仍處于支配性的地位,塑造著我們的文學觀念與關于文學的想象。在 2000年左右雖然有反思“純文學”的倡議,但一方面“純文學”并不足以涵蓋 1980年代文學的復雜性,另一方面這一反思很快陷入何為“純文學”等理論爭辯,并沒有得到深入的展開。在我看來,1980年代文學建基于一系列文學命題與文學觀念之上,這些命題與觀念構成了一種“文學范式”,一種對文學的特殊理解。這樣的“文學范式”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的,而只是特定歷史時期與特定文化氛圍的產物。在今天,我們既應該認識到這一文學范式的歷史合理性,也應該認識到其局限與不足,在一種新的語境中沖破舊日觀念的束縛,從而使文學獲得新的生機與活力。
在我看來,構成 1980年代“文學范式”的命題與觀念主要有:(1)文學的“主體性”;(2)文學的“向內轉”;(3)“新的美學原則”;(4)“寫什么”與“怎么寫”;(5)“創新”;(6)先鋒,或“現代主義”;(7)“文明與愚昧的沖突”;(8)文學要“走向世界”。以上這些觀念構成了 1980年代“文學范式”的不同側面,形成了一個系統性的文學觀念集合體,也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文學觀念的集體無意識。
比如,文學的“主體性”與“向內轉”的觀念,主要處理的是文學與現實的關系,強調文學相對于(政治)現實的“獨立性”,強調文學由關注現實到關注“主體”的轉變。如果在文學史的脈絡中梳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觀念與五四文學中的“為人生”、以及左翼文學重視生活的傳統構成了一種對話關系,尤其是對《講話》中“生活是文藝創作的唯一源泉”的一種反駁。我們應該看到,這樣的文學觀念有其歷史合理性,在“文革文學”的公式化、概念化之后,強調創作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強調藝術的獨立性與多元化,是一種時代的選擇,只有如此,才能使文學走上更加開闊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這一觀念如果走到極端,也會為文學帶來傷害。30年來,我們文學的弊端大抵在此,比如強調“向內轉”而割裂了文學與現實、世界的連接,文學似乎不能表現“自我”之外的事情,從強調“日常生活”到“私人生活”,再到“下半身寫作”,讓文學的路越走越窄。而在這 30年間,中國與世界都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一變化并沒有納入作家們關注的視野,他們無法以一種開闊的視野把握這一巨變。
在 1980年代的審美規范中,“為誰寫作”并不重要,當時更引人關注的問題是“寫什么”和“怎么寫”這個命題,在當時的語境中,這一命題的提出本身就具有傾向性——即相對于“寫什么”,“怎么寫”是更加重要,也更值得關注的問題。我們不在這里展開對這一對命題的分析,只是想指出,無論是“寫什么”,還是“怎么寫”,都是寫作進入構思階段時期的問題,并沒有解決作家寫作上第一推動力的問題——即為什么寫作的問題。一個作家可以懵懂地開始寫作,但在他的創作與成長過程中,遲早總要面臨為什么寫作這一問題,這也是決定一個作家能否持久寫作的一個重要因素。對于為什么寫作的問題,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有不同的回答,有的說是要出人頭地,有的說是要改變命運,有的說是要展現個人的才華,還有的說是為了讓朋友們更加喜歡自己——當然其中也不乏開玩笑的因素。但是我們分析各種回答,可以看到,作家除了“個人”的因素之外,并沒有在根本上解決為什么寫作的問題,而他們所說的“個人”因素也并不是可以持久寫作的穩定動力,比如當改變命運、出人頭地之后,當個人才華充分展現之后,寫作的意義又何在?
現在看來,1980年代我們的文學中發展出來的是一種精英化、西方化、現代主義式的“新的美學標準”,但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以這樣一種美學標準,很難將當代中國人豐富復雜的經驗與情感容納進去,現在我們處于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有必要對這樣的標準進行反思,從而促進中國文學的發展。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談到,“中國文學的偉大不在于能否得到外國人的承認,而在于能否得到本國讀者的歡迎,能否將中國的獨特經驗表達出來,能否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在我看來,《平凡的世界》之所以可以挑戰 1980年代文學,恰恰在于它跳出了精英化、西方化、現代主義式的美學標準,更貼近中國經驗,更貼近中國人的欣賞習慣,因而也更能為中國的普通讀者接受。
當我們反思精英化、西方化、現代主義式的美學標準的時候,并不意味著要走向大眾化、中國化、現實主義的審美規范,也不意味著要簡單地回歸“人民文學”,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有必要超越簡單的二元對立,將“人民文學”與“八十年代文學”這兩種文學傳統相對化,在融匯創新中創造出新的美學。這種新的美學應該表現出當代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應該具有高度的藝術性,應該是一種新的創造。
我們所說的“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也不是本質化的,而是在歷史中發展變化的,我們的文學要扎根于當代中國的現實之中,但也要有歷史的眼光與世界的眼光,只有具備了歷史的眼光,我們才可以在歷史的發展與變化中發現當代經驗的獨特性;只有具備了世界的眼光,我們才能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中發現中國經驗的獨特性。我覺得以這樣的眼光扎根于當代中國的現實,我們就有可能創造出當代的經典。我們未必要像《平凡的世界》那樣寫,而要像路遙在他的年代寫作《平凡的世界》那樣創作。
注:《北京青年報》2015年 03月 13日,《李陀:〈平凡的世界〉是對 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的挑戰》
李云雷,1976年生,山東冠縣人,200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馬文所副所長、《文藝理論與批評》副主編,現任職于《文藝報》。在《文學評論》《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發表論文與評論上百篇,著有評論集《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重申“新文學”的理想》《新世紀底層文學與中國故事》,小說集《父親與果園》等。曾獲 2008年“年度青年批評家獎”“十月文學獎”、《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等,部分文章曾被譯為英文、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