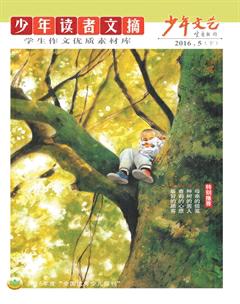感恩是讓心靈之美回到原地
段奇清
不久前,家住休斯頓梨城的艾德·登茨勒收到一張讓他頗感納悶的明信片。
因為這明信片上的背面用手工整地寫著英文:“堅強的人能拯救自己,偉大的人能拯救他人。為1944年感謝你。中國人。”明信片的正面是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一些美國和中國軍人聆聽著一位美國大兵用小提琴伴奏兩個中國軍人演奏傳統弦樂器二胡。明信片寄自中國,郵戳日期為2011年8月27日,背面還寫有登茨勒不認識的漢字。
這位88歲二戰老兵,1944年隨美軍著名的志愿軍部隊麥利爾突擊隊參加過緬甸戰役,1945年又服役于中國戰區作戰部隊。但他并不明白為什么會于60多年后突然來了這么一張明信片。“我想象不出它是何人寄來的?”困惑之余,登茨勒決心找出寄明信片的人是誰。
登茨勒詢問了歷史學家兼麥利爾突擊隊聯誼會主席羅伯特·帕薩尼西,以及幾年前因為一個中國歷史研究項目曾采訪過登茨勒的美國研究員帕特·盧卡斯,可終無結果。
這時,一位在美國宇航局會說中文的工程師同事告訴他,明信片上他所不認識的漢字意為“國家記憶”。其他的事情這位工程師就說不上來了。
盡管這樣,登茨勒卻高興異常,因為他想到:既然是“國家記憶”,代表著“國家記憶”的重要新聞媒體一定會有過報道。于是,登茨勒便致電《休斯敦紀事報》。果然,事情有了突破性進展。
《休斯敦紀事報》一名記者做了一些互聯網偵探和搜索后便對登茨勒說:中國深圳日報網上曾有一篇文章報道說,中國廣東省的深圳外國語學校的學生曾決定寫明信片感謝幫助中國抵御日本侵略的美國二戰老兵。這些學生是在2011年夏天參觀二戰照片展時想出這個主意的。明信片上的照片都是展覽的照片,已匯集成冊,題名為《國家記憶》。
中國學生的感謝一下子讓登茨勒的思緒回到了70多年前。他10歲那年,在一家工廠做工的父親突然得了重病,幾個月后不治身亡。安葬父親后,沒有工作的母親面對3個嗷嗷待哺的子女,不禁哀愁萬分,她不知過了今天明天能否有什么讓孩子們充饑。在這時,有一位中國移民盡管自己收入微薄,可硬是省吃儉用,傾心支持他們家。二戰時,當美國對日宣戰后,已是成年的登茨勒立即參軍來到中國。
“哈哈哈!這真是太棒了!”當弄清事情的原委后,登茨勒笑了,“我希望寄來明信片的中國學生知道我有多么感激他們的這份心意。這對我真是一種莫大的幫助,我前些時剛患中風,回憶過去那些我以為自己已經記不起來的事情,將有助于我的康復。”
現年87歲的歷史學家兼麥利爾突擊隊聯誼會主席羅伯特·帕薩尼西對這件事有一定了解,他對登茨勒說,據他所知,至少有4個其他突擊隊老兵和他們的后代收到了相似的明信片,圖片和文字信息各異,但結尾感激的話語卻完全是一樣的:“為1944年感謝你。”
可不是,郵政確認:另一位家住紐約的86歲的老兵杰伊·坎貝爾,也收到一張明信片,上面的文字同登茨勒的一樣,不過,照片畫面是一個豎起大拇指的中國男孩。堪貝爾當年參加麥利爾突擊隊在緬甸作戰,并且獲得三顆紫星獎章。
“那些老兵中很多人都不大愿意談論往事。”杰伊·坎貝爾的女兒戴比·坎貝爾說,“父親就只是對我說過,‘如果我告訴你我們當時的所見所聞,或說是噩夢般的經歷的話,你肯定會把我當瘋子看待。所以我料想當年的情形一定是非常惡劣與殘酷的,父輩們的付出是非常巨大的。”
得知明信片是一名中國學生寄來的后,杰伊·坎貝爾很高興。“哇噻! ”他說。“有意思,不是嗎?哇噻!哇噻!回到原地” 坎貝爾所說的“回到原地”,是說感恩讓人的精神之美回到原地。
原來,杰伊·坎貝爾的父親出生于中國,在日本占領滿洲里后被日本鬼子殺害。他們家庭遭此大難,幸虧有一些中國人伸出手來救助,他們一家人才得以度過那段凄風苦雨的日子。所以美國一經對日宣戰,他立即報名參軍,并要求去太平洋前線作戰,既是為父報仇,也是要感謝中國人。”
發表在中國深圳日報網上的那篇文章中還說,提供二戰期間在中緬印戰區服役過的老兵姓名和地址的是美國前將軍約瑟·史迪威的孫子約翰·伊斯特布魯克。這篇文章還引用一個名叫梅怡的老師的話:這些寄往美國的明信片證明了在中國,年輕人是不會忘記歷史的。“通過這種方式,學生們既表達了他們的感激之情,同時也知道中國的和平來之不易,大家必須為之奮斗。”
感恩是讓心靈之美回到原地,在世界各國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下,感恩的情愫一定會在人們的心原永駐,由此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馮國偉摘自《青春期》2014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