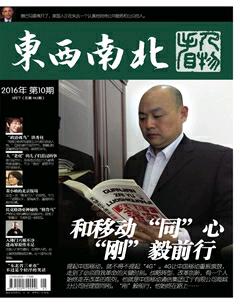洋醫院中國生存記
盧伊+孫楊
洋醫院在大陸發展仍面臨諸多現實困難,這些體制外的“鯰魚”需更為自由的發展空間。
家住北京東三環燕莎附近的李潔發現8個月大的女兒發燒了,與其他家長心急火燎趕往兒童醫院掛號不同,她第一時間是給小區附近的一家英式家庭診所打電話預約門診。
幾十分鐘后,收拾妥當的李潔抱著女兒出現在診所,無需再掛號,母女倆直接被安排到一間獨立的診室。診室被布置得像是一間兒童房,堆放著玩具的矮桌,每個桌角都被細心地包了起來,防止小患者在玩耍時磕傷。在等待期間,先有護士進來,為寶寶登記資料、量體溫、簡單問詢病情,隨后主診醫生進來診治。
因為是長期固定會員,醫生立刻調出孩子過往病例和治療情況瀏覽,然后開始對心肺、嗓子、耳朵、手腳等全身各部位逐一查體,詢問最近的起居、飲食、情緒等方面情況。經過15分鐘的檢查和問詢,醫生診斷孩子是普通的病毒感染引起的發燒,僅需服用簡單藥物即可;又花費約5分鐘的時間,大夫向李潔詳細解釋了如何服藥和護理,待李潔支付了610余元的就診費用(其中診療費600元,藥費10余元),母女倆便離去了。
整個看病過程中,李潔母女始終都沒有離開過診室,所有服務都是由醫護人員完成的。沒有印象中焦急等待的驗血、影像檢查、輸液建議,只有醫生細致耐心的查體、提問和解答,這些都與傳統公立醫院的就醫體驗大相徑庭。
自1989年大陸開放外資辦醫,洋醫院在大陸發展已經整整27年,它們逐漸成為掌握先進技術和優質服務的高端醫療的代名詞,并作為醫改深水區中“鯰魚”,被寄予同公立醫院競爭醫療市場,破解醫改難題的期望。
然而,受醫療服務理念難被接受、配套政策未能完善等因素限制,洋醫院在大陸發展仍面臨諸多現實困難,這些體制外的“鯰魚”需更為自由的發展空間。
外國和尚來念經
對許多外資醫院的創始人而言,他們不僅看重大陸醫療市場中的巨大商機,更看出其中沉疴,他們開始希望以老外特有的視角幫中國人搭建新的平臺解決問題。
和睦家醫院創始人李碧菁是最早一批介入中國醫療市場的外國人。在進入中國的前10年里,李碧菁一直幫助公立醫院引進海外醫療設備,并提供中外同行交流學習的機會。和公立醫院打交道的次數多了,李碧菁逐漸發現了中國醫療系統的一個怪圈:中國不乏優秀的醫生,但患者依然頻頻抱怨就醫環境、服務水平和安全條件。一個想法油然而生:自己完全可以為中國消費者搭建一個全新的平臺,為他們提供更好的就醫環境和醫療服務體系。
從開始構思到第一家和睦家醫院落地,李碧菁花了整整7年時間。發展至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青島都設立了和睦家醫院和康復診所,它們采用美式全科醫療模式,在更為舒適溫馨的環境中提供個性化的綜合醫療服務,成為大陸醫療市場中最為成功的外資醫療品牌之一。
“我就是沖著中國的新醫改回來的”,同李碧菁相比,英國醫生謝吉伯的表達更為直接。謝吉伯坦言,1986年第一次來大陸時,當時醫療條件落后,醫院沒有一次性的輸液用具,玻璃藥瓶也要多次使用。但隨著醫改深入,數年后再來時,大陸醫院已經建設得更大,環境更好了,硬件設備也齊全先進,唯一沒變的是等候看病的人還是那么多,排的隊還是那么長。
2006年,在獲得外國醫生在京短期行醫資格后,想一探究竟的謝吉伯關閉了在倫敦苦心經營了15年的私人診所,舉家遷往北京,并在朋友的幫助下,先后來到東城海運倉和海淀雙榆樹社區做起了全科醫生和慢性病專家顧問。
在胡同里,謝吉伯終于觸碰到中國醫療問題最真實的一面:由于大陸醫療資源分配極其不平衡,同公立醫院相比,社區醫療條件較差、醫生收入低,大部分患者只是來社區醫院開些常用藥,在病情診斷方面,他們更寧愿去公立醫院排很久的隊。這些,都同謝吉伯在英國行醫的體會截然相反。
謝吉伯介紹說,英國的醫療服務體系分工明確,以專科醫生為核心的公立醫院主治疑難雜癥,更多慢性病、常見病則交給家庭醫生在社區開辦的診所解決。除遭遇緊急情況外,英國人都必須嚴格遵守“社區首診制度”,即當居民患病時,必須首先經社區的家庭醫生診治,醫生再根據其病情判斷患者是否需要轉到公立醫院進一步治療,這樣就分流了公立醫院的壓力。
在病情診斷和開藥方面,醫生需要恪守一套規范化的臨床標準,確保患者不必遭遇過度醫療和亂收費。從衛生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社區家庭醫生還能通過慢性病管理等形式降低醫療運作費用,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對經濟發展有利。這樣一來,困擾中國醫療系統已久的看病貴、看病難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
“病人信任的是這個體系,而不是某個醫生。”今年36歲的杜春瑩醫生曾經是北京一家公立醫院的內科醫生,在謝吉伯的外資診所做起全職家庭醫生后,她開始感到不同醫院在服務理念和處理醫患關系上的巨大差異。
杜春瑩說,過去在公立醫院工作就像流水線作業,病人多、時間緊,患者的癥狀描述和血檢結果成為醫生診斷的重要依據,不僅許多病癥得不到更全面的診療,醫生對癥狀的解釋和開藥的偏好不盡相同,很難獲得患者的信任。但在謝吉伯的外資診所,杜春瑩發現自己需要花上更多時間和耐心檢查身體,同患者及家屬溝通,通過電話、微信和醫療軟件監測病情,確認恢復狀況,時間久了,建立醫患信任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困難。
隨著外資醫療機構準入政策不斷松動,謝吉伯終于得到在中國試驗推廣英國模式的機會。2014年12月,謝吉伯的“健康快線”家庭診所在中產人士和海歸居民相對較多的燕莎商圈落地,這也是目前北京唯一一家推廣英式醫療模式的診所。
初到北京時,謝吉伯只是覺得這里離醫改政策的制定者更近,推廣英國醫療模式的示范作用和影響力可能更大。隨著近年來不斷有發改委、區衛生局和社區的管理者和醫護人員來診所考察、取經,謝吉伯更堅定的要把診所辦下去,“因為我來中國推廣英國模式,并不僅是想做好一門生意,更多是想改變。”
亟待理解的醫療服務模式
盡管政府和海外投資者對外資醫院期待甚高,但在民營醫院市場份額不足20%的今天,外資醫院的市場影響力仍十分有限。除和睦家、美中宜和等早已在中國站穩腳跟的外資醫院外,大多醫院仍處于叫好不叫座的資本積累階段,有些甚至陷入停業危機。
對在華外資醫院而言,眼前最大的發展阻礙就在于其海外醫療服務模式很難被民眾接受理解,遭遇水土不服。
據北京和睦家醫院院長盤仲瑩回憶,和睦家醫院創建之初,許多婦產科主任都很好奇美國醫院是如何實施分娩手術的,但當他們發現孕婦就在各自房間而非產房里分娩時,專家們紛紛指出這樣做可能導致感染。但盤仲瑩卻十分淡定,“實際上美國都是這樣操作的,我們也從沒出現過院內感染。”
更多尖銳而直接的質疑聲則出自患者。
“最難改變的就是世人的觀念。”謝吉伯甚至用“洗腦”來形容改變中國患者的就醫觀念有多困難。謝吉伯說,很多病人第一次來診所看病,主要是聽說診所環境好、服務好、私密性好,但其實他們并不了解英式的診治流程和醫療服務理念,對于他的很多看病方式充滿了質疑和不信任。即便是很多受過較高教育、甚至有過海外醫療經歷的白領和中產,也未必能完全接受整套英式醫療服務,只不過是“更容易洗腦些”。
在謝吉伯看來,中國人非常認同“久病成醫”,他們更習慣于自我診斷,做自己的醫生,而真正的醫生反倒成為印證他們判斷的人。因而在診所,謝吉伯經常碰到患者堅持要求驗血驗尿驗便,一定要親眼看到白血球等指標才肯罷休;還有的患者,僅僅看到家庭診所的宣傳,就誤以為家庭醫生就是提供上門看病服務的醫生,打來電話提出各種要求。
為了適應中國患者的就醫習慣,謝吉伯在堅持英國醫療方式的基礎上,又對診所進行了幾處“本土化”改造:比如添置了影像、血檢等令患者覺得更有權威性、更專業的檢測設備;另外設置了中醫和藥房——英國實行醫藥分開制度,診所普遍沒有藥房。謝吉伯自己也變得更善于應對質疑,一遍遍地向坐在面前充滿疑惑的中國患者解釋,什么是家庭醫生,為什么沒有必要做化驗,為什么可以不吃那么多藥。
即便如此,謝吉伯仍表示,“個別患者甚至以難聽的話語直接表達他們的誤解和不信任”。
最尖銳的質疑則直指外資醫院收費不合理。在謝吉伯的診所,就有患者長期形成了醫生不值錢、檢查和藥品才值錢的觀念,認為診所收取幾十元的藥費相對合理,但450元至600元的診療費純粹是亂收費,并拒絕付款。類似情況在其他外資醫院也時有發生。
與公立醫院僅收取少量掛號費、藥費和檢查費的做法不同,外資醫院的大部分費用則用來支付醫護人員工資和維護診所運營,這恰恰是大多患者所難以理解的。
在國外,人們普遍認可醫患雙方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和購買者,醫護人員的勞動價值能夠在診費中得到體現。“醫生按照醫療流程提供服務,患者則購買這種服務,這是一個標準的交易關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鵬說,目前國內對醫療服務的認識仍存在缺陷,許多人雖然認可服務收費,但卻認為醫生的知識技能、技術水平僅算是醫療,和藹可親、噓寒問暖的態度才算是服務,但實際上這兩部分都屬于醫療服務的范疇,既需要醫生提供,也需要患者付費購買。
廣東省衛計委原副主任廖新波也指出,國人普遍缺少購買服務的概念,他們并不認為醫生服務、護士服務、藥事服務、甚至醫院的優質服務是需要購買的,而把藥費和檢查費當成看病費用的全部。“到外資醫院看病,如果醫生沒開藥或只開一點藥,而收費卻遠高于公立醫院時,他們心理上就會接受不了。”廖新波說。
目前外資醫院的收費標準的確普遍高于公立醫院。如北京和睦家醫院急診門診的平均價格為1700元,而包括中醫產后調養和康復理療服務的自然分娩套餐價格為6.6萬元。
醫療成本高昂和無法納入現有醫保體系,都迫使外資醫院為了生存,將自身定位由親民轉向高端。相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這種“高大上”的醫療方式顯然更適合那些擁有商業醫保或收入較高的在華外國人和富人,患者群的大幅縮小對自負盈虧的外資醫院而言無疑是致命打擊。
(馬芳薦自《鳳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