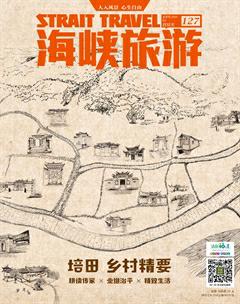篳路藍縷培田人的生計與進取
黃達隆
初識培田,感覺這里和大部分閩西、閩北的村落一樣,被生生夾在群山之間,交通異常不便。而交通的不便,自然愈發影響到經濟的發展,培田逐漸呈現出和其他村一樣的空心化情況:年輕人背井離鄉到城市務工,村落中以老人和婦女、兒童為主。然而這樣的村落,為何能夠在過去的八百年間不僅繁衍至今,更經歷了長時間的繁榮發展?
如果只是在培田小住幾天,你很難不被這里的山水田園風光所打動。河源溪靜靜穿過村落,打開門就能迎進一片翠綠山色,夜晚的頭頂是毫無遮攔的星空。然而山水美景只是都市人對鄉村環境的浪漫包裝。
標題
在古代,群山環抱中的培田自然地理情況近乎惡劣。龐大的武夷山脈、玳瑁山脈、彩眉山脈和博平嶺山脈等等穿插其間,重巒疊嶂,環境閉塞。清代《汀州府志》形容唐代時偏僻荒涼的閩西時候,用了“舊傳為山都(山鬼)所據”這樣令人不寒而栗的字眼。又因為閩西山林地區,瘴癘橫行,交通不便,甚至被人稱為“蠻獠之所”。直到宋元時期,因為躲避戰亂,才有大量漢民遷入閩西山區。
當時的連城到汀州一帶稱為河源里,培田因為地處河源溪上流而稱為上河源。培田先祖八四郎公來到河源里之時,除了久居此地的畬、苗二族以外,還有四十多個其他姓氏,吳姓僅僅只是當地小姓。然而物種的選擇總是伴隨著優勝劣汰,經歷幾代更迭,經歷了饑荒、瘟疫等天災人禍,其他姓氏或遷出或消亡,只有吳氏先祖在當地勤勉立業,站穩了腳跟,成為河源里的殷實大戶。一直到了六世祖郭隆公時,才將住宅從上籬遷到村東面,起名“培田”。從此,培田以此為基礎開始發展。
雖然早期有田可耕、有山可樵,但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到了明朝中葉,耕地日益緊張,培田村民只能開始出外謀生,逐漸轉向工商業。當時的培田商人利用山區物產從事竹木和紙業的經營,又因培田在地理位置上有古驛道和河源溪的交通運輸之便,好好地賺了一筆。有意思的是,雖然吳氏家族倡導“士、農、工、商”,讀書排在第一位,但是他們并不死讀書。一方面考取功名入仕為官,另一方面他們在家訓中則提倡“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農工商賈,勤勉乃事。”他們不僅不在乎這種排序,更絲毫不避諱家族經商的經歷。反而以經商所獲,資助家族文化事業、公益事業,維護村落的風水,所以當族人生意最為興隆的時候,也是村落大發展的時候,村中建筑越來越多,宅子越蓋越豪華。當時培田從商人士之多,勢力發展之快,商業網絡除了遍布省內的福州、廈門、泉州以外,甚至跨出省界,直達潮汕和兩廣地區。
在培田商人的庇蔭下,村莊也得到了空前的建設。在培田村中行走,我們很容易就能從建筑的外觀上看出他的年份來——越是簡單的宅邸,年代就越古老;而越是華麗、龐大的住宅,就是經濟大發展的時候建起來的。培田著名的“九廳十八井”,或是客家傳統的大型“圍龍屋”式的建筑,更多是清代康乾時期所建,巨型的民居宅邸建筑如“官廳”和“繼述堂”,面積都超過6000平米,宅邸內的房間皆超過100個,所花在建屋上的時間、金錢亦非現代人所能想象。而在這些巨型豪宅的中廳內,雕梁畫棟、漆金點彩、飛檐翹角,同時對風水和形制有著極高的要求,精致的木雕工藝經過幾百年依然栩栩如生,更能看出當時培田商人對于自家宅邸要蓋得如何彰顯氣勢,有著極高的格調。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何培田被稱為“民間故宮”了。
然而只有在外經商的客家人對于家鄉的庇蔭,是遠遠不夠的。學者羅香林在分析客家文化社會時曾經指出,“客人家庭,很奇怪的是在同一家內往往兼營農工商學兵種種不同的業務。”商人在外經商,家中的土地耕種則由婦女或是居家干練的男人來耕種;農閑時候,則在家從事普通工作,例如織布制扇或其他手藝。農和工簡直無法分開。由于客家地區大多數耕地不足,這種以大家庭為依托,分工協作的生計模式,則是歷代客家人謀求生存和發展的策略。
直到現在,我們還能在萬安橋頭的天后宮中看到這樣的聯句——“工賈士農盡是神州赤子”,這種價值觀,讓培田客家人“能屈能伸”,既能克服艱苦的山區條件,也能夠守住家中的一畝三分地勤勉耕作,還能走出山區在外經商獲得成功,讓“士農工商”靈活而有機地結合,從而使家族繁衍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