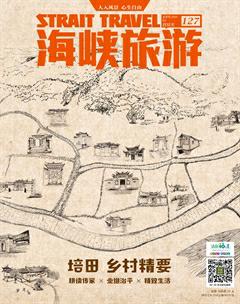精致生活
鐘祥瑜
培田的精致,不僅在建筑細節上,也在鄉民的書畫中。民國后近百年,培田家族式微,村落一多半是“富農”身份,子女無法接受良好教育,但在民間,對詩書的向往卻沒有停止。
右1是培田農民書畫家吳烈作品。右2是吳曉霞的工筆畫。
歷史上,培田擁有美麗的林泉田園,居所華麗精致,庭院蘭桂清雅,擁有兩棟藏書樓,藏書萬卷,且設有習武場、跑馬場,南山書院聞名遠近,書院私塾名師輩出,村落設有詩友會、孔圣會、朱子社等文藝組織,且擁有自己的戲班和曲藝團隊。這樣的基礎設施能為鄉民提供何種生活?晨起,凈手為廳堂中的祖先和天井外的天地奉上一柱香火,一杯清茶;享用從土地到餐桌級別的綠色飯食;在庭院擺弄花草;靜心閱讀,練習書法字畫;相約三五好友竹林漫步,山谷聽泉,詩文唱和,或跑馬場上沿溪策馬,勤練騎射;逢年過節邀親友至家中齊聚,請來戲班唱堂會,修竹樓內還有池塘可泛舟其上,愜意非常。農忙時節,下地勞作,農閑時節則習武弄墨,女人們可在容膝居內社交,家常之外,還有打理生活的基礎技能。
這些記載于吳氏族譜上的鄉野日常,足以讓當今的我們垂涎。走在培田的古街和宅院里,建筑的精致細節還能彰顯當年的雅致,只是村落士紳階層經過民國后近百年的戰火和運動的磨難,早已四散,歷史再也沒能給鄉村培育新的士紳階層的社會空間。有過書院和私塾經歷的老一輩培田人,成了最后一代鄉紳,他們繼承了家族教育和鄉村信仰,經歷過大洗牌后劫后余生,如今再度被社會關注,成了培田“浮在水面上的人”,他們往往熱愛書畫和閱讀,主持鄉村信仰儀式,熱衷于表述過往。 大屋里居住的尋常人家,已經不是能夠感性看待山林、可以吟出詩句的士子,家家戶戶遍植蘭桂的家居審美因低廉易得而流傳下來。古今之別,因旅游發展的契機而重新讓培田子民深感遺憾,這種遺憾對官方和民間都有正向的催促力,他們在一遍遍闡述輝煌的時候,也在給自己的生活樹立一個標桿,這些只有在末代鄉紳心中藏有的標桿如今深入更多培田人心,于是有了書畫院、教育促進會、培田理事會,有了正月的書畫比賽、春節的春聯書寫、十番樂、西洋樂,政績也好,生計也罷,至少在閑暇時光,鄉村不是只有聚眾打牌,也會有人研墨繪丹青,絲竹之樂繞梁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