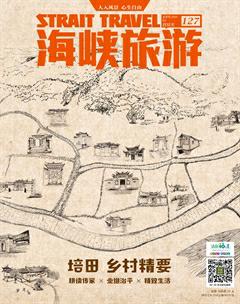山林·田園·手藝
四五十歲的父母,九零后的兒子,構成了鄉村完整的家庭生態。母親曹林鳳是剪紙能手,父親吳亞春主理紅米田和二百畝竹林,兒子吳錦亮管理民宿、接待旅行團,還有國家托管的原始森林,從家庭流出的產品有草藥、竹制品、香菇、木耳、紅米、姜糖、剪紙、燈籠。一家人分工明確,實踐著新農人的自給自足。
“看天吃飯”不易,但當城市緊缺的農產品從山林田園和溪流中通過網絡走出鄉村時,換來的是比過去更好的收益而不僅僅是維持生活。新鄉村農人的自己自足,讓我們有了重新尊重土地和村落的理由。吳亞春一家便是如此。
1993年出生的吳錦亮比我之前見到的開朗許多,不知道是否因為經常帶團的原因,更會表達自己。山林是他最喜歡待的地方,于他而言,山林是大寶庫,也是重要的經濟來源。如果不下雨,他都會上山,背著竹簍,后面跟著他家的小狗“九十九”。我們見過“九十九”在山林中上躥下跳撒歡的樣子,歡樂地讓人嫉妒。對于城市客而言,山只是山,也許帶著休閑戶外的標簽,而對長在山林邊的鄉村而言,山是另一片田。它不需要太多經營,只要愛護,就會回贈你很多。錦亮能夠認得百十種草藥,知道5月的山上有樹莓,雨后艷陽有蘑菇,什么時候該采哪種野菜,隨手抓一把草告訴你它可以治咳嗽。這種知識在當下的標準中無從考評,卻足夠讓人動容。即便我會謹慎地質疑草藥的功效,卻不得不向往人與山林的認知和貼近,大部分人,如我們這樣脫離自然存活的物種,面對山林田園、四時物候,幾近無知。錦亮對山林近乎癡迷,有時帶上食物,在山里一住就是一周。山上的竹林有一棟小屋,是當年他們放羊的住所,如今也成了帶團體驗的山野廚房,也是錦亮的山居民宿。興致來了,他會在山里露營,有時是帳篷,有時就在大樹間拉一個吊床,頂上支上天幕。“遇到蛇怎么辦?”“那我就可以加餐了!”錦亮笑了,不知道是否在嘲弄我們的膽小。
曹林鳳本就是手巧的人,經過熱心人士的點撥后,開始用剪紙表現培田古村,引起了媒體更多關注。為游客現場剪頭像、為旅游團提供剪紙和燈籠等手工課,是目前收益較好的項目。容膝居依舊是她熱愛的工作空間。
吳亞春只在有酒的時候,才顯得多話和風趣。客家人的家庭有著嚴格的男女分工,一家之主的丈夫,更需要保有家庭地位和尊嚴。平日里,吳亞春板著臉的時候居多,如今家里做起民宿,人來人往,把酒言歡的機會增多,笑臉也時時掛在臉上了。我們親眼見證客家人的勸酒功力,米酒的香甜又具有偽裝性,三杯兩盞下肚,不勝酒力的人才驚覺頭眼昏花。培田鄉建團隊“耕心”為他們找來的民宿改造建筑師,入住的第一個晚上,就被接風洗塵的熱情和勸誘,醉得只能扶墻而走,第二天清晨談酒色變。“米酒不會宿醉頭痛,”這是客家人對米酒的愛的表達。農忙的時候,吳亞春主要負責紅米田的打理,紅米遲于一般中稻收割,村里只有他們種植,惹得愛吃稻米的鳥類和昆蟲,都向田里聚集,十分頭疼。他們建議大家種植紅米,并愿意提供稻種,可惜培田目前還在耕作的人家更傾向種植有經濟保障的煙葉。放眼望去,綠油油的田地里煙葉繁盛。紅米目前的市場價格不錯,在吳亞春家的微店里總是供不應求,山貨也是緊俏,在民宿和團隊接待逐漸上軌道后,他開始勸說曹林鳳回家一起經營,不用一味守著容膝居,剪紙總是看的比買的多。
曹林鳳的剪紙,當初被社區大學帶動起來的關注度,經過媒體的渲染,如今依舊是培田的旅游體驗項目之一。曹林鳳的手很巧,頭腦很靈,除了剪紙,還有竹編、竹制玩具、燈籠,并且一直在推陳出新中。游客依舊是周末和節日的時候居多,生意也沒有因為知名度帶來太多的改善。民宿客人來了,她要忙著準備三餐,團隊接待里,也總是少不了她的剪紙、燈籠的手藝環節。民宿和外聯,主要由兒子打理,她的工作場所還是容膝居,盡管丈夫勸她回家幫忙,她還是想堅持。我想,也許容膝居的工作,讓她看起來像是一位職業女性,且上班時間富有彈性,也是她接觸外界的窗口,她無法割舍。曹林鳳隱忍,甚至堅硬,和她的人生經歷有關,她不止一次地表述自己在重男輕女的環境下作為女人的痛苦和反擊。即便媒體關注她,她依舊希望可以獲得實實在在的消費而不是過多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