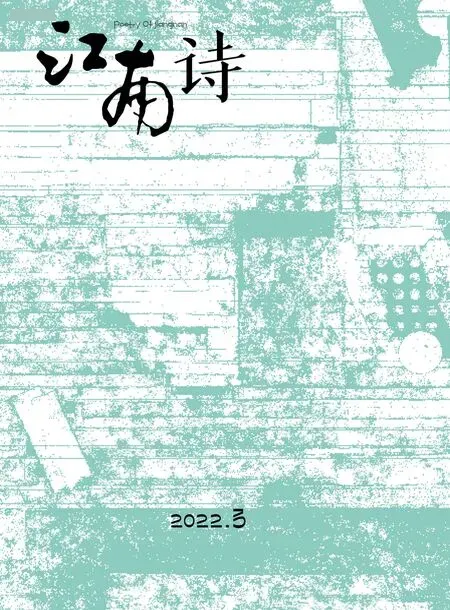消逝與抵抗
——菲利普?拉金的“保存”詩歌
◎劉巨文 Liu Juwen
?
消逝與抵抗
——菲利普?拉金的“保存”詩歌
◎劉巨文 Liu Juwen
“我寫詩是為了保存我所看到、想到和感到的事物(如果我這樣可以表明某種混合和復雜的經驗),既為我自己,也為別人,不過我認為我的主要責任是對經驗本身,我努力讓它避免被遺忘。為什么要這么做,我也不知道,但我認為保存的沖動是一切藝術的根本。”[1]Larkin, Philip. Required Writing: Miscellaneous Pieces 1955-198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84. p.79.1955年,在回應德·約·恩賴特的約稿中,拉金對自己的詩歌觀點做出了解釋。“保存”是這段話的關鍵詞,因為它清晰地為拉金及其詩歌所要負的責任做出了界定。首先,“保存”意味著有什么東西在消逝,這些東西的消逝迫使拉金利用詩歌作出抵抗。其次,“保存”的內容是拉金的自我經驗,而這些經驗遭受著被遺忘,最終消逝的威脅。拉金的所要保存的經驗來自于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在時間中的必死是拉金詩歌的核心,也是詩歌抵抗責任的依據。這一觀念從根本上造就了拉金詩歌的獨特性。簡單來講,拉金成熟時期的詩歌往往是具體清晰,不回避和逃離日常生活世界的矛盾和缺陷,不指向超驗世界,充滿物質感的——這正是拉金與艾略特和葉芝等現代主義詩人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之一,也是拉金確立自己詩歌的根本性依據之一。
一
盡管拉金曾聲稱日常事物是可愛的,他的詩卻往往透露出一股消極的味道。這一點常常被人詬病。西莫斯·希尼對他的批評最為典型,他認為拉金的詩過于黯淡,在面對死亡時,喪失了“人類精神偉大勞役”[2]西莫斯·希尼:《希尼詩文集》,吳德安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177頁。的責任感。切·米沃什也對拉金“生活都是可憎的”態度持批評態度,認為雖然“死亡不會錯過任何人”[3]Milosz, Czeslaw. New and Collected Poems: 1931-2001.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p.718.,但對于詩歌來說,拉金的表達并不得體。不過,如果考慮拉金面對和書寫的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況,他的詩歌的合理性是存在的。
拉金所面對的日常生活實際上已經喪失了絕對價值的庇護。這些絕對價值主要包括基督教和一系列追逐超驗秩序的思想觀念,在二十世紀中期前后的英國已近乎喪失說服力。克萊頓·羅伯茨稱“這是一個懷疑的、混亂的時代”[1]克萊頓·羅伯茨,戴維·羅伯茨,道格拉斯·比松:《英國史(下)》,潘興明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579頁。,正是這一現象的真實寫照。拉金對基督教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他聲稱“現在人已經不可能成為基督徒了”,“上帝搞得我很抑郁,這卑鄙的家伙在哪里?”[2]Brennan, Maeve. The Philip Larkin I Knew.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70.對于其他追逐超驗秩序的思想觀念,拉金也不認可。在這一點上,他和他的運動派詩歌同人態度類似,無法相信那些“宏大的理論構造體系”,傾向于“對所遇到的一切都采取經驗主義的態度”。[3]Conquest, Robert. New Lines. London: Macmillan & CO,LTD, 1956. p.xv.這種深切的懷疑和否定促成了拉金轉向日常生活的書寫,也為他帶來了危機,即日常生活在喪失絕對價值庇護后,其本身的價值意義陷入難以確定,無法逃避時間消逝中的必死的困境。對于拉金來說,人類存在于日常生活的物質世界,心智的活動只能在這個世界展開,沒有天堂和超驗秩序對每一刻都在迫近的死亡給予救贖或撫慰。無疑,這是一個極為嚴峻的問題,因此,我們發現日常生活時間消逝中的必死在拉金的詩歌中的構成是壓倒性的,并讓他驚恐不已。
生活首先是厭倦,然后是恐懼。
不管我們是否利用,它都會過去,
留下那些隱藏不見未被選擇的東西,
以及歲月,然后是歲月最終的結尾。
——《多克瑞和兒子》[4]菲利普·拉金:《高窗》,舒丹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8頁。本文引用拉金詩歌漢譯本均出自本書,其他引用不再另行標注。
日常生活在時間中的必死在拉金看來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是一個強制性的事實。宗教已經喪失絕對意義了。他所去的教堂醞釀著“一種濃重、陳腐、不容忽視的沉寂”,即便他停留在那里,辨析出“更為嚴肅的饑渴”,但最終無法回避“那么多死去的人”。醫院肉體上的修補只是“一種超越死亡之念的/掙扎”,“它的力量不能勝過教堂”,無法抵抗死亡迫近的黑暗,盡管每個夜晚人們都在徒勞地嘗試,獻上“奢侈的,虛弱的,撫慰的花朵”。來自古老信仰傳統的救贖撫慰和現代醫學的治療都是無效的。情愛也是如此,人類世代延續創生性的力量在拉金的詩歌中也承受著死亡的質疑。性被視為一個空洞的“氣泡”,脆弱、短暫、易碎,是一種虛假的“伯明翰魔術”。婚姻則阻抑選擇,是厭倦和失敗的代名詞,導致的只是代代傳遞的痛苦,最好的選擇是“趁早跳將出來,/可別養什么孩子”。工作是現實世界中的具體行動,卻像癩蛤蟆一樣“蜷伏在我的生活上”,既讓人厭倦,又無法逃離,最終會陪他“走過墓場路”,走向死亡。包圍人類的自然生命也是如此,樹木隨春天來臨開始的重生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假象,因為“它們簇然一新年年如是的把戲/正被刻寫在樹的年輪”中,“它們也會死亡”。大地上所有生命和人類一樣,都會被死亡取消,都是有限性存在。
正是這種日常生活在時間消逝中的必死激發拉金在詩歌中尋求某種程度的抵抗。一如在《春天》中他對愛情的討論,“那些與她最無緣的人最能欣賞她”,只有意識到愛的匱乏的人對愛才是最渴望和理解的。因此,日常生活的有限性反而讓他專注于對日常生活的思考,不斷尋求為日常生活中具體的存在賦予獨特的詩歌形式。詩歌,在拉金看來蘊含著巨大的價值,畢竟詩歌本身具備某種程度永恒性,而寫詩無疑是與死亡對抗的積極行動。
二
“我認為對于生活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保存它,如果你是個藝術家,可以經由藝術。”拉金在1957年寫給莫妮卡·瓊斯的信中再次強調了詩歌的所應承擔的責任和可行性。這種認識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貫穿了拉金整個成熟時期的寫作。直到1983年,在他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仍堅定地捍衛“保存”的價值,認為自己的詩歌“保存了經驗和美”。[5]Larkin, Philip. Required Writing: Miscellaneous Pieces 1955-198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84. p.83.對于“保存”的內容,拉金側重于真實的日常生活經驗。美是日常生活經驗中的美,即便是丑或惡,也要被誠實的面對和書寫,絕不對這種有限性做過分的修飾。這一點在《讓詩人選擇》中被他對濟慈《希臘古甕頌》“美和真”的戲謔性的改寫所闡明。
它們(《1914》和《一無所獲》)可以被看作我有時想自己寫的兩種詩的代表性作品:美的詩和真的詩。我一直相信美就是美,真就是真——這不是你們在世上所知道的、該知道的一切,我認為一首詩通常要么始于那是多么美的感覺,要么始于那是多么真的感覺。[1]Larkin, Philip. Further Requirements: Interviews, Broadcasts, Statements and Book Reviews.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2001. p.39.
濟慈在《希臘古甕頌》的結尾讓古甕說:“‘美即是真,真即是美’——這就是/你們在世上所知道的、該知道的一切。”[2]濟慈:《濟慈詩選》,屠岸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15頁。對于濟慈的“美和真”,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濟慈在詩中描述的“希臘古甕”,是想象的產物,是處于超驗世界中的永恒存在,與現實世界的有限性不同,它是可以克服時間和死亡的;其次,“美即是真,真即是美”,美和真之間之所以可以等值互換,與“希臘古甕”被設想成超驗存在有關。它是本體性的,類似柏拉圖的理念,一旦美和真產生區別,那么就意味著某種程度上變成洞穴中的陰影,是虛假的,有限的,相對的。相應,拉金戲謔性的改寫也有兩點需要注意:
首先,拉金側重的是自于日常生活中具體可信的感覺經驗。拉金不相信超驗世界的存在,這一點和濟慈迥然不同,因此,他才特別強調“一首詩通常要么始于那是多么美的感覺,要么始于那是多么真的感覺”,而在1981年在接受約翰·海芬頓的訪談時,又再次對“真”做出了說明,“我的意思是有什么東西在我的脖子里磨它的關節。”[3]Larkin, Philip. Further Requirements: Interviews,Broadcasts, Statements and Book Reviews.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2001. p.49.因此,這就意味著拉金真的詩和美的詩都是誠實面對日常生活經驗的結果。和濟慈的“希臘古甕”相反,拉金的“美和真”不指向超驗世界。這一點在《一座阿倫德爾墓》中有明顯體現。該詩描寫的是一對伯爵和夫人墓上的雕像,拉金圍繞這座雕像展開了對時間、愛和藝術的思考。雕像本身作為藝術盡管留存了下來,但仍然無法絕對意義上避免時間的侵蝕,“時間已使他們變得/不真實”。很顯然,拉金認為“雕像”作為藝術是存在與現實世界中的,在抵抗時間的同時,也要被時間侵蝕,這和濟慈超驗的“希臘古甕”永恒之美無疑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其次,拉金的“美就是美,真就是真”,這種區別劃分也是在具體日常生活世界中展開的。日常生活經驗是“混合和復雜的”,充滿矛盾沖突的,這是日常生活的特性。拉金無法借助絕對超驗存在把矛盾消弭,只能接受矛盾的復雜存在。他的詩歌充滿了矛盾,并且這些矛盾往往處于一種“既……又”和“既不……又不”交織的臨界狀態,任何一方都無法戰勝對方,不是黑白分明的對立關系。因此,在他的詩歌中總是充滿了懷疑和否定,判斷與判斷之間持續不斷的辯駁,態度總是搖擺的,難以確定。布萊克·莫里森曾指出,“在他自言自語的時候,邀請讀者來聆聽,大膽地做推測性的解釋,然后用另外一種解釋推翻它,他講的話里充滿結結巴巴和自我修正(‘是,真實;不過……,’‘沒,沒什么不同;相反,多么……’)似乎為代言人的誠實做擔保。”[4]菲利普·拉金:《菲利普·拉金詩選》,桑克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頁。這無疑是一個精準的描述,也證明了拉金對日常生活經驗的理解,即“混合和復雜的”,而這種矛盾狀態恰恰支持了拉金對“美和真”的區分,因為在超驗世界,美和真是可以等值互換的,而在日常生活中差異和矛盾才是最真實的存在。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在日常生活經驗中,拉金可能更注重“真”,即誠實的面對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他想寫美的東西,也認為自己有些詩屬于美的詩,但更多的情況下,美和真是混雜在一起的,共同構成日常生活經驗。然而,正如拉金在海芬頓的訪談中所言,“我想寫的詩是有關世界是怎樣的美麗,人們是怎樣的不可思議,但不知為什么,詞語卻拒絕降臨。”[5]Larkin, Philip. Further Requirements: Interviews,Broadcasts, Statements and Book Reviews.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2001. p.61.因此,真正激發他的是日常生活的必死,是日常生活經驗在時間中不斷被摧毀的命運激發他賦予詩歌以“保存”的責任,一如他在《年歲》中所寫到的:
到如今太多的東西已經飄走,
從這里,我頭腦的窩巢,我必須轉身,
好知道我留下了什么樣的痕跡,無論是腳印,
野獸的足跡,或一只鳥熟練的展翅。
三
保存日常生活經驗,拉金的這一詩歌使命強烈影響了他的詩歌品質,讓他的詩歌具備強烈的物質感。物質感來自于日常生活世界的有限性存在。對于拉金來說,日常生活中的人、事和物無一例外都無法像超驗存在一樣永恒高懸,而是活生生具體可感的,必然消逝的。為了對抗日常生活的這一困境,拉金選擇在詩歌中特別注重從包圍自己的日常生活的具體經驗細節中出發來組織展開詩歌。在1983年接受《巴黎評論》訪問時,他非常明確地指出詩歌的“職責是抵達原始經驗”。[1]Larkin, Philip. Required Writing: Miscellaneous Pieces 1955-198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1984. p.58.這種態度是經驗主義式的,因此,拉金傾向于從對日常生活世界具體真實存在的觀察,傾聽,觸碰,而不是通過對超驗世界的想象展開寫作。他必須讓自我所經驗到的日常生活停駐在詩歌之中,以此才能更有效地對抗時間消逝帶來的必死。
《這里》是一首非常典型的詩,可以說明拉金的這種傾向。該詩完成于1961年,記錄了拉金從倫敦返回胡爾一段旅程的詩。“我的意思是這首詩是頌揚一個地方,胡爾。胡爾是一個迷人的地區,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像。”[2]Larkin, Philip. Further Requirements: Interviews,Broadcasts, Statements and Book Reviews. London: Faber & Faber Limited, 2001. p.59.詩歌本身也證明了這一點。詩歌的題目“這里”本身非常明確地指向一個現實的地點。拉金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對“這里”展開細致入微的描寫。詩歌始于拉金在火車上對郊野的觀察。火車是運動的,正是在運動中,拉金不斷變換著視角,納入那些讓自己感興趣的場景:“陰影”、“田野”、“小車站”、“天空”、“稻草人”、“野雞”、“干草堆”、“河流”、“鷗鳥”以及“軟泥”等。這些事實性的存在沒有因運動被拋諸過去,而是帶著一種孤獨的安寧意味被保存在拉金的詩中,在他的精確描寫下獲得了凝固的效果。
從詩歌的第二節,拉金進入了城市,他使用的手法仍然是直接描寫。“圓頂”、“雕像”、“尖塔”、“吊車”、“街道”和“游船”,“來自濕冷住宅區的居民,由悄悄行駛的/平板電車沿筆直的道路帶來”等,這些都是視覺景象,似乎很客觀,沒有什么態度可言,但是,它們的出現本身就與上一節某種程度上的孤獨的安靜形成了對比,表明城市是聚集人群欲望之地,而這一切都是經由具體的事實性存在顯明的。接下來的“廉價西服,紅色廚具,時髦的鞋子,冰棒,/電動攪拌機,烤箱,洗衣機,吹風機”一系列商品的密集列舉更是強化了城市的質感。不僅僅是視覺,拉金也調動了嗅覺來抓取經驗,比如,“在街道盡頭帶著魚腥味的/田園牧歌式的船只里”,則是來自于真實的胡爾的味道。另外,“田園牧歌式的船只”和“奴隸博物館”存在也為城市增添了時間深度,給出一個更廣闊的存在背景。
在詩歌的第三節和第四節,拉金又把視線投向了郊野。在郊野是“迅速被陰影遮蔽的麥田,長得像樹籬一般高,/是孤絕的村莊”,在這些描寫中又回響起詩歌第一節中蘊含的種孤獨安寧意味。而在詩歌的第四節,拉金踩著前面具體堅實的描寫鋪墊進入了某種沉思之境。
……這里寂靜
像熱氣靜止。這里樹葉在忽視里變濃,
隱藏的野草開花,被疏忽的水流加快,
充滿光亮的空氣升起;
而穿過罌粟花淡藍的模糊區域
那塊土地突然終止在身影和卵石的
海灘之外。這里是不設防的存在:
面對太陽,沉默寡言,遙不可及。
盡管這種沉思頗有迷幻之意,但仍指向“這里”。自然存在物“樹葉”、“野花”、“水流”、“空氣”和“罌粟花”等本身的生長和流逝,進入一種自足,孤獨,但不失生意的狀態。盡管“面對太陽,沉默寡言,遙不可及”,“不設防”,但“這里”還是存在著。
從整首詩來看,我們可以獲得這樣的結論,拉金正是依靠視覺和嗅覺等日常感覺經驗的收納完成了對“這里”(胡爾)的描述。在詩歌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拉金描述的所有事物不是漫無邊際,無意義的,相反,正是依靠這些專注的描寫,使拉金對“這里”的認識逐步滲透了出來,最終抵達本詩的結尾,打開了詩意舒展的空間。這是依靠人對日常生活具體經驗,而不是超驗想象展開詩歌的方式,正是這種方式讓拉金的詩歌充滿可觸摸的物質感,某種程度上完成了對日常生活經驗的“保存”,抵抗了時間的侵蝕,讓它們不被遺忘。在拉金成熟時期的詩歌中,這一特征是非常典型的。他的《寫在一位年輕女士照相簿上的詩行》、《去教堂》、《我記得,我記得》、《布里尼先生》、《降靈節婚禮》、《去海邊》、《消逝,消逝》、《大樓》和《星期六展會》等都是很好的例證。這些詩集中于對日常生活經驗的描摹,不斷在描摹中對經驗本身進行思考,最終完成了對日常生活經驗的“保存”。
聯系拉金的詩歌,回顧希尼和米沃什對拉金的批評,我們可以發現,拉金的詩歌確實包括了大量日常生活中消極面,尤其是在時間中的必死。但是,如果因此就否定拉金,則顯得不甚公平。面對日常生活在時間中的必死,拉金無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誠實地面對自我與自我經驗到的日常生活世界,死亡迫使他努力保存,寫出了頗具物質感的詩歌,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強顏歡笑對他來說是不真實的,而寫作本身,不管是悲觀的還是快樂的,只要基于真實去表達,就是一種積極的行動。
人 物
汗漫的“跨界”有著地域、職業和文體的多重性:從中原到江南;從高校教員到企業高管;從詩到散文。在變遷中“散懷抱”,自認為是一個在俗世中沉浮的人,而寫作則是“自救的浮木”“還鄉的棧橋”。今天的汗漫,更以散文家著稱,無論其散文是“新散文”“后散文”還是“詩人散文”,他在同代散文家中都是出類拔萃的。將詩的精準、飽滿和自覺,移植到散文的多樣化寫作追求中去,這是“散懷抱”之一種,使人想起1990年代周濤的一句話——“解放散文”。(沈葦)
主持人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