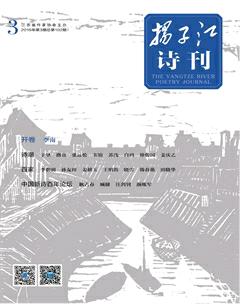接水氣的詩學分享與憂思
耿占春 臧棣 汪劍釗 顏煉軍
耿占春:我們承諾了在瘦西湖的船上,在三月揚州的風景中,就今天詩歌教育和現代詩的闡釋問題談一談。詩教是一個悠久的傳統,但對現代詩來說,無論是詩的教育還是詩的闡釋,都與現代詩的實踐脫節很遠,不僅如此,人們還要回過頭來,責怪現代詩看不懂等等。這么說來,詩的解釋能力與現代詩的教育這兩個問題其實也是關聯在一起的。我知道汪劍釗老師已經對詩歌教育寫過一些東西,要么從你這兒開始?
汪劍釗:坐在游船上,面對詩一樣的風景,我們視而不見地談論詩歌,實在有點浪費。這幾年,人們說到新詩的很多問題,歸根究底,還是出在教育上。而教育的問題,實際上還不完全是詩歌教育,它可能跟我們整個的語文教育有關。
在語文教材的編寫中,帶出來一個跟詩歌有關的問題,即對詩如何理解。我曾經在《詩江南》雜志上主持過一個欄目叫“詩歌課堂”。創設該欄目的最初起因要追溯到七八年前。當時,我女兒上小學五年級,有一天,我意外地發現她辛苦地在背一首語文課本上的詩,這是她的作業。說實話,這真是一首非常低劣的作品,低劣到我甚至都不愿意將它稱之為詩,只想將它稱作一段分行的文字。作品題目是《這兒,原來是一座村莊》。這首所謂的“詩”,且不說表達的情感如何矯揉造作,充滿了虛夸、膚泛的氣息。實際上,它作為散文都是不合格的。通篇的散文化句式,其中有些句子還極其拗口。比如里面就有這樣的句子:
他們開著卡車,運送水泥、鋼材,
提著皮包,和外商談判辦廠。
伴著燈光,學習雜交水稻的知識,
和著樂曲,翩翩起舞放聲歌唱。
即使把這一節文字放在散文的形式中,它們也顯得非常瑣碎、拖沓,只能算仍然沾著口水的口語,根本談不上什么詩的美感。“提著皮包,和外商談判辦廠”,你們試著念一下,是不是別扭?這里,作者使用了“江陽韻”,刻意設計了“廠”和“唱”的押韻,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音樂上因復沓而形成的應和效果,但這種勉強的湊韻并不能帶來很好的旋律感,而且因為隨后接踵相連的“判”和“辦”二字的出現,造成了極其拗口的發聲,切斷了人們自然的呼吸吐納,根本無法在節奏上形成流暢、和諧的效果。
整首詩共有四十行,按照教學要求,這是一篇需要背誦的課文。我當時覺得特別無奈。一方面,我覺得這是很爛、很糟糕的東西,任由孩子去誦讀,就像看著她吃有毒的食品;另一方面,我也沒有辦法阻止,因為,如果她背不下來的話,老師就可能在課堂上給她打零分。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就開始關注起中小學課本上詩歌的篇目。根據不完全的瀏覽,我發現,中國大陸的語文課本所選的詩歌篇幅就很少,一本有三十篇左右課文的教材中,選入的詩歌可能僅有七八首,而在這七八首詩里面,新詩又大概只占有三四首的份額。更讓人沮喪的是,這些好不容易被選入的所謂新詩,其被選入的眼光又是非詩的。其中絕大部分的篇目都跟詩毫無關系,甚至離得很遠。為此,我后來有意寫過幾篇文章,針對中小學語文課本中所選的詩歌篇目提出了一些看法。我想告訴大家,它們為什么不是詩或者它們缺少了哪些詩的元素。我有個計劃,寫一系列文章,最后或許能夠整理成一本書,題目就叫做“中小學語文課本所選詩歌篇目之批判”。我已完成了七八篇,發表后在詩歌圈內還是有點影響力,得到了不少朋友的鼓勵和嘉許。如果能把這種反響擴散到社會上,效果可能更好。另外,我還有一個計劃,就是除了批判以外,我們還應該做一個“立”的工作,告訴大家哪些詩歌可以被選入語文課本。現在有很多參與編選語文課本的人,他們對詩歌不了解,不知道哪些是好詩,哪些是垃圾。
耿占春:劍釗所談的這個問題觸及詩歌教育的根本性癥結,語文教學跟意識形態有相似之處,語文教學變成了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工程,而非為著喚醒學生對世界的感知、想象和語言表現能力。這樣的語文教學刪除了孩子們心中不符合所謂正確標準的那些感受力,結果只能讓一代人再次變得內心空洞、乏味,從一開始就刪除了想象力與創造力。不僅一篇文章一首詩要有什么鮮明的主題思想,還需要政治正確,甚至情感正確,選擇詩歌文本的時候是如此,教學與講解的時候也是如此。所謂政治正確,情感正確,正確的觀念,都是非常概念化的東西。這樣就屏蔽了人的豐富的感覺、想象,就屏蔽了感受力。因為感性的事物、日常生活的感性經驗,那些人們可以感覺的東西,其中并不提供什么政治正確或情感正確,也不提供什么所謂的主題思想,就像現在,對水的感覺,對一條河,對瘦西湖環境的感覺很難有什么政治正確,對它的描寫也很難有什么中心思想,現在的語文教學方式,它所灌輸的,就像在實施意識形態工程,它造成的是一堵無形的墻,隔離了孩子們與經驗世界的真實關聯,刪除了感性的豐富性,將超額的、超量的感覺與想象屏蔽在人的意識與感覺之外。
現在語文教學中沿襲下來的那種觀念正確與情感正確,主題思想與段落大意之類的講解模式,是一份急需清除的意識形態遺產。意識形態的一個屬性就是將思想生活簡單化,它的一個典型的話語特征就是數字加概念,什么“兩個凡是”,幾要幾不要,幾講幾不講,五講四美三熱愛,把概念數字化,把數字概念化,完全不考慮概念與經驗世界的具體聯系,這與簡單化的處理人的思想這一政條主義傳統有關,與權力意志粗暴地對待人的思想情感有關。
這里說一下為什么詩歌不能納入這樣的教學與解釋模式,詩歌涉及到體驗、感覺、感知,而任何一種真實的體驗都是一個連續體,從晦暗的無意識到比較清晰的意識階段,再到超越清晰進入更幽深的層面,體驗是一個連續體,任何一首好詩所處理的都不單單是一個層面的東西,尤其不是純粹清晰的意識層面的經驗,詩歌渴望表現出經驗的連續體。當然,現在語文教育中傾向于選擇那些簡單意識的東西,那種能給人帶來意識多重性、體驗的多層級的詩篇是不會被選擇的,即使偶爾有復雜一些的詩歌入選,老師也多半不知道怎么對待它,這其實不光是小學中學教育問題,包括大學里我們的同行,很多老師搞現當代文學,他們都說我讀不懂現代詩,而且覺得很自豪。
臧 棣:剛才兩位從現象和原理分別講到漢語新詩的接受與教育,在當代的文化語境里,這確實是一個非常詭異的問題。這些年,在談論當代詩歌的閱讀問題的時候,我們都對公眾和當代詩歌之間的疏遠感到揪心,甚至惱火。我們實際上面臨著兩個棘手的話題:一,公眾質疑當代詩歌太難懂,難以進入,難以領略它的優異。二,公眾對當代詩歌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來自長時間積累的無法判斷當代詩歌的好壞造成的。它實際上是一種審美標準的焦慮反應。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普通的讀者面對如此多樣的當代詩歌,他沒有可以依循的標準去鑒別它的優劣,這的確會引起很大的心理嫉恨。這個讀者,可以從字面上讀懂每個字,甚至對每一行詩的意思,都能從語法上讀通,但這些詩句,這些詞語,組合在一起完成的那個詩歌文本,卻很可能依然顯得意義含混,寓意模糊。這的確產生閱讀心理失衡的問題。
讀不懂和詩歌教育的關聯,到底是什么樣的一個問題,其實很復雜。這個問題,很可能不像我們現在想象得那么簡單。比如現在,假如公眾反映當代詩歌不好懂,當代詩歌晦澀難懂,或者當代詩歌的寫作越來越缺乏標準,詩歌界的回應通常都會把問題歸罪于讀者的問題。在我們的潛意識里,讀不懂詩歌,無法鑒別詩歌的好壞,是讀者自身的問題。是讀者自身需要提高的問題。而在詩人這一邊,好像很無辜,對此種情形,此種狀況,完全不需要負任何責任。這實際上,是把詩人和公眾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陣營。我以前,也習慣這么看待這個問題。但現在,我覺得,從詩人這一邊,我們也許要換一種眼光來看待這個現象。我們應該堅持這樣的文化立場:詩人和公眾很可能不是一種對立的關系。不管愿意不愿意,詩人身上其實寓居著一個公眾。至少,詩人的成長經歷表明,我們每個詩人都是從公眾這一陣營里走出來的。這種關系,也許永遠都以某種方式積存在詩歌和社會的聯系中。我們以為它已經割斷了,但其實它還在那里。而無論如何被詩歌的難懂所隔絕,公眾身上也寄居著一個詩人。就像法國詩人蘭波表明的,每個人都是潛在的詩人。所以,詩,應該被視為一種生命的契約關系。這樣,從這個契約關系的角度出發,我覺得,詩人必須對當代詩的難懂或公眾抱怨當代詩的難以進入的情形負主要責任。我們不能把問題簡單地推給公眾。認為讀不懂當代詩歌,主要是公眾自身的問題。尤其應避免居高臨下地指責公眾的詩歌水平有問題。在閱讀詩歌的問題上,作為一種閱讀身份出現的公眾,他們當然會有自己的問題。但我認為,他們反映出的問題,也許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問題。我現在傾向于認為,這個問題雖然表面看起來不是我們的問題,不是詩人的問題,但我們其實有責任去解決它。
顏煉軍:剛才占春老師的發言和臧棣老師的發言非常有意思。到底是語文教育的實踐者或讀者為現代詩的讀不懂負責,還是詩歌寫作者和研究者負責?還是要把責任歸到意識形態上面去?我們可為的空間在哪里?兩位的發言代表了不同向度的省思。詩歌作為獨特的語言藝術,正如占春老師所言,不應該被知識化甚至意識形態化,但目前語文教育的結癥恰恰在于此。某種意義上,理想的詩歌閱讀或教學過程本身,就應該是對知識、意識形態乃至一切固化的言語形態及其背后的經驗和想象結構的反省、重構,由此而更新、優化對生活與世界的認知,這與臧棣老師講的漢語新詩的先鋒特質是一致的。現代詩歌的先鋒特質一方面與生俱來地具有反抗、反諷的因子,但也有作為語言游戲的天然氣質,甚至可以說,前者是通過后者來實現的,兩者是由二而一的關系。詩歌的閱讀或教育,恰恰是通過對后者的再現,來實現前者,也就是語文課里所說的“主題”或“中心思想”。現代詩歌的主題可能是符合或違反意識形態或者被規定好的種種“常識”,但最致命的問題是,作為活態的言語混凝術,詩歌通向“主題”或“中心思想”的過程,可能恰恰是目前教育中被刪除,或者說沒有能力再現的部分。語文教育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是課文講述的主題,而是課文實現主題的秘密的、鮮活的路徑,詩歌尤然,構成一首好詩的語言、文化、經驗、想象需要在教育實踐中還原甚至放大。從這個角度而言,漢語新詩在基礎教育方面面臨的問題,顯然是目前人文教育危機一個重要癥兆:由于“主題”或“中心思想”的獨裁,我們的孩子只能學習被規定好的、固化的“說了什么”,而沒有機會登堂入室,去探究“如何說”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恰恰是最難,最“晦澀”的。剛才,臧棣老師提到詩人在這個危機面前,需要反省,可以做一些建設性的工作,我非常有興趣,請您繼續深入講講。
臧 棣:既然煉軍“窮追不舍”,我就繼續談談我的看法。當代詩歌的難懂,有沒有其自身的問題呢?這個話題其實相當詭異。按阿多諾的想法,如果現代詩歌不寫得晦澀,那么它也就喪失抵抗現代物質世界的意義。如果我們把阿多諾的想法再往前推一步。他的觀念中其實蘊含了這樣的審美立場:詩的晦澀,意味著我們正在從事拯救個體生命的事業。詩,必須寫得晦澀。這樣,詩才能在現代世界的頹敗中構成一種反對的力量。但我們知道,這個觀念其實是相當西方化的。它是一種基于西方現代經驗的對詩歌的現代功用的理解。它的實施方法,它的實施過程,都會造成非常復雜的文化方面的問題。如果我們的確曾致力于把詩歌寫得很先鋒,寫得有意識的很難懂,甚至把詩的晦澀作為詩歌的一個門檻,那么,我們就不能把詩的難懂造成的問題簡單地推給社會,推給公眾。注意,我說的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問題歸咎于公眾的不努力。我并不是說,我們應該拋棄詩的難懂,或說放棄詩的晦澀,我的意思是,既然我們寫出的詩,造成了公眾和詩歌之間的隔閡,或疏離。而這種詩的隔閡,又是我們有意實施的一種語言意圖,那么我們也就必須積極地應對它產生的后果。某種意義上,完全可以這么看:詩的難懂,恰恰是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一種生命的機遇。也就是說,我覺得,如果換一種思維方式,換一種角度看,我們其實完全可以把公眾對詩歌的難懂的抱怨,看成是當代詩的一種機遇。我們應該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當代詩的難懂,如果我們把它作為一個詩歌教育問題來積極看待的話,至少有三個方面,我們其實是可以把事情講清楚的。第一,當代詩的意義,當代詩歌的文化價值,就在于它的難懂。這方面,它的思想淵源,審美動機,阿多諾都已講得非常明確了。換句話說,從詩歌教育的角度看,我們完全可以這么表明我們的立場,或者闡明我們的態度:詩的難懂,其實是詩歌的一種正常狀態。當代詩的難懂,不僅對公眾的閱讀來說是如此,而且對詩人的閱讀來說也是如此。只不過,前者習慣于本能的抱怨。后者的抱怨則隱藏得比較含蓄而已。但既然我們已講明,詩的難懂,是正常的。不僅是公眾會遇到的問題,也是詩人自己會遇到的問題。這樣,就會在詩歌文化的共識方面減少一些不必要的審美焦慮。第二,也必須講明白,當代詩的難懂,也許只是一種文化幻覺。因為從寫作的效果看,大部分當代詩人其實缺乏一種將詩歌寫得復雜的能力。很多被視為讀不懂的詩歌,其實都沒那么難懂。比如,顧城的詩。顧城的組詩《頌歌世界》,在1980年代的詩歌閱讀中,曾被視為相當難懂的。但在我看來,這組詩其實從來就沒那么難懂過。當代詩的難懂,其實可以歸結為一種文學的分類現象。比如保羅·策蘭的詩歌,比如王敖的詩歌,比如車前子的詩歌,它們很可能永遠都存在著難懂的問題。但另外一些當代詩,盡管曾在我們的詩歌閱讀中,擺出各種各樣的難懂的面貌,但其實都是可以讀懂的。第三,從詩歌觀念的角度講,我們其實也可以告訴詩歌的讀者。詩歌的閱讀,從根本上講,它是一種開放的心理體驗。它不是以是否能讀懂為自身的目的的。它的要義是以作品為契機實施我們的體驗與理解。閱讀詩歌,其實就是體驗詩歌。舉個極端的例子吧。某種意義上,我們可能都沒看懂這個世界的意義,但我們也都按各自的機緣生活在其中。詩,在我們面前的呈現的東西。其實也是如此。所以,我覺得,目前可能還要做的迫切的工作,恰恰是修正我們自己的關于詩歌的觀念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所談的詩歌教育問題,首先應是針對我們自己的教育。
顏煉軍:我非常贊同臧棣老師的積極態度,但似乎只有詩人和詩歌研究者還遠遠不夠,一種詩歌文化和詩歌教育氛圍,著實需要各方面的共同促進。剛才幾位老師都說道,在中國當下的知識共同體中,漢語新詩基本上是不被理解的。這與西方現代知識共同體對于西方現代詩歌的深度認同和闡釋非常不一樣。比如,我們講起波德萊爾就會去讀本雅明的書,講起荷爾德林就去讀海德格爾,講起史蒂文斯就要讀布魯姆,講起布羅茨基就要讀桑塔格。西方現代知識分子對于詩歌和現代藝術的深度認同和闡釋熱情,至少達成了這樣的效果:我們想要了解優秀的西方現代詩人或藝術家,幾乎都可以找到與之匹配的闡釋文本,甚至不只一家,甚至連一些歷史學家都來對現代文學文本展開卓越的釋讀。比如《啟蒙時代》的作者彼得·蓋伊都能寫出《歷史學家的三堂小說課》那樣高水準的書,其中講到里爾克時,可以看出其專業程度。《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講起現代詩歌也是頭頭是道。這種情況,在漢語新詩所處的語境中,幾乎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很少看到哪位當代中國哲學家或其他人文知識分子來解讀漢語新詩,質疑其合法性的人倒是不少。這種窘境,可能也反過來加劇了新詩被誤解的程度,無數不讀詩或已經喪失詩歌閱讀能力的人文學者跟大眾媒體一起,要么漠視詩歌,要么指責詩歌。簡言之,新詩寫作者和研究者的工作缺乏知識共同體的呼應,嚴重影響了漢語新詩的教育普及。在這樣的情況下,臧棣老師剛才講的“機遇”也就打了很大折扣了。
耿占春:煉軍說的情況在西方學界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臧棣在昨天的會議發言中提出過這個問題。這個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為什么西方當代的知識共同體能夠將詩歌作為他們的思想經驗,他們不僅閱讀現代詩,他們也能夠讀懂現代詩,的確,不要說文學學者,就是一些哲學家、哲學教授對詩都有很多人精通,不亞于專業詩歌批評家,甚至做得更好。當代詩歌確實已經成為歐美知識共同體可以共享的意義資源和符號資源,除了那些專門闡釋過當代詩歌的思想家之外,許多知識分子表現出一種知識共同體的特征,像麥克盧漢,傳播學的奠定人,他的著作大段引用瓦拉美和象征主義詩歌,莎士比亞就不用說了,那是他的專業,他的著作文章倒是沒有對傳播學文獻做什么綜述,也很少對自己的概念做嚴格的界定與解釋,按照我們這里的規矩的話就是很不規范了。但他的理論洞見往往來自詩歌,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社會學家鮑曼,倫理思想家查爾斯·泰勒,不要說那些特別文學性的法國思想家了,他們的著作都會大量使用文學與詩歌經驗,也會非常自覺地運用詩歌修辭,更是借助詩性思維,表現出他們轉換當代世界經驗的能力,創造意義的靈感與構建符號世界的能力。這些思想家他并不把意識活動當成封閉自足的東西,也不會把已經固定的思想范疇當作唯一的論域,比如說無意識、直覺、感受、情感、欲望、身體等等,都是思想認知的對象,尤其是當代思想領域,不只是意識及其意識活動的過程,身體、欲望、各種感官的感覺,它們所帶來的意識的啟明,所產生的意義感,以及對它們的符號化表達,都已成為知識的對象。如果將知識界所關注的問題僅僅限制在所謂的意識領域或觀念領域,將意識領域限制在所謂的正確政治領域,這就屏蔽了經驗與感知的隱秘層面,屏蔽了體驗的連續體,當代詩歌與藝術中更微妙的意義實踐及其符號表達就不能進入他的感知視野。這種主動的屏蔽或感知力的自我封閉使得當代知識界無法與詩歌或與藝術家結成一個知識共同體,詩歌與藝術不能變成他們知識創新的重要資源。其實這不是詩歌本身的挫敗,這是整個知識界的挫敗。
除了當代中國知識界的認知視野有限之外,可能還有其他一些很深的顧忌,政治正確的顧忌,和其它一些隱藏得很深的思想禁忌,變成智力弱化的根源。現在不少人在文章中會談論身體、欲望等等,但一般而言只是轉述者,是對西方學者已經命題化或主題化之后的一個引用,而并非與知識者自身的“心源”相通的表達。讀不懂詩或不讀詩就是一個證據。夫子說的有道理,不學詩無以言。所謂讀懂讀不懂,就在于詩歌閱讀及其隨之而來的闡釋,是否與自身的內在體驗相通的問題。閱讀一首詩是一種緊張的搜索內在經驗世界的過程,是喚醒內心感知的過程,也是重新激活那些符號,并以此重新結構自身的內在經驗及其意義的過程,這是一種充滿張力的雙重意義上的闡釋活動,對一首詩的闡釋意味著讀者的自我闡釋活動。無論他是一個人文學者還是一個普通讀者,是教師還是學生,讀詩都需要他不僅會把意識,把意識過程,也會把欲望,把無意識、情感及內心生活過程的觀察作為一個對象,他會向內在的與外部世界的超量的感性經驗敞開。
閱讀一首詩就是自我不設防的瞬間,就是徹底敞開自身,它需要向未知的、不確定的、未完成或未形成的狀態接近,它需要向復雜性、多義性或歧義性敞開,而不是屈服于固化的意識及其單義性。如果說在閱讀一首詩的時刻這些是關閉的,人們就無法接受一首詩提供的一切,如果閱讀過程中讀者只在自身的意識領域掃描,局限于狹隘的意識領域,如果他屏蔽了自身跟無意識的關聯,屏蔽了往往“不正確”的情感或歧義性的經驗,他就無法讀懂現代詩。實際上,單義性的知識是一種弱智狀態。
如果說敢于使用自身的理性,是一項社會性的啟蒙事業,而詩歌則是一種向內的啟蒙,敢于使用我們自身的感受力與想象力,敢于將欲望、無意識、體驗的連續性等等知識化。社會啟蒙這項事業我們的社會遠未完成,理性也遠未成熟,遠未發展出一種社會生活層面上的理性,或制度層面上可以操作的理性技藝,這項未竟的事業難道不是與“向內的啟蒙”一直被局限在詩歌小圈子里有關?與不讀詩或讀不懂詩有關,與人們同樣不敢使用自身的豐富復雜的感受力相關?當人們并不理解自身、并不認知自身的時候,當人們甚至知識界也聽不懂詩歌、即聽不懂他們的內心語言的時候,所謂的理性也顯得極其蒼白與貧乏了。
顏煉軍:剛才大家講了新詩教育的基本癥候和原因。我因為曾經直接或間接參與過一些教材編寫。在上面各位老師內在談論之后,我想談談漢語新詩教育的歷史由來,和目前詩歌界前輩和同仁做的一些工作。歷史地看,在基礎教育課程領域,無論是古典教育體系中的蒙學教材,還是五四以來以開明語文課本為代表的教材,它們所依據的教育理念都被1949年開始的意識形態強行中止了。與之同步,漢語新詩在1949年以后幾乎長期是空白的。五六十年代即使偶有新詩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也是延安文學這一脈的詩作。直到最近十來年,中外現代詩歌才慢慢進入到教材中。
在這方面,新詩寫作者和研究者在教育普及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有成效但還是沒有整體的突破。比如,就我所見,錢理群先生領銜主編,前些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的一套詩歌讀本,詩人蔡天新編的《現代詩歌100首》等,都有比較多的讀者群。詩人西渡編過一本《名家讀現當代詩》,把一些經典作品的經典闡釋匯編,也反響不錯。王尚文、西渡主編的《現代語文讀本》(6冊)也編入了不少好的漢語新詩作品,北島主編的《給孩子讀的詩》,也有很大的銷量,雖然我做語文老師的朋友反映,這本書給孩子讀,還是有些難度。這類選本或教材,也影響了一部分基礎語文教育工作者的教學實踐。我做過一個很有限的統計,在各級語文教材中,我們常見的新詩作品基本上都是下面這些:徐志摩《再別康橋》、聞一多《七子之歌》《死水》、卞之琳《斷章》、戴望舒《我用我殘損的手掌》、穆旦《贊美》、艾青《我愛這土地》、食指《相信未來》、北島《回答》、舒婷《致橡樹》、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些作品,基本上不出愛國、愛情和勵志主題,或者被理解為這些“主題”。可以說,漢語新詩作依然是作為某個“主題”被選入教材,而不是作為藝術和語言形式的典范進入教材。這與長期支撐語文教材理念的語言工具論是一致的,而語言工具論背后,其實就像剛才占春老師講的,是以意識形態的需求作為第一動力。90年代后期,語言學和語文教學領域,一直有這個爭論,比如語文教學領域有一本很有影響的論著《語感論》(王尚文著),就主張從工具回到語感,按我們詩歌角度來說,就是從知識回到感覺和經驗,從主題回到言語形式。要推動這個轉變,需要一整套的工作,至今依然很艱難。
從建設性的角度來說,專業研究者和詩歌寫作者還是有些好的工作可以做。因為專業研究和論述,要轉換為一線語文教師教學實踐的資源,還是需要做一些適當形式的普及和推廣工作。之所以有這個想法,也是因為跟一些語文老師有較多接觸。不久前有朋友約我去杭州一個職業的中學做一個詩歌講座。職高的語文老師因為沒有升學壓力,許多人很有職業理想,很多老師很想教好現代詩,但是不知道怎么教,他們老問我有沒有一本類似于教參一樣的書,告訴語文老師某首詩怎么教。我想了一下,今天在新詩研究領域,你說還真沒有哪本書可以作為語文老師的參考書,比如說聞一多《死水》怎么講,講臧老師的《菠菜》怎么講。
基于這個處境,理想的解決辦法,自然是希望知識共同體逐步解除對新詩的偏見和漠視,一起自上而下地促進一種美學變革意義上的詩歌教育轉型。最沒辦法的辦法,則只能是新詩寫作者和研究者自己來從事一些建設性的工作。首先,還是得從詩歌闡釋與批評的工作做起。漢語新詩自誕生以來,已經產生了不少經典的作品,也有更多的好作品需要專業的闡釋和批評來發現。闡釋空間是無限的,我們依然期待理想的詩歌批評:一個個強有力的闡釋與批評,能夠為詩歌讀者發現的作品,進而逐漸改變漢語詩歌史序列,改變目前不理想的大眾詩歌趣味。八十年代以來的巨大詩歌業績,依然需要大量有效的闡釋批評工作,把好的作品從混沌中推出。其次,目前非常需要教育工作者和詩歌寫作者、研究者合作,編選出優良的、適合中小學語文教育實踐需求的選本。《唐詩三百首》的初衷,一開始也是為了“發蒙之助”。目前,市面上還看不到一本得到公認的,作為中小學語文課教參的漢語新詩選本,雖然對于漢語新詩中的許多作品我們尚未達成美學共識,但這個工作現在其實可以做了。
汪劍釗:煉軍講到闡釋,我覺得這里還有一個值得探討的事,那就是,很多搞創作的人在理論準備上的不足。在詩人中間,重創作輕批評的傾向可能也需要扭轉。據我所知,有很多搞創作的人就覺得,我只要能創作,看不看理論書,懂不懂理論,都沒什么關系。很多人完全是憑經驗、憑天才從事寫作,這樣的人,可能一時也能寫出點很好的作品,但他通常就走不遠。我一直認為,真正優秀的詩人一定具備出色的批評意識。有了好的理論修養,他就擁有了敏銳的藝術辨別力,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是好詩什么是壞詩,在他自己的領域里具備了專業的眼光。成熟的理性可以約束激情的泛濫,而且也可以進一步刺激想象力的誕生。我說的這種情況在很多年輕詩人那里還是比較嚴重的。應該校正這種錯誤的認識。另外,理論修養和批評意識的缺乏,實際也導致他對現實、歷史和社會的洞察力的不足,他無法應對現實的復雜性,自然也限制了他對社會和生命的豐富性的體驗。
臧 棣:煉軍剛才的梳理和建議都很有意思。說到底,我對目前的詩歌教育并不滿意,對詩歌教育和教育體制之間的關系也不滿意。比如,我們通常會覺得,目前的語言課本中呈現的當代詩歌,不單不足以反映當代詩歌的成就,甚至構成了對當代詩歌的一個極端的扭曲。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也有審美趣味和教育理念的原因。很多課本里的詩,都是按照一種過度的自我純潔的方式選出的;要么是太甜膩了,要么是智力的低幼化。它們背后的遴選尺度,也帶有過度的潔癖。似乎什么詩,適合未成年人閱讀,存在著一個非常干凈的標準。有時,我猜想,我們把事情想得太復雜了。我們在語言課本里選的東西,也許有好的詩,但在風格上,在類型上,太單一,太純凈。我們把我們以為什么東西不適合青少年閱讀這件事本身,想得太細致了,想得太透明了。如煉軍剛才所講到的,我們確實可以在詩歌選本方面,做一些工作。我們對詩歌教育的現狀發出了很多不滿,我們還可以做出一些更實際的編選工作。比如,我曾設想,某個財力雄厚的出版社,可以請10當代詩人,每人按自己的眼光,按自己心目中的適宜青少年閱讀的詩歌,各自選出150首左右的現代詩,每首詩后面,再適度附上一些解釋性的文字。這樣,至少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供選擇的、風格多樣的作品范圍。如果像劍釗剛才希望的那樣,詩人們如果已經有較好的理論和闡釋水平,就可以來支持這項工作。
但是,我的真實看法其實有點消極。一方面,我認為提供這樣的選本系列,作為一種編選工作,非常重要;因為它至少提供了一個閱讀詩歌的基礎。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我們所說的青少年讀者如何閱讀這些選本,以及它們終究會在年輕的心靈中產生怎樣的效果,我其實并無太多的把握。我回想自己接觸詩歌的經歷,有一個現象始終令我感慨:就是我十二三歲讀杜甫老年寫的東西,讀李商隱成年后寫的東西,從沒有過任何人暗示或告誡我,那是不是我那個年齡的人閱讀的。但為什么,我們對自己有權去決定年輕人應該閱讀什么樣的詩歌這件事這么自信。我覺得,我們還是要看開一點。我甚至覺得,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念:即事實上,絕大多數當代詩,無論多么艱深的,或者號稱多么難懂的,其實都是適合他們閱讀的。什么樣的詩,只有到什么樣的年齡才可以閱讀—這其實是一種很荒唐的想法。它里包含的觀念其實也很落伍。
汪劍釗:臧棣說到選擇標準的“荒唐”,我突然想到有一個紐約派的詩人,就是隆·帕杰特,我請他到北外做過一次講座。他談起在美國怎么教孩子寫詩的事,很有意思。他說,他教孩子們說謊。大家知道,說謊在中國肯定是一件壞事,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誠實。帕杰特所說的說謊跟實際生活中的說謊不一樣。他讓孩子們扯天大的謊,這個謊言背后實際蘊藏著孩子們的想象力。你的謊說得越大越好,在某種意義上,說謊把想象的空間給擴大了。我們語文教育上對中心思想的劃定恰恰是一個反面,把本來很大的空間限制在一個點上。帕杰特則想辦法讓一個點向面的方向發展。另外,他還有一個觀點,每個人都會做夢,只要會做夢就能寫詩。因為,夢里的世界擺脫了我們邏輯、理性和道德的束縛,是一個特別自由的世界,它是想象力發揮的最佳空間。也因此,他認為,人人都是詩人。
顏煉軍:我有點同感,就是語言的游戲性、童話性。我女兒在兩歲半的時候都不愛吃蔬菜,想了很多辦法她都不吃蔬菜,后來我想到一個很詩歌的辦法,夾起一點菜,問她這像什么?只要像她喜歡的東西她都吃掉,比如,拿起一根胡蘿卜說這像個鐮刀或蚯蚓,她就會吃。后來每次飯桌上端來她不認識的食物,她都會問這像什么才吃。昨天王彬彬老師在會上發言時講中國人一在公共場合就說假話。我覺得這個里面涉及到幽默文化。我們中國有非常強的諷刺傳統,但是沒有幽默傳統,幽默傳統就是說從政治文化層面上我可以調侃、我可以調笑。在教育層面,幽默可以轉化為語言游戲,回到一個詞跟一個詞之間如何搭配在一起,撞出來一個新的狀態,通過語言內在的民主選擇,來促進人在精神上的,感覺上的主體的完成。這個過程,其實是對世界和自我充滿驚奇和幽默的發現,也應該是詩歌教育必須的,但在我們的大部分詩歌教學設計里面,可能恰好缺乏對這個環節的重視。
耿占春:新詩教育面臨的這些缺失,可以在現代文學史上找到一些原因。五四以后文體分化,詩歌、散文、小說,沒有了對詩歌經驗綜合的處理經驗。一般都認為詩歌負責抒情,說一點格言、句法,就是有一點情調。比如說像徐志摩、戴望舒就比較符合這種標準,因此比較流行。而穆旦寫得更復雜,因此在大眾層面就沒有被理解,也長期缺乏強有力的闡釋,給出大眾能夠理解的其他標準。詩歌不只是抒情,其他文體能呈現的,詩歌可以,比如論說文可以講道理,詩歌的道理也許講得更好,但是不是一個層面上的道理,詩歌其實是非常綜合的。
顏煉軍:占春老師講得對。歸根到底,當代詩歌中被教材或大眾所接受的部分,其實也是偏于抒情的,有情調的那部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子最為流行的幾首詩。還有張棗,大部分喜歡他的人,都基本停留在《鏡中》《何人斯》,而對他最好的作品缺乏進入能力。現代詩的綜合特質所具有的魅力,還遠未被認知。要推進這個方面的啟蒙,的確需要大量的工作,當然,如臧棣老師所言,這未必就能討好。
剛才臧棣老師講到一個一個問題我也常常在想,比如我們覺得哪些詩適合孩子讀?這個標準的依據在哪里?一方面我們可能會忌諱詩歌或其他文學中比較成人的素材或細節給孩子看,但一方面他們也漸漸需要這方面啟蒙,詩歌或文學閱讀可能就是完成這種啟蒙的一部分。比如,濟慈有一首《詠死》,如何給孩子讀?當代詩中一些與死亡、消極、兩性有關的作品,是不是一定要在教材中被純潔化?我不知道,古人會不會給他們的孩子讀陶淵明寫的充滿絕望和感傷的挽歌?西方近代形成的童話文學傳統,的確是一種處理這一問題的路徑,但是其中純潔化地處理血腥、色情、政治的方式,其實也一直被反思。早在柏拉圖的對話里,蘇格拉底就開始反對這些內容給孩子讀,也因此來攻擊作為希臘人老師的荷馬,但這種純潔化一直就沒實現,事實上,我們每個人成長過程中都有偷偷地閱讀“禁書”的體驗和記憶。許多人對現代詩歌美學上的指責或道德化的指責,其實也常常陷入這樣兩難境地。
臧 棣:煉軍所談的,其實就是文學教育的文化困境。從根本上說,詩歌教育還是一個文化方面的問題。它的解決應從兩方面著手。第一,詩歌的教育,和個人的成長有關,和個人的生命機遇有關。說到底,一個人如何面對詩歌,如何和詩歌發生關系,是一種自我教育。作為一種自我教育,它可以說是不受限制的。它可以開始在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的任何年齡階段。在成長的年代,一個人八九歲讀《紅樓夢》,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那么,同樣,由于某種機緣,一個人十歲左右讀惠特曼,讀里爾克,讀海子,也該算是十分特例的事情。一個人閱讀什么,這其實是一種開放的生命情境。所以說,我們必須改變我們自己的某種想法。
第二,我們能做的另一件事,是發出一種文化呼吁。強調一個人的詩歌教育事關他的生命智慧的養成。一個人所擁有的詩歌教育,可以拓展他自身的生命視野,強化他的生存洞察,提升他的人生境界。這樣的文化氛圍的營造,也是十分重要的。現代的社會文化格局中,對詩歌的無視,甚至輕蔑,太根深蒂固了。而我們自己有時也會深陷在一個輿論的裹挾之中,跟著叫嚷—詩歌是無用的。詩,其實從來就不是什么有用或無用的事兒。詩是一種生命現象。詩是一種最根本的生命能力。我們必須這樣講述詩的故事,必須這樣描繪詩的形象。
耿占春:今天大家講了方方面面的問題,從詩歌教育的作品選擇、判斷力與良好趣味問題開始,到對詩的晦澀的理解和審美動機的重申,從“去中心思想的專制”到現代詩作為一種個人教養問題,各位老師都表達了許多靈機一動也是深思熟慮的想法。希望這些想法不是被三月的一陣清風吹散,而能夠被聆聽被質疑被討論,我們的期待不僅是中小學語文教師什么時候懂得闡釋現代詩,更期待著孩子們能夠通過現代詩的閱讀,開啟新的感知領域,豐富語言和提問的方式,獲得對意義的新體驗,而不是習慣于語言的陳詞濫調,一旦面對意義的繁復就不知所措,在需要感受力去認知、闡釋的符號面前蒙頭轉向,稀里糊涂;也期待著什么時候我們的人文學者,即那些哲學家、社會學家、倫理學者、傳播學者,還有文學批評家……能夠內行地闡釋與引用現代詩的時候,我們就真的才算有了一種“知識共同體”,才擁有可以共享的意義資源,可以共享的經驗、感知與符號表達。這意味著,改進詩歌教育、增進闡釋詩歌的能力,不僅是中小學教育的問題,不僅是詩歌圈子里的課題,也是更廣泛的思想層面上重新構建知識共同體的一項事業,是與現代歷史以來社會啟蒙并進的一種“向內啟蒙”的志業。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