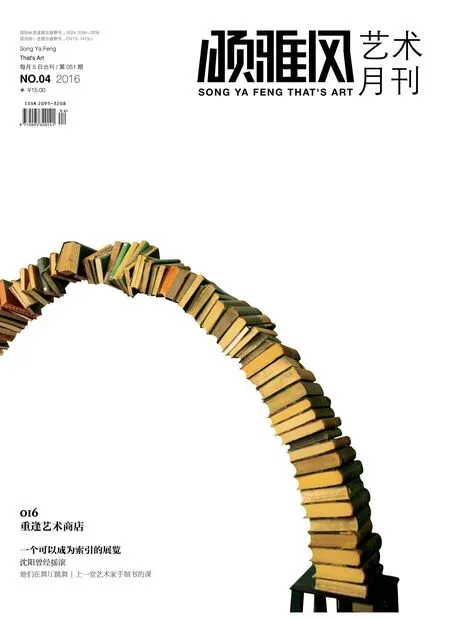一個可以成為索引的展覽
文/李璠 圖/芳草地畫廊
AN INDEX IN STILL WATER
?
一個可以成為索引的展覽
文/李璠 圖/芳草地畫廊
AN INDEX IN STILL WATER

除了欣賞展覽中那些具體的作品,并體會其中哲思的同時,我倒更愿意把鄭路的展覽“唯止”看作是一個可以成為拓展“知與感”的索引式展覽。這些作品大多從人類文明的各種普遍存在獲取靈感,既可以是白居易的詩歌,也可以是三島由紀夫的小說,或是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又或是愛因斯坦的一句話。

鄭路《三千米煩惱絲》不銹鋼絲尺寸自由2016年
鄭路在芳草地展覽館的首個個展“唯止”精心挑選了一個十分詼諧的日子,4月1日,既繞開了大部分展覽熱衷于周六開幕的習(xí)慣,也不失為令人印象深刻的宣傳捷徑。素白的展覽海報上由“止”字延伸出來的清晰冷靜的分割線倒也和鄭路的性格十分貼切,預(yù)示著此次展覽展出的8件以雕塑、裝置及新媒體等多種呈現(xiàn)方式的作品,將由“止”為主軸被貫穿起來。
除了代表鄭路之前風(fēng)格的雕塑《玩止水》《潮騷》之外,其他的包括《冬至》《三千米煩惱絲》《洞庭風(fēng)細》《心外無事》等在內(nèi)的6件作品都屬于新作品,且都是比照芳草地的展陳空間專門設(shè)計和布置的,不能不令人感嘆鄭路勤勉和精細的態(tài)度。而當你走近這些新作細細觀賞時,不難發(fā)現(xiàn)鄭路的這些作品除了充分地調(diào)動光、彩、空間、時間的元素與水的特質(zhì)結(jié)合,來達到層次豐富的感官體驗之外,更是從多元文化資料庫中延伸出來的靈感。換句話說,盡管每件作品在語言上都有著整潔大氣的鄭氏風(fēng)格,但幾乎每一件作品都有一個相對明確的傳統(tǒng)來源,而這些多樣化的傳統(tǒng)無時不刻地展現(xiàn)著屬于這個時代信息量最為廣闊的一面。

01鄭路《洞庭風(fēng)細》不銹鋼、影像直徑640cm 2016年

02鄭路《潮騷》不銹鋼、烤漆500cm×410cm×280cm 2016年
熟悉鄭路的人都應(yīng)該會對他的雕塑《玩止水》有深刻的印象,這件以白居易詩歌《玩止水》文字構(gòu)成的雕塑,造型瞬間定格的運動的水。大量的辭藻除了得到了一種密集的意象外,還產(chǎn)生了一種弦外之音的敘述。然而作為此次展覽承前啟后的序幕,《玩止水》是鄭路思緒的新開端。
如策展人黃篤所言:“鄭路或用水或日光作為介質(zhì),借用‘時間’與‘水’和‘光’之間共存的‘變化性’概念進一步討論物質(zhì)的‘存在’和‘變化’過程及其關(guān)系,進而掀開了與之相關(guān)的時間、空間、語境、條件、過程、狀態(tài)、心性等聯(lián)系。他最終以當代語言賦予或表現(xiàn)了它們以虛靜氣闊和恢宏意境的美感,使作品所蘊育的歷史與現(xiàn)實、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顯性與隱形、詩意與視覺,生命與象征的意涵得到充分的視覺展現(xiàn)。”
所以,除了欣賞展覽中那些具體的作品,并體會其中哲思的同時,我倒更愿意把鄭路的展覽“唯止”看作是一個可以成為拓展“知與感”的索引式展覽。這些作品大多從人類文明的各種普遍存在獲取靈感,既可以是白居易的詩歌,也可以是三島由紀夫的小說,或是美國好萊塢的電影,又或是愛因斯坦的一句話。這些作品脫胎換骨,內(nèi)化于心的過程,都確確實實以“鑒”的形式映照和啟迪著觀者(鄭路的“唯止”正是假借《莊子? 德充符》中的“人莫鑒于流水,而鑒于止水,唯止能止眾止”,達到真正“止”的境界,才能停止一切動相,唯“止”能“鑒”)。
比如大眾都十分熟悉的馬遠的《水圖》,其中有一幅正是《洞庭風(fēng)細》。“波浪如鱗,不激不怒,使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只不過這一次,鄭路用不銹鋼媒介,以浮雕的形式再次呈現(xiàn),將古畫微妙靈動的意境停留在光影之中——運用記錄下的太陽光耀活動,以幻燈投射在直徑六米左右的圓盤上,在室內(nèi)形成一個亦真亦幻、波光淋漓的動態(tài)波紋。從古畫到固化,再到光影,《洞庭風(fēng)細》經(jīng)歷了從創(chuàng)作到再創(chuàng)作的反復(fù)還原重置的過程。這件作品,我坐在它面前的長椅上足足盯著看了20分鐘,恰因為那循環(huán)往復(fù)的細碎光屑實在太具有催眠氣質(zhì),讓人只想放空冥想,尤其是看多了當下過于喧囂奪目的很多展覽,更覺這種安靜的狀態(tài)難得。

01“唯止”展覽現(xiàn)場

02《洞庭風(fēng)細》創(chuàng)作過程
相比《洞庭風(fēng)細》的中國美學(xué)意境,《未知的圓周》除了形式上具有國際化氣質(zhì),更是偏向于物理性的感知體系。黑色不銹鋼球體為元素的空間裝置,大小不一、或聚或散,鏡面光滑的球體,在相互接觸、或與墻面聯(lián)系之處,各自有著一環(huán)一環(huán)的凹凸水紋;這些從實體轉(zhuǎn)化而出的漣漪,一方面暗示了互動可以同時證明自身和他者的存在,一方面也呼應(yīng)了科學(xué)大師愛因斯坦的名言:“當知識之圓不斷擴大時,未知的圓周也一樣。”
與愛因斯坦名言同時貼在墻上的還有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的那句名言:“也許是天生懦弱的關(guān)系,我對所有的喜悅都摻雜著不祥的預(yù)感。”配以與其小說同名雕塑《潮騷》在鏡面上倒像映射,似乎也能看到三島由紀夫剖腹那個瞬間內(nèi)心的狂狼。作品截取了海浪的一個斷面,一個沒有起始的浪,將前面眼神的部分過渡為瓶頸的鋼板,作為終結(jié)。作品采用反常規(guī)的呈現(xiàn)方式將海浪倒置,巨浪從天而降,營造了另一種場景效果和閱讀情境。而當觀眾在鏡面反射和真實空白之間找尋邊界的時候,時不時會有好奇的孩子從作品的一端穿過走到另一端,許多保守謹慎的大人們才恍然大悟。
《雨鼓》《心外無事》《冬至》則從芳草地實際空間中直接獲得靈感,在這個空間里,雨天的聲音、嘈雜的人聲、冬至射入的暖陽都成為了鄭路用作品重新和這個空間對話的依據(jù)。這三個作品可以說是此次展覽里感受性非常強的作品,《雨鼓》直接采用僑福芳草地大廈頂部結(jié)構(gòu)的原材料ETFE膜來進行再創(chuàng)造,覆蓋于整個展廳頂端,再配以機械鋼珠裝置,觀眾可以自由穿行其間,將整個空間模擬為一個鼓的發(fā)聲現(xiàn)場。而這一切則得益于對雨季里芳草地的動態(tài)印象。《心外無事》則將展廳外部的陽光通過柱體內(nèi)部的鏡面結(jié)構(gòu)折射進展廳,使其投射在一個小的盆景上。將展廳外部商場內(nèi)嘈雜的聲音收納,并傳導(dǎo)進展廳。這種聲源呈線性傳導(dǎo),觀者只能在特定角度聽到聲音。如深山中的花,未被人看見,則與心同歸于寂,既被人看見,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冬至》則用視頻的方式記錄冬至當天展館內(nèi)日照變化,將金色亞克力切割成日光的輪廓,并懸浮固定在天花板或墻壁上,將其逐一定格。4月展覽開幕時,太陽逐漸向北回歸線直射,展廳內(nèi)的日照時間日趨變長,日影逐漸變短,和預(yù)置的金色亞克力“日光”部分重疊,但大多數(shù)已經(jīng)逐漸分離,從而形成了時間、空間及物質(zhì)之間在視覺維度上的錯亂與重置。當然,這些過于解析式的話語只能大概描述作品形貌,要讀懂這些作品,就請在展覽館的雨天來,在狂歡的購物節(jié)來,在冬至的下午來,才能體會這其中的美感。

“唯止”展覽現(xiàn)場


鄭路
《雨鼓》(細節(jié))
綜合材料
1100cm×780cm×340cm 2016年
最值得玩味的《三千米煩惱絲》,有著佛語解惑般題目,其創(chuàng)作動機卻是來自于一部美國電影《歡樂谷》(Pleasantville,1998)。一根長度差不多三千米的不銹鋼鋼絲,鍍有七彩的金屬絲線,隨意地纏繞并充斥整個空間,綿密而又虛幻,像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亂發(fā)。但如果你就此認為,這是一個規(guī)勸世人斬斷情絲的作品就太過想當然了。借由鄭路的這個作品,我回來后搜了這部我從未聽說過的電影。從劇情來看,頗有點當下流行的穿越劇的味道:David是一名沉迷于50年代黑白連續(xù)劇《歡樂谷》的內(nèi)向小伙子,在一次和他姐姐Jennifer爭奪電視遙控器的過程中,兩人鬼使神差地進入到《歡樂谷》的劇集中。在歡樂谷里,性別差異不明顯,夫婦結(jié)婚后分床睡,空氣永遠是72華氏,總之,一切都穩(wěn)定而舒適,更沒有人質(zhì)疑過這是否就是美好的生活。David如魚得水,而Jennifer就很不適應(yīng)。在她看來,這里的生活需要刺激和改變,她也的確這么做了,歡樂谷的生活因為她由黑白變成了彩色。
“歡樂谷”基本上是古典的正面烏托邦的化身,然而影片本身正是對這樣一種所謂的完美社會秩序進行質(zhì)疑,而其中最關(guān)鍵的因素正是以色彩作為隱喻。顏色的變幻就是“選擇”,是“秩序”的破壞。只有當人真正做出改變的時候,才會出現(xiàn)色彩,而與此同時,成為一個秩序外的異類意味著伴隨著各種不確定的代價。由此,《三千米煩惱絲》的彩色讓人在致密的壓抑感中獲得了一種奇特的愉悅,從中也能感到對于勇于承擔的個性、反抗、改變的直面與贊頌。
由“唯止”感到的是心的靜止感,和思想的漫游感。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從鄭路的作品中延伸到更多的領(lǐng)域,文學(xué)的、電影的、古典的、物理的。而我們唯一要擔心的可能是在這么多平行延伸的線索讓人可思可鑒的時候,鄭路未來更想從哪一個小切口更深地震撼我們的內(nèi)心。廣與精中,確立一個更符合自己的面貌,對于藝術(shù)家,這正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取舍問題,一個實實在在要確知何可為何不可為的糾結(jié),或許考驗鄭路定力的時刻才剛剛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