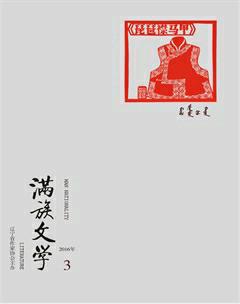論近年遼寧抗戰題材傳記文學創作的藝術創新
曉寧
黑水白山,被兇殘日寇強占。我中華無辜男兒,倍受摧殘。血染山河尸遍野,貧困流離怨載天。想故國莊園無復見,淚潸然。
爭自由,誓抗戰。效馬援,裹尸還。看拼斗疆場,軍威赫然。冰天雪地矢壯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復東北凱旋日,慰軒轅。
——趙尚志《黑水白山——寄調滿江紅》
東北黑土多悲情,壯士從容慨而慷。
這首又名《從軍歌》的曲詞,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表達了作者誓死報國、抗戰到底的決心。此歌悲壯有力,氣勢磅礴,曾在東北抗聯部隊中廣為流傳。的確,那段血與火的歷史給我們東北的白山黑水留下太多斑駁的記憶,而遼寧,由于特殊的歷史機緣在抗日戰爭中始終處于風口浪尖之上。作為后人的我們,對先烈的深情緬懷、對歷史的真實再現與深刻反思之后,搶救殘存史料,為前人修史做傳,為后人留存記憶、寫民族魂魄、燭照未來之路,更成為我們傳記文學作家肩負的神圣歷史使命。
近年,遼寧涌現出眾多以抗戰為背景題材的傳記文學作品,如遼寧少年兒童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紅色少年讀本——抗戰鐵血關東魂”系列英雄傳奇,包括常星兒的《馬占山傳奇》、胡世宗的《趙一曼傳奇》、肖世慶的《李紅光傳奇》、劉兆林的《鄧鐵梅傳奇》、李燕子的《李兆麟傳奇》、王鴻達的《冷云傳奇》、白小易的《馮仲云傳奇》、肖顯志的《黃顯聲傳奇》、孫少山的《楊靖宇傳奇》、李文實的《周保中傳奇》、于德北的《閻寶航傳奇》、周蓮珊的《趙尚志傳奇》等多部傳記作品。另外,還涌現了徐光榮的《趙一曼》、王海晨 胡玉海的《世紀情懷——張學良全傳》、徐徹的《張作霖》《張學良》、陳醒哲的《王鐵漢將軍傳》《鐵血雄魂——唐聚伍與遼東抗日義勇軍血戰實錄》、王興華的《錫伯夫妻抗日傳奇》《小八路張一波——風雨一生寫傳奇》等作品,從不同歷史人物身上折射出東北人民抗戰的宏大歷史主題和生發場景。
通過對近年遼寧抗戰題材傳記作品的閱讀與研究,筆者發現新世紀以來的傳記文學作品,在堅持傳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秉持中國史傳敘事傳統的創作觀念主導的總前提下,還生發了屬于自身在藝術探索上的獨到之處。這種創新是應和了時代精神的召喚,把握時代精神的要求,在尊重歷史的前提下,更為注重傳記文學作家的自我塑造、自我提升的能力。作家在歷史人物面前、在史實分析面前更自信,自我言說的空間有很大拓展。并且在歷史價值觀演進的同時,傳記文學作家更注重將史實性與文學性最大限度地進行了接軌,對故事的推進、人物形象的塑造、文本的可讀性、藝術化表達方面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使得新世紀的遼寧抗戰題材的傳記文學創作取得了突破性的創新。這種創新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抗戰題材傳記文學的文本中可以看到唯物主義歷史觀價值觀的演進與創新。
歷史唯物主義價值觀認為,一切歷史都是變動的、不斷向前發展的。所以要寫好人物傳記,必須了解人物所處的歷史環境與時代背景,把人物置于一定的歷史環境和時代背景之中,抓住人物本質,從環境中說明人,論其世知其人,才能寫得典型真實。同時還應把所寫的人物放到他所處的社會關系中去,從表面現象深入到人物和各種社會關系的內在聯系,抓住人物的本質進行記述。正如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任何人的思想和行動都受一定的社會關系的制約,人物傳記就是要寫出一定的社會關系造就了一定的人,而這個人又怎樣對當時的社會關系施加一定的影響。馬克思的論點為人物傳記的創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指導思想,也為真實地描述人物的本質特征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遼寧的傳記文學創作正是遵循了這樣一種唯物史觀,在具體的挖掘史料,再現人物過程中又不拘泥于刻板的史實,而是盡可能地復原真實的歷史,對一些模糊的歷史資料進行了合理的論證與演繹,確立屬于自己的價值判斷。
如“紅色少年讀本——抗戰鐵血關東魂”系列英雄傳奇這套叢書,把愛國主義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用生動形象的人物、用一個個具體的戰爭場面、用細膩而又充滿感情的語言表現出來,在不知不覺中,拉近了孩子們與抗日英雄的距離,這樣就輕易地觸發了孩子們的愛國主義熱情。另外,它不僅為那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英雄立傳,還添加了像馮仲云、周保中、閻寶航、冷云、黃顯聲、鄧鐵梅這樣的“無名”或者“無大名”的英雄,讓孩子們去認識他們,去認識歷史的本來面目。
東北抗戰,是中華民族最艱苦、最頑強的一段斗爭歷史。叢書中收進的十二位抗日英杰,涵蓋了整個東北抗日戰場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較有代表性的人物,突出大視角、注重文化的傳承性,同時也富有時代氣息,注重藝術感染力,為青少年喜聞樂見。通過先烈們的斗爭故事,再現他們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無怨無悔獻身的精神,也是用一種新的形式對青少年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熏陶和教育,可以進一步塑造青少年一代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是當前非常必要的,可以說這是一種有創意的嘗試,必將收到良好的實際效果。
又如,《鐵血雄魂——唐聚伍與遼東抗日義勇軍血戰實錄》,是傳記文學作家陳醒哲繼《王鐵漢將軍傳》和《盛京醫事》兩部傳記之后的又一部四十萬字的長篇力作,亦是他的“遼寧史傳”系列三部曲之一。作為長期持續關注東北抗戰史特別是遼寧抗戰史的專家,陳醒哲不辭勞苦實地調研采訪,多方收集資料,潛心分析研究。憑借一個史學家的特有歷史觀和學術品格,客觀、清醒、理性地還原了那段幾乎要埋藏于塵埃之下的血雨腥風的歷史。真實地再現了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運動不屈不撓的斗爭,挖掘了抗日志士、歷史人物金戈鐵馬、熱血豪情、氣吞萬里如虎,誓死捍衛祖國山河的大義精神,實則令人感懷。
全書以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中國人民奮起抗爭的一段轟轟烈烈的抗爭史為背景,敘述了作為東北抗日義勇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唐聚伍為首的遼寧民眾自衛軍在遼東地區的抗戰史實。還有遼寧民眾自衛軍后期的抗戰記錄,以及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后,唐聚伍再次組織東北游擊隊出關抗戰,直至血染疆場、以身殉國的血戰歷程。全書通過詳細記述抗日義勇軍從組建到發展壯大、抗擊日寇殊死搏斗的經過,塑造了以唐聚伍為代表的,包括馬占山、李潤春、鄧鐵梅、苗可秀、王鳳閣……等諸多抗日將領的英雄群像;再現了歷史烽煙下中國人民捍衛國土家園、捍衛生命尊嚴,堅決鏟除侵略者的帶有民族血性的英雄壯舉。同時,這本書也揭示了遼寧抗日義勇軍抗戰的艱難復雜過程,他們心憂國難,面對強敵,毫不畏懼,而是奮起反抗,以生命熱血保衛祖國,這是一種為民族大義而不惜個人犧牲的英雄主義精神,更是激勵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不斷前進的重要精神動力。無論是主人公唐聚伍,還是其他英雄人物,他們的身上都閃耀著濃重的愛國主義光輝。本書用重筆刻畫了主人公唐聚伍的武將形象,以誓師抗日、到遼東幾次著名的戰役,一直到轉戰熱河參加長城抗戰,其部隊成為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創作的“原型”,到最后“血沃平臺見忠魂”,以身殉國。他英勇壯烈地踐行著自己的血誓:“殺敵討逆,救國愛民”。作品對東北抗日義勇軍其他英雄的細致刻畫與描繪,也都尊重史實,真實再現,令他們的形象與主人公彼此烘托,共同譜寫了一曲英雄贊歌。所以,本書的史實與信息容量是非常豐厚的,是一部研究抗日戰爭史、特別是東北抗日戰爭史的確鑿史料和豐富資源寶庫。endprint
可以認為,遼寧的傳記文學創作,在堅持正確唯物史觀的基礎上,勇于在前人沒有開拓過或開拓不足的疆域內探索新的創作生長點。作家打破歷史評價的陳規,貼近人民、貼近土地,以田野調查的方式捕捉到最鮮活的歷史場景、人物活動,歷史在這里不再冰冷,而是一副生動的生活畫卷。
其次,遼寧抗戰題材傳記文學創作體現了對中國史傳敘事傳統的繼承與創新。
“秉筆直書”歷來是中國史傳文學的傳統,不虛構渲染,不隱惡揚善,不拔高溢美,不貶責降低,據事“直書”,只有做到“情真而不詭”,“事信而不誕”,才能有益于人,傳之久遠,這也是史家做傳的基本遵循。遼寧作家很好地遵循了這種中國的史傳傳統,以真誠之心、求實態度、細心考證、嚴謹取舍,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寫出了歷史的本來面目,特別注意從人物的復雜性中對人物作出公允的評價。
歷史是絢麗多彩的萬花筒,歷史人物有其復雜性。在錯綜復雜的歷史條件下,大量的歷史人物功過摻合,斑瑜互見。有的人功大于過,有的人過大于功。因此,我們對歷史人物要全面研究,具體分析,一分為二地看人物的好與壞,功與過,絕不能因為一個人后期不好,就把前期的功勞一筆勾銷,也不能因為做過一些錯事,就把其他方面的貢獻全部抹煞,而是要尊重事實,尊重歷史。所以寫人物傳記,一定要從當時社會歷史的客觀條件出發,實事求是地記載和評價歷史人物,真實地反映歷史人物的本來面目。
由王海晨、胡玉海二位歷史學家共同創作的《世紀情懷——張學良全傳》,作為張學良逝世之后第一本“全傳”,以近百萬字的宏大篇幅再現了張學良這位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創造者、推動者,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人生傳奇履歷,以及伴隨著他個體生命而推進的跌宕起伏的整個20世紀中國歷史。在中國文學史上,通常以個人的“離合之情”來書寫國家的“興亡之亂”,這似乎已成為一種象征式、寄興式的寫法,這種以個體人生折射時代歷史的寫法,受到讀者的一貫認同,符合中國人傳統的審美價值觀。
而本書,對傳主張學良這一特定人物的選擇則同樣沿襲了此傳統,因為他特殊的歷史際遇,使得他個人的“離合之情”完全與國家與時代的“興亡之亂”緊緊地毫無縫隙地粘連一處。他,就是一部歷史,一部永遠解讀不盡的書。他身前死后,千秋功罪,有太多值得探尋之處,特別是他的人格個性,他在歷史轉折關頭的所做所為,對整個民族命運的影響都具有深刻的意義,值得開掘的空間很大。本書正是憑借著這樣一種宗旨“用治史的方法寫人物,通過人物寫歷史,寫人物在歷史上留下的刻痕……用哲學的思辨寫傳主的人生軌跡……借用文學的筆法復原歷史,給讀者一個可以用眼睛看,可以用耳朵聽,可以用手去觸摸,可以用心去碰撞,可以和傳主去對話,也可以和世人去對話的立體的真實。”于雕刻人物豐滿性格的同時,勾沉了百年中國近現代史。對歷史上重大的事件、重要的轉折、主要推動者均給予價值和道義的考量、判斷。如此開闊的視野,是源于作者宏富的知識積累,對歷史的理性分析,科學客觀的治學方法,最重要的是作為知識者的社會責任感和對歷史負責的態度,這在全書中有著多處體現。
張學良,作為一個頗具傳奇性的歷史人物,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太多。據不完全統計,僅關于他的傳記性作品就不下幾十部,若加之各種體式的文學創作、影視劇改編等等形式的文藝作品,估計不下百余部。這樣密集地被書寫、被傳頌,被過度闡釋,反復地進入人們視野當中的歷史人物,想推陳出新,有所創意地再現他,其難度相當之大。因為受眾已經對其人生履歷基本情況爛熟于心,毫無陌生之感,這無疑為做他的“全傳”增加了很大的難度。初觀本書,其似乎依然按照一個時間的邏輯順序來表現張學良的人生軌跡,與其它同題材的傳記作品并無二致。但是隨著閱讀的深入進行,我們會發現,在詳盡地記述張學良的人生故事之下,本書還是有所側重的。即以刻畫人物性格為主線,重點塑造了張學良做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的性格特征,并以他人生中三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即“東北易幟”、“調停中原大戰”、“發動西安事變”為主線,在歷史轉折關頭凸顯他的命運和他的歷史影響。可以說,作者在這三個重要事件上所傾注的筆墨和對歷史問題的反思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本書的史料價值和文學價值,也鮮明地表達了作者所持有的歷史觀、哲學觀。
比如,在全書開頭的序言《張學良與20世紀中國》中,作者就張學良一生中幾個重大的政治軍事事件給予了澄清和概述,反駁了一些已有的不客觀的歷史觀點,客觀公允地亮出鮮明的論點。如“我們既要肯定張學良和東北地方當局爭取中東路權益和接管中東路的動機,又要批評他們在行為上的盲目性,致使良好的愛國動機,卻造成了辱國的結果。”、“張學良作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東北地區的封疆大吏,‘九一八東北淪陷,他是難辭其咎的。”、“我們之所以說張學良是‘千古功臣,是因為張學良有大功于國家和中華民族。”等等。作者首先在大的是非觀念上定下了全書的基調,又在以后的各個章節中詳盡地分析了逐個觀點,特別是對張學良以愛國主義為主調,不惜犧牲個人利益、秉持民族大義的精神形成是家庭與時代各種因素共同復雜作用的結果,進行了詳細的揭示和闡述。使讀者在敘事過程中看到一種層層遞進的因果關系,看到一個人的思想和性格的形成過程,是歷史的多重因素交相重疊、互相作用的結果。這是符合唯物史觀的一種寫法,一種可信的判斷和思考。
遼寧的傳記文學作家在堅持中國史傳敘事傳統的前提下,敢于突破,銳意創新,大膽推演,做出符合史實的結論,顯示了特有的創作勇氣。
再次,近年遼寧抗戰題材傳記文學在藝術表現手法上,探索了將史實性與文學性相融調和創新之舉。
通常來講,史傳式作品在完成了內容的考證與再現之后,其寫法就顯得至關重要,怎樣推進故事、塑造人物,完成對歷史的表達,成為每個史傳作者面臨的問題。遼寧抗戰類傳記文學在注重史實考證方面做足功課之后,在文學性的探索、如何提供完美的藝術表達方面同樣做了很多實踐。重點在于如何將浩如煙海的歷史材料有效地結構成傳記文學作品,以發揮最大的功效。遼寧的抗戰題材傳記文學創作盡量地“借用文學的筆法復原歷史”,給讀者一個可觸摸的、可對話的、富有硬的風骨和動的血脈的傳奇形象。而這一想法的實現,則是通過故事化的途徑來實現,以故事的講述、部分可靠虛構式的小說化情節、人物語言神態的描摹來完成的。在故事化的同時,又不乏理性的思索。endprint
王興華的長篇傳記文學《錫伯夫妻抗日傳奇》正是對歷史的又一次深入打撈。他發掘書寫主人公陶翙鳴、關玉梅傳奇人生的同時,有意或無意間對那段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驚心動魄的時段進行了回顧,將特殊時代造就的英雄傳奇故事作了詳盡的文學化的放大,令熟知者或不熟知者對抗日戰爭,尤其是東北抗日戰爭的歷史有了感性的認識。他在尊重客觀史實的基礎上,又對歷史做了故事化的加工,令讀者在比較輕松流暢的閱讀心態下完成對歷史鋒煙的再次回顧。這部人物傳記能夠立足于遼寧(沈陽)本土,輻射整個東北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的最前沿,細膩入微地刻畫了錫伯族主人公陶翙鳴、關玉梅夫婦身上那種為革命事業不惜犧牲一切的大無畏英雄精神,對他們作為革命者機智果敢、無私美好的人性進行了熱情的謳歌。在當下以經濟利益為驅動的社會思潮對人們影響頗深的情況下,面對傾斜的人文道德底線,個人私利與欲望的泛濫,本書無疑為人們唱響了一曲為全人類美好的未來,重振自我犧牲精神的樂章。
如果說這本書的最大意義在于通過對英雄傳奇的復原來記錄塵埃遮蔽下的歷史,在平實的敘述中激發人們對歷史人物傳奇人生的崇敬,從而升華為深沉的愛國主義情感,永恒地激勵后世之人,那么這本書在敘述及藝術技巧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可貴的探索,值得我們關注。總的來說,即是一個“傳記文學怎樣寫?”的問題,既宏觀,又具體可微,并且不可或缺。具體到本書中,面對繁多的革命史志、采訪手記等寫作資料,如何復原近一個世紀前人們的生活狀態,英雄的人生足跡,將最真實場景生動地展現給當代讀者,是需要作家反復打磨的。作者顯然找到了很好的方式,他在充分注重歷史真實性客觀性的前提下,采用了故事化的敘述方式,對一些情節、場景、人物對話、細節、行動進行了適當的虛構,如此便能在敘事中娓娓道來,不乏生動、精彩之筆,引人入勝。比如在寫到主人公關玉梅領導抗聯部隊反擊“討伐”、奇襲遠征等章節就描寫得非常生動明快、富有傳奇色彩,極大地豐富了文字的可讀性。同時也在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中凸顯了人物性格,令人看到了一對勇敢、頑強,有著堅定共產主義信念的紅色夫妻的光輝形象。同時,整部書的語言樸實、細膩、感情真摯,在富于東北地方特色的基礎上,又加上適當的注釋,也非常明晰易懂。
近年,遼寧傳記文學創作在藝術表現上有諸多的藝術探索與創新,總體上可讀性增強,文學性提升,更為讀者喜聞樂見,這與時代的召喚與作家的自覺性密不可分。
綜上,舉目當下文壇,目力所及之處,多是對報告文學(包括傳記文學)創作的一種擔憂和危機之感。許多專家學者提出這種文體的創作乏善可陳,從內容到寫法少有創新,已經陷入一種自我循環的誤區,或為文學之外的利益驅使,做出違背作家道義良心的不實的寫作。可見,報告文學、傳記文學作家必須面對著從思想上和藝術上重新的洗滌和調整,重新尋找到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的文本言說方式,重振紀實性文學體裁的魅力,使其發揮出更大的社會功能。認識歷史,總結當下,以期建立更民主、更理性、更文明的社會。同時,紀實性作品的文體創新,也是時代提出的一種迫在眉睫的問題。在信息時代、媒體時代,信息爆炸,快餐式的文化消費觀念流行,傳記文學也必須探索自身創作的調整,適應閱讀理念的變化,如果一味抱殘守缺則會失去更多的閱讀人群。筆者認為,傳記文學一方面應該繼承一些中國傳統傳記文體的優勢,同時應融入更多現代理念和語言形式的變化,在文本長度上適當縮減,更符合現代人的閱讀習慣。在語言的表述上應更富有張力和沖擊力,形成鮮明的效應,才能先聲奪人。所以,時代給傳記文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給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必須以新的姿態來挖掘歷史、表達歷史,將現代人對歷史的理解用現代的形式表達出來,以新鮮的經驗、準確的判斷、感性的觸摸、理性的升華來打磨文字,找到歷史人物與現代文本的對接點,提供好讀好看的傳記文學作品。在這個意義上,遼寧的抗戰題材傳記文學創作做了可貴的嘗試。
〔責任編輯 叢黎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