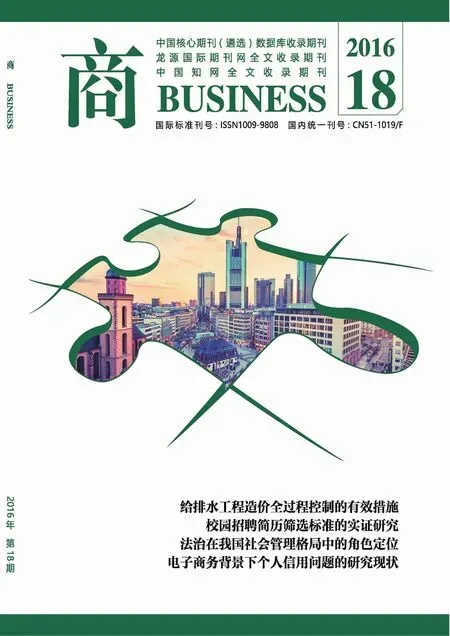我國“親親相隱”制度現代化的途徑
黃云龍
摘要:“親親相隱”制度是中國古代的一項基本法律制度,在歷史上發揮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在現代社會卻銷聲匿跡。我國現行刑法窩藏、包庇罪的主體范圍并沒有將親屬排除在外,而規定為一般主體。民眾面對親情與法律,很難做出選擇。所以,在刑事立法中應當適當縮小其主體范圍,使“親親相隱”制度成為刑法更具人性化的有力推手。
關鍵詞:親親相隱;窩藏包庇罪;現代化一、“親親相隱”制度在窩藏包庇罪中的現狀及其影響
從我國刑事法律的立法現狀來看,我國《刑事訴訟法》和《刑法》都傾向于處罰犯罪人的親屬拒絕提供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言和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幫助的行為。例如,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8條規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作證既是一種義務,這種義務是強制的,并不以證人與犯罪分子的關系而加以區分。同時,《刑法》第310條窩藏、包庇罪中,將該罪的主體設定為一般主體,同樣也反映了上述立法傾向。這種現實狀況使得犯罪分子的親人不但失去了拒證權,而且在某種層面上來講他們的人權也遭受了損害。[1]如若人們都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國家的威信將自己犯罪的親人親自送入監牢,那么這樣是不是一種對社會倫理道德的踐踏呢?在這樣一個情與法的天平上,難道人人都可以經受住嚴峻的考量嗎?這種情況下,我們確實需要冷靜的思考其所產生的影響,在我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與法律本身的沖突。法律具有懲戒犯罪、震懾預防犯罪的作用。且法律懲罰的都是惡性較高、危害性較大的犯罪行為。窩藏、包庇罪,在客觀上并沒有直接造成巨大的人身財產損失。只是親人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而做出的出于人的善良本性的行為,是不應該被視為嚴重的犯罪行為的。刑法的“謙抑性”也要求我們將這種行為排除在其外。先哲孟德斯鳩也曾在《論法的精神》中質問“妻子怎么能告發她的丈夫呢?兒子怎么能告發他的父親呢?為什么要對一種罪惡的行為進行報復,法律竟然規定出一種更為罪惡的法律。”[2]從刑罰的功能上來看,犯此種罪行的犯罪人并不會對自己的行為產生較大的悔過表現,沒有較強的羞恥感。相反的,犯罪人極有可能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符合道義的,是正義的事。加之社會上的輿論并不會對行為人加以大力抨擊,這更是降低了刑罰在社會中的威懾力。
(二)對犯罪人本身的影響。從實施窩藏、包庇的犯罪人方面,此類犯罪人一般都是出于對親人的愛護,在主觀上并不想觸犯法律,主觀惡性不強。主要是由于主觀過失,一念之差造成的犯罪,大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是當他們進入監獄,復雜的環境會不會使其產生不良的反應這很難說。在現行關押制度中,理論上初犯和慣犯應該分開管理。但是,我國監獄在實際操作中卻很難精準的達到這一水平,有時候近乎形同虛設。這種情況下,此類犯罪人又屬于初犯,在監獄中難免會受到其他犯罪人影響。或是教會其其他的犯罪手段,或是有意識無意識的沾染上慣犯的不良風氣。不但得不到教育改造,反而會給社會增加了不良隱患,這對其本身和社會都是另一個不好的萌芽。
其次,此類犯罪人在實施犯罪之后本身就擔驚受怕,想到親人為保全自己,自身也身陷囹圄,更是自責萬分。在這種情況下,此類人容易產生兩種狀況:一是感到社會與法律的不公,加深對自己的埋怨,自此便一蹶不振,變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廢人。二是在獄中聽到其他犯罪人的教唆,加深對社會的仇恨,出獄后實施報復行為,走極端路線。
二、“親親相隱”制度在其他法域的體現
在我們看來,西方社會都是務實主義,極有可能親情淡漠。事實上,在研究過西方一些國家的法律規定之后,筆者發現,“親親相隱”制度在許多西方國家的法律中都有所體現,包括《德國刑法典》、《日本刑法典》、《泰國刑法典》、《法國刑法典》等。例如《法國刑法典》第434-6條的規定與我國《刑法》第310條的規定較為相似,二者都規定了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幫助后的處罰,但不同的是,《法國刑法典》明確將犯罪嫌疑人的直系親屬,兄弟姐妹、配偶甚至將眾所周知的姘居的人都排除在該規定的規制范疇之外。該條規定明顯的體現了《法國刑法典》對于“親親相隱”制度的采納。
由于歷史原因,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的法律制度與我國大陸地區的法律制度存在差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屬于典型的英美法系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屬典型的大陸法系法律,臺灣地區法律較為特殊總體上屬于大陸法系法律,與此同時,也具有一定的英美法系法律的特色。表面上看,這三個地區都著西方特色,但是,這三個地區的法律對于“親親相隱”制度都有所繼承,典型的規定如《臺灣刑事訴訟法典》180條。該條法律明確規定以下幾類主體可以拒絕作證:第一,配偶、五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姻親。第二,家長或家屬。第三,與被有婚約者。
三、“親親相隱”制度在現代的可行性
(一)從證據制度方面。就目前我國司法實踐而言,證人證言仍然是一項較為重要的刑事證據。并且,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但是當證人與犯罪嫌疑人是親屬關系時,這種法律規定的義務是否合理值得我們思考。眾所周知,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回避的規定中,明確要求與案件又利害關系的司法工作人員應當回避,這其中的利害關系就包括親屬關系,筆者認為這是給予對司法工作公平公正的考量。那么,對與被告人有親屬關系的證人施加作證的義務筆者認為是不合理的。首先,讓一名證人提供自己親屬有罪的證言,這是不人道的。另一方面,在這種情況下,親屬的證人證言的可靠性也將大打折扣,即存在親屬做偽證的巨大的可能性。這種不實的證言,一方面會增加刑事審判障礙,嚴重的會使刑事審判活動走向歧途,嚴重影響刑事審判的公平公正。另一方面,法律勢必要對這種作偽證的行為進行評價,這就又會發起一個刑事訴訟程序,從而耗費大量的司法資源。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既然強迫被告人的親屬履行作證的義務,存在著上述的弊端,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不如將被告人親屬作證的義務轉變為被告人親屬的一種權利。即證人可以選擇是否作證,如果證人不愿作證,則證人可以選擇回避。
(二)從立法程序方面。大部分學者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都提出對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中的內容進行較大范圍的修改,廢除其中的硬性規定,增加一些彈性條款,并對“親親相隱”的主體、對象、范圍等做出明確規定。但是,在中國的國情下,面對如此龐大的受眾,我們無法那么容易的將其實現。所以,我認為應該將這種大規模修改變動改為推行試行條例,先在適合的試點進行普及,觀察效果。這樣做是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和輿論譴責,畢竟各個不同地區間都有各自的習慣和差異。根據這些差異,各個試行點可以將修改意見不定期的上報,以便立法機關可以最快的掌握試行的漏洞,以便及時更正補充。
從《刑法》規定來講,筆者認為,可以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對我國《刑法》第310條窩藏、包庇罪進行修改,即仿照《法國刑法典》的規定,將該罪的主體要件做出排除性規定,即將被告人的親屬排除《刑法》310條規定的犯罪主體要件之外,具體而言,親屬的范圍包括:配偶、直系血親、兄弟姐妹。但在修改的同時也應當注意,在我國《刑法》引入“親親相隱”制度保障被告人親屬權利的同時,也要注意維護社會安定,保障公民人身權利與財產權利。因此,應當對使用該條規定作出限制性規定,對于嚴重暴力犯罪,涉恐怖主義犯罪,不得適用該規定。
參考文獻:
[1]岳禮玲.刑事與人權保障[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李立眾.刑法一本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