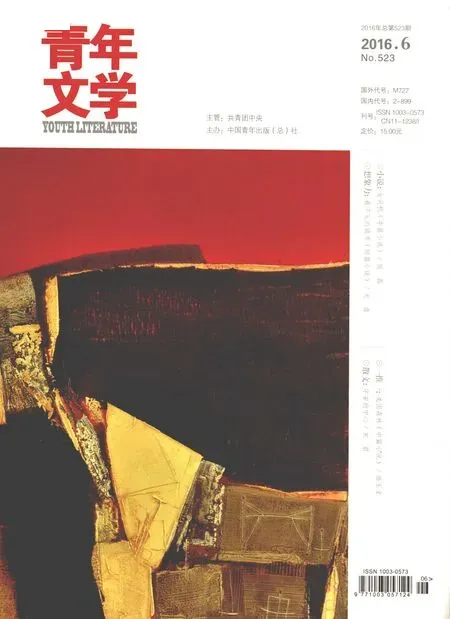記 食
⊙ 文/周潔茹
記 食
⊙ 文/周潔茹
樸田的早飯
吳小姐說要請我吃早飯。
可是我們并不在揚州,我只知道揚州的早飯好吃,我童年的時候父母經常帶我去揚州。我父母是這樣的,一個星期要上六天班的年代,他們在那個最珍貴的第七天洗完了被子,打掃好了房間,然后搭一班三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去無錫,吃一客王興記小籠饅頭。后來有了我,全家改去揚州,吃早茶,看一下瘦西湖,全是寒冷冬天里的事情。所以我的童年滋味,竟然是揚州,一個真的很瘦的湖,一個富春茶社,三丁包子,千層油糕,燙干絲,三省茶。
我也有三十年沒有吃到揚州的早飯了,我不知道揚州的早飯是不是有點變化,到底三十年了,人是面目全非了,包子呢?
而且我們也不是在揚州,我們在常州。
所以吳小姐說要請我吃早飯,我第一個想到的只能是德泰恒的豆腐湯。
所以吳小姐在電話里笑到喘不過氣來,等她笑完,我問她,是不是德泰恒已經沒有了?她說是吧。我說文筆塔還在的吧?她說好像吧。
我記憶中還有一些吃早飯的地方,比如義隆素菜館。
也不是它有多好吃,一個地方能夠被留下,刻在心里,肯定也是因為那些它與你之間發生的事情。
我在義隆素菜館碰到過我的化學老師,吃完面,老師跨上了他的自行車,跟我說再見,他都沒有像一個真正的老師那樣叮囑我要好好生活,以前上學的時候他也沒有叮囑過我要好好學習,他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給我看考卷上的51分,然后細致地把那個5改成了6,然后對我說,你母親還好吧?我老是想寫他家的事,可是他老是什么都不說,要不是我母親是他的同班同學,我就真的錯過了他家那風風雨雨的歷史長劇,我會以為他真的只是一個化學老師,紅鼻子,小個子,5改成了6真的一點都看不出來。
所以吳小姐說要請我吃早飯,盡管我不認為有什么常州的早飯可以超越義隆素菜館的素面和豆腐干絲,但是我愿意去觀察。
吳小姐的車停在我家樓下,我一時沒有認出來。
她的車,該是一輛黃色甲殼蟲,也就是他們講的,二奶車。吳小姐生氣地說,甲殼蟲怎么是二奶車了甲殼蟲怎么會是二奶車,迷你庫珀才是二奶車。不過那也是十年前了。十年了,誰不換個車,有的人二奶都換了十個了。我上了車,說,為什么是奔馳,那誰說的,“騎自行車哭,坐奔馳笑”?吳小姐白了我一眼,說,那是寶馬,那是寶馬好吧,“寧愿坐在寶馬里哭不要坐在自行車上笑”的寶馬。我說好吧我們去吃早飯吧。吳小姐的車開出去了一段,說,土豪才開寶馬。
車停在一片仿古建筑的大門口。
可以停的嗎?我問。
可以。吳小姐堅定地答。
真的可以嗎真的嗎?我又問。
可以可以可以。吳小姐答,沒有什么是不可以的。
我們肯定路過了一個名人故居,但是因為太早,門關著,我也沒有能夠進去看一眼,可是看了一眼也不會怎樣,名人都不是這里的人,他只是死在這里,這里的人對死在這里的人格外敬重,雕了像又故了居,這里的人卻對生在這里的人蔑視,很多人就跑到外面去了,死在別處。
吳小姐推開一扇木門,我瞬間落到了古代。一個院子,全是古代的家具,還有樹和水缸、蟋蟀和睡蓮,我站在大門口,不知道怎么辦才好。
坐啊坐啊。吳小姐說。
院子中央是一個小方桌,四張小板凳,我坐了下來。院子的四面八方就走出很多人,全是年輕的男人,每一個都長得一模一樣。他們在小方桌上放下了各種各樣的吃食,又散落到院子的四面八方。
一起啊一起啊。吳小姐說。
好啊好啊。他們溫和地答。
然后就剩下吳小姐和我,搖著扇子,開始吃早飯。
我吃到了糍飯糕和不夾油條的米飯餅,快要失傳的常州早點心。
太會買了。我說。
吳小姐一笑,說,他買的,他知道是什么,也知道哪兒做得最好。
我順著吳小姐的眼睛望過去,早晨清淡的太陽光,一個正在給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澆水的好看的男人。于是我中年的滋味,就是這樣一個院子,院子里一個穿著古代衣服的男子,水簾之下,竟然還出現了一道彩虹。
如果我是寫穿越劇的,此處該是《瑯琊榜》的第一集了,但是我不是,我吃完了糍飯糕,伸手過去取了第二塊米飯餅。
我還在輕工幼兒園上小小班的時候,每天早上的早飯,都是一塊米飯餅。西瀛里,一個只賣米飯餅的老奶奶,花手帕包住那塊溫熱的米飯餅,一路走,一路吃。女兒牽著母親的手,數著地上的方格,希望這條去幼兒園的路永遠也走不完。
遇到了一對要飯的母子。
女兒說,今天的米飯餅是苦的。
女兒說,那個要飯的小孩,給他吧。
于是缺了一口的米飯餅,由女兒的手,傳給要飯的小孩。
要飯的小孩接了過去,大口吃起來,站在要飯小孩后面的要飯的大人,也沒有說什么。
女兒回頭張望,他吃不吃得出來米飯餅是苦的?趕上班的母親快要遲到,心急透過了手心。終于還是到了幼兒園的大門口,女兒放聲大哭起來。
米飯餅
母親生在青果巷,母親的姐姐們都生在青果巷。外公去世,家道中落。姐姐們出外謀生,嫁人,或去工廠做工,母親還在新坊橋小學上小學,與外婆相依為命。放學回家,一碗冷飯,茶泡飯,已經很滿足,有時候冷飯也沒有,做完功課,早早上床,床邊的墻角已經長上了青苔,孤兒寡母的家。
所以到了早晨,母親上學前,外婆枕頭下摸來摸去,兩個角子,買一個米飯餅吃,是母親一整天的指望。
可是角子給了賣米飯餅的老太婆,卻沒有米飯餅拿出來。
母親在旁邊站了好一會兒,肚子咕咕地叫。鼓起勇氣問一句,最低的聲音,我的米飯餅還沒有給我。
賣米飯餅的老太婆叫起來,錢呢?你又沒給錢!
母親走開去,上學的時間到了,眼淚含在眼眶里。
母親再也沒有吃過一口米飯餅。
母親的女兒倒愛極了米飯餅,每天上幼兒園的條件,就是一塊米飯餅。
母親要搭公交車去上班,七路車,去是一個鐘頭,回又是一個鐘頭,每天送完幼兒園都要遲到,遲到就沒有全勤獎,獎金也不算什么,只是總被人嘲笑。
這個女兒總是發惡,要穿昨天的花裙子,要別前天的花手帕,樣樣滿足她,還是賴在地上。母親終于發怒,砸碎了父親的玻璃煙缸。問她到底還要什么,女兒望著碎了一地的玻璃,最后再要一塊米飯餅,當個臺階下。
女兒不去幼兒園。不合群的女孩,每天都孤獨,唯一的朋友是另一個被確診了的孤獨癥男孩。這個男孩有一天不見了,女兒鼓起勇氣問一句,最低的聲音。老師說他永遠不會再回來,因為他不乖,就像每天不睡午覺打擾到其他小朋友的你。
不睡午覺的女兒被關在儲藏室,直到母親來接才被想起來,放出來。這個女兒再也沒有睡過午覺,而且天大的黑都不能再叫她害怕了。
母親不說話,幼兒園門口賣手作的小攤,給女兒買了一只絨布做的獅子。
你不吃肉,也不要藏在碗底。母親說,藏到碗底下又有什么用呢?總會被發現。
女兒不說話。
這個幼兒園的飯已經是全城最好吃的了。母親說,可是你什么都不吃。
燉雞蛋讓我嘔。女兒說。
為什么?母親說。
女兒不說話。
你知道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小孩連一口飯都吃不上嗎?母親說。
燉雞蛋讓我嘔。女兒說。
為什么?母親說。
就像雞蛋死了,爛成一攤,女兒說。
燉蛋雞湯
妹妹不吃肉,大概是從五歲開始的,問她為什么?她說吃動物的肉很殘忍。可是哥哥就很愛吃肉,無肉不歡。
媽媽有一些吃素的印度朋友,她們講豆子里也有蛋白質,她們和她們的小孩都很強壯。于是媽媽給妹妹吃豆腐,妹妹只吃豆腐,也慢慢地長大了。
媽媽把妹妹帶去中國,媽媽小時候的朋友們很高興,因為這位媽媽總是不回家,她們都快要把她忘記了。其中一個朋友帶她們去吃最好吃的本地菜。
這個菜館是我的朋友帶我去的。媽媽的朋友說,一般的人找不到。
這個朋友的朋友正幫忙開著朋友的車,微微一笑。媽媽沒有說什么。非常好的車,連媽媽都不認得那是個什么車。
果真是弄堂底的一個菜館,外頭已經停了好幾臺好車,都是媽媽不認得的車。
媽媽朋友的朋友要到一個包間,外頭幾臺車都要不到的,包間里面卻很簡陋,只有一張桌子。媽媽朋友的朋友推開門走出去,自己端了幾碗元麥糊粥來,應該是非常相熟的菜館。
妹妹起先拒絕,按照媽媽另外一個朋友的說法,妹妹對食物有與生俱來的潔癖,只吃比較可靠的食物。媽媽請求她試一口,她試了一口,沒有表現出很強烈的反應,不厭惡,也不喜歡。
至于那些白切豬肝和糖醋排骨,她可以當作沒有看見。
上來了一盆燉蛋和一窩雞湯。媽媽朋友的朋友站起了身,給媽媽的朋友盛了一碗燉蛋,然后澆了一勺雞湯在上面。
妹妹就對媽媽說,你是不是很嫉妒你的朋友有這樣的老公?你的老公就從來沒有為你夾過一次菜。
媽媽朋友的朋友趕緊給妹妹也盛了一碗燉蛋,又給媽媽也盛了一碗,澆上一勺雞湯。
媽媽對妹妹說,親愛的,他們并不是老公和老婆,他們都有自己的老公和老婆,所以他們只是朋友。
于是妹妹對媽媽朋友的朋友說,謝謝叔叔,這是我吃過的最好吃的燉蛋。
媽媽的朋友突然哭了。
醬油拌飯
我第一次見到醬油拌飯是在柏拉阿圖城的一間日本餐館,兩個本科男生。落了座,一個男生要了一份加州卷,另一個男生只要一碗米飯。米飯端來,他把桌上的醬油滴了幾滴在米飯里,攪拌均勻,一大勺放入口中,臉上的表情都是滿足的。
快要二十年前的往事,那個時代還沒有深夜食堂,日本版的韓國版的,我只記得黃油拌飯,一塊黃油慢慢融化到熱米飯里,那一分鐘,都看得入神。
我寫信告訴父母這件事情。去國離家,每天與父母通一次電子郵件,報平安,也是寫日志,后來越來越忙,也就不寫了。但是留下了二十萬字的家信,我寫了十萬,父母寫了十萬,父母用的手寫板,辨識度很差,一個字,往往要寫好幾遍。
我在信里說竟然在美國看到醬油拌飯。窮的嗎?難道真有那么好吃?母親回復郵件說,小時家貧,醬油拌飯都吃不上,放學回家,冷飯都沒有一碗,只好做完功課去睡覺,后來上山下鄉,十年插隊,拌飯的只有咸菜,到了年關隊長說要清洗醬缸,倒出所有醬料,里面一只大老鼠,已經浸到皮脫肉爛,和咸菜混在了一起。原來知青們的這一年,吃的都是“老鼠咸菜”。
我出國的時候安慰母親,我不會苦的。母親說洋插隊也是插隊。送別的機場,母親紅了眼睛。我到美國的第一個傍晚,自己剪了長發,穿上圍裙,炒一盤豆角,炒了很久,豆角還是生的,我終于哭了。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她。
父親另外復了一封信給我,說他小時候就是吃醬油拌飯。醬油拌飯很好吃啊,父親還畫了一個笑臉。父親家里是有錢的,有錢人家的小兒子,也是看著臉色生活的,為了上學堂的錢,跟大哥低頭。筷子若是高了若是快了,哥嫂的眼睛都會看過來,寧愿自己摸到廚房的角落,盛一碗飯,醬油拌了,站著吃,可以吃兩大碗。正是長身高的年紀,哪顧得上什么體面。我小時候父親給我講過一個體面老爺的笑話,一個很要體面的鄉下老爺喜歡吃大麻糕,可是總有一些芝麻漏在桌縫里,芝麻很香,老爺很想吃,正好下人過來回報個什么事情,老爺機智,一拍桌子,豈有此理!芝麻從桌縫里彈了出來,老爺吃到了芝麻。父親講完總要哈哈大笑,我總是不明白他笑什么。如今想到他年幼時站在廚房吃醬油拌飯,我也要哈哈大笑,都笑出了眼淚。
大麻糕
有人從家鄉來,問我帶什么給我才好。我不好意思說我要青果巷巷頭上現炸的蝦餅,我就說什么都不要。他們就說,大麻糕吧,好不好?
我的家鄉能夠拿得出手的吃的,只有大麻糕?
只有大麻糕。
大麻糕是什么?其實不是大麻的糕,只是芝麻和面粉做成的餅,甜的或者咸的,每天的早飯,配一碗濃茶,或者豆腐湯。
我很不喜歡大麻糕。大人們又總喜歡買來吃,于是很勉強地吃下一塊椒鹽小麻糕,皺著眉。其實還挺好吃的,我只是厭倦這樣的生活,空心燒餅,為什么要每天每天吃,就不能吃點別的嗎?
我也經常見到麻糕桶。我小的時候,做大麻糕的就都是外地人了。那些師傅站在麻糕桶的后面,餅坯蘸清水,一塊一塊貼入燒熱的大桶里面,小火慢烘,三分鐘就好,長鏟刀起出麻糕,再飛快地貼進新的生餅坯。總有老奶奶一次買走一爐的大麻糕,于是站著等下一爐,也不過幾分鐘。可是站在旁邊,都會覺得很厭倦。
我后來離開家,思念這個,思念那個,都沒有思念過大麻糕。
搬到香港,父母來看我,帶來了大麻糕。他們以為要和美國一樣,烤蘋果派送給鄰居們。可是香港和哪兒都不一樣。住在日本的朋友搬新家,要買禮物送給一條街的鄰居,禮物都不用很貴重啊,但是要花心思包裝,裝進禮物袋,一家一家去送。我說日本人的那一套很奇怪啊,一條咸菜都包得精美,要多假就有多假。我的朋友笑笑說,鄰居奶奶家的橘子樹長得真好啊,樹枝伸過墻頭,果子掉在了我家的院子里,我讓小朋友們把橘子撿到籃子里,送回給鄰居奶奶,鄰居奶奶笑呵呵地說,掉在誰家院子里的果子,就是送給誰家的禮物呀。
我很嫉妒她的鄰居有一棵橘子樹。我住在香港,我沒有院子,我住的是樓房,鄰居們從來不笑。
我不能跟父親說,不要送大麻糕,在香港不要送。我也不能阻止父親總是會跟的士司機說謝謝。我也會說謝謝,給多小費,有時候,我只是從來不笑。
大麻糕裝在精致的盒子里,送給香港鄰居。鄰居說謝謝,內心肯定是驚詫的。那一盒千里迢迢的大麻糕,有沒有被好好地吃掉?鄰居沒有告訴我。大家還是不笑,有時候點個頭,一句話都沒有。
父母后來來看我,再也沒有帶過大麻糕,豆渣餅都沒有帶過一包。
越南粉
鄰桌的老伯把生牛肉片翻到碗底,靜候三分鐘,如同深夜食堂里的黃油拌飯。
我要的是扎肉,不用等,白白的,浮在湯面上。
這碗香港的越南粉,仍然叫我想起加州。我第一次吃越南粉,在加州。一周買一次菜,有時候搭火車去到下一個站,那兒有一個中國店。中國店的旁邊就是越南米粉店。
搭火車買不了什么,一把蔥,一棵白菜。不喜歡這樣的生活,又要過下去。回不了頭。
一碗生牛肉金邊粉,許多芽菜,多到超出想象,一枝九層塔,一枝不是一片,大半個青橙,不要也得要。于是我記憶里的越南粉,像美國,豐富,熱情,不管不顧。
牛肉片必須薄,要不再滾的湯也不能讓它熟。用了猛勁的湯,仍然不好吃。湯不好吃,粉也不好吃,仍然要去吃。又沒有別的可以吃。
生牛肉沉到碗底,九層塔撈走,青橙汁一點點。桌上有辣椒魚露,從來不用。已經不好吃了的越南粉,好像已經壞掉了的愛情,還能更壞嗎?
等三分鐘,肉熟了嗎?還是老了?有人告訴我愛不愛都要多等兩天,有時候隔了夜就沒了愛,有時候要確定一下這次能多久,有時候不是愛,原來不是愛。
很窮的時候,黃油拌飯真好吃啊。很缺愛的時候,寂寞也當作愛。
越南粉好像過橋米線啊。我好多年沒有吃到云南米線了,有一年我去了兩次云南,會不會是因為過橋米線?云南的早飯總是米線,好吃到哭的米線,什么都有,五顏六色,還有真的菊花的花瓣。
小時候住的小城,有一天搬來一家云南米線店,唯一的一家,在最繁華的一條街,一對老夫婦和一個很帥的兒子開的。這個兒子喜歡文藝,很快和城里的文藝青年打成一片,樂隊的,電臺的,街上晃來晃去的男女青年。我太小了他們都不帶我,我十四五歲,要是十八九歲就好了,我又不能再早出生幾年。我只能看著他們,多想跟他們一樣。他們去米線店吃米線,我也去,但得跟著我媽。有時候能夠遇到他們,他們嘻嘻哈哈,我只是一個眼巴巴的小姑娘。
他們說他和一個電臺姐姐談戀愛,我也真的在米線店見過那個姐姐。后來米線店家的兒子和米線店都不見了,后來電臺姐姐去了電視臺做女主播,我跟她提起米線店,主播姐姐迷茫,什么米線店?什么時候有過米線店?
我在下班的路上發現了一間米線店,店主是一對更老的老夫婦。我總覺得就是他們,應該是他們,不過換了一個地方,那個再也沒有見過的兒子,肯定去了更大的城市,肯定的。我要了一碗過橋米線,所有擺成花的材料一起落入湯底,應該有一個順序的,可是沒有人告訴我那個順序,從左到右,還是從右到左,如果菜和米線遲早會在一起,為什么不是一開始就在一起?就像譚仔米線。譚仔米線在香港一直都是要排隊的,很擠的空間,很多的眼睛,如果放菜,還放米線,等那三分鐘,就會像做戲。很多人又不喜歡燙,很多人沒有時間,海皇粥店都推出了溫輕粥,香港人連等一碗生滾粥變涼的時間都沒有。
有的小姑娘愛上年長的男子,他們的經驗消磨了她們。被提前消費了的姑娘,被老愛情教壞了的姑娘。我們長成老少女,肯定是因為在真正少女的時候沒有真正地戀愛過,和一個真正年輕的男人。也許很多時候,我們就是需要等那三分鐘。
中國餃子
在我快要離開加州的時候,我邀請我的鄰居們來我家吃中國餃子。
我去中國店買了餃子皮,它們的顏色很黃,我懷疑它們是玉米粉做的,然后我買了各種各樣的青菜,所有的青菜看起來都一樣,也許我把芥藍也買了,總之,各種各樣的青菜,我把它們放入一口大鍋水煮,然后撈出來切碎。在我切它們的時候,阿拉伯鄰居按響了門鈴。她覺得切青菜很好笑,執意親自嘗試,而且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國菜刀,她說酷。在她切青菜的時候,我騰出手來切雞胸肉。
生雞肉切到一半,我打電話給我媽,我說我們家的餡確實都是熟的嗎?我媽肯定地說是,我媽說有一次我正包著餛飩,你就這么走過來,拎起一只生餛飩吃了,要是餡是生的你吃得下去嗎?我放下電話,想起那只生餛飩的滋味。我為什么要生吃一只餛飩呢?我倒是看過一個電影,犯了罪要潛逃的男子,跑去見母親最后一面,母親正在包餃子,兒子拎起一只生餃子塞進嘴里,不說話,只是咀嚼,母親笑了,進廚房下餃子,兒子望著母親的背,一滴眼淚流下來,他只好奪門而去,他還在咀嚼那只餃子。
我媽不包餃子,我媽包餛飩,我生吃那只餛飩是想知道那顆眼淚怎樣落下來。餡是熟的,面皮是生的,那半生半熟的餛飩的滋味也真的足夠我記住一輩子。
韓國鄰居代替了阿拉伯鄰居,顯然她是見過中國菜刀的,只是她的方法是一手握刀柄,一手按刀背,以蹺蹺板的方式切青菜。她倆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切起青菜來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把雞肉和青菜倒入一口玻璃缸,開始攪拌。我從網上打印了一些做餃子的資料,我按照那些資料加入了醬油和一只生雞蛋。攪拌的同時我掃了一眼電視,一個穿著牛仔褲的廚師正在用一個大針筒把調味汁注射進一只雞里。
然后呢?我開始發愁,她們都在等待著我的餃子。
我從廚房的窗子往外面看去,就看到了一個香港人,她正要去網球場。最后她幫助我把餡都弄進皮里去了,她還說餃子下鍋以后要推一推。
餃子終于上桌了。
阿拉伯鄰居用刀挑開面皮,叉起一團餡放進嘴里,發自內心地稱贊,中國餃子,酷。我望著她,心里想,早知道你要把皮和餡分開來吃,我就不用包了。
三絲魚卷
每到過年,就會有好多人送來好多魚。就好像香港人過年要買褲一樣,褲是富的意頭,魚也是余的意頭。
我母親很為那些魚犯愁,因為太多了。青魚和鰱魚,每一條都在十斤以上。江南冬天,水龍頭里冰冷的水像刀子一樣流出來,空氣里都是小刀子,手伸出去就是傷。要把那些魚都剖洗處理,有時候要做到晚上,到了晚上,又有人送來了新的魚。那個時候是不可以收錢的,過年的時候可以收魚,不能不收。那些魚開膛破肚,一排一排掛在廚房,竹簽頂住身體的兩側,凝固了的血,便不覺得是血,冷血的生物,也不覺得它們是生物。我走來走去,當看不見,我也不吃魚。
魚被送去炸,做成爆魚,打成魚漿,做成鮮魚圓,然而還是有很多,往往要吃到過完年。
每年都是母親親手準備年夜飯,三口之家,不是需要很多菜,然而總是許多菜。湯和甜品,熱菜和冷菜,每一碟冷菜上面都要放香菜,不只是裝飾,父親愛吃,卷起來,蘸加了糖的鎮江香醋,也是習慣,所以我長大以后總也不習慣香港人的紅醋,我也總是接受不了醬油做蘸料。
爆魚配白酒,就沒有那么濃郁了,羊糕和肴肉,糖醋小排,如意菜,總要有如意菜,黃豆芽的形狀是一把如意,所以是如意菜。離開家快要二十年,都不會忘記。可是忘記了是幾時學會飲酒的,獨生女兒,陪著父親喝杯好酒,是幸福。
所有的年菜中我最喜歡炒素和豆渣餅塞肉,都是外婆的菜,傳到母親手里,應該在我手里失傳了。還有甜飯,白到透明的圓糯米,自己洗的紅豆做餡,金絲蜜棗和蓮子心做底的八寶甜飯,每一個年都是甜的。
酒喝了一杯,母親會去廚房炒盤熱菜,鮮筍魚肚,清炒蝦仁,紅燒甩水。總有一道三絲魚卷,青魚皮卷了鮮筍絲火腿絲和香菇絲蒸,最費功夫。我從來不吃,我不吃魚。我有一個朋友說過我家的三絲魚卷是她吃過的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她說你有多幸福你都不知道。我的這個朋友父親早逝,有一個弟弟,家庭的負擔很重,終于找到條件還不錯的丈夫,待她也還好,有一天她跟我講,如果時光可以倒流,如果神再給她一次選擇,她會要回她的父親。
我在美國找一盤唐人街的夫妻肺片,橫跨了兩個州的時候,突然理解了我的幸福。我想那一道我從來沒有吃過的母親做的三絲魚卷,肯定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東西。毫無疑問的。
湯圓店
不是元宵節,為什么要吃湯圓呢?
所以有人帶我去吃湯圓,我覺得很不自在,但我還是去了,因為我很喜歡那個人。十七八歲的時候,只要和喜歡的人在一起,什么都可以。
一間小小的湯圓店,只賣湯圓,一個沉默的老奶奶,板著臉,都不笑的。芝麻湯圓和鮮肉湯圓,沒有第三種餡,不過有小圓子、可可和白糖。
我要了白糖圓子,并不覺得十分好吃,只是煮熟了的圓子,澆上白糖水。家里也做圓子,酒釀桂花圓子,酒釀和糖蜜桂花都是自己做的,我大概知道做酒釀的工序,浸過一夜的圓糯米,蒸熟,拌入酒釀,然后等待。頂要緊的是干凈,溫度和時間。糖蜜桂花也是,自己采摘的鮮桂花,一層花,一層糖,壓得密實,玻璃的罐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層次。
我在想他為什么要帶我來這間湯圓店,他是一個主播,他們都說他長相太好。你們一定是會分手的。我的朋友都這么說。
我看著他,他在吃一只鮮肉湯圓,好像挺開心,我也見過他因為要趕去讀夜校,冰箱里的冷飯澆上番茄炒雞蛋,吃得又快又香。
后來我們分手,再沒有人帶我去吃湯圓,我獨自去了一次湯圓店,要了可可小圓子,不過是白糖圓子,多加一勺可可粉。
小小的湯圓店,很快就不見了。一個地方總有一個地方的習慣,不是元宵節,為什么要吃湯圓呢?這個地方的人都是這么想的。
我后來在香港,才知道湯圓還有花生餡的,蓮蓉餡的,紅豆沙餡的,可是我一直都不喜歡那些味道。香港人真的好愛吃湯圓,冬至吃湯圓,元宵節當然也吃湯圓。糖水店里也常年賣著姜汁湯圓,糖不甩,沒有餡的水磨糯米粉大丸子,蘸了花生碎吃。旅途中認識的一對情侶,有一年來到香港,想不到請他們吃什么呀,坐在滿記,要了糖不甩,那個姑娘連連地說,太有趣了,太有趣了。他們回去以后結了婚,生了一個寶寶,圣誕節的時候寄來家庭照卡片,我就想起了他們,一個覺得糖不甩都很有趣的姑娘,他們的生活,肯定也會是很有趣的吧。
后來我想,我年輕的時候,那家小小的湯圓店,那些小圓子,其實也是挺好吃的。
愛喝酒
我喝了酒會笑。
所以我不大喝酒。這個世界,一點也不好笑。
我倒是羨慕那些喝醉了就睡著的人,我也羨慕喝大了就可以打人的人。我太想打人了,要是能夠借一口酒。可是我喝不醉。要想笑一次,也太難了。
周圍都是跟你繞來繞去的人,繞到天亮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想說什么。酒桌上才直接,我干了,你隨意。酒桌上的話拿到生活里說多好。可惜只能是酒桌上的話。
我從不把酒敬來敬去,又不是結婚,又不是畢業禮,我又沒有出新書,所以我往往沒有這個機會說。我干了,你隨意。這話聽得倒挺多,笑到簡直昏過去。
凱麗的新書出版,出版社為她安排了巴士廣告,四個姑娘帶了一瓶香檳去車站慶祝,大家都穿著裙子穿著紅色高跟鞋,紐約的冬天很冷,但大家都不覺得冷。好不容易出了新書,好高興。等了幾輛巴士終于等到,有人在作者的臉旁邊畫了一支迪克。香檳都開了,還是水晶杯,凱麗不高興了,姑娘們都不高興了。有什么不高興的,香檳又沒有罪。要是我,仰著頭,飲下那一杯。
我去年開了一瓶氣泡酒,我說我能夠出我的小說集我才開香檳,我是一個寫小說的,我知道我是寫小說的,可我出不了我的小說集。可惜我美國的女朋友都留在了美國,我在香港只有七年,七年建立不了一場友誼。跟我同時回到香港生活的姑娘帶來了寫著字的蛋糕,我們喝了氣泡酒,吃了蛋糕,她卡拉了一首《至少還有你》送給我。
肯定有人喝酒上癮,就像喝止咳水上癮。我好像對什么都不上癮,我只是好奇。我去云南的時候他們告訴我,二鍋頭配雪碧,難以置信的滋味。于是趁著十號臺風天買到一壺進口二鍋頭,配一罐雪碧,第一口的滋味,不就是二鍋頭?加多點雪碧,不就是雪碧?加多點二鍋頭,不就是二鍋頭?加多點雪碧,雪碧沒有了,二鍋頭就是二鍋頭。
你為什么總要加點什么呢?黃酒加姜絲,黃酒還加話梅。酒品也是人品,你太花哨。夏天和小時候的一個姑娘喝酒,運河旁邊,半支威士忌,不加冰。姑娘喝了酒,花生米一顆一顆扔到我的頭上。
停。我說。
她繼續扔,一邊扔一邊笑,我的頭上和衣服上全是花生米,還是炸過的,酒鬼花生。
停。我又說。
她說,做回一個上躥下跳的你真是太可悲了。
我說你就沒跳?
她就哭了,一邊哭一邊說沒有人愛你。
我終于笑了。我干了,我自嗨。你喝不喝你嗨不嗨我不知道哎,我干了這杯,轉去下一桌。

⊙ 金銳秀?樹殤7
周潔茹:江蘇常州人。出版長篇小說《中國娃娃》《小妖的網》,小說集《我們干點什么吧》《你疼嗎》等。二〇〇〇年移居美國,二〇一六年出版長篇小說《島上薔薇》,現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