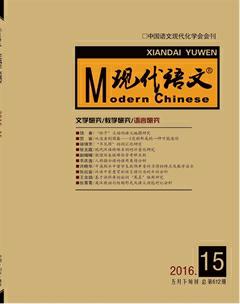淺談誦讀法在高職院校古詩文教學中的運用
◎劉 春
?
淺談誦讀法在高職院校古詩文教學中的運用
◎劉 春
《江蘇省五年制高等職業教育語文課程標準(試行)》(以下簡稱《課程標準》)中關于閱讀與鑒賞目標的表述,必修課程為“能借助注釋和工具書,讀懂淺顯的文言短文”、“加強語文積累,背誦并默寫教材中規定的篇目或段落”;選修課程·提高模塊為“能背誦教科書中的詩文名篇或名句名段,豐富文化積累,加深文化熏陶”。可見《課程標準》重視五年制高職學生對詩文的背誦、積累和文化陶冶。而省編教材中古詩文也占了較大的比例,古詩文教學歷來是語文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如何落實好《課程標準》中古詩文教學目標,筆者認為誦讀法是古詩文教學的首選方法。在古詩文課堂教學中,我們運用誦讀法已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一、關于誦讀法的再認識
誦讀法是我國古代語文閱讀教學的經驗之一,也是古代閱讀教學的基本方法。王槐松先生在《文言文誦讀法古今談》中將文言文誦讀法概括為:通過對文言文的眼觀、口誦、心悟,熟讀、精思、成誦,達到對詩文全面深入理解的教學方法。
誦讀將無聲文字化作有聲語言,口誦耳聽,口耳并用,讀思結合,聲情并茂,這樣就能夠理解文章的內蘊,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誦讀法在我國古代得到了普遍而廣泛的運用。南宋著名教育家、哲學家朱熹說:“凡讀書……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要是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朱子童蒙須知》,《養正類編》卷一)清人崔學古說:“毋增,毋減,毋復,毋高,毋低,毋疾,毋遲。”(《幼訓》)可見,讀的要求是:第一,大聲誦讀;第二,讀得準確,一字不差;第三,多遍誦讀,達到純熟,以至能夠背誦。目的是:第一,能夠上口;第二,能夠記住;第三,通過熟讀更好地理解。
同時,古人也并不主張糊里糊涂地讀,糊里糊涂地背。朱熹提倡“三到”——眼到,口到,心到。眼到是看,口到是讀,心到就是理解領會。他說:“讀書須是仔細。逐句逐字,要見著落。若用工粗鹵,不務精思,只道無可疑處。非無可疑處,理會未到,不知有疑爾。”(《朱子語類輯略》卷二)又說:“看文字須入里面猛滾一番,要透徹,方能得脫離。若只略略地看過,恐終久不能得脫離,此心又自不能放下。”(《朱子讀書法》卷一)崔學古說,讀書應該首先“求明,不先求熟。明則自然易熟”。所以他主張先把文章講明白,然后要學生讀,并且要他們復講,講后再讀,讀熟再溫。他說:“得趣全在涵詠。”(《少學》)這些意思合起來,就是朱熹再三強調、宋元以來人們一致奉行的“熟讀精思”的原則。
誦讀與一般的默讀、瀏覽在作用上是有較大區別的。因為語言是由音和義構成的,文字則是由形、聲、義構成。形、聲、義同時發揮作用,便能深深地感悟語言。通過誦讀,能夠將古詩文的神韻化作自己的語言素養,真正成為自己的血肉。誦讀還有激發思考的作用。一邊緩緩讀,一邊細細思考,“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味”。同時,因為誦讀使古詩文學習伴隨著強烈的情感體驗,大大增強了閱讀的形象感和情趣感,能再現作品所創造的形象,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如臨其境,使古詩文閱讀成為一種充滿藝術魅力的享受。
然而,我們在古詩文學習中,對誦讀的認識還不夠到位。或將它當成一般的朗讀,或僅把它看作記記背背。其實,“誦”和“讀”從詞源上說,是有差異的:“誦”是一種寓情于聲、以聲傳情的情態化表達方式;“讀”則是“抽繹其義蘊,至于無窮”,是對詩文意義的深切體味。正因為如此,誦讀的要義是玩味、品味,“得他滋味”。它當然包含了背誦,但又絕不僅限于背誦,可見,誦讀是一種特殊的“聲讀”法。
總之,誦讀是要將古詩文作品的神韻情感讀出來,在有感情地熟讀的基礎上,把那些最精彩的篇章背誦出來。
二、誦讀的具體做法和運用
作為我國古代語文閱讀教學的寶貴經驗,誦讀法應該被我們吸收借鑒和創新運用。在教學中,要指導學生根據具體的古詩文課文和教材要求讀準字音,讀清句子,讀出語氣,讀懂意思。關于誦讀的一些具體做法,現代作家和語文教育家朱自清先生在《論朗讀》一文中已有過論述,結合他的有關說法,下面談談具體做法。
(一)讀。朱先生認為:“讀詩重意義,注重清楚,要如朱子所謂‘舒緩不迫,字字分明’。”指導學生在讀的時候,要有抑揚頓挫,也要有口氣,每個字應該有相當的分量,不宜滑過去。當然這是就總的法則而言的,結合具體情況,還需要區別對待。一般說來,我們很容易將古詩文的每一個字都讀得很響亮,其實是沒有必要的。如賈誼的《過秦論》開頭一段有這樣一句話:“外連衡而斗諸侯。”這里“斗”字到底應該怎么讀?是平讀,還是或抑或揚?這是應該細細思量的。在當時秦國的外交策略中,連橫是重要的國策。它通過設計,使東方各國之間產生矛盾,相互爭斗,促使敵人力量相互牽制、不斷內耗,以達到坐收漁利之目的。因此它不是力爭和斗勇,而是斗勝和斗智。由此看來,這里的“斗”字宜抑不宜揚,要讀得它曲折有致,將原文微妙的寓意形象地展示出來。
(二)吟。吟特別注重音調節奏,重在表現神韻。它需要慢聲誦讀,而“慢聲”即為悠長柔和之聲,與吟相關的是詠,又帶有歌唱的意味。因此,吟就是有味道地讀,非吟不能體會古詩文的口氣。“吟”好像電影里的“慢鏡頭”,將那些不自然的語言的口氣慢慢表示出來,讓人們好捉摸著。如范仲淹作《嚴先生祠堂記》,結尾句原為:“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其時,他的朋友就說:“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范問何字,朋友回答說:“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范沉吟片刻,欣然從之。我們徐徐吟詠,便可發現,這幾句話修改前后的味道是不一樣的。“德”字是仄聲字,氣促音啞,吟起來沒有底氣,也很難有余音繞梁三日不絕之感,沒有“風”字的洪亮、開闊和悠長;且“德”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與云山江水相連不夠和諧統一。唯有“風”字,能形象傳神地表達出漢高士嚴子陵先生不為塵俗所累、不為勢利所動的高風亮節。試想,不是有滋有味地去吟,僅靠默讀瀏覽,恐怕是不容易體會其“未安”之處的。
(三)誦。我們認為背誦不是增加記憶的手段,而是積累語言的手段。對較短的優秀古詩文篇章,應在理解的基礎上流暢地背誦;對那些較長的優秀詩文,盡量熟讀全文,其最精彩、最關鍵的部分最好也能背誦,但沒有必要將這些作品的全文一字不落地背出來。至于化整為零,各個擊破,聯想想象,加深記憶,反復咀嚼,強化效果等等,應成為我們背誦的一些基本方法。
下面再以《阿房宮賦》第二課時教學為例,來說明誦讀法在五年制高職古詩文教學中如何運用。
選入教材的《阿房宮賦》是一篇著名的文賦,非常適合誦讀教學。老師在第一課時放手讓學生自讀、默讀初步理解文意,歸納整理語言現象的基礎上,第二課時就集中精力師生一道來誦讀課文,在誦讀過程中深入理解文章內容,在誦讀過程中深入領悟文章句式特征,在誦讀過程中深入把握文體特征。教師將教學過程設計為四個步驟,即激趣導入、以識促讀、理解詞句、涵詠品讀。整個教學過程從始至終都貫穿一個“讀”字,把看似平淡的教學手段運用到極致。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從容涵詠,有時讓學生自由誦讀,有時小組齊讀,有時指名學生試讀,有時老師示范讀,有時聆聽專家誦讀等等。在誦讀文章過程中,教者適時地點撥誦讀中應注意的重音、節奏、語氣以及感情處理等一些細節。本節課通過誦讀培養了同學們學習古文的興趣,大家讀得有味,學有收獲。在上課結束時,老師還要求同學們課后再反復地誦讀,特別是利用好早讀課時間放聲地誦讀文章。并且將背誦這篇文章作為課后作業。總之,運用誦讀法教《阿房宮賦》,老師可以把誦讀教學法運用得淋漓盡致,也收到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江蘇省教育廳.江蘇省五年制高等職業教育語文課程標準(試行)[S].江蘇職教網,2009.
[2]褚樹榮.新專題教程.高中語文3·古詩文閱讀新視點[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劉春 江蘇鎮江高等職業技術學校 21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