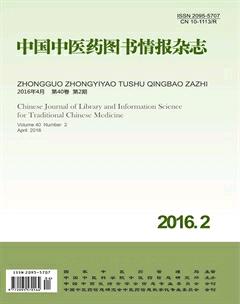透過歷史學的塵埃看中醫
朱玲 楊峰
摘要:歷史學與中醫學兼具科學性與人文性,二者具有相似的起源,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都曾遭遇“科學與否”的紛爭,科學派史學的時代已經過去,將文化的觀念滲透到歷史研究的文化生命史觀在一定程度上賦予歷史學研究新的生命。這一點在中醫的發展中亦可借鑒,進行中醫與文化的相關研究十分必要。中醫學要告別科學之爭,珍惜源遠流長的浩瀚醫籍,將之發掘、繼承、提高,從歷史學、詮釋學等人文學科借助力量,同時勤于臨證,注重提升實踐能力,或許是中醫學未來發展的出路之一。
關鍵詞:歷史學;中醫學;比較研究
中圖分類號:R2-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5707(2016)02-0014-04
歷史學與中醫學作為兼具科學性與人文性的學科,在歷史發展進程中都曾遭遇過“科學與否”的爭論。特別是中醫學,自鴉片戰爭之后,伴隨著西學東漸之風,中醫科學化、中醫廢止論都曾甚囂塵上,中醫學一度遭遇了生存危機。盡管在國家的中醫政策扶持下,中醫得到了保護與發展,但中醫是否科學,用現代科學的方法來研究、衡量中醫是否可行,都是中醫藥發展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本文試從歷史學的過去與現在中找尋中醫學發展的可能出路,以及通過歷史我們學會了什么,又該怎樣面對未來。
1.歷史學與中醫學
1.1兼具科學性和人文性
將歷史學歸屬于人文科學不會有太多異議,作為人文科學的歷史學具有2種基本屬性,即科學性和人文性。將中醫學歸為人文學科可能有很多人不認同,但中醫學有太多無法抹去的人文特征,如理論體系的陰陽五行及整體觀念一直以來就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思想,是中國傳統哲學的根基所在。而有學者也指出,中醫學實際上是一門兼有自然科學屬性的人文學科。
人文學科,以其驗證方法的非實證性、非量化性和社會功能的潛隱性、長周期性等學科特征而與狹義的“科學”相區別。歷史和中醫兼具科學與人文2種屬性的特點導致其發展歷程中會遇到類似的困擾。
1.2起源探悉
1.2.1古史與古醫書均來自口傳 遙遠的古代是神話的時代,人們無法脫離鬼神思想。絲毫不摻雜神話色彩的史實大多屬偽,或至少也存有人為竄改的痕跡。事實上古代典籍的形成,是先有口傳而后才見諸文字。即使在文字己廣泛應用的時代,亦未必一一轉于文字。古史由口說轉入于文字,是情理的自然形成,其著作形式和應用語言可能遠在千百年后。《黃帝內經》托于黃帝,《神農本草經》托于神農,或以文法辨其不類,而不知承學者本其口耳相傳之說,而成書不能不用后世文法也。章學誠則據《公》《轂》二傳(《公羊傳》和《轂梁傳》),解釋《春秋》,論證上古口傳制度的重大功用,其體制皆為口語對答之詞,口傳之跡明顯,證明了口授在先,而后轉入文字的實情。中醫學的奠基之作《黃帝內經》的書寫體例亦是黃帝與岐伯、雷公的對答之詞,明為口傳無疑。而其并非一時一人成書的觀點也已被學界廣泛認可,戰國時期則僅僅是其成書年代,而距離其中知識流傳的年代可能十分遙遠。
1.2.2歷史起源于神話,中醫從巫術叢林走來 神話學和歷史學都已證明,人類(無論是哪個民族)早期的歷史與神話不可分割地糾結在一起,要明確區分哪是人哪是神,哪是神話的延續哪是歷史的開端,是十分困難的。
人類醫學的早期形態是巫術醫學。隨著人類理性進步和經驗積累,醫學才逐漸告別巫術形態,進入經驗醫學、實驗醫學等階段。中醫學同樣是從巫術叢林走出的,甚至至今仍殘留其印記。
歷史與中醫的起源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了神話和迷信的色彩,或許正因為這種特征使得二者在今天仍要面對唯科學主義者的拷問。據此我們在判斷古醫書的真偽及成書年代時都應慎重,不能因為其中的神話迷信成分而人為貶低其價值,其次不能僅根據語言體例來判斷成書時間。
1.1.3均面臨“科學與否”的爭論
《辭海》對科學的定義為:發現和認識自然、社會、思維發生發展的知識體系,具有定性、定量、可重復性等特點。
“科學”一詞由近代日本學界初用于翻譯英文中的science及其他歐洲語言中的相應詞匯。1893年,康有為從日本引進并使用“科學”二字,辛亥革命后,“科學”二字便在中國廣泛運用。按達爾文的表述,科學只是我們了解事物本質的手段,而絕不是目的。從某種意義上說,科學僅僅只關注真實或者事實,而不關注真理。
準確的“科學”定義在這里并非十分重要,在討論這一命題時大多已經把“科學”當成了“自然科學”,當成了一種建立在西方文明背景下的對知識的評價標準。這種狹義的科學認知就是歷史與中醫這2門學科為何總要被放在“科學”的神臺上審問,而后得出或是或非結論的原因之一。
如果從廣義的“科學”定義來看,其拉丁文本義是“有組織的知識體系”。歷史和中醫都是有組織的知識體系,所以廣義的科學必然包含二者。因此問題的責任似乎應該落在那些否認歷史為科學者的肩上,而不在那些承認歷史是科學者的肩上。
中醫作為有著系統理論體系的學科,存在了幾千年并且至今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既然無法避免的出現了科學與否的爭論,我們就應該知道原因。具體的緣由除了關于“科學”的狹隘定義外,還有20世紀初科學主義思潮對學術界的沖擊。中醫是否屬于科學以及是否需要向科學靠攏的問題近年來方成為討論熱點,其實這個危機和爭論早己出現。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醫存廢之爭即是明證。經歷了浩劫幸存下來的中醫,為了自身生存發展,不得不接受中醫科學化主張,用西醫方法和近代醫學標準促使中醫科學化,以現代科學與醫學手段和規范來揭示、衡量中醫,事實證明這并不是中醫的真正出路,而且最終難免步入中醫西醫化的歧途。
科學主義的思潮同樣侵襲了歷史學。其趨向是將史學與科學連帶考慮與討論,或以科學成分強加于史學,或要史學成為科學之史學,或要史學屬于科學。
表面看這些僅僅是單純的一種學術風氣,其實與其同時代思想有相當深厚的關系。由于近代西方知識技術沖擊,西方優越的觀念在中國越發盛行。這種沖擊也使中國近百年來被科學主義的陰影籠罩。史學界和中醫界的這種治學風氣,均是受科學主義的影響。但正如西方史學家葛隆斯所言,那些希望歷史成為純粹科學的人實際上卻使歷史成為科學的附庸。這句話用在中醫上也同樣貼切。將中醫附庸于科學會使其喪失其獨立性,甚至走向毀滅。
2.歷史學的解決方法
由于近20年來西方歷史哲學方面若干突破性的發展,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乾嘉考證惡化歷史主義統治中國史學界的時代過去了,至少也快要過去了”。所謂“乾嘉考證惡化歷史主義”就是科學派史學。科學派史學之后,歷史學也進行了很多的變革與創新,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就是文化生命史觀。
2.1錢穆先生創立的文化生命史觀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寫道:“文化與歷史之特征,曰‘連綿,曰‘持續。惟其連綿與持續,故以形成個性而見為不可移易。惟其有個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謂之有生命、有精神。”中醫又何嘗不是綿延幾千年而仍然有十分頑強生命力的學科,甚至其理論基礎在幾千年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也并未動搖。可見其和歷史、文化的學科特性十分相似。錢先生又說:“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而省略文化,我們也不能很好地認識中醫。中國傳統文化在中醫基礎理論形成發展過程中一直相互滲透、相互促進。
史學功能的特殊性是深切的文化關懷。將文化的觀念滲透到歷史研究的各個角落方能賦予歷史新的生命。雖然錢先生的史學觀念并未占據主流,但在近代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這一點在中醫的發展中亦可借鑒,進行中醫與文化的研究勢在必行,中醫的文化復興是中醫全面復興的重要途徑。
2.2后現代主義觀念是對傳統歷史研究的挑戰
后現代主義強調事物的復雜性、多樣性、相對性和無結構性,反對現代主義籠罩一切、建立制度和社會體制的思潮。自出現后逐漸在西方學術界蔓延,先是人類學、社會學,然后到教育學、政治學,最后是歷史學。后現代主義承認史學研究的對象與科學研究對象間的差異,撇開原來糾纏不休的主觀與客觀之間的關系,承認史學無法像科學研究那樣客觀中立。語言學和文化學轉向給歷史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擴充了歷史寫作的視野和維度。
3.中醫學可能的出路
3.1中醫文化研究的加強
正如語言學和文化學的轉向給歷史研究開拓了新的維度一樣,有關中醫的文化研究也是一種值得探索的路徑。
中醫文化研究要立足中醫,通過對中醫學的思想基礎、理論基礎、科學內涵、理論架構的研究,厘清中醫文化脈絡。這關系到中醫學的認可接受度,還能準確評估中醫在全民醫療保障體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從另一角度看,中醫文化研究可以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與科技有關的思想要素的反思與評估提供歷史依據,更可以提供正在實踐著的現實依據。
3.2研習經典,精于臨證
在中醫發展的漫漫長路中,涌起了中西結合或中醫西化的風潮,還有一種則是所謂“純中醫”的聲音。這大約始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基本主張是拒絕現代技術與手段,走全面復歸傳統的、通過“一個枕頭,三個指頭”就實現診療的“純中醫”之路,這顯然在當代社會醫療環境中太不現實。
推動中醫現代發展的動力是中醫診療實踐與理論的矛盾,換言之,中醫學存在的根基必須于實踐中求生存。只有真實的療效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只有在實踐中不斷豐富,自我完善,揚長避短,更好地面對疾病譜以及人的生理體質、心理狀態的不斷變化,才能成為適應新時代的醫學。
3.3詮釋學等新學科的引入
詮釋學作為理解與解釋的學科,在西方已有很漫長的歷史,在經歷了作為圣經解釋學、羅馬法解釋理論、一般文學批評理論,以及人文科學普遍方法論之后,20世紀60年代出現了哲學詮釋學。其最鮮明的特征就是它所強調的理解與解釋的與時俱進品格、實踐品格和創造品格,其影響迅速波及西方人文科學,甚至自然科學。
哲學詮釋學對當今中醫經典文獻研究無疑極具啟發性。以往我們總習慣于認為,經典文本的正確解釋只能有一個,除此以外,一定是錯誤的。以這樣的價值標準去看待歷代醫家的注解工作,顯然容易忽視、抹殺其工作意義。相反,如果按照哲學詮釋學的觀點,今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比古人更好地理解經典和他們自身的意圖。
隨著中國詮釋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研究中國傳統理論的現代化構建方式已受到越來越高的重視。中醫學作為一個融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等諸多學科的傳統醫學理論體系,與其交叉融合己成必然。中醫詮釋學研究是對中醫理論研究特色、思維方法的哲學審視,是通過現代詮釋學研究方法,對中醫理論及方法進行理解和解釋的一門學科。
例如具體到中醫內科學的理論學術體系的發展也是通過對經典著作的不斷闡釋來實現的。因此,臨床實踐也是一種詮釋,它既是詮釋的基本手段,也是詮釋的目的所在。通過獲取臨床療效,一方面可以使內科學理論得到充分的實踐證明,另一方面又可不斷豐富和完善內科學理論。
4.小結
中醫科學化、中醫西醫化的道路已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但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即使是青蒿素的發明、屠呦呦的獲獎,并不能成為中醫科學化唯一的方向。作為同樣曾經面臨科學之爭的兼具人文特性的學科,我們可以從歷史學的發展中有所獲益,徹底告別科學之爭,改變西方科學化的唯一的評價標準,對中醫進行全新定位,換一種更加圓融的角度去思索問題。珍惜我們源遠流長的浩瀚醫籍并將之發掘、繼承、提高,從“歷史學”“詮釋學”等人文學科中汲取新鮮血液,或許是中醫學未來發展的出路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