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棧
高軍
進入冬季了,天水棧作為一個半山腰的小村莊,盡管很朝陽但還是讓人感到已經很冷了。戰士報遷到這里,要用鉛字印刷第一版了,作為政治部主任的肖華從青駝寺趕了過來。他感到腳凍得有些麻木,就使勁跺了跺,又向手上哈了幾口氣,交叉著搓了搓手背,和報社的工作人員就有關問題進行了再次交流,看到報紙馬上就要出來,他心中感到一陣輕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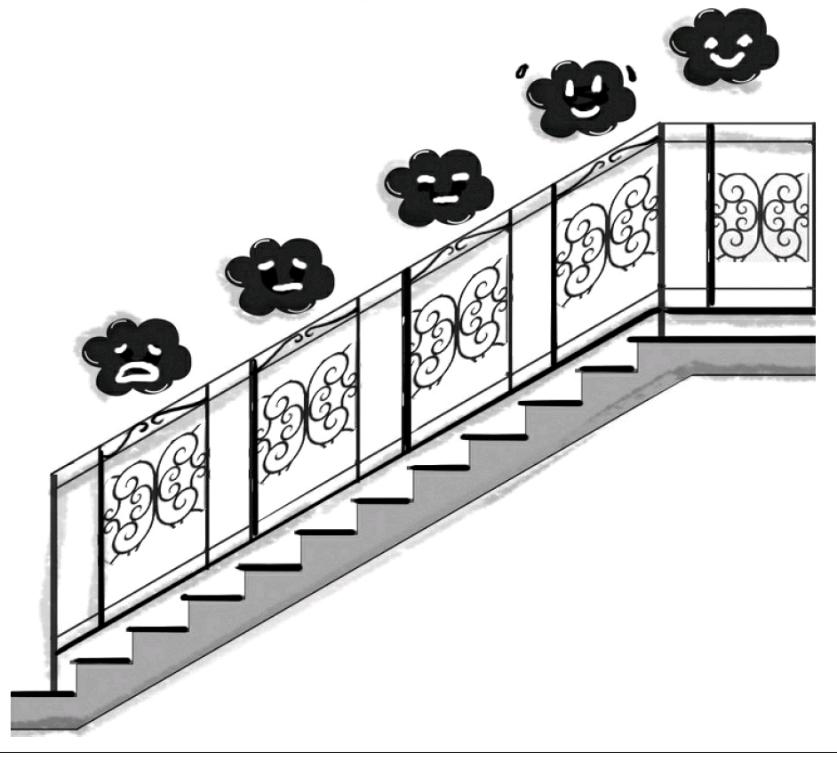
肖華看到時間比較充裕,就準備到村子里轉轉,和老百姓拉呱兒拉呱兒。
報社由于先行到來,對村子里的情況比較熟悉,肖華叫上一個戰士就出門了。他們剛向東走出有半里路光景,就聽到從一戶的庭院里傳出一陣陣哭聲。肖華問:“這是?”戰士告訴他:“這家有人去世了,應該是正在進行一些儀式吧。”
“咱們去看看。”戰士想阻攔,但肖華幾步就跨進了庭院。
只見死者還在屋內正面新搭的靈床上躺著,家人們坐在地上一邊燒紙一面哭泣,喪禮主事者迎過來:“同志來了,你們……”
“我們過來就是看一下,”肖華神情肅穆,語調低沉,“入鄉隨俗,我們是不是應該磕個頭啊?”
主事者臉色平和下來:“部隊的同志,這些說道就免了吧。”
看到肖華堅持,主事者告訴說,還需要過一會兒,現在要先入殮:“這老人病了很長時間,頭發太長了,都覺得這樣叫他走了于心不忍,正等著找人來給拾掇一下,再進行入殮呢。”
不一會兒,有一人回來,告訴主事者:“我到孫祖街上問了所有的剃頭匠,都嫌給死人剃頭不吉利,剃頭刀子以后就沒法用了,沒有人愿意來。”
“這可怎么好,這可怎么好?”主事者急得團團轉,死者親屬也都眼巴巴地看著他。
肖華心中一動。最近,他不論走到哪里,總是帶著不久前在反“掃蕩”中從日軍那里繳獲的一把理發用的推子,一邊和當地老鄉拉呱兒一邊給他們剃頭。老百姓知道他手中的洋玩意兒叫推子后,就都管剃頭叫推頭了。他覺得這樣和群眾說說話,效果會更好一些。他猶豫了一下,敞開了自己帶過來的小包,拿出了那把推子:“我來吧。”
“肖主任,這……以后……”陪他來的戰士囁嚅著。
肖華拿著推子,向死者走去。主事者和家人都露出感激的表情,跟在后邊。肖華面向死者,先低頭鞠了三個躬。死者的長子輕輕抱起了父親的頭,熱切地望著肖華。肖華在靈床前蹲下來,右手捏著推子的兩個把兒,輕微的咔嗒聲響起來。隨著咔嗒咔嗒有節奏的聲音,死者的頭發一縷一縷落下來,理完后死者的面容顯得光鮮了很多。為死人理發,很不得勁,肖華站起來的時候,感到了腰有些酸,腿腳也有些麻木。
入殮儀式開始,人們將棺材抬到屋內打開,把棺蓋放在一旁。先過來了兩個婦女,拿著笤帚,在棺材內認真掃了一遍,當地人叫作掃棺。又有人過來,先往棺材底部鋪麻桿子、栗子枝,在大的一頭放上一個瓦盆,盆內放了一只縫制的布雞,在棺材小的那頭放上一個不大不小的土塊。這時,死者凈面已經結束,主事者往他手中放上了銅錢。長子抱頭移尸入棺,讓死者頭枕布雞,足蹬土塊,仰面而躺。然后孝子孝眷繞棺一周,看死者最后一面。孝子孝眷持剪刀虛擬著鉸向死者衣帶,并邊鉸邊喊:“爺呀,留后帶(代)!”一切儀式完備后,用兩尖釘釘牢棺蓋,就是蓋棺了。此時,痛哭聲再次響了起來。
“放心,有辦法的。”返回報社的路上,肖華看了陪他來的戰士一眼,“再說了,咱們革命戰士,都是不信神不信鬼的唯物主義者,哪能講究這些……”
第二天,在師部駐地青駝寺,肖華抽空叫來了衛生員,拿出那把推子,囑咐道:“用酒精給消消毒,讓它繼續為我們干活啊。”衛生員送回推子來的時候,肖華招呼師部一個會理發的戰士,“我的頭發有些長了,麻煩你給我理理發。”
幾天后,鉛字印刷的第一版《戰士報》在天水棧問世,發行量也增加了很多。肖華拿著印制精美的報紙,高興地從頭到尾地看了一遍。
“不行,咱們得再去看看報社的同志們。”他吩咐政治部的一個戰士,就又往天水棧去了……
肖華在沂蒙山區生活了五年,多次到過天水棧,和老百姓很熟悉。前幾年,新華社記者在天水棧采訪,有個老人說起戰爭年代,用食指指著自己的頭說:“說來你可能不信,肖華——他是將軍啊,當年給我剃過頭。”然后看著村前寬闊的水泥路,“那時候,這里根本沒有像樣的路,來一趟真不容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