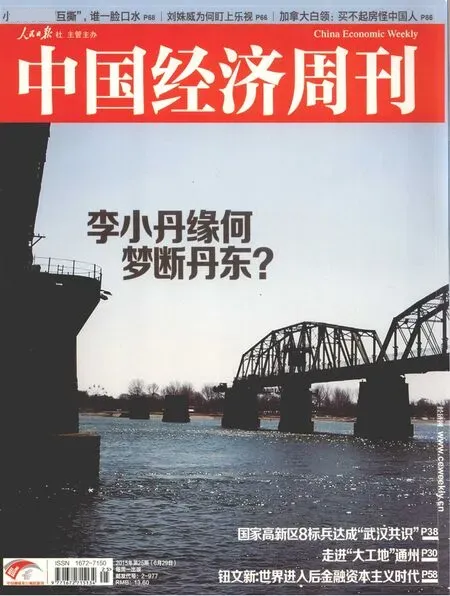只有激勵到位,才能驅(qū)動創(chuàng)新
葛豐
歷來敢為天下先的深圳日前率先推出落實(shí)科創(chuàng)體制改革精神的地方細(xì)則,其中明確政府所屬科研機(jī)構(gòu)的科技成果的使用、處置和收益權(quán)將下放到項(xiàng)目承擔(dān)單位,科研人員成果轉(zhuǎn)化收益比例也將提高到70%以上。
這一大膽創(chuàng)新符合科技發(fā)展規(guī)律。在此之前,由于我國科研力量大量集中在國有部門,而國有部門的科研活動又長期面臨激勵不足、激勵失范等體制性障礙,結(jié)果就是:雖然中國的科研投入已連年實(shí)現(xiàn)大幅度增長,但其投入/產(chǎn)出比卻很值得懷疑。譬如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這一最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有資料顯示,目前全國5100家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完成科研成果3萬項(xiàng),但其中能轉(zhuǎn)化并批量生產(chǎn)的僅20%左右,形成產(chǎn)業(yè)規(guī)模的則僅有5%左右,遠(yuǎn)遠(yuǎn)低于發(fā)達(dá)國家70%到80%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率。
如此低的成果轉(zhuǎn)化率,顯然難以支撐創(chuàng)新驅(qū)動發(fā)展戰(zhàn)略,因此,要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新驅(qū)動轉(zhuǎn)型發(fā)展,就必須先行從科創(chuàng)體制機(jī)制入手,解決好科研創(chuàng)新本身驅(qū)動力不足的問題,其中最關(guān)鍵的,就是要在激勵機(jī)制這一核心領(lǐng)域,勇于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實(shí)踐。
人的行為通常是特定激勵、約束機(jī)制下的產(chǎn)物。哈佛大學(xué)管理學(xué)家威廉·詹姆斯研究發(fā)現(xiàn),在缺乏激勵的一般崗位上,員工僅能發(fā)揮其實(shí)際工作能力的20%~30%,而受到充分激勵的員工,其潛能則可以發(fā)揮出80%左右。由此可見,有效的激勵是激發(fā)員工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的核心變量。
科研創(chuàng)新活動的特殊性,導(dǎo)致其比一般崗位工作更需要激勵配套。因?yàn)閯?chuàng)新活動可以簡要?dú)w納為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相互作用、相互轉(zhuǎn)化、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其中隱性知識不僅重要,而且只可能存在于科研人員個體頭腦中。因此,如果僅依據(jù)較易觀測且基本歸屬于單位的顯性知識,對創(chuàng)新活動進(jìn)行評價(jià)并對創(chuàng)新成果進(jìn)行切分,那么在微觀上,必然會抑制科研人員的創(chuàng)新動力與活力;同時(shí)在宏觀上,也會因?yàn)槿狈ξ⒂^基礎(chǔ)而導(dǎo)致創(chuàng)新活動無法耦合為理想中的“擴(kuò)展秩序”。
這種激勵機(jī)制對科技創(chuàng)新乃至一國興衰的重要性,無論怎樣強(qiáng)調(diào)都不為過。英國科技比較史學(xué)家李約瑟博士在其《中國科學(xué)技術(shù)史》中,曾經(jīng)提出過極為著名的“李約瑟之謎”。其后學(xué)人們針對這一疑問,給出了多方位、多角度的精彩解答,而其中最基本,同時(shí)也是最接近于共識的一項(xiàng),無疑還是古代中國未能如西歐那樣,發(fā)展出一整套適合于科技創(chuàng)新的市場體系與市場規(guī)則,激勵行為人因?yàn)榇_信的利益回報(bào)而積極投身發(fā)明創(chuàng)造。
科研人員也是人,他們的勞動需要得到足夠尊重與恰當(dāng)回報(bào)。習(xí)近平總書記在不久前召開的全國科技創(chuàng)新大會上提出,“科技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要協(xié)同發(fā)揮作用,兩個輪子一起轉(zhuǎn)”。我們希望并且相信,這一論述當(dāng)能推動以激勵為核心的科創(chuàng)體制及其相關(guān)體制加速變革、深刻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