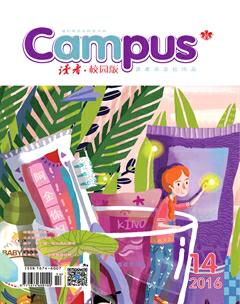真正的學習不只是入腦,還須走心
武志紅
我有一個朋友,小學一二年級時數學成績一直很差,因為她完全搞不懂加法是什么意思。
一天,她走在街上,看著街上的兩個物品,突然間明白了:哦,加法,不就是兩個數加在一起嗎?就像這兩個物品加在一起。
明白這一點后,她的數學成績一下子實現了飛躍。
這種明白,心理學上稱之為頓悟,英文為“insight”,國外還有一個有趣的說法叫“啊——哈”,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頓悟發生時,心里不自覺地會有這兩個感嘆:“啊!哈!”
頓悟,是一個人自己對某種事物之規律的一種發現。這是“我”的發現——這是頓悟的根本價值所在。
有了頓悟,就意味著一個人真正領會了些什么,這是真正的學習。
與頓悟相對應的,是模仿學習。
模仿學習,即我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是什么,但我從別人那里知道了這個道理是什么。
模仿學習永遠是跟在別人的后面,而頓悟永遠是嶄新的。即便你頓悟到的一個發現可能是無數人都發現了的,但對你而言,這是嶄新的,而且真的是你自己發現的。
譬如說,小學生都知道1+1=2,但是,第一個總結出這個規律的人,那必定是驚天地、泣鬼神者,而輕松通過模仿學習獲得這一知識的人,就領略不了頓悟的那種美了。
就說說我的這位朋友吧。她回憶說,當時她覺得大腦中有一道白光閃過,整個世界突然變亮了很多。然后,或者說幾乎是同時,那個頓悟“加法不就是兩個事物加在一起嗎”從心中涌現了出來。
頓悟,經常顯得很是有些愚笨。
美國偉大的催眠大師米爾頓·艾瑞克森有閱讀障礙,他讀書時的多數時間里就是在翻字典,因為他不知道字典是怎樣排序的,所以,每次查找一個字,他都是從頭查起。
一直到16歲,一天他在家中的地下室里查字典,突然間好像一道白光將整個地下室照亮,一種巨大的喜悅從心中涌出,他發現:原來字典是從A排到Z的。
原來如此,他自己發現了字典排序的奧秘。
自己發現這個奧秘的過程,就是這樣的美。
相反,一開始就被告知字典是如何排序的我們,有幾個人能有幸體驗到這種美呢?
在逛一些心理學專業論壇時,看到網友們貼的文字,我感覺到郁悶,好像論壇上活躍著一個又一個大師。其實,不過是網友在轉述大師們的理論和語句而已。
大師們構建起自己的理論和語句,那必定是經歷了無數的頓悟,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原來字典是從A排到Z的”那種美。
這個歷程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通過模仿學習而知道這些理論和語句的表面道理所在,是很容易的。
甚至,都容易到了這個地步——好像自己在轉述時就已掌握了其全部精髓。
但是,這一定是一個幻象。這種掌握沒有經過你的心與你的靈魂,它只是頭腦上的知道而已。
舉一下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大學時就知道了弗洛伊德講的俄狄浦斯情結(戀母情結),但是,直到半年前我才通過一系列的頓悟,部分解開了我自己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結,然后才能比較好地在這一點上和我的來訪者一起工作。
假若沒有我對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結的領悟,那么我也很難陪伴我的來訪者在這一點上抵達真正的領悟。
心理學畢竟還是比較窄的領域,我們還是回到常見的話題上吧。
記得那年春節聯歡晚會,看到“百家姓女孩”王仙妮上場表演時,我心里有一種巨大的悲哀涌出——這到底有什么意義?
后來,中央電視臺心理訪談節目對王仙妮做了深度訪談,更進一步加深了我的這種悲哀——這到底有什么意義?!
王仙妮倒背如流的不僅僅是《百家姓》,還有像什么《唐詩三百首》這類書。這種記憶力讓一位老師一時震驚,以為她是天才,但當這位老師詢問王仙妮是如何理解一些簡單的句子時,王仙妮完全說不上來,這位老師再一次震驚了。
我猜,這種震驚也許和我的悲哀有共同之處。
在上高中時,我也背過《唐詩三百首》和《宋詞三百首》,還有像高考范圍內需要背誦的課本,我也都背過了,甚至連魯迅的一些文章我也全文背誦了。不光是為了高考,更主要的是愛好。
然而現在,這一切都在我的腦海中不復存在了。說來悲哀,它們真的只是進入到我的頭腦中而已,它們不曾碰觸到我的心。
假若時間可以重來,那么,我會很慢很慢地去讀唐詩宋詞,希望再讀的時候,能恍然間穿越時光隧道,好像又回到作者的時空中,碰觸到他的心,與他的心弦以同一個節奏跳動。
錢學森在去世前向溫家寶總理感慨,新中國沒培養出一個大師級的杰出人才。之所以如此,我想,因為我們盛行的就是模仿學習,忽略了讓孩子們自己去領略知識與人生的重要性。
現在的教育體系造成的學習壓力越來越大,孩子們似乎一天一天地只能在超高負荷的模仿學習中疲于奔命。如此一來,不管他們長大后能多么純熟地掌握知識與技術,都是有巨大欠缺的——他們從未體會過頓悟的美,他們身上將難以閃現原創精神的光彩。
那么,你是否愿意試一試,慢下來,用心去體會這個世界,通過一次又一次的頓悟,真正感受到這個世界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