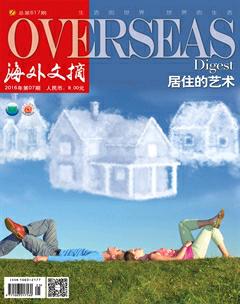習慣的力量
蒂爾·伯勒爾++孫開元
每個人生活中都有各種各樣的習慣,這些習慣如同自動導航系統一般,告訴我們做什么、怎么做。如果你能掌控大腦中的這個自動導航系統,你就能隨心所欲地養成好習慣、改掉壞習慣。
我盯著自己放在鍵盤上的手指,心里有些愧疚和失望。現在,我希望我的手指看上去能與往日不同。剛開始打算寫這篇關于習慣的文章時,我發誓要打破自己的一個習慣——咬手指。努力的結果讓我深刻領會了一句話:積習難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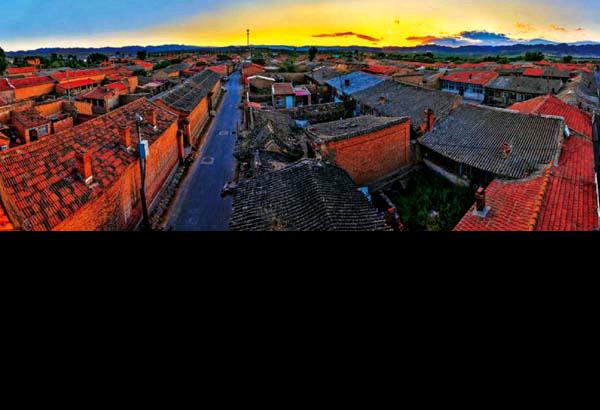
堅持、堅持如果沒有馬上成功、那就繼續嘗試、直到好行動成為好習慣
習慣為何難以養成又難以去掉,這個問題一直沒有定論。盡管如此,對于駕馭習慣的美好憧憬是那樣令人向往,各種關于習慣的理論層出不窮。比如,一種為人們所接受的智慧認為,無論是養成一個習慣或者改掉一個習慣,都需要21天。
理論說得有板有眼,能夠證明這一說法的證據卻一直少之又少。但是現在情況出現了轉機,隨著神經科學的發展,探查大腦內部的工作機制成了可能,這就意味著我們可以史無前例地制作出一張精確圖像,觀察一個新習慣形成時大腦回路的反應。我們甚至想象出了一個“思維開關”,讓習慣為我所用——招之即來,揮之即去。
何為習慣
我們若想了解習慣,遇到的第一個挑戰是分清哪些行為是真正意義上的習慣。我們通常認為,習慣包括從刷牙到不文明的餐桌舉止或吸煙等各種行為。從科學上來講,習慣泛指人在某個特定情境下形成的不易改變的行為,通常是不自覺形成的。一旦習慣形成,它就如同是一個啟動了自動控制的程序,讓我們不必多想就能做出行動。
習慣能讓我們的生活更輕松。想想吧,如果你每天都需要提醒自己刷牙或者乘車上班,活著會有多累。麻省理工大學神經學家安·格雷比爾說:“我們在生活中所做的很多事情其實都是屬于習慣行為,僅此一點就令人吃驚。”南加州大學學者溫迪·伍德對學生行為進行了跟蹤調查,最后得出結論:我們的日常行為有40%是在習慣的驅使下完成的。她發現,學生們在做熟練的事情時,比如開車、鍛煉或刷牙,他們腦子想的常常是別的事情,習慣讓他們能夠一邊做事一邊思考,思想更為自由。
這讓我們想到了一個詞:熟能生巧,但是也表明,一種意識行為轉化為習慣時,我們大腦中的某些物質發生了改變。這正是格雷比爾在她的實驗室里研究的課題之一。她的主要任務是訓練一些嚙齒類動物和靈長類動物學習新本領,反復進行,直到它們的行為形成習慣,她在這一過程中監測它們的大腦活動。
她的實驗室最先發現的成果之一是習慣和大腦紋狀體有關,這一區域對于人和動物的運動、情緒和獎勵機制起著重要作用。老鼠學會了穿越迷宮,并且能習慣沿老路走出迷宮后,它們的大腦紋狀體區域腦波活動開始減緩。格雷比爾推測,腦波減緩表明可能是大腦這一區域的活動變得更協調和高效,促進了習慣的形成。
在另一項研究中,格雷比爾訓練幾只猴子辨別屏幕上閃現出的圓點,然后給它們水果獎勵,它們很快發現了以最快速度發現圓點的辦法,于是就能最快得到獎品。數次實驗后,猴子發現圓點的方式已經成了習慣,這時,它們大腦紋狀體細胞的活動也變得更協調。
重要的一點是,研究顯示紋狀體在一種行為的開始和結束時都會變得活躍,似乎是自動導航程序開始和結束的信號。格雷比爾在對老鼠和猴子進行的研究中一次又一次發現了這一現象。她說:“它們真正地形成習慣后,每次行動的開始和結束時,它們大腦中的很多神經活動就會進入這種狀態,仿佛是在調整思路。”你也許覺得這是大腦在開始習慣行為時尋求平衡,格雷比爾則稱之為“組塊”,也就是心理學家喬治·米勒的記憶理念:將零碎信息經過心理調整變為多個組塊,更容易記憶。比如記一個電話號碼,如果你將一長串數字當成一個整體,可能反復很多次才能記住。
積習難改
一種習慣的組塊讓我們不必把寶貴腦力用在簡單的行動上,但是它也有一個不利之處:讓我們改掉壞習慣相當困難。
大衛·尼爾是“觸發行為咨詢公司”創建人,他的公司專門為客戶解決決策和習慣上的問題。他說,壞習慣之所以難以改掉,也許是因為我們總是以目標為導向、以目標為動力,一種習慣形成時我們沒能真正意識到。拿我來說,我覺得咬指甲可以緩解緊張,而且如果我想戒就能戒掉;其實呢,我咬指甲時自己根本沒意識到。僅僅想戒掉是不夠的,因為習慣是無意識舉動,在我們大腦里已經根深蒂固。
不過,明白了這一點能讓我們以另外一些方式理解習慣。紋狀體幫助形成了習慣,但是格雷比爾推測大腦的下邊緣皮質這一小塊區域也是形成習慣的推手。有研究發現,動物切除了這一大腦組織后,它們要么是沒有了以前的習慣,要么是更多以目標為導向的方式行動。
這是因為一種習慣形成和結束時,下邊緣皮質內的神經發生了改變,格雷比爾決定用光遺傳學研究這一區域,這一技術能通過光的刺激來控制神經的活躍和靜止。動物大腦中的下邊緣皮質停止工作時,它們的習慣立即消失,老鼠們不再按熟悉的路線走迷宮。過了一段時間,老鼠們形成了按另一路線走迷宮的新習慣,直到格雷比爾再次對它們的下邊緣皮質進行刺激,它們的新習慣隨即結束,又恢復了原來的老習慣。
這一發現讓我們產生了一個有趣設想:針對下邊緣皮質進行研究,或許能幫我們改掉壞習慣。不過光遺傳技術至今沒有在人類大腦上進行實驗。經顱磁刺激技術是將微量電流作用于頭部外層,可以替代光遺傳技術,科學家已經研究用其治療上癮癥。深度大腦刺激是另一種選擇,醫學界現在已經將其用于治療抑郁癥和帕金森癥,用于強迫癥的治療正在進行。
然而,這些研究至今還沒能幫我改掉咬指甲的習慣。我希望知道的是:有的習慣我想保持,有的習慣我想放棄,大腦能甄別它們嗎?若是真的能駕馭習慣,我希望自己能夠不再視幸福為理所當然,而是每天心懷感恩地生活。
大腦如何對待好習慣和壞習慣的證據來自格雷比爾的另外一些實驗。老鼠學習走一條簡單的迷宮,走向左的路線可以得到巧克力牛奶,久而久之走這條路線成了它的習慣。后來實驗者在巧克力牛奶中摻入了化學制劑,導致老鼠生了病,而且不再對巧克力牛奶有食欲,它們仍然會走老路。它們無力改變自己的行動:那已經是一種習慣。
對于意志力的研究也能證明大腦不會區分好習慣和壞習慣。經歷一些磨難似乎才能體現人的意志力,比如我們想戒掉辦公室的零食、想強迫自己去健身房,而我們在一天的生活中動用的意志力越多,它就越容易耗盡,也就是說我們放棄繼續努力的可能性越大。
精神治療學家、《重新連線》一書的作者理查德·康納說:幸運的是,我們的能量儲備能在一夜的休息之后得到恢復,于是我們能夠帶著新能量開始每一天。可是在諸如緊張或疲憊的時候,能量得不到及時補充,我們就會恢復舊習慣,無論它是好是壞。隨著工作完成期限的臨近,我的指甲越來越短。難怪學生們考試前幾個星期各種習慣會增多,比如吃不健康零食。而另一方面,讀書、運動,這些好習慣也會增強。
目標導向系統和習慣系統
大衛·尼爾說,這是因為大腦中有兩個競爭系統:目標導向系統和習慣系統。目標導向系統是貴族系統,需要努力和強大的精神動力。這一系統難堪重負的時候,比如緊張考試的一周,習慣系統就會乘虛而入。習慣系統是一把雙刃劍,對人有利有弊。所以你要保持警醒,不要讓習慣“越過雷池”。
“人們容易返回到最頑強的習慣,無論它是好是壞。”溫迪·伍德說。有的習慣會比另外一個習慣更頑強,原因何在?多數習慣是以目標導向行為開始的:你想讓房間更整潔,所以你每天早上起床后疊被子;我想更開心,所以開始寫日記。但是天長日久,這些事就成了自動行為,會在無意識狀態下完成。
加州大學科學家克里斯蒂娜·格萊梅爾訓練老鼠以兩種方式按下操縱桿獲得甜飲料,一種是目標導向方式(只在它們口渴時進行),另一種是習慣行為(每次它們進入特定房間時進行)。
下一步,格萊梅爾使用光遺傳技術和化學方法阻斷了老鼠大腦中的某些區域。當一個叫作“眼窩前額皮質”的區域受到抑制時,老鼠們的行動習慣性更強,它們甚至在吃飽時也會按壓控制桿獲得食物。這一區域活躍起來時,它們的目標性更強。
格萊梅爾在老鼠的大腦中發現了負責這兩個系統的不同的兩個部分:目標導向行為依靠的是眼窩前額皮質和紋狀體中央部分(類似人類大腦尾狀核),而習慣依靠的是紋狀體外側部(類似人類大腦殼核)。
她的結論在對人進行的實驗中也得到了驗證。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心理學家桑內·威特研究了人們“動作失誤”和無意中恢復舊習慣的區別。譬如,有時人們本打算開車去商店,結果不知不覺中開車去了上班的地方。在這項研究中,志愿者學習玩一個電腦游戲,贏得金錢獎勵。他們學會之后,游戲規則改變了,容易動作失誤的人即使會輸錢,也繼續按原來的習慣按鍵盤。對他們的大腦掃描發現,和保持了目標導向行為的人(適應新規則并保持贏錢)相比,這些人的大腦殼核與腦皮質之間有著更強的聯系。
至于我們的大腦是如何連線從而形成習慣,每個人都存在個體差異。對于有些人來說,形成習慣和改變習慣的關鍵就是理解這些差異。《提升:掌控習慣》一書作者格蕾琴·魯賓說:“你在生活中常聽到很多建議:早上起來先做這件事,從簡單的事情開始做起,犒勞自己一天的胃……這些建議對有些人來說有時會管用,卻不會總是管用。”
康納的觀點與此不謀而合,在他的書中,康納列舉了一些或許會導致形成壞習慣的因素,比如過度的冒險或完美主義。和魯賓一樣,他強調,養成好習慣的第一步是在自己的個性中培養自我認知能力和洞察力。
我們也知道,習慣會憑借某些暗示或情境而形成。確實也許正是這些暗示讓大腦發出信號,告訴紋狀體“打開開關”,開始一種自發行為。我們在某些環境下,也會有做某些事的沖動。在一項實驗中,尼爾和伍德讓志愿者分別在電影院和會議室觀看電影光碟。在兩個環境中,他們給志愿者新鮮的爆米花和放了一個星期的爆米花。習慣吃爆米花的人在電影院中觀看光碟時吃了更多的陳爆米花,雖然他們承認這些爆米花味道不是很好。但是在會議室觀看同一光碟時,他們沒吃那么多爆米花。環境起了關鍵作用。
下一步是根據這一線索制訂一個明確的計劃。我打算在第一天臨睡前寫一篇日記,所以我把日記本放在了床前。每天晚上關燈前,我會先寫一篇日記。
“制訂出這樣簡明計劃的人通常效率會高很多。”威特說。有一個明確的計劃還能讓你更容易地做出明智的選擇,讓你即使在意志力薄弱的時候也能夠堅持下去。
與壞習慣一刀兩斷
正因為習慣和環境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旅行、換工作或者搬家的時候,是我們改掉舊習慣培養新習慣的最好時機。伍德在學生們進入大學前后研究了他們的習慣,她發現,他們看電視或去健身房的習慣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改變,這些習慣是好是壞姑且不論。他們的生活環境改變了,新習慣應運而生。
即使一些細節的改變也能助你一臂之力——比如我把日記本放在床頭這個暗示。“對于環境的小改變就能切實地起到大效果,這很令人驚奇。”尼爾說。
就我的咬指甲而言,想改變一下咬指甲的環境難度更大:我需要用手指打字,片刻不能離開它們。尼爾建議我把指甲涂上顏色,這樣能改變一下視覺感受。這個方法起了作用,雖然作用不大。
但是涂完指甲一個星期后,指甲油開始褪色,我洗凈了指甲。我向自己承諾盡快重新涂上指甲油,但是還沒等我意識到,我又開始咬指甲。
改掉舊習慣的另一要點是不要對這樣的小反復太過憂慮。倫敦大學學院對嘗試養成新習慣的大約100人進行了跟蹤研究,結果發現,偶爾一兩天的反復沒有影響到他們的長期目標。所以,如果你打算節食一個月,這期間有一天舊習復發,不要因此自認失敗。“你在腦子里建立了為期30天的節食計劃,”康納說,“僅僅在第31天時你放縱了一次胃口,你的30天節食成果不會消失。”魯賓建議,為了不讓小的反復像滾雪球一樣一發而不可收,可以把一天的生活劃分為幾部分。打個比方,如果你在上午開會時吃了過量餅干,在這一天的其余時間不要破罐子破摔。相反,你可以以中午作為另一個起點,重新開始節食生活。
康納說:“無論你的目標是什么,重新開始會比較容易,因為你剛剛行動過一次。”意志力如同練習樂器,它可能會被消耗,但是它也會越挫越勇。
一種好習慣的養成需要多長時間?康納說,至少要堅持3個月,這比人們通常認為的“養成習慣要21天”需要更長時間。倫敦大學學院研究發現,養成一個新習慣所需要的時間長短因人而異,平均時間是66天,但總體是從18天到254天不等。
我的親身經歷證實了這一說法。我寫日記的習慣實行起來比較輕松,一兩個星期后我對寫日記就已經習以為常。而相比之下,改掉咬指甲這個習慣就屬于254天的節奏了。要知道,堅持數月說明我有著鍥而不舍的精神。而且我也明白,每個人改掉一個習慣都會遇到困難。即使身為心理學家的威特也無奈地向她的同事承認,她一直沒能放下嚼泡泡糖的習慣。“不幸的是,研究習慣并不意味著你就任何壞習慣都沒有。”她說。寫文章說的頭頭是道,也并不保證你對習慣能駕馭自如。
怎樣改掉一個壞習慣?
1.制訂行動計劃。計劃出你要什么時候實行一種新習慣,并讓它成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把新習慣和你已有的習慣結合起來,比如刷牙后用牙線、午飯時吃一個蘋果、下班回家的路上去健身房。
2.明確目標。如果你想減少吃甜食,飲食規則就要為這一目標服務,比如永遠不在工作時間吃東西,或者只在一個星期的某一天吃一次。
3.體貼自己。格蕾琴·魯賓說,負罪感和羞恥感并不能幫你實現目標:“能夠體貼自己的人會表現得更好。”
4.從現在開始。一周第一天、一月第一天、一年第一天都是改變習慣的好時機,但是魯賓說:“開始行動的最好時間是在當下。”
5.要有恒心。有些習慣需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養成或改掉,所以你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譯自美國《新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