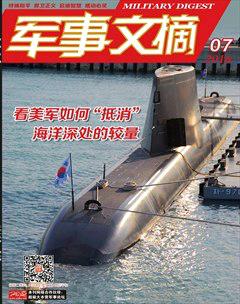越南戰爭:史上首場“藥物戰爭”
劉雅芳
越南戰爭被專業人士視為史上第一場“藥物戰爭”,因為美國立國以來,參與越戰的軍人服用的“精神作用性物質”的水平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波蘭國際政治學者盧卡什·卡明斯基所述,越南戰爭是“藥理學與暴力的決定性交點”。
以人們耳熟能詳的安非他命為例。卡明斯基在《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中指出,二戰后,幾乎沒有權威研究詳細論述此類藥物如何對士兵的表現產生影響,美軍卻毫不猶豫地將這種俗稱“快快”的非處方藥物送往越南。安非他命會被發放給那些執行遠程偵察和伏擊任務的部隊。
美軍對神經類藥物的使用一直有內部標準:在準備戰斗的48小時內只能服用20毫克安非他命,但這項標準很少被落實。一名老兵告訴卡明斯基,軍方發放安非他命就像給小孩發糖那樣,從不理會政府機構推薦的用藥量和頻率。《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一書援引了1971年美國眾議院特別犯罪委員會的一份報告,1966年至1969年,美軍共使用了2.25億片興奮類藥物,包括安非他命的各種衍生品,比二戰時期增長了1倍有余。彼時,美國海軍每人每年平均服用21.1片興奮劑,空軍每人每年是17.5片,陸軍“僅有”13.8片。
當時有研究顯示,被派駐越南的士兵中,大約每30人中就有一人服藥過量。簡而言之,美國軍方對興奮劑濫用持默許態度,無論這可能誘發何種結果。事實上,老兵們普遍意識到,安非他命會強化人的攻擊性和戒備心。一些老兵回憶,每當“快快”的效果消失,他們就會焦躁,感覺自己像“在大街上開槍掃射那樣”。
精神刺激類藥物不僅能增強戰士的戰斗力,還有助于降低連續戰斗對參戰者情緒造成的不良影響,避免士兵因心理壓力而當場崩潰。諸如葛蘭素史克公司生產的氯丙嗪等化學品,第一次被作為日常軍需物資,投放戰場。

據此,卡明斯基在其專著中指出,如此大規模地使用精神類藥物,加上大量征用心理醫生等因素,有助于解釋為何在越南戰爭中,美國軍人遭遇“戰斗創傷”的幾率如此低:二戰時,美國士兵的精神崩潰率高達10%,朝鮮戰爭時期的精神崩潰率是4%,而到了越南,這個比例只有1%。
如果你為這樣的數字而欣喜,那無疑是目光短淺的。抗精神病類藥物和興奮劑的效果是迅速且短暫的,若不輔以適當的心理治療,過量服藥只能減輕或暫時壓制問題,讓問題牢牢“嵌入”當事人心靈深處。幾年以后,戰地綜合征會以幾倍的力量爆發。
多數精神類藥物并不能根除導致壓力的原因,就像用胰島素治療糖尿病一樣,可以緩解癥狀,但疾病還在。明確了這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與之前的戰爭相比,越戰中很少有士兵因為在前線精神失常而被送療;另一方面,越戰老兵在戰后卻被規模空前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困擾。很大程度上,這是將矛盾往后拖延的必然結果。
《嗑藥:藥物與戰爭簡史》一書提到,遭受創傷后應激障礙困擾的越戰老兵的確切數量目前仍不得而知,但有民間統計者認為,數量在40萬至150萬人之間。1990年發布的《全國越戰老兵再調整研究報告》稱,在東南亞地區經歷過作戰行動的士兵中,有15.2%遭受創傷后應激障礙折磨。從道德層面上講,在越戰中發生的一切,就好比對一個受了傷的士兵施加催眠術,然后再把他送回槍林彈雨中那樣。
摘自《青年參考》2016年04月27日
責任編輯:劉靖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