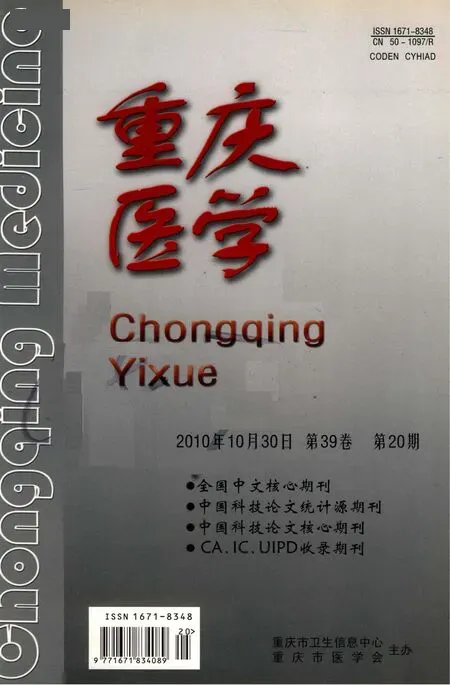肩關(guān)節(jié)雙注射治療早期凍結(jié)肩的臨床研究
張 茂,段群力,譚洪波
(1.武警8740部隊(duì)醫(yī)院,四川 南充 637000;2.解放軍昆明總醫(yī)院全軍骨科中心,云南 昆明 650032)
原發(fā)性凍結(jié)肩是臨床常見的疾病之一,嚴(yán)重影響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凍結(jié)肩早期治療均以保守治療為主,臨床治療方法很多,包括理療、針灸、激素注射、玻璃酸鈉注射、局部封閉、痛點(diǎn)注射等單一方法及組合方法[1-2]。口服NSAIDs類藥物是最方便也是最普遍的一種方法。如何能夠簡便、有效盡早解除疼痛,恢復(fù)肩關(guān)節(jié)功能是所有治療追求的目標(biāo)。2003年10月至2006年7月作者對(duì)武警8740部隊(duì)醫(yī)院門診76例早期凍結(jié)肩患者分組行肩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及肩峰下雙注射德寶松加利多卡因,觀察患者肩關(guān)節(jié)功能和疼痛改善情況。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自2003年10月至2006年7月門診確診Ⅰ、Ⅱ期凍結(jié)肩患者 76例,年齡34~73歲(平均 53.7歲),男 23例,女53例,病史10~60 d(平均 28 d)。左肩 37例,右肩 39例。排除其他原因?qū)е碌奶弁春突顒?dòng)度受限后,診斷由病史和體檢判斷:無誘因起病,患側(cè)肩關(guān)節(jié)疼痛伴夜間痛,肩關(guān)節(jié)主動(dòng)、被動(dòng)活動(dòng)均明顯受限,上舉小于100°,外旋小于健側(cè)的一半,肩關(guān)節(jié)正側(cè)位X線片顯示關(guān)節(jié)正常。凍結(jié)肩Ⅰ期(又稱急性期)界定為起病急劇,疼痛顯著,活動(dòng)受限但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注射后活動(dòng)可恢復(fù)正常。凍結(jié)肩Ⅱ期(又稱凍結(jié)期)疼痛相對(duì)減輕,活動(dòng)受限,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注射后活動(dòng)僅可部分恢復(fù)。本組患者凍結(jié)肩Ⅰ期為13例,凍結(jié)肩Ⅱ期為63例。
1.2 治療方法 患側(cè)肩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注射德寶松注射液0.5 mL加2%利多卡因2.5 m L,同時(shí)肩峰下每周注射1次德寶松注射液0.5 m L加2%利多卡因2.5 m L,共 3次。如果患者疼痛顯著,活動(dòng)受限但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注射后30 min內(nèi)活動(dòng)可恢復(fù)正常,界定其為凍結(jié)肩Ⅰ期。如果患者疼痛顯著,活動(dòng)受限但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注射后30 min內(nèi)活動(dòng)僅部分恢復(fù)正常,界定其為凍結(jié)肩Ⅱ期。注射后一般不予口服抗菌藥物,院外行功能鍛煉。
肩關(guān)節(jié)功能鍛煉方法:在注射治療后,每天進(jìn)行肩關(guān)節(jié)鐘擺、環(huán)轉(zhuǎn)運(yùn)動(dòng),并在醫(yī)生指導(dǎo)下回家進(jìn)行棒操或攀墻,或行被動(dòng)滑輪上牽等功能鍛煉,每天 3~5次,每次20 min。第1個(gè)月每周門診復(fù)查1次,此后每個(gè)月復(fù)查1次,根據(jù)患者肩關(guān)節(jié)恢復(fù)情況適當(dāng)調(diào)整鍛煉次數(shù),必要時(shí)進(jìn)一步檢查和治療。
肩關(guān)節(jié)腔及肩峰下雙注射方法:取坐位,患肩關(guān)節(jié)暴露,取肩峰和鎖骨交界點(diǎn)內(nèi)側(cè)凹點(diǎn)為穿刺點(diǎn),消毒鋪巾,戴無菌手套,注意嚴(yán)格規(guī)范的無菌操作技術(shù),應(yīng)用普通7號(hào)注射針頭垂直皮膚向下穿刺,有落空感表明進(jìn)入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注射后拔出。另在肩峰外側(cè)中點(diǎn)下緣水平進(jìn)針約2 cm,回抽無血,進(jìn)行肩峰下注射,兩注射點(diǎn)均貼消毒敷料 24 h(圖1)。
1.3 肩關(guān)節(jié)療效評(píng)定方法 從開始注射后1、3個(gè)月及末次評(píng)分采用VAS視覺模擬疼痛評(píng)分評(píng)定主觀疼痛癥狀改善情況,Constant肩關(guān)節(jié)功能評(píng)分進(jìn)行療效評(píng)定。康復(fù)標(biāo)準(zhǔn)為相對(duì)對(duì)側(cè)最大損失15°外旋和前屈或最大損失3個(gè)脊髓水平內(nèi)旋。
1.4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各組內(nèi)評(píng)分結(jié)果行自身治療前、后對(duì)比的t檢驗(yàn)。
2 結(jié) 果
患者從首次治療后1、3個(gè)月及末次的門診隨訪,其各項(xiàng)評(píng)分測定結(jié)果和統(tǒng)計(jì)分析結(jié)果(圖2、3)。本組患者的術(shù)后疼痛程度及功能評(píng)分與術(shù)前相比均有顯著提高(P<0.05)。沒有藥物不良反應(yīng)和關(guān)節(jié)注射感染等情況。其中9例關(guān)節(jié)功能鍛煉期間失訪,但對(duì)末次隨訪評(píng)分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76例中的72例符合研究確定的康復(fù)標(biāo)準(zhǔn),平均3.6個(gè)月,其中凍結(jié)肩Ⅰ期患者為6周(2周至3個(gè)月),凍結(jié)肩Ⅱ期患者為4個(gè)月(2周至18個(gè)月)。凍結(jié)肩Ⅰ期患者康復(fù)速度超過凍結(jié)肩Ⅱ期患者。同時(shí)4例不符合研究確定的康復(fù)標(biāo)準(zhǔn),于注射后平均5.7個(gè)月(3~8.5個(gè)月)入院接受關(guān)節(jié)鏡下手術(shù)治療。

圖1 肩關(guān)節(jié)注射示意圖

圖2 治療前、后VAS評(píng)分比較

圖3 治療前、后Constant評(píng)分比較
3 討 論
原發(fā)性凍結(jié)肩是由盂肱關(guān)節(jié)囊攣縮或順應(yīng)性喪失所致的自發(fā)性盂肱關(guān)節(jié)的活動(dòng)受限,病變集中于關(guān)節(jié)囊包括滑膜層和滑膜下組織。在關(guān)于粘連性關(guān)節(jié)囊炎分期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臨床、關(guān)節(jié)鏡和組織學(xué)表現(xiàn)進(jìn)一步定義了凍結(jié)肩的分期[3]。凍結(jié)肩Ⅰ期,患者表現(xiàn)為疼痛和活動(dòng)受限,在麻醉狀態(tài)下活動(dòng)范圍不喪失,病理分析顯示為炎癥性滑膜炎和正常的關(guān)節(jié)囊。凍結(jié)肩Ⅱ期患者表現(xiàn)為疼痛和活動(dòng)受限,但在麻醉狀態(tài)下活動(dòng)范圍不能完全恢復(fù),病理顯示滑膜增生和關(guān)節(jié)囊纖維形成及纖維化;凍結(jié)肩Ⅲ期患者表現(xiàn)為中度疼痛和顯著的活動(dòng)喪失,輕微滑膜炎關(guān)節(jié)囊纖維形成和關(guān)節(jié)囊瘢痕形成。凍結(jié)肩Ⅳ期為功能恢復(fù)期,功能恢復(fù)期關(guān)節(jié)炎癥逐漸恢復(fù)吸收,滑膜逐漸恢復(fù)及滑液分泌,關(guān)節(jié)容積逐漸恢復(fù)正常。
凍結(jié)肩的粘連性關(guān)節(jié)囊炎既是炎癥又有纖維化,早期的血管增生性滑膜炎導(dǎo)致后來的滑膜和關(guān)節(jié)囊纖維化[4]。細(xì)胞因子參與組織損傷和修復(fù)過程,它們的持續(xù)作用導(dǎo)致組織最終的纖維化。Rodeo等[5]報(bào)告轉(zhuǎn)化生長因子-β,血小板衍生生長因子和肝細(xì)胞生長因子在原發(fā)和繼發(fā)性凍結(jié)肩患者的關(guān)節(jié)囊活檢標(biāo)本中染色增加,提示這些細(xì)胞因子參與炎癥和纖維化過程。Stergioulas[6]報(bào)道基質(zhì)金屬酶可能也與凍結(jié)肩的粘連性關(guān)節(jié)囊炎有關(guān)。凍結(jié)肩肩峰下滑囊也存在滑膜的病理改變,由于肩峰下滑囊的滑膜病變導(dǎo)致患者康復(fù)鍛煉時(shí)疼痛,影響疾病恢復(fù)效果。
對(duì)凍結(jié)肩的治療傳統(tǒng)上認(rèn)為其具備自愈性,治療主要集中在對(duì)癥方面。然而,長期隨訪研究證實(shí),經(jīng)過最少3年隨訪,仍然有50%的患者有疼痛或(和)關(guān)節(jié)僵硬,該研究報(bào)道的平均恢復(fù)時(shí)間為12個(gè)月[7]。肩關(guān)節(jié)周圍肌肉與凍結(jié)肩有關(guān),手術(shù)方法有采用手術(shù)松解攣縮,切除肱二頭肌肌腱的關(guān)節(jié)內(nèi)部分并松解肩胛下肌;或者因?yàn)閺?qiáng)調(diào)喙肱韌帶的重要性并建議對(duì)它進(jìn)行松解以改善肩關(guān)節(jié)的外旋;Mitra等[8]在手術(shù)治療肩關(guān)節(jié)僵硬患者中診斷了1組“旋轉(zhuǎn)肌間隙損傷”患者,他們強(qiáng)調(diào)切開手術(shù)中重建岡上肌和肩胛下肌旋轉(zhuǎn)間隙的重要性;也有學(xué)者選擇進(jìn)行更為急進(jìn)的關(guān)節(jié)鏡清理治療,手術(shù)結(jié)果顯示改善了癥狀,但是手術(shù)帶來的并發(fā)癥和手術(shù)本身的創(chuàng)傷及費(fèi)用,使得該方法具備局限性。凍結(jié)肩患者多存在肩峰下間隙的病變,包括肩峰下滑囊炎和岡上肌鈣化等[9]。
早期關(guān)節(jié)內(nèi)皮質(zhì)激素注射能減輕滑膜炎癥,從而限制纖維化的發(fā)展和縮短自然病史。凍結(jié)肩的粘連性關(guān)節(jié)囊炎自限性特征,支持滑膜對(duì)啟動(dòng)和調(diào)整關(guān)節(jié)囊的纖維化進(jìn)程有一定作用。隨著滑膜炎癥的消退及關(guān)節(jié)囊瘢痕形成的終止,關(guān)節(jié)囊得到重塑關(guān)節(jié)的活動(dòng)度得以恢復(fù)。Marx等[1]比較盂肱關(guān)節(jié)腔注射皮質(zhì)類固醇和6周的物理治療“疼痛僵硬的肩關(guān)節(jié)”患者,雖然不清楚有多少患者是真正的凍結(jié)肩,但是他們發(fā)現(xiàn)注射組在第3、7周顯著改善疼痛和運(yùn)動(dòng)。Lee等[10]運(yùn)用盂肱關(guān)節(jié)腔注射皮質(zhì)類固醇或者注射皮質(zhì)類固醇并用19 m L利多卡因擴(kuò)張關(guān)節(jié)治療粘連性關(guān)節(jié)囊炎患者,他們發(fā)現(xiàn)運(yùn)用少量局麻藥并同時(shí)運(yùn)用皮質(zhì)類固醇能更好地改善運(yùn)動(dòng),雖然VAS評(píng)分基本相同。Elleuch等[11]總結(jié)許多使用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注射糖皮質(zhì)激素的研究后認(rèn)為:成功的治療取決于癥狀的持續(xù)時(shí)間;癥狀出現(xiàn)1個(gè)月內(nèi)治療后,平均1.5個(gè)月癥狀恢復(fù);癥狀出現(xiàn)2~5個(gè)月者恢復(fù)需要8.1個(gè)月;出現(xiàn)癥狀6~12個(gè)月后治療者,平均需要14個(gè)月恢復(fù)。
本研究中作者發(fā)現(xiàn)患者癥狀恢復(fù)平均3.6個(gè)月,許多患者不到3個(gè)月癥狀基本就恢復(fù)了。凍結(jié)肩Ⅰ期患者恢復(fù)較凍結(jié)肩Ⅱ期患者恢復(fù)快,凍結(jié)肩Ⅰ期患者為6周(2周至3個(gè)月),凍結(jié)肩Ⅱ期患者為4個(gè)月(2周至18個(gè)月)。以前的基礎(chǔ)科學(xué)研究指出,早期的凍結(jié)肩粘連性關(guān)節(jié)囊炎僅表現(xiàn)出滑膜炎而無關(guān)節(jié)囊纖維化,盡早抑制滑膜炎將減少關(guān)節(jié)囊瘢痕形成,改善關(guān)節(jié)運(yùn)動(dòng)范圍[12]。本研究選擇對(duì)肩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及肩峰下雙注射糖皮質(zhì)激素和局麻藥同時(shí)抑制了盂肱關(guān)節(jié)和肩峰下滑囊內(nèi)的炎癥,減少了盂肱關(guān)節(jié)和肩峰下滑囊內(nèi)的粘連,因?yàn)榧缧浼凹绶逑禄覂?nèi)炎癥的抑制對(duì)改善肩關(guān)節(jié)周圍肌肉功能也有很大的幫助,有利于凍結(jié)肩術(shù)后的功能恢復(fù)特別是外展功能的恢復(fù)。局部注射局麻藥抑制關(guān)節(jié)活動(dòng)疼痛對(duì)肩關(guān)節(jié)功能鍛煉也有一定改善。
總之,肩關(guān)節(jié)腔內(nèi)及肩峰下雙注射糖皮質(zhì)激素和局麻藥對(duì)早期階段凍結(jié)肩粘連性關(guān)節(jié)囊炎的炎癥具備一定抑制作用,并能緩解關(guān)節(jié)活動(dòng)疼痛,促進(jìn)肩關(guān)節(jié)功能鍛煉。盡早確診凍結(jié)肩和早期注射皮質(zhì)類固醇和局部麻醉有利于該疾病的早期治療。
[1]Marx RG,Malizia RW,Kenter K,et al.Intra-articular corticosteroid injection for the treatmentofidiopathic adhesive capsulitis of the shoulder[J].HSS J,2007,3(2):202.
[2]魏安寧,曾令全,傅洪.當(dāng)歸、地塞米松、布比卡因復(fù)合治療肩周炎的療效觀察[J].重慶醫(yī)學(xué),2005,34(8):1197.
[3]Ng CY ,Amin AK ,Narborough S ,et al.Manipulation under anaesthesia and early physiotherapy facilitate recovery of patients with frozen shoulder syndrome[J].Scott Med J,2009,54(1):29.
[4]Austgulen OK,Oyen J,Hegna J,et al.Arthroscopic capsular release in treatment of primary frozen shoulder[J].Tidsskr Nor Laegeforen,2007 ,127(10):1356.
[5]Rodeo S A,Hannafin JA ,Tom J,et al.Immunolocalization of cytokines and their receptors in adhesive capsulitis of the shoulder[J].J Orthop Res,1997 ,15(3):427.
[6]S tergioulas A.Low-pow er laser treatmentin patients with frozen shoulder:preliminary results[J].Photomed Laser Surg ,2008,26(2):99.
[7]Khan JA ,Devkota P,Acharya BM ,etal.Manipulation under localanesthesia in idiopathic frozen shoulder-a new effective and simple technique[J].Nepal Med Coll J,2009,11(4):247.
[8]Mitra R,Harris A ,Umphrey C,etal.Adhesive capsulitis:a new management protocol to improve passive range of motion[J].PMR,2009,1(12):1064.
[9]張曉星,唐康來,陳光興,等.關(guān)節(jié)鏡下關(guān)節(jié)囊松解治療原發(fā)性凍結(jié)肩的早期臨床隨訪[J].中國矯形外科雜志,2006,28(9):1291.
[10]Lee HJ,Lim KB,Kim DY,et al.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for efficacy of intra-articular injection for adhesive capsulitis:ultrasonography-guided versus blind technique[J].Arch Phys Med Rehabil,2009 ,90(12):1997.
[11]Elleuch M H,Yahia A ,Gh roubi S,et al.The contribution of capsular distension to the treatment of primary adhesive capsulitis of the shoulder:a comparative study versus rehabilitation[J].Ann Readapt Med Phys,2008,51(9):722.
[12]劉春梅,唐康來,韓琳,等.關(guān)節(jié)鏡下松解治療原發(fā)性凍結(jié)肩13例術(shù)后的康復(fù)護(hù)理[J].重慶醫(yī)學(xué),2006,35(13):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