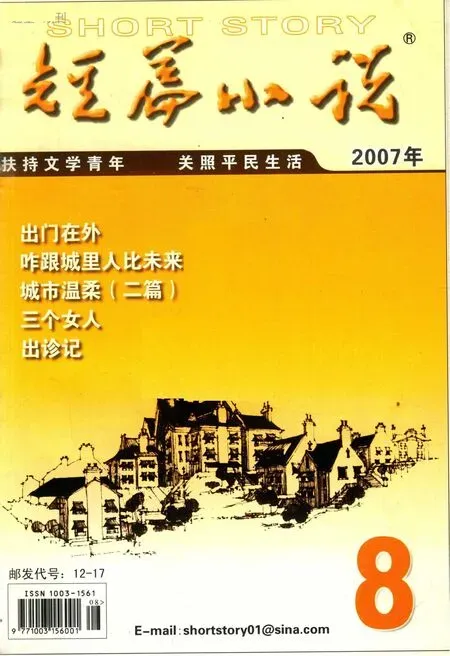喪偶之后
◎王東梅
?
喪偶之后
◎王東梅
01
雪然站在老屋門前,目光如慢鏡頭,移至老屋側邊那扇色澤暗淡的木門上。門上的紅漆早已褪落,東一塊、西一塊地裸露在外。那些勉強留在門上的,也難以蓋住木門的滄桑。兩邊的門框處,剝蝕的白幡在隨風擺動。
雪然的目光掠向門框,心倏地被一下下撕得好痛。腦海里,和羅大笑的婚禮好像剛剛才辦過,怎么轉眼間,門上就貼著祭奠他的白幡呢?
抬手,那笨拙、滯澀的兩扇窄門,疲憊地“吱嘎”應聲作響。空空的屋內,帶著一股冷清的霉味。新屋建起后,婆婆帶著桃果果、杏果果搬到新家,這老屋除了這股冷清的霉味,便是一些老舊的、破敗的、不能再用的家什了。
雪然嘆了口氣,打開四壁的窗戶通通風,然后拎著掃帚,挽起袖子,利索地在老屋里清掃起來。經過一番整治,空氣中多了絲鮮活。一道陽光透過老屋的窗子照在桌面,衛哥的電話就在這時打了進來。
衛哥問:雪然,你到家了嗎?
到了。雪然握著手機的胳膊,順勢把掃帚夾在腋窩里,另一只手仍不落閑地抹著窗角的蜘蛛網。
你一路還好不?路上暈車沒有?
好!還是那個接電話的姿勢,只是手中的抹布又移到了舊衣柜上。
雪然……電話那頭欲言又止。
嗯,你說。雪然停下了手中的活兒。
電話卻沉默了。好一會,才傳來衛哥的聲音:雪然,你是真的回去相親嗎?
雪然怔了怔,咬著嘴唇,喉嚨上下動了半天,還是“嗯”了一聲。
聲音剛落,雪然感覺到電話那端,衛哥的呼吸重了起來。遠處,八歲的大兒子桃果果牽著五歲的妹妹杏果果,正向老屋走來。
雪然匆匆說了一句:衛哥,我掛了。就“啪”地合上手機,一顆心懸在半空,乒乓地亂跳起來。
第二天,婆婆換上了雪然從深圳為她買來的新衣,吃過早飯,去了湖村的鎮街。中午返回時,雞鴨魚肉菜拎回了一堆。隨后又請了隔壁的八嬸和春子娘來幫忙,三人殺雞、剔魚,整整忙了半下午。
到黃昏,灶上的香氣開始在屋子彌漫。婆婆沖著房內吩咐:雪然,一會有客人要來,你快去洗把臉、換件新衫子,最好畫點妝什么的。邊說,邊笑著探頭往內屋望。
晚上的客人是八嬸娘家的子侄曉光,婆婆作主請的。婆婆說:人還不錯,在下屋墩種大棚培植鮮平菇。前些年離的婚,也就一個兒子。
這些,婆婆電話中給雪然說過。雪然當時一聽是離過婚的,心中就打起小鼓,不再言語了。
婆婆說:男方她見過,還不錯,是老實厚道的那一種。他離的那婚也不是男家錯,聽說女家性子烈,動口罵人,還帶粗打了曉光他娘,鬧得曉光他娘喝了農藥。最主要的,他愿意上門給咱家頂煙食(倒插門的意思)呢!你就回來見他一趟吧!
婆婆說得很誠懇,雪然不想違她老人家的意。想著好長一些日子沒有見到婆婆,桃果果、杏果果也不知長高沒有?想著,就請衛哥幫忙訂了票。
天黑透的時候,曉光來了。矮實實的個兒,雪然端菜到門口時,他剛剛進屋,看到雪然,他招呼的話沒有說出口,額頭上就淌起一層細汗。幾句話在舌頭上結結巴巴地打著結,最后又轉個彎才吐出來。
雪然當時忍不住就“噗哧”一下笑起來。還真是老實厚道呢!婆婆說得一點不假。只是,她真的能和這類男人相處好嗎?會過得開心嗎?這些她真沒有想好。在羅大笑走后的這幾年時間里,她早已習慣詼諧風趣的衛哥在電話里、在生活中,處處哄她、逗她開心。
婆婆過來時,雪然還怔在廚房半天沒動。婆婆笑著輕扯她的衣襟,示意雪然到廳堂吃飯。一伙人在八嬸的笑中都上了桌。
02
后夜的時候,纏著曉光鬧了半宿的桃果果、杏果果兄妹終于睡去。雪然手機又一次響起來,還是衛哥的。從中午到現在,手機上有他的十來個未接電話了。
雪然看了看旁邊酣睡的一雙兒女,再次摁掉了手機。想了想,干脆爬起來倒出手機電池,才重新躺上床。
靜謐的夜,偶爾有一兩聲蛙鳴傳來,雪然躺在床上,思緒隨著蛙鳴,一陣陣飄得老遠。她一會想起羅大笑,一會又想起了衛哥。想到羅大笑,一顆心懸在半空,空落落地難受得緊。想到衛哥時,心莫名地沉下來,泛起一陣陣酸楚。
她揪著被子捂在臉上,任淚再次如同早前無數個夜晚那般淌在被褥上。只待明天太陽出來后,隨空氣散去。
迷迷糊糊中,窗外傳來聲響。她坐起來,看了看熟睡的一雙兒女,輕手輕腳地走至窗邊,外面黑黑的、靜靜的。她剛想摸回床邊,玻璃窗上的聲響又傳過來。這次是輕叩,有節奏地輕叩。
雪然心一驚,拉開燈走到窗邊。推窗,窗外驀然站著衛哥。雪然揉了揉眼,真是他!
天殺的!雪然捂著嘴輕罵,手卻讓衛哥隔窗箍著,一把拉過去貼在他臉上。我不叫你相親!這次回來之前,我都想好了。這次返深圳,我就跟阿英攤牌,我娶你!我一定要娶你!隔著防盜窗,衛哥喘著粗氣,溫熱的氣息一陣陣傳了進來。
雪然的淚不爭氣地大滴、大滴滾下來。三年了!衛哥終于對她許下承諾。屋內,桃果果輕喃了一聲,雪然忙示意衛哥放開她的手,抹去眼淚,躡手躡腳溜出了房。
第一次見衛哥,是在她和羅大笑的婚禮上。那晚的喜席過后,羅大笑的一群同學借酒勁,一伙擁著鬧洞房。當時就數衛哥鬧得歡,新奇的招數一出又一出,整得雪然叫苦連天。但是新婚之夜又不便發作,只得強顏歡笑著應和。以致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她看不得衛哥。看見他來,就不給他好臉色看。
婚后四年,羅大笑出事了。壓模機齊齊絞去了他的右臂,送到醫院,卻因失血過多已搶救無效。衛哥在深圳沙井這邊聽到羅大笑離開的噩耗,連夜開著他的紅旗去了平湖。看著哭成一團的雪然,他幫忙處理好羅大笑和工廠間的賠償事務,又陪著雪然,把羅大笑的靈柩送回湖南老家安葬。看著雪然成天渾渾噩噩地伏在羅大笑的靈前流淚哭泣,衛哥再三勸說,雪然終于答應和他一起來沙井。
初來沙井,雪然進了衛哥出租車公司不遠的一家電子廠,工資、待遇都還不錯。可工作不到一星期,雪然就連受了三次罰款。
因為是她工作時老走神,一次一次地錯把不良品流到后臺。當第三次罰款單下來后,雪然收拾好自己的私人物品,離開了這個工作剛剛一星期的電子廠。
之后,衛哥在沙井人行橋不遠的夜市,為雪然聯系到一個攤位,賣日雜小百貨。每天下午三點,衛哥會準點過來,幫忙雪然出攤,然后去兜幾圈客。到了晚上七點左右,他又習慣地把出租車停在天橋一側,一邊待客,一邊幫忙雪然張羅攤位上的生意。
直到一年后,夜市不遠的家福生活超市轉讓。在衛哥的提議下,雪然低價接了過來,并重新裝修了一番。
店子剛開張那陣,生意連著幾個月都很清淡,雪然愁得不行。衛哥冥思苦想了幾日,讓人印了一些名片。雪然看著名片上印的“十元起送”的送貨傳單,望著衛哥,一時哭笑不得。
衛哥拍了拍胸膛:嘿嘿,看我的!抓著名片,一陣風地跑了。
傍晚時,衛哥空著手回來。雪然店中的電話也開始響起來,都是鄰近住戶要貨的。雪然對著電話手足無措,衛哥笑嘻嘻接完電話,利索地揀貨、打包。
出門前,又吩咐雪然:電話再來你就接。人家要什么,你記著就行。幾樓幾戶、要些什么,你一一記清,我回來一一給他們送去。話畢,對著雪然邊擠眉弄眼,邊提著貨品,一路后退、一路往小區走。雪然陰霾多月的臉上噗嗤笑出了聲,心倏地松下來。
晚上清賬,營業額比以往見漲不少,雪然的心情極好。看著勞累一天的衛哥,心里很是過意不去。
關門后去隔壁潮州餐館叫了幾個小炒,又拿出店里最好的紅酒,開瓶給衛哥斟了一杯,又給自己也滿上。兩只杯子在半空中“哐啷”輕撞后,她動情地說:衛哥,謝謝你!謝謝你這幾年盡心幫我。
應該的、應該的。衛哥一飲而盡。
雪然又給他滿上:衛哥,羅大笑有你這樣的同學,是他的福氣。我代他謝謝你。
雪然再次給衛哥的杯子斟滿。衛哥的手卻蓋在杯口上,盯著雪然半天不動。
好一會兒,他松開放在杯口的手,一把抓住雪然,雙眼鎖著雪然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雪然,我對你的好,不全是因為我和羅大笑是同學。你是真不能懂嗎?
雪然故意別過頭,避開衛哥灼熱熱的目光,手連連抽退,欲掙脫衛哥緊攥著的手。衛哥用力,再一次拉著雪然的手,覆在他的掌心,眼睛亮亮地緊盯著她說:這么久了,難道你真沒有一點感覺么?
雪然的手在衛哥的掌心里微微淌汗,心開始一陣陣稠起來。她不是聾子,更不是瞎子,羅大笑走后的這幾年時光,如果不是衛哥,她都不知該如何走下去!
她慢慢翻轉過手心,別過頭迎著衛哥的目光,手跟著回握了衛哥的手。衛哥扳過她的身子,一把擁她入懷中,溫熱的嘴唇在雪然的耳際游動。嗅著衛哥身上淡淡的煙香,雪然的呼吸開始“哧兒哧兒”地粗重起來。她顫栗著,雙手輕輕摩挲著衛哥堅實的后背,曲線豐滿的身體同時緊緊地貼在衛哥胸前……
逼仄的出租屋床上,雪然感覺自己就像截冬日里枯死的木頭,在一夜間,陡然又開出了一朵又一朵嬌媚的花。
03
阿英的電話在第二天一早打了進來。衛哥在被窩里摟著雪然,對她豎起食指,示意她不要作聲。隨后接通電話,把手機放在耳邊說:跑了個長途。
電話那端,阿英的聲音明顯大了起來:長途、長途,又說跑長途!你的錢呢?都沒有看到錢在哪?是不是跑哪鬼混去了?
衛哥翻了一個身:沒呢!老婆,我真的跑了長途。剛剛太累,就在車上瞇一會兒,一會兒就回去。回去跟你說,行不?
收了線,衛哥一個翻身向雪然壓過來:寶貝,咱們來趟長途?
雪然心中感覺很不是滋味,轉了一個后背對衛哥,躺在那兒半天沒有說話。
過了一會兒,她光著身子下床,在衣櫥頂蓋上,抽出她放錢的皮夾子,數出幾張鈔票,放在衛哥褲袋中的錢包里,對坐在床上的衛哥說:師傅!看著,這是你的長途“的士費”!
衛哥坐在床上,嘴hold著了。
轉眼快到暑假,店里的飲品開始熱銷起來,要求送貨的人也越來越多。雪然趕走衛哥,招了一個送貨的小弟打零工。
其后衛哥來了幾次,雪然都故意冷著臉不理他。
但衛哥每次來,還是習慣忙上忙下整理店面,這兒清清、那兒抹抹。有時還會干脆去菜市場買菜,煲好湯,嬉皮笑臉雙手端過來,一聲聲道:啟稟太后,您的用膳時間到了!
雪然的心又軟了下來。
七月,婆婆帶桃果果、杏果果兄妹來了深圳。店里的生意更忙了,有時忙起來,雪然也得跟著跑外送。好在婆婆能幫著照看店鋪,剛上小學的桃果果也學會去冰箱里加冷飲。這段日子,衛哥不便常來,婆婆和兒子能幫上忙,讓雪然著實心安不少。
七月過了一半,婆婆突然變得沉默起來。雪然問了她幾次,她什么也不說,轉身把自己關進房中。
跟著變得沉默的還有桃果果,好像雪然得罪了他。雪然在家,他就跟奶奶一起躲進房中;雪然外出送貨,他小心翼翼走到收銀臺前守著。這個從小失父的孩子,心思過早地比同齡的孩子成熟很多。雪然問他,他每次總是別過臉,什么也不說。
雪然把目標轉向了小女兒杏果果。
杏果果的話讓雪然大吃一驚。杏果果說:前些日子房東阿嬸來催租,阿媽你不在,房東阿嬸把衛哥叔當成了我爸,和奶奶嘮了很久!
當初開這個店,談房租、訂合同都是衛哥一手負責管的。雪然也沒有為此刻意解釋,喪偶之痛不是誰都能說出口的。另外,她還有一層私心,她怕一個喪偶的身分,會給自己的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和麻煩。
衛哥借著載客路過的借口,偶爾還會過來幫忙,每次都給婆婆和桃果果、杏果果兄妹買很多吃食。衛哥前腳剛走,婆婆后腳當著雪然的面,一聲不吭地把衛哥送來的東西,全給扔進垃圾屋里。
其間衛哥也還帶著阿英,來看過婆婆一次。
婆婆對著阿英說了不少感激話,阿英還是多年前那副沒心沒肺的樣子,對著婆婆,直把衛哥夸上天。雪然在店里沒有去接口談論什么,她有意用收銀的借口,不去接話。確切地說,她不知怎么面對阿英。但一對耳朵倒沒有閑著,一刻不停地繞著他們的談話轉。
阿英對婆婆說:衛哥這人很不錯的,大方義氣,親戚朋友間,對誰都好。看我這手,阿英對婆婆抖動著她手腕金燦燦的鐲子:純金的,我生日時衛哥送的。
雪然聽后,心一酸,不舒服起來。
婆婆說:真是不錯,你有福。說這話的時候,婆婆的眼睛有意無意掃向雪然。雪然迎著婆婆陰冷的眼光,心倏地很痛、很痛,不安也加重起來。
八月底,婆婆帶著桃果果、杏果果兄妹回湖南老家去讀書。衛哥送他們到車站搭車,婆婆幾次欲言又止,臨上車,借故支開衛哥,對雪然說:有合適的,你找一個,媽不會反對的!
雪然看著婆婆,眼睛落在地面上,不敢出聲。
04
天亮的時候,雪然別過衛哥,悄悄溜回了自己的屋子,桃果果、杏果果兄妹已不在床上。她剛收拾好隨身的行李,婆婆就走了進來。婆婆看著雪然紅腫的雙眼,嘆了口氣,一言不發退了出來。
雪然跟到廚房,看到婆婆在灶臺邊抹眼淚。看到雪然,她轉過身,在碗柜里抓了幾只雞蛋走去灶邊,說是給雪然下蛋面。雪然蹲在灶前幫忙添火。婆婆問:雪然,你怨媽不該著急給你張羅人是不?媽知道曉光配不上你,可是這孩子心實呀!他一定會對咱們娘幾個好的。
不是的,媽。店鋪在深圳還關著門哩,我心慌著,所以想提早走。
婆婆拿著雞蛋的手停在半空,說:羅大笑走了快四年,丟下我們一家老的、少的,全靠你一個人撐。媽不是老封建,好的人你找一個,我不反對。咱家有個男人,這群老的、少的,也不會受外人欺。當然了,你要是……要是遇上了你認為更好的,桃果果、杏果果還有媽給帶著,你一個人放心去……婆婆說這話的時候,聲音里帶著哭腔。
媽……你趕我?雪然哽咽著,淚一下涌了出來。
不,不是的。只是桃果果、杏果果終究是我孫兒。他們還小,我怕……我怕他們過去會遭委屈……
婆婆抹著眼淚,把最后一個雞蛋打進了窩里,又指著桌上菜籃新鮮的平菇問:要不要再加點新鮮的菇子?
他來過啊?雪然盯著桌面問。
來了。他來時你不在房,可能……可能去廁所了吧!送來后坐了一會就走了,說是還要給批發市場送批新貨。
雪然的心緊了一下,感覺臉上有些發燙。她用手摸摸桌上的平菇,一個個鮮嫩肥大。
婆婆在一旁又說:曉光這孩子看起來是老實了些,但不笨。我去他們那個墩看過幾次,很勤勞、很能干的。難得的,他還愿意上門來我們家撐門戶。
婆婆停了停,看著雪然,又小聲說:當然,我也不是說那個誰誰不好。不過有句老話說得滿好:寧拆十座廟,不毀別人一樁婚!就說咱家吧,羅大笑先一步走,你一個人拉扯這個家,多不容易啊!
雪然埋頭沒有作聲,好一會兒,她抬頭,望向門外。院子里,桃果果、杏果果兄妹正在一蹦一跳地“踩房子”玩,初陽照在杏果果高高聳起的辮子上,一上一下地彈跳著。
婆婆在一旁說:那是曉光一早給杏果果綁的。
雪然仰起了頭,她真的好怕聽到自己眼淚碎落一地的聲音。
責任編輯/何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