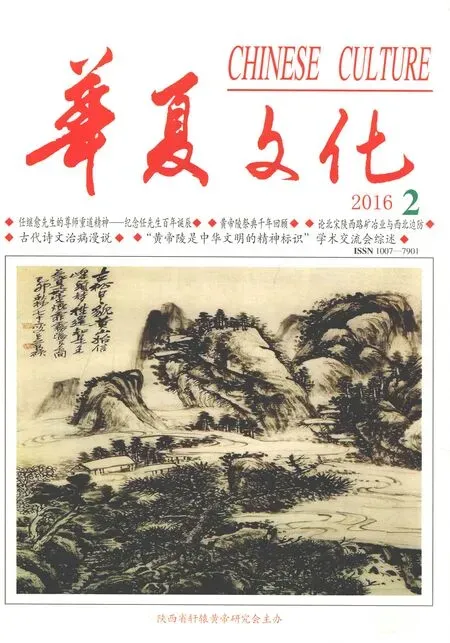也談“泰皇最貴”
□ 李京澤
?
也談“泰皇最貴”
□ 李京澤

在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之中,有一段記載,秦始皇統一天下后,令群臣議帝號,“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這一段史料十分有名,常為學者引據。這引發出我們對以下幾個問題的思考:群臣口中的“泰皇”究竟意指何人?為何“泰皇”處在“最貴”的地位?
細細考究,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疑點:商人崇“上帝”,以其為最高神;周人崇“天”又崇“帝”,二者在最高神的地位上可以等同。《尚書·多方》曰:“惟典神天”,《尚書·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詩·大雅》的《蕩》與《烝民》中皆曰:“天生烝民”,可見“天”是周人心目中最高神。那么,為何泰皇竟能高過以“天”為名的“天皇”,而成為“最貴”者呢?我們認為,泰皇即太一神,來源于楚地信仰的最高神“東皇太一”。
按顧頡剛先生的考證,“皇”字在戰國以前,并無名詞性的“帝王”含義,而多作形容詞,意為“大、美、光美”,也可以作副詞和動詞,但都不脫此義。“皇”作為名詞實際上是戰國以后出現的,在傳世文獻中初見于《楚辭》。《九章·橘頌》開篇即言:“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此處的“后皇”可以“命”橘樹“生南國”,故當為神名。《九歌》亦有《東皇太一》一篇。《九歌》本是屈原據民間祭神樂歌改作或加工而成,“東皇太一”亦是神名無疑。“東皇太一”這一神名的出現,很值得我們注意。《九歌》中以東皇太一為“上皇”,其意當與“上帝”類似。《東皇太一》篇居于《九歌》之首,大約也可反映出“東皇太一”地位在楚地最高。關于“東皇”,顧頡剛先生推測為“人間既然有東西帝,天上就應有東西皇了”。現在看來,此說不無牽強之處,當屬臆測。《楚辭章句》曰“祠在楚東,故稱東皇”。那么,《楚辭》所見之“東皇太一”,其本名應當正是“太一”。
“太一”信仰,流行于戰國到漢代,最初緣起于道家“太一”、“道”的哲學觀念,后被神化。太一的神化至少在屈原時代就已出現,最先崇拜太一神的地方當為楚地。如上文所述,《九歌》中的“東皇太一”,應當就是當時楚人祭祀太一神的反映。這與道家學派在楚地的興起有關。《老子》中雖然沒有提到“太一”二字,但卻經常提及“一”和“大”的關鍵,并以之為世界本源的“道”的異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強為之名曰大。”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可見“大”和“一”在道家思想中,最初便被賦予了“先天地生”的“天下母”的意義。后來《莊子·天下》中說老子和關尹的學說“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這時出現“太一”的名稱,其含義仍偏向于哲學概念。郭店楚簡中有《太一生水》一篇,其中亦有“太一生水。水反輔太一,是以成天”。以及“天地者太一之所生也”的文字。這些“太一”毫無疑問就是指哲學概念上的“道”。然而,與莊子活動時間差不多的屈原《九歌》中,太一就已經成為明顯的神名了。因此我們認為,“太一”這一概念由原先“大”、“一”概念拼接而成,在此過程中可能就伴隨著太一的神化。以至于“太一”一詞在戰國諸子口中成為至高原初的哲學本體,而在巫覡平民的口中就成為至高無上的太一神了。
太一在《九歌》中被稱之為“東皇”,又被稱為“上皇”,這也是太一概念被初次加上“皇”名。因為“皇”字在《九歌》、《九章》中已經有了名詞性的意義,《九章》中已有指可使橘樹“受命”的神“后皇”之名,可以推測在太一成為神名以前,“皇”已經成為最高神的代稱,取代了過去的最高神“帝”。《離騷》開篇即言:“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是以商周時期的最高神“帝”已然成為楚人祖先神高陽氏的稱號,而原先上帝的代稱,則變成“上皇”了。當“太一”作為“先天地生”的“天下母”出現,“皇”這一最高神稱號就自然地附于太一。《易傳》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呂氏春秋·大樂》言“太一生兩儀”,太極即太一,兩儀即天地,太一是天地的本源,“泰皇”當然較“天皇”、“地皇”為“最貴”。
然而“泰皇”的含義卻不止如此。秦臣廷議,其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既然是天神,為何說“古有”?難道在秦人眼里當時就沒有“泰皇”在天上了嗎?“三皇”之說,初見于《周禮·春官宗伯》:“(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呂氏春秋·貴公》中也有關于“三皇”的記載:“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用眾》:“夫取于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這里的“三皇”,往往和五帝連稱,且立功名,儼然成為上古世俗帝王的代表了。根據前文所述,“皇”本為最高神的名號,帝也本為神名。有趣的是,在《呂氏春秋》中,“帝”的名號照樣被作為神名使用:“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孟秋之月……其帝少皞”、“孟冬之月……其帝顓頊”,此處“四帝”顯然是作為神名來使用。按“四帝”信仰本是流行于秦地逐步形成的傳統信仰,即“白帝”、“青帝”、“炎帝”、“黃帝”,在《呂氏春秋》中就表現為“太皞”、“炎帝”、“少皞”、“顓頊”。《呂氏春秋》中的“帝”號,除了具有神性,也具有人性,是一種“神人二重性”的尊號。“皇”的名稱也一樣。《管子·兵法》言:“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皇”被當做世俗統治者可以達到的一個階段,其條件便是“明一”、“察道”。“皇”這一稱號,也具有了神人二重性,既為天神,又為遠古帝王。本來為神的“帝”與“皇”,可能在戰國諸子口中日漸“人化”,更多地被當做遠古帝王而非高高在上的神來,以期達到更好地宣傳自身政治主張的目的。“帝”與“皇”在此階段,經歷了一個“從神到人”的變化;而在當時人看來可能恰恰相反,“三皇五帝”都是“從人到神”的。其證據便是“帝”成為某些族群的祖先神。《史記·秦本紀》開篇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出土的秦公一號大墓石磬有“天子郾喜,龔桓是嗣”、“高陽有靈,四方以鼐”的字樣。而顓頊又是《呂氏春秋》四帝之一,可見當時秦人將自己的祖先神與“帝”結合了起來。這與楚人號稱自己為“帝高陽之苗裔”有異曲同工之處。對于當時流行的“三皇”,秦人很可能也用同一種宗教觀點看待——三皇既是人,又是神;既是遠古帝王,又是高高在上的天神。這樣的三皇五帝,就具有了某種英雄神、祖先神的特點,而失去了作為“帝”與“皇”時最高神的地位了。因此,秦臣廷議帝號時的“天、地、泰”三皇,才被冠以“古有”的前綴。至于泰皇何以最貴,則是由于其“先天地生”的身份,貴于天地二皇。
(作者:陜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學歷史學院,郵編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