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文學的地平線(4)
朱偉

李陀
上世紀80年代下半期,李陀很重要的作用是因1986年第六期起擔任了《北京文學》的副主編。1986年第五期前,《北京文學》的主編是《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副主編是王蒙與蘇辛群,王蒙是兼任,主持工作的是辛群。1986年林斤瀾上任當主編,辛群退休了,老林拉了李陀當副主編,另一位副主編陳世崇原是編輯部主任。林斤瀾與李陀、陳世崇搭檔,成就了《北京文學》的黃金時代。
林斤瀾當主編,是從1987年第一期使《北京文學》煥然一新的。從這一期開始,《北京文學》一下子開了五個專欄,挑頭的是汪曾祺的“草木閑篇”。汪老頭與林斤瀾是一唱一和的老哥們兒,自然要助陣的。小說方面,李陀負責布陣,將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放到了頭條。這一期老林寫的《新年告白》宣言,調子很低。他說:“融洽和諧,活潑寬松是春光,是百花齊放必需的氣氛。到哪里去討這氣氛?原來這氣氛是要自己創造出來的。”“《北京文學》能有多大能耐?一共才吃幾碗干飯?不過是仰望春風拂面,有一些飄忽如柳絲的想法。”
現在回頭看,李陀在小說推陳出新方面,比我們預想的要謹慎得多。《人民文學》1987年一、二期出了大事,《北京文學》相對更顯保守。不僅是第一期的亮相,之后若干期都沒有重要作品的集束,記得我們當時很有出乎意料感,覺得李陀上臺也不過如此。但李陀就是在不慌不忙中,將余華、蘇童、劉恒,直至后來的曹乃謙、丁天,一個個把莫言、馬原之后的一批人推了出來。
余華其實1984年就在《北京文學》第一期發了一個頭條《星星》,寫得很稚嫩。星星原是孩子王,興趣于鄰居家孩子學琴。父母給他買了小提琴后,專致其中,如入了魔。大家都無法容忍他的琴聲騷擾,于是父母就把琴賣了。孩子失了琴想琴,后來他偶遇在電視上見到的拉琴的孩子,那孩子被他的故事感動,就邀他合拉一把琴。這樣的小說可以為頭條,可見當時《北京文學》的標準。那時余華還在他父親的牙科診所學牙醫。
《十八歲出門遠行》真屬脫胎換骨之作。1986年余華在《北京文學》發表《老師》,還是那種寫師生溫情,細節娓娓道來的小說,寫年齡拉遠的師生距離,僅結尾是他成熟后常用的句式:“老師死了,就如黃昏的風琴聲一樣消逝了。”而《十八歲出門遠行》敘述已變得非常老到。這個短篇的開頭令人感覺并不新奇:出門遠行,搭車,那時凱魯亞克的《在路上》已經是人人傳誦了。但敘述過半,車壞了,坡上下來的騎車人開始搶蘋果,卸車,最后司機抱著“我”的背包坐上拖拉機遠去,出其不意,才醒悟他寫的是荒謬。而結尾與父親的對話,“你十八了,應該去認識外面的世界了”,又是陽光燦爛的感覺。僅6000字,結構上有這樣意外的跌宕,當初確實有耀亮感。
《十八歲出門遠行》一下奠定了位置,李陀的鼓蕩起了極大的作用,他逢人便推薦。同樣情況,還有1987年第二期推出的蘇童的《桑園留念》。蘇童的第一篇小說是發表在南京《青春》雜志上的,叫《第八個是銅像》,一部阿爾巴尼亞電影的片名。這篇《桑園留念》同樣是他成熟的開端。與余華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營造一個空間不同,蘇童的小說是敘述一個長度——從“我”第一次碰上肖弟毛頭,到認識丹玉與辛辛;最后,丹玉與毛頭抱在一起死了,名字刻在了石橋上;辛辛變成了一個腆著大肚子的女人。蘇童的小說里有性,有感傷,那時他還是純情少年呢。余華卻對性情、感傷都無興趣。《十八歲出門遠行》中他已經熱衷“鼻子軟塌塌地不是貼著而是掛在臉上了”。一年后他在1988年第一期《北京文學》上發表中篇小說《現實一種》,還記得讀他這個中篇時的顫栗心理:他怎么可以這么輕松地寫親人間連環的殺戮——從一個孩子對另一個孩子打耳光、卡喉嚨起,到逼孩子去舔血,一腳把孩子“像布一樣踢飛起來”;然后哥哥平靜地看著狗舔足底,將捆綁的弟弟活活舔死;再然后哥哥被槍斃,醫生們分解他的器官。結尾醫生說:“盡管你很結實,但我把你的骨骼放在我們教研室時,你就會顯得弱不禁風。”莫言后來寫《檀香刑》,應該由他啟發的。
《北京文學》的1988年上半年特別引文壇注目:第一期發了《現實一種》,第三期發了劉恒的《伏羲伏羲》,淋漓盡致地寫年輕叔嬸的偷情故事,最后結尾是主角楊天青裸體扎在水缸里自殺,大家發覺他的“本兒本兒大”。張藝謀后來將它拍成了《菊豆》。第六期又推出山西曹乃謙的《到黑夜我想你沒辦法》,每篇都僅千把字。第一篇寫親家租女人,黑旦把自家女人送走,回來的路上念叨:“球,去吧去吧,人家少要一千塊,就頂是把個女兒白給了咱兒,橫豎一年才一個月。”第二篇寫溫孩的女人黑夜不給他脫褲,不下地,下地回來還不給做飯。老一輩就說:“樹得刮打刮打才直溜。”溫孩就把女人打了,壓在她身上說:“日你媽你當爺鬧你呢,爺是鬧爺那兩千塊錢兒。”以簡練至極的“山藥蛋”式敘述,寫不動聲色的真實殘酷。之前已有陜西楊爭光,但楊爭光是《中國》推出的,曹乃謙是李陀在《北京文學》推的,不一樣。這些小說也就是在林斤瀾主編下的《北京文學》才能推出,還安然無恙,它們無疑給了劉心武壓力。無此壓力,是不會有《人民文學》1989年的小說專號的。
李陀在《北京文學》當副主編期間,更重要的工作是為莫言、馬原之后的第二撥(他的排序是余華、葉兆言、格非、蘇童、孫甘露、北村等)作家正名。他于1988年、1989年發表了兩篇在當時很有影響的文章,一篇叫《昔日頑童今何在》,“頑童”指1985年在文學革命中成長起來的批評家們。李陀感嘆他們對1987年后文學的失語,他認為:“與1985年的變革相比,這次改變不僅更為激烈,而且在文學與現實的關系、作家與社會的關系、讀者與作品的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上,變革得更為徹底。”由此他對那些彼此熟諳的批評家的說法是刻薄的:“1985年才剛過去,他們似乎一下就從一群頑童躍進成為一群老頭兒。”
另一篇文章叫《雪崩何處》,更明確認為,余華為首的這批作家意味著“作者文學的出現”。所謂“雪崩”,是指“工農文學時代的正式結束”,指“語言的解放”,“歸根結底意味著世界的更新”。他說,“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創了現代漢語的新紀元,“今天會不會再一次重演這樣的局面呢?我想有一定的可能”。
現在回頭,他顯然夸大了這批作家的作用。因為本是各式各樣、此起彼伏、參差不一在構成著文壇。但他對這批作家的推動,無疑幫助了這批作家茁壯成長。記得在《雪崩何處》中,他坦誠記載了自己用1985年的閱讀經驗,初讀《十八歲出門遠行》時的惶惑。他說,因此惶惑,對余華“寫作的追蹤和關切,也成了我對自己在寫作閱讀上所持的習慣立場和態度進行不斷質疑的過程”。
李陀因此是他那代人中,罕見不斷在甩開他人前行的。(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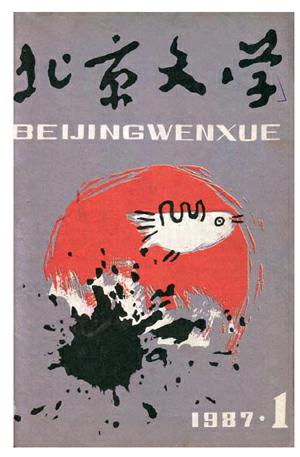
《北京文學》1987年第1期,林斤瀾與李陀、陳世崇搭檔正式亮相,新開5個專欄,發表了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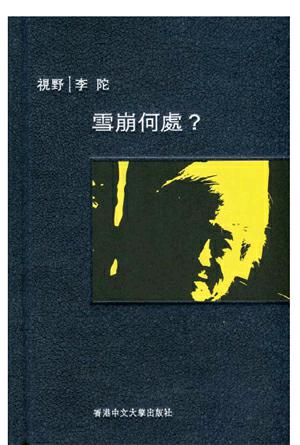
李陀80年代的一些重要文章都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結集出版,書名就叫《雪崩何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