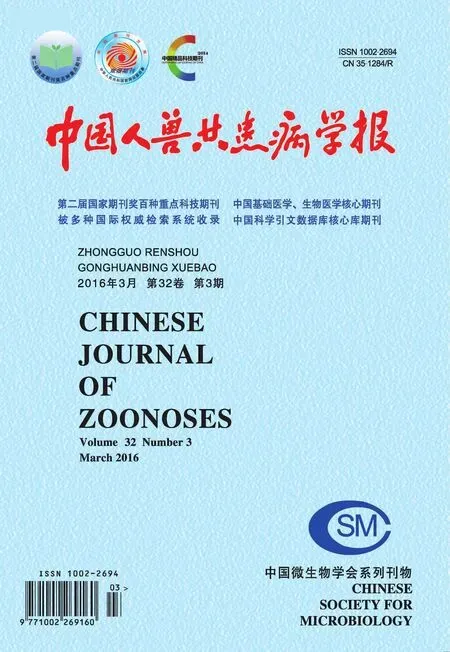噬菌體對人腸道正常菌群生態平衡及耐藥性的影響
賴志豪,謝玉龍,馬 超,馮曉穎,曹 虹
?
噬菌體對人腸道正常菌群生態平衡及耐藥性的影響
賴志豪1,2,謝玉龍1,2,馬超1,2,馮曉穎1,曹虹1
1.南方醫科大學公共衛生與熱帶醫學學院微生物學系,廣州 510515;2.南方醫科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廣州510220
摘要:腸道微生態是指寄生在宿主腸道內的微生物總稱。隨著人類微生物計劃的開展,腸道微生態代表著人體內最復雜和種群數量最多的共生微生物生態系統,作為一個“微生物器官”被廣泛研究。早期對腸道微生態的研究多集中在腸道細菌群落的結構和動態變化,往往忽略了噬菌體的存在。但是近年來因為抗生素的濫用,噬菌體在腸道中的作用日益得到重視。本文擬對腸道細菌、噬菌體、抗生素三者間的關系進行綜述,闡述腸道微生物間協同進化的機理,為治療腸道相關的疾病提供新思路。
關鍵詞:腸道微生態;腸道細菌;噬菌體;抗生素

1噬菌體在腸道生態網絡中的作用
噬菌體是能感染細菌、真菌、放線菌或螺旋體等微生物的病毒總稱,其中烈性噬菌體是細菌的天然“殺手”,具有殺死和清除細菌的能力,而溫和噬菌體則多存在于細菌里和宿主形成共生關系。早在1922年,從細菌疾病愈后的病人糞便中分離得到了常見的噬菌體,當時提出噬菌體可能與腸道對抗有害細菌有關,且其抗菌效果可能比機體的免疫系統更顯著。近年來,Qin等[1]從124個糞便標本中,通過宏基因組測序,集結并區分出3.3百萬個非冗余微生物基因,共計5 767億個堿基對的序列,發現約有5%是編碼噬菌體的相關蛋白,表明了噬菌體在腸道平衡中的存在和重要性。通過透射電子顯微鏡還發現人類糞便中的噬菌體主要為有尾噬菌體目(包括長尾噬菌體科、肌尾噬菌體科、和短尾噬菌體科)[2]。
一方面,噬菌體在腸道菌群中充當選擇壓力,通過減少菌群種類或者引進新特性以調節菌群結構和代謝。在噬菌體的壓力下,細菌能通過多種機制產生或獲得耐/抗性,包括已經報道的吸附抑制、DNA穿入阻滯、限制-修飾(restriction-modification, R-M)系統、規律成簇間隔短回文重復序列(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palindromic repeats, CRISPR)系統及頓挫感染。然而,很多情況下細菌一旦獲得噬菌體抗性,通常就會缺失具有細菌性致病力的細胞表面特征[3]。
另一方面,前噬菌體也被證明對宿主菌的有益:1)前噬菌體作為基因重組的錨點,發揮轉座子一樣的作用;2)前噬菌體可以通過插入中斷基因,沉默非必要基因而產生代謝丟失;3)前噬菌體通常賦予宿主針對同源噬菌體的免疫;4)前噬菌體可導致附近細胞細菌的溶解;5)前噬菌體可以通過轉化和轉導來誘導新的適應性因子;6)噬菌體抑制子有沉默宿主基因的可能。然而這種適應性因子對噬菌體生命周期不是必須的,通常是溶原性轉化因子。這種因子廣泛存在而并不局限于病原菌上,分為三類:存活因子(營養吸收系統)、防御因子(標記抗原)和攻擊因子(毒力因子)[4]。通過上述機制展現出更高的代謝活性和更快的生長速率,提高溶原性細菌整體的競爭適應性,以保證病毒DNA的維護和傳播。
目前,關于噬菌體在腸道微生態中的生理或病理過程已經有一定的研究基礎。Babickova和Gardlik[5]認為在正常情況下,腸腔中的噬菌體與共生菌之間維持著數量上的平衡,起著傳遞某些適應環境以及排斥其他病原菌的利己基因。不但如此,噬菌體還能直接與胃腸黏膜層上的糖蛋白直接作用起到抵御病原菌入侵的作用。部分健康人中,還在循環系統中檢測到噬菌體,這提示了它們能通過腸道上皮屏障;而當炎癥性腸病發生時,黏膜層上發現有更多噬菌體,大量噬菌體的產生與共生菌宿主的死亡有關,這導致了部分利己基因有可能傳遞到病原菌中,同時,由于黏膜層的缺失,噬菌體和黏膜糖蛋白的作用就會減弱,上皮屏障的缺失導致噬菌體顆粒進入到黏膜固有層甚至是血液循環系統中。在黏膜固有層中,噬菌體可能會引起局部的免疫反應,與之相對的,在進入到循環系統后就可能會引起系統性的免疫反應。
噬菌體的病毒顆粒被發現可減少活性氧物質的產生,以抑制T細胞和轉錄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 B, NF-κB),的激活促進耐受,并發揮抗腫瘤活性[6-7],且有研究表明腸道中注射噬菌體引起的免疫抑制能同時抑制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8]。
噬菌體感染細菌后能在細菌細胞內增殖,產生子代噬菌體,并最終裂解細菌,通常稱為裂解性噬菌體。利用裂解性噬菌體控制細菌性感染稱為噬菌體療法。這個基本過程一般包括:高效感染宿主菌、潛伏生長、爆發期[9]。裂解性噬菌體感染宿主細菌后,可釋放出子代噬菌體,感染和裂解其他宿主菌。噬菌體療法自上世紀以來隨著抗生素的廣泛應用而被忽視,近年來抗生素耐藥菌的快速產生使其重新得到關注。早期的噬菌體療法在傷口和皮膚感染、呼吸道、消化道、泌尿生殖道感染中均有應用,其給藥途徑取決于給藥目的和噬菌體性質,通過靜脈和胃腸道用藥是最常規的使用方法,除此之外還能經皮給藥、霧化吸入、膀胱沖洗等[10]。
然而,噬菌體療法的應用還存在以下障礙[9]:1)就噬菌體本身來說,其宿主譜狹窄,需要不停發現、分離新的噬菌體,且對pH敏感,口服給藥需用膠囊劑型。而溫度、濕度、最小有效濃度的定量仍待研究;2)宿主的免疫反應可直接或間接抑制噬菌體,宿主可通過巨噬細胞和抗體直接對抗噬菌體;不但如此,細菌刺激宿主,而宿主對細菌的免疫會間接抑制噬菌體療法的效果[11]。更需要注意的是,一些裂解性噬菌體快速大量地破壞體內菌群,有可能導致內毒素和超級抗原的產生和釋放[12];3)細菌對噬菌體存在抗性的可能:實驗發現單一培養的菌株可在數小時或數天內發展成對噬菌體抵抗[13],且細菌在體外比在體內能更快地形成對噬菌體的抗性,但噬菌體的雞尾酒療法則可控制和延緩噬菌體抵抗的菌株的形成[14];4)尚未有噬菌體治療的標準,也缺少權威機構對此的監管,且大眾對噬菌體療法缺乏正確認識,持畏懼、質疑態度,最終都限制了噬菌體療法的推廣應用。
2腸道噬菌體與抗生素抗性
2.1噬菌體攜帶抗生素抗性基因(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宏基因組分析表明,病毒DNA有大量ARGs[15],溫和型噬菌體在獲取抗生素抗性基因過程中有重要作用,噬菌體毒力基因整合到細菌DNA,形成前噬菌體,在宿主中進行組裝。當噬菌體的裂解周期激活,從細菌染色體分離,產生新的噬菌體后繼續進行誘導,直到宿主菌裂解,釋放更多噬菌體到細胞外。游離噬菌體攜帶ARGs,有助于ARGs的傳播。多數噬菌體被視為高度種間特異性[16],但也有實驗中卻觀察不到噬菌體具有物種特異性,例如腸球菌噬菌體能在不同菌屬的腸球菌中傳遞抗生素抗性基因tetM(四環素)和ant2-Ⅰ(慶大霉素)等,噬菌體在不同種屬之間轉移抗性基因,拓寬了噬菌體攜帶ARGs的范圍[17]。
對豬病毒基因組的分析揭示了腸道存在適應性基因,但從抗生素抗性基因數據庫看來,病毒基因組中抗性基因僅占0.01%,有猜測這些抗性基因早在抗生素治療前就存在于細菌基因組或者在前噬菌體或在胞內噬菌體內[18]。Quirós等[19]分析了糞便樣本中噬菌體DNA,所有樣本呈現ARGs陽性。對每克糞便樣本中不同的ARGs進行定量,blaTEM(β內酰胺酶基因)的豐度最大,其次是qnrA(喹諾酮抗性基因)和blaCTX-M1,armA(抗氨基糖苷類基因)陽性的樣本數量少,但有著顯著的高密度,個別樣本呈陽性qnrS和mecA(甲氧西林抗性基因)。
2.2抗生素影響ARGs的傳遞抗性基因往往由于可移動的遺傳因素造成的,如質粒,轉座子和噬菌體。而平行基因轉移是腸道細菌交換遺傳物質的一種機制,其中一種平行基因的轉移就是依賴噬菌體[20]。大部分人類腸道的噬菌體以前噬菌體形式存在,在選擇壓力下的腸道環境中,噬菌體的適應性是以群落為基礎,并能維持腸道微生態的功能穩定。因此,當抗生素作為一種選擇壓力,噬菌體會編碼不同的機制去調整宿主細菌對抗生素的敏感性,最終提高噬菌體的適應性。
Colomer-Lluch等[21]用環丙沙星處理糞便污染的水樣本中的細菌,分離并提純噬菌體DNA,將DNA上的抗性基因與未處理的樣本進行對比。PCR擴增發現廢水中噬菌體DNA上的存在4種ARGs(blaTEM,blaCTX-M,qnrA,qnrS)并且提出使用喹諾酮類抗生素作為溫和噬菌體的誘導劑,能夠誘導編碼qnr的噬菌體,數量上qnrA比qnrS多,陽性率較qnrS高,但密度較qnrS低,且經EDTA或檸檬酸鈉處理后,噬菌體的DNA中的qnr和其他抗性基因序列(blaTEM和blaCTX-M)均有增加。
同樣是環丙沙星,在Modi等則在實驗中更深入發現了環丙沙星處理組小鼠的噬菌體攜帶了編碼大量喹諾酮外拍泵的基因(如norM、mexD、mexF),且氨芐西林處理組小鼠的噬菌體攜帶了編碼抑制細胞壁合成的調節基因(如vanRS)。這種交叉抗性受特定的藥物調節(如氯霉素的乙酰基轉移酶);同時,多耐藥泵(如mdtK)也參與了這一耐藥過程。這些發現都表明,經過抗生素處理,噬菌體基因組成為宿主細菌多重耐藥的潛在源頭。因此,他提出噬菌體是腸道重要的適應性基因遺傳庫,而抗生素處理使噬菌體整合的頻率增加,并使大范圍的宿主受到刺激,這擴大了腸道細菌的遺傳基因庫,使得遺傳多樣化,并且使基因更容易遺傳到腸道細菌上[21]。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治療尤其能使編碼整合酶的基因豐度增加。整合酶對于前噬菌體誘導來說是一個標志,因為它們對于溫和噬菌體從溶解細胞到溶原現象是必須的[22],整合酶豐度的大量出現暗示了噬菌體介導的腸道的細菌溶解。此外,抗生素治療也導致了代謝過程相關的基因(如氧化應激的殺傷效應)增加,適應性的反應(如DNA修復)加強,或者增強了聚糖降解和菌群的其他代謝能力[20]。
3抗生素處理后噬菌體對腸道微生態的作用機理
腸道微生態的功能已經不局限于能量、代謝、免疫、屏障方面,而且在人體心臟發育、神經系統等也有重要作用[23]。微生態協同進化的過程,本質上就是微生物基因組上發生適應性變化[24]。溫和型噬菌體和宿主菌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互利共生的關系,有學者認為多數噬菌體從腸道宿主的前噬菌體進化而來[4]。Fischetti在A群鏈球菌中發現了噬菌體誘導因子,認為噬菌體已經進化到能感受外界環境,并在合適的時間感染敏感的宿主細菌[25]。而在進化的過程中,一個作為選擇壓力的外界因素就是抗生素。腸道細菌、噬菌體、抗生素三者構成了腸道微生態協同進化的要素(如圖1)。

圖1 參與腸道微生態協同進化的成分
Fig.1Compositions participating in co-evolution of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3.1噬菌體-抗生素協同效應(Phage-Antibiotic Synergy, PAS)早在1978年的一個報告中,非致死性濃度的青霉素引起一噬菌體抗性的鏈球菌菌株對外源性噬菌體易感,這種效應被稱為PAS[26]。而現在PAS被定義為暴露在非致死濃度的某種抗生素下刺激宿主細菌的烈性噬菌體的產生[27]。有報告顯示,低劑量的頭孢噻肟,頭孢菌素,能增加7倍尿道的大腸埃希菌的噬菌體(MFP的產量,進一步佐證了PAS的存在[28]。
PAS是獨立于SOS通路的,在一個recA突變種(即缺少SOS系統主要的成分)菌株中,卻展示出陽性PAS,提示SOS系統并沒有在PAS中顯示出其作用。然而,在沒有SOS系統作用下的PAS卻也能導致細菌成絲作用(細菌只延長不分裂的異常生長)的發生。在PAS中,成絲作用可能是多種通路的:成絲作用中,細胞的物理形態變化明顯地促進噬菌體結集,可能是由于有效改變或擴大前噬菌體的宿主庫,以及修復了某些限速的步驟;成絲作用能進一步引發在肽聚糖層的干擾,從而可能導致了對噬菌體裂解基因(如溶菌酶,穿孔素)的敏感性增加,最終加速了細菌的裂解和增加噬菌體的產量。Comeau等還表示不同的噬菌體-宿主系統中,PAS在分子機制上有偏差。例如,在噬菌體(MFP-大腸埃希菌系統中T4噬菌體感染的大腸埃希菌并沒有增加噬菌體的產量,但是顯著縮短T4樣噬菌體的感染周期,因此噬菌體才會快速產生和擴散[28]。
而關于PAS原理的應用,Ryan等通過增加非致死性濃度的頭孢噻肟導致T4噬菌體濃度的增加,T4噬菌體和頭孢的組合能顯著增強對細菌生物膜的破壞,首次證明了PAS能顯著促進對生物膜的控制[27]。Kamal等基于PAS原理證實了抗生素尤其是美羅培南,環丙沙星和四環素能結合噬菌體共同去刺激增加噬菌體的產物或活性,由此提高對細菌的殺傷[29]。這些都暗示了噬菌體和抗生素聯合療法較單純的噬菌體療法顯示出優越性。
PAS是反映噬菌體生活周期,在抗生素的選擇壓力下顯示出進化優勢,并可視為細菌一種適應環境的能力。
3.2“Community Shuffling”模型

圖2 “kill-the-winner”機制在“Community Shuffling”模型中的作用[4]
Mills等提出的“Community Shuffling”模型(暫無中文名)較好地描述了當腸道微生態受到外界選擇壓力時噬菌體和細菌的種群構成和動態變化(如圖2),腸道前噬菌體的誘導能引起生態失衡,通過改變正常共生菌和病態共生菌的比率來改變腸道微生物組分。根據Lokta Volterra模型或者“kill-the-winner”(暫無中文名)動態,多數噬菌體-細菌的相互作用是捕食關系,意味著在快速生長的宿主中噬菌體也能快速擴增,而生長減退的宿主就無法用來提供噬菌體的復制[30]。Minot等也證實了當細菌的氨基酸及碳水化合物前體合成、離子轉運及代謝、翻譯機制、細胞壁/膜生物進化相關的基因大量增加時,病毒樣顆粒(virus-like particle, VLP)的重疊群在復制、重組和修復以及某些未知功能的基因也有所增加,提出了當病毒通過編碼去實現復制時,也募集宿主細胞進行翻譯,產能和合成大分子前體的機制[31]。“kill-the-winner”動態在模型中就能保證了微生物多樣性(尤其是噬菌體)的長期維持。這就不難解釋有60%~70%的細菌基因組包含了前噬菌體序列[32],而且很多細菌是多溶原性的,溫和型噬菌體可以結合其基因到細菌基因組,并且通過溶原性轉化來改變宿主細胞的表型。相對地,在無外界選擇壓力下,某些溫和噬菌體控制的病毒基因組展示出顯著的基因穩定性,細胞膜為噬菌體的感染和生長提供場所,維持噬菌體在細胞膜內的長期共存,同時也就解釋了“空間避難所假說”[4]。
Siringan等[33]在研究中討論了噬菌體與空腸彎曲菌的關系,一定程度上補充了“Community Shuffling”模型。他們甚至把噬菌體宿主間的關系總結為兩點,即“假溶原性”和“攜帶狀態”。
假溶原性準確來說是指當噬菌體與宿主細胞作用時,噬菌體的核酸既不建立起長期、穩定溶原性細菌,也不引發溶原反應,而僅僅是存在于細胞中呈現一種非活動狀態。這種狀態往往發生在細胞外界條件苛刻的條件下。當營養充足時,病毒基因組就能建立起真正的溶原性細菌,或者激活溶原反應溶解細胞。對于假溶原性,也有研究認為噬菌體基因組事實上是作為宿主內的一個不穩定的游離基因而存在的。
攜帶狀態的生活周期(carrier state life cycle, CSLC)描述的是噬菌體與細菌間一種穩定的平衡狀態,一部分細菌對噬菌體是有抗性的,然而,部分敏感的宿主能包含噬菌體并且與之共同發展。CSLC一個重要特點是在培養條件下噬菌體能通過持續消耗敏感的宿主菌細胞而增殖。當這樣的菌株被分離后,表現出了對二重感染的抗性并且能在瓊脂培養基上形成少量斑塊。不同于其他溶原性菌,噬菌體的核酸并沒有整合到宿主的基因組里。
然而,仍然存在一些問題,細菌宿主表達噬菌體編碼的基因是由于本來就存在的溶原性細菌的大量增殖或者是繼發的噬菌體增殖所造成的,仍有待探討。
4結語
以往對腸道微生態的研究多集中在抗生素對細菌的影響,如在選擇壓力下,腸道菌群DNA損傷誘導的SOS系統,能夠防止抗生素調節的細胞死亡,誘導耐藥性變異的發展[34]。然而,對微生態協同進化的認識更多的已經逐漸從“宿主-病原體”到“宿主-病原體-噬菌體”的觀念轉變。
任何噬菌體轉化的抗性基因都能夠加速腸道微生物的進化。腸道相關的噬菌體已經被證實能編碼產生毒素,病毒因子或耐藥性的基因,并且有通過減少宿主種類等來改變群落結構和代謝的潛力[35],而這些變化往往是對微生物本身的生存有利的。抗生素作為選擇壓力的一種,PAS篩選出了極少數具有抗性基因的噬菌體,并引發它們的大量復制,增加了平行基因的轉移頻率,“kill-the-winner”動態則在“Community Shuffling”模型中通過引發大量前噬菌體基因的誘導,導致表達抗性基因的宿主菌比率大量增加,在這些過程中,噬菌體更趨向于作為一種微生態體內平衡和適應的調節制劑。全面認識微生態協同進化這一長期過程,能為近年興起的噬菌體療法奠定理論基礎,同時也為治療更多腸道疾病提供新思路。
參考文獻:
[1]Qin J, Li R, Raes J, et al. A human gut microbial gene catalogue established by metagenomic sequencing[J]. Nature, 2010, 464(7285): 59-65. DOI: 10.1038/nature08821
[2]Letarov A, Kulikov E. The bacteriophages in human- and animal body-associated microbial communities[J]. J Appl Microbiol, 2009, 107(1): 1-13. DOI: 10.1111/j.1365-2672.2009.04143.x
[3]Cai LT, Chen XJ, Liu YX, et al. Bacterail pathogens resistance to phages during the phage therapy[J]. Biotechnol Bull, 2014(07): 33-36. (in Chinese)
蔡劉體, 陳興江, 劉艷霞,等. 噬菌體治療中細菌對噬菌體的抗性[J]. 生物技術通報, 2014(07): 33-36.
[4]Mills S, Shanahan F, Stanton C, et al. Movers and shakers: influence of bacteriophages in shaping the mammalian gut microbiota[J]. Gut Microbes, 2013, 4(1): 4-16. DOI: 10.4161/gmic.22371
[5]Babickova J, Gardlik R. Pathological and therapeutic interactions between bacteriophages, microbes and the host in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J].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5, 21(40): 11321-11330. DOI: 10.3748/wjg.v21.i40.11321
[6]Miedzybrozki R, Switala-Jelen K, Fortuna W, et al. Bacteriophage preparation inhibition of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generation by endotoxin-stimulated polymorphonuclear leukocytes[J]. Virus Res, 2008, 131(2): 233-242. DOI: 10.1016/j.virusres.2007.09.013
[7]Pajtasz-Piasecka E, Rossowska J, Dus D, et al. Bacteriophages support anti-tumor response initiated by DC-based vaccine against murine transplantable colon carcinoma[J]. Immunol Lett, 2008, 116(1): 24-32. DOI: 10.1016/j.imlet.2007.11.004
[8]Gorski A, Nowaczyk M, Weber-Dabrowska B, et al. New insights into the possible role of bacteriophages in transplantation[J]. Transplant Proc, 2003, 35(6): 2372-2373. DOI: 10.1016/S0041-1345(03)00811-X
[9]Zhang Z, LiJH, Lu YY, et al.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 virulent bacteriophage φEn-ZZ8 isolated fromEnterococcusfaecalis[J]. J Microbes Infect, 2015(4): 241-246. (in Chinese)
張哲, 李菁華, 逯茵茵,等. 糞腸球菌裂解性噬菌體φEn-ZZ8生物學特性的初步分析[J]. 微生物與感染, 2015(4): 241-246.
[10]Oliveira H, Sillankorva S, Merabishvili M, et al. Unexploited opportunities for phage therapy[J]. Front Pharmacol, 2015, 6: 180. DOI: 10.3389/fphar.2015.00180
[11]Sarhan WA, Azzazy HM. Phage approved in food, why not as a therapeutic?[J]. Expert Rev Anti Infect Ther, 2015, 13(1): 91-101. DOI: 10.1586/14787210.2015.990383
[12]Hodyra-Stefaniak K, Miernikiewicz P, Drapaa J, et al. Mammalian Host-Versus-Phage immune response determines phage fateinvivo[J]. Sci Rep, 2015, 5: 14802. DOI: 10.1038/srep14802
[13]Lu TK, Koeris M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bacteriophage therapy[J]. Curr Opin Microbiol, 2011, 14(5): 524-531. DOI: 10.1016/j.mib.2011.07.028
[14]Hall AR, De Vos D, Friman VP, et al. Effects of sequential and simultaneous applications of bacteriophages on populations ofPseudomonasaeruginosainvitroand in wax moth larvae[J]. Appl Environ Microbiol, 2012, 78(16): 5646-5652. DOI: 10.1128/AEM.00757-12
[15]Minot S, Sinha R, Chen J, et al. The human gut virome: inter-individual variation and dynamic response to diet[J]. Genome Res, 2011, 21(10): 1616-1625. DOI: 10.1101/gr.122705.111
[16]Reyes A, Haynes M, Hanson N, et al. Viruses in the faecal microbiota of monozygotic twins and their mothers[J]. Nature, 2010, 466(7340): 334-338. DOI: 10.1038/nature09199
[17]Mazaheri Nezhad Fard R, Barton MD, Heuzenroeder MW. Bacteriophage-mediated transduc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in enterococci[J]. Lett Appl Microbiol, 2011, 52(6): 559-564. DOI: 10.1111/j.1472-765X.2011.03043.x
[18]Allen HK, Looft T, Bayles DO, et al. Antibiotics in fee induce prophages in swine fecal microbiomes[J]. MBio, 2011, 2(6): pii: e00260-11. DOI: 10.1128/mBio.00260-11
[19]Quiros P, Colomer-Lluch M, Martinez-Castillo A, et al.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in the bacteriophage DNA fraction of human fecal samples[J].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14, 59(1): 606-609. DOI: 10.1128/AAC.01684-13
[20]Sun CL, Relman DA. Microbiota’s little heloers’: bacteriophages and antibiotic-associated responses in the gut microbiome[J]. Genome Biol, 2013, 14(7): 127. DOI: 10.1186/gb-2013-14-7-127
[21]Modi SR, Lee HH, Spina CS, et al. Antibiotic treatment expands the resistance reservoir and ecolohical network of the phage metagenome[J]. Nature, 2013, 499(7457): 219-222. DOI: 10.1038/nature12212
[22]Groth AC, Calos MP. Phage integrases: biology and applications[J]. J Mol Biol, 2004, 335(3): 667-678. DOI: 10.1016/j.jmb.2003.09.082
[23]Turnbaugh PJ, Ley RE, Hamady M, et al. The human microbiome project[J]. Nature, 2007, 499(7164):804-810. DOI: 10.1038/nature06244
[24]Zhang L, XU YC, Li XP, et al. Gut microbiota and their co-evolution with host[J]. Progr Mod Biomed, 2010, 01: 168-172. (in Chinese)
張亮, 徐艷春, 李曉平,等. 腸道微生態系統及其與宿主的協同進化[J]. 現代生物醫學進展, 2010, 01: 168-172.
[25]Fischetti VA.Invivoacquisition of prophage in Streptococcus pyogenes[J]. Trends Microbiol, 2007, 15(7): 297-300. DOI: 10.1016/j.tim.2007.05.003
[26]Verhue WM. Interaction of bacteriophage infection and low penicillin concentrations on the performance of yogurt cultures[J]. Appl Environ Microbiol, 1978, 35(6): 1145-1149.
[27]Ryan EM, Alkawareek MY, Donnelly RF, et al. Synergistic phage-antibiotic combinations for the control of Escherichia coli biofilmsinvitro[J]. FEMS Immunol Med Microbiol, 2012, 65(2): 395-398. DOI: 10.1111/j.1574-695X.2012.00977.x
[28]Comeau AM, Tetart F, Trojet SN, et al. Phage-Antibiotic Synergy (PAS): beta-lactam and quinolone antibiotics stimulate virulent phage growth[J]. PLoS One, 2007, 2(8): e799. DOI:10.1371/journal.pone.0000799
[29]Kamal F, Dennis JJ. Burkholderia cepacia Complex Phage-Antibiotic Synergy (PAS): Antibiotics stimulate lytic phage activity[J]. Appl Environ Microbiol, 2015, 81(3): 1132-1138. DOI: 10.1128/AEM.02850-14
[30]Chibani-Chennoufi S, Bruttin A, Dillmann ML, et al. Phage-host interaction: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J]. J Bacteriol, 2004, 186(12): 3677-3686. DOI:10.1128/JB.186.12.3677-3686.2004
[31]Minot S, Sinha R, Chen J, et al. The human gut virome: inter-individual variation and dynamic response to diet[J]. Genome Res, 2011, 21(10): 1616-1625. DOI: 10.1101/gr.122705.111
[32]Paul JH. Prophages in marine bacteria: dangerous molecular time bombs or the key to survival in the sea?[J]. ISME J, 2008, 2(6): 579-589. DOI: 10.1038/ismej.2008.35
[33]Siringan P, Connerton PL, Cummings NJ, et al. Alternative bacteriophage life cycles: the carrier state ofCampylobacterjejuni[J]. Open Biol, 2014, 4: 130200. DOI: 10.1098/rsob.130200
[34]Parrella A, Lavorgna M, Criscuolo E, et al. Eco-genotoxicity of six anticancer drugs using comet assay in daphnids[J]. J Hazard Mater, 2015, 286C: 573-580. DOI: 10.1016/j.jhazmat.2015.01.012
[35]Ogilvie LA, Bowler LD, Caplin J, et al. Genome signature-based dissection of human gut metagenomes to extract subliminal viral sequences[J]. Nat Commun, 2013, 4: 2420. DOI: 10.1038/ncomms3420
DOI:10.3969/j.issn.1002-2694.2016.03.017
通訊作者:曹虹,Email: gzhcao@smu.edu.cn
中圖分類號:R3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694(2016)03-0295-06
Corresponding author:Cao Hong, Email: gzhcao@smu.edu.cn
收稿日期:2015-10-26;修回日期:2016-01-24
Influence of phages on human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balance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LAI Zhi-hao1,2,XIE Yu-long1,2,MA Chao1,2,FENG Xiao-ying1,CAO Hong1
(1.DepartmentofMicrobiology,SchoolofPublicHealthandTropicalMedicine,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China2.SecondClinicalMedicalCollege,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220,China)
Abstract:Intestinal microecology, a concept of the general microbes which parasite in the host intestine, representing the most complex and the most diverse commensal microecological system in human body, has been studied widely as a microbial org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Microbiome Project.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 of gut microflora, which usually neglecting the existence of phages in the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there has been a raising attention on the roles of phages in the intestine due to the widespread use of antibiotic.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mechanism of intestinal microbial co-evolution and provide the new ideas for treating the intestinal disease, in this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among intestinal bacteria, phages and antibiotics has been discussed.
Keywords:intestinal microecology; intestinal bacteria; phages; antibiotic
2012年廣東省“大學生創新實驗計劃”項目(No.212112017);2014年度南方醫科大學“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No.20141212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