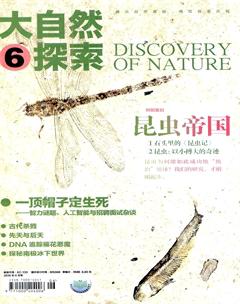先天與后天
曾潔
科學家們近年來一直在研究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和外界環境是怎樣對我們的基因造成影響的。這一研究也許會顛覆迄今為止我們對于進化論的理解。
1953年,DNA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使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這兩個名字變得家喻戶曉,同時,這個發現還奠定了我們對生物特性是如何代代相傳的了解。但DNA或者說是基因組,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表觀基因組”這個角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表觀基因組是指由環境和飲食等因素所引起的、對DNA和其周圍蛋白質所進行的微小化學修飾。通過對這些修飾的研究,我們得到了一些非常驚人的結論:你從你母親的DNA那里繼承到的綠眼睛或者是黑皮膚,可能跟當初你外婆撫養她的方式有直接的關系。

DNA 是環繞在一種名為組蛋白的蛋白質四周的螺旋形結構。
表觀遺傳修飾
表觀遺傳修飾是如何在我們的DNA結構中起作用,并將其遺傳給我們的后代的呢?
我們細胞中的DNA并非是一個又長又直的分子,相反的是,它是環繞在一種名為組蛋白的蛋白質四周的螺旋形結構。DNA包繞著一個由八個組蛋白組成的蛋白質結構,續行一段之后又包繞另一個組蛋白團體。這樣的進程在一個細胞中要重復數百萬次,通過這種方式,才將我們近2米長的DNA全部疊裝在直徑只有零點幾微米的細胞核中。
當一個細胞接收到了來自環境的信號后,DNA和組蛋白同時也會受到微小的化學修飾,這種能夠調節DNA表達的行為就是表觀遺傳修飾。自然界中存在著種類巨多的修飾作用,尤其是針對組蛋白的修飾。而這些修飾的作用和位置,其排列和組合往往復雜到讓人眼花繚亂,因此也造成了基因表達擁有極高的靈活性。又因為細胞在分裂時會將這種表觀遺傳修飾傳遞給它的子細胞,所以這種對基因表達的影響也會一直延續下去。
生長發育的奇妙之旅始于一個擁有無限潛能和無限結局的細胞,而對人類而言,大量的這種細胞都將分化成某種特定的形態。幾十年前,還沒人知道細胞分化和DNA之間有什么聯系。曾經有那么一個假說:細胞分化時會將它們不需要的DNA給“扔掉”。舉個例子來說,神經細胞會“丟掉”編碼血紅蛋白的基因,因為血紅蛋白是存在于血液中攜帶氧氣的組織;又例如肝細胞會“丟掉”編碼角蛋白的基因,因為肝細胞并不需要角蛋白。
直到20世紀70年代,曾經在英國牛津大學后來又到劍橋大學工作的約翰·格登教授才通過實驗否定了這一猜想。他將蛙卵的細胞核替換為成年青蛙的細胞核,再對蛙卵進行培養,結果蛙卵變成了蝌蚪,并最終變成了一只完整的青蛙。這說明個體不同部位的細胞所含的DNA并沒有任何不同。1996年,蘇格蘭羅斯林研究所的伊恩·威爾穆特和基思·坎貝爾與他們的同事一起利用一只綿羊的乳腺細胞克隆出了綿羊多利,證明了格登教授的發現在哺乳動物身上也同樣適用。
2012年,格登教授因為他的發現獲得了諾貝爾獎。在他那項發現之后的幾十年間,研究者們在對表觀遺傳現象背后機制的研究上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些機制的實現有賴于DNA的微小化學修飾,此外,一種特定的蛋白——組蛋白也跟我們的遺傳物質息息相關。這些化學修飾被稱為表觀遺傳修飾。
數百種不同的酶能增加或去除基因組在不同位置上發生的表觀遺傳修飾作用,而數百種不同的蛋白質又能將這些修飾組合進行綁定,并最終改變原來的基因組。這些表觀遺傳修飾會受環境刺激影響,還可以讓我們的細胞去適應那些基因表達所發生的改變。因此表觀遺傳為我們提供了溝通起先天(基因組)與后天(環境)之間的橋梁。

對于哺乳動物來說,一次成功的繁殖必須要有適當的來自父母雙方的表觀遺傳修飾。
一些表觀遺傳與生物幼年時候的環境有關,例如早期妊娠期。這一具體例子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荷蘭。這個國家的某些地方遭受了災難性的食物短缺,有好幾個月的時間,人們每天的卡路里攝入量還不到正常水平的40%,這段時間后來被稱為“饑餓嚴冬”。在這段時間內懷孕的嬰兒出生時都表現得很正常,但隨著年齡逐漸增大,他們開始呈現出高于常人的患成人肥胖和2型糖尿病的概率。這是由于他們的基因在懷孕早期就被表觀地修改了,這樣才能保證他們在當時匱乏的物資水平下盡可能多地利用所有的資源活下去。如果饑荒持續下去,這樣的改變倒不失為一個好處,但在物資充沛的現今社會,這樣的表觀遺傳改變就成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表觀遺傳學提供了研究成人疾病在胚胎時期或幼年起源的一個新方法,例如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開始展開的,現在規模達到約1.5萬個家庭的埃文親子縱向研究發現,童年時遭到虐待的孩子在長大后心理健康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我們都知道遺傳信息通過父母傳遞給他們的子女,但表觀遺傳信息是否也是如此傳遞的呢?20世紀80年代,劍橋大學的阿奇姆·蘇尼拉教授的研究證明了這個猜想。事實上,對于哺乳動物來說,一次成功的繁殖必須要有適當的來自父母雙方的表觀遺傳修飾。通過對大鼠進行的體外受精實驗,蘇尼拉發現只有當一個卵細胞和一個精子的細胞核融合之后,動物才可能被生出來。沒有動物能在兩個卵細胞核融合或者兩個精子細胞核融合的情況下出生并存活,雖然從基因水平上來說以上三種情況并沒有任何差別。
后代總是傾向于看起來更像它們的父母,以此來說明它們繼承了父母的表觀遺傳信息,但現實并不總是恰如人意:一些幼鼠跟它們的父母長得很不一樣,這說明我們對于表觀遺傳信息傳遞方法的了解還是很模糊。后代外貌發生變化的比重跟環境刺激也有很大關系,例如給雌鼠飲酒等。

我們的遺傳信息來自父母,但外界對其影響不容忽視,包括貌、行為和疾病等。
通過對這些老鼠的研究表明,表觀遺傳信息既能通過父母遺傳給子女,又會受到環境因素的影響。這就引出了下一個問題:受到環境因素影響而產生的表觀調節是否能通過父母遺傳給子女呢?
經典的達爾文進化論也許會說當然不行。事實上這個問題更像是達爾文的主要競爭對手,19世紀法國博物學家讓-巴蒂斯特·拉馬克提出的“生物能把后天獲得的特征遺傳給子女”理論。可如今,原來那套達爾文進化論經典的理論越來越面臨著威脅了:荷蘭饑餓嚴冬的受試者們出現了一系列的適應癥,例如,經歷了童年饑荒而產生的代謝缺陷問題現在被發現也會遺傳給后代。
不幸的是,要想把遺傳、表觀遺傳和環境因素在人類身上產生的影響完全區分開來是非常困難的。為了取得更加確信的證據,研究者們又一次將目光投向了嚙齒動物。
許多研究都表明,當雄性嚙齒動物出現營養不良時,它們的后代也會出現新陳代謝障礙。但另一項利用恐懼適應原理來進行的實驗更是讓研究者們大吃一驚。雄性小鼠通過一些特定的訓練后會將特定的味道和電擊聯系到一起,當再次把它的后代小鼠暴露在只有這種氣味的環境下,也足夠使這些小鼠“聞味喪膽”。通過對這些小鼠的后代進行試驗,研究者發現它們也跟自己的父輩一樣害怕這種味道,即使這些小鼠從未受過電擊。這些小鼠同它們倍受精神創傷的父輩們一樣,腦子里的某些關鍵基因也受到了同樣的表觀遺傳修飾。
這是否意味著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模型就完全錯誤了呢?當然不是,即使現在很多表觀遺傳學家都喜歡把自己比作是新時代的拉馬克,但達爾文的進化論模型依然是生物進化學中不可或缺的理論。大多數情況下,精子和卵細胞都能抵御由環境影響帶來的表觀遺傳變異,但相對地一些已經建立起來的修飾作用也很有可能會傳遞給下一代。即使是這樣,這些修飾和它們所產生的影響也基本上會在幾代之后消失掉。這就是我們所推測的,表觀遺傳性改變從本質上來說是非常不穩定的。
這種表觀遺傳信息的逐代傳遞可能會給生物帶來一些短期的適應性效益:既能讓它們以此來抵御暫時的環境變化,又不會改變它們傳承了數千年的潛在基因序列。這種后天獲得性遺傳在某些情況下的確會發生,但卻不太可能在長期的自然選擇中占主要的作用。
盡管如此,仍存在著越來越多的順理成章的趨勢來“責怪”表觀遺傳,因為它所帶來的一些現存問題,尤其是對它所帶來的人類肥胖癥的流行。盡管這個研究結果聽起來那么娓娓動聽,但它卻決不是我們逃避問題的借口。對你的身體健康來說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此時此刻你的生活習慣:不會有人在2016年的今天長胖而只是因為他的爺爺在1960年喜歡吃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