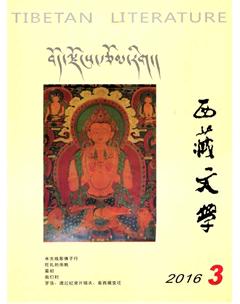夜宿藏家小屋(外一篇)
百合
汽車沿著岷江的河谷走了幾個小時后,開始慢慢地向上盤爬。
“看!大熊貓!”有乘客驚叫著,坐在車廂走道一邊的乘客也都站起來爬到窗前看。我坐的后排座比其它的座位高,所以不用站起身,也看到了大熊貓。所有的乘客都興奮了起來。
司機大聲地說:“這是臥龍山大熊貓自然保護區,誰要是敢殺害、捕捉大熊貓,就要被敲腦殼的!”
乘客們三三兩兩地接著司機的話茬議論了起來。
翻上一座高峰,往下望去,只見岷江就在腳下白浪滾滾,隱約可聞水流湍急之聲,再放眼眺望,遠處云山繚繞之中,透出一片金光,太陽正在擠出云層。汽車已經爬了很高了。再看汽車在山下剛剛走過的路,像一條羊腸小道在山麓間盤旋。我發現自己被夾在懸崖絕壁和一座幾乎是垂直的山麓之間。雖看不見天,但見滿目蒼綠。一會兒,窗外什么都看不見了,像走進了霧里,我感到心里一陣奇悶,我對身邊的女士說:“麻煩,給我騰個塑料袋,快!”我把我的背包推向了她。我同時向著車窗的玻璃望了一眼:我的臉色已經成了青色,并且鼓著發白的嘴唇,一口一口地向上倒氣。女士不敢怠慢,趕忙從我的背包里拿出裝毛巾的塑料袋,遞給了我。才過了片刻,我又叫道:“麻煩,再給我塑料袋——快!”她把我的一個裝衣服的塑料袋給了我。大約是怕我出危險,她站起身大聲地對司機喊道:“喂,師傅,麻煩你停停車好嗎?”司機問:“搞啥子事情?上廁所?”她說:“不是,有人生病了!”司機說:“病了我才不能停車。”她都急了:“為什么?”司機大聲說:“現在正在過巴朗山,海拔4523米,病人怎么受得了?我得趕快開,翻過巴郎山,病人才得到安全了!”事已至此,我只能暗暗叫苦,只能聽天由命了。我后悔沒有打聽好路況,就到了這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地方。
“巴朗山的雪峰!”車里的乘客騷動起來。
“你看,咱們剛才是在云里,不是在霧里。咱們現在從云里出來了!你快看!天多藍,雪多白,景色多美!”我身邊的這位好心的女士大聲地給我打氣,只希望我能撐過這座山。我感動極了。
有個乘客大聲地說:“其實云和霧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霧高了,就是云;云低了,就是霧。”
我咧著已經沒有知覺的嘴唇,笑了一笑,艱難地對這位老師說:“照相,照……巴朗山……機子在背包里。”她說:“對,照相,把巴朗山照下來。——我把你也照下來。”我慘白著臉無力地說:“別,別照我。——太難看了!”她說:“就這樣照,這樣最自然了,這樣最有紀念意義。來,笑得好看一點,把你的形象和巴郎山疊在一起。”她拿起我的照相機幫我搶下了幾張珍貴的鏡頭。汽車飛快地向山下駛著,彩色的經幡隨風獵獵地飄蕩,一處接一處。車上的人們停止了驚呼喧鬧,我也停止了嘔吐,司機掛著空擋下山,一切都靜了下來,仿佛怕驚擾了經幡下沉睡的神靈。我深深地感覺到了佛的存在,心中的沉靜和肅穆油然而生。
一路的經幡,讓我感覺到了香巴拉王國的存在,感覺到神靈對我的注視,感悟到神靈對我的指引,到了這里,我的心靈不由得不潔凈,我的靈魂不由得不升華。這時,高山反應的痛苦仿佛已經不存在了,多年來疾病的痛苦也不復存在了。我注視著車窗外邊,心靜如水。
“因為道路被泥石流沖斷,所以,原定發往阿壩縣城的班車停開了。”阿壩州馬爾康縣城的汽車售票員很有禮貌地對我說。我失望極了。我的失望不僅僅是沒有了到達我心中的目的地的汽車,而是縣城的街道上根本就沒有藏族人!
一路上照顧我的好心的女士已經在四姑娘山下了車,我一個人拖著灌了鉛的腿,扛著疼痛欲裂的腦袋,眼睛在縣城的街道上極力地搜索著,期望著能看到一兩個穿著藏袍的藏族人,以不枉我千辛萬苦地來到這人跡罕見的川西高原上。同時,我還得盡快找到住的地方,否則我就會趴倒在大街上。
我找到了一個小旅館,接待我的是位中年男子,他說他叫白瑪,他還說這個旅館是他妻子經營的,他是他們家鄉的教師,是暑假來給妻子幫忙的。我問白瑪:“你們這里不是藏民區嗎?我怎么看到的是滿街的漢族人?”
白瑪聽了我的話,笑了。“你沒見過藏族人?剛才在街上看見的和現在坐在你面前的不是藏族人嗎?”
我吃了一驚,說:“那些人不是和漢族人一樣嗎?他們為什么不穿藏族服裝,卻穿漢族服裝呢?您看,您也是西裝革履的,真看不出,您也是藏族人。”
白瑪寬容地說:“現在漢族和藏族的交往日益增多,怎么說呢?——在內地城鎮里的少數民族基本上都跟漢族差不多了。但是,只要你仔細分辨,你在大街上還是能分出哪一位是漢民,哪一位是藏民的。因為我們藏族人長得都比較粗獷。”
“剛才在街上,我跟他們說話,他們都說漢語,他們怎么不講藏語呢?”我又問。
“在我們本民族之間,相互說的都是我們民族的語言。在縣城居住的藏族人,差不多都會講漢語。”
我感到體力不支了,頭疼得像要炸開似的,胸悶、氣短,并且昏昏欲睡。
白瑪的妻子桑吉卓瑪穿著漂亮的藏族服裝來給我送開水。我眼前一亮,說:“我想去你們藏民居住的村子里看看,我怎么才能到達藏民居住的村子?”
桑吉卓瑪是個好心的女人,她說:“我們的村子就在山上,離這里有幾十里路,你要是想去,我一會兒就可以帶你去。”她還說:“我的丈夫也要回學校去,因為學校就要開學了。”
我高興地從床上跳了起來,喊:“太好了!太謝謝你們了!”
其實這時,高原反應給我身體帶來的不適,并沒有絲毫地減輕,只是因為心里鼓起的那股我自己也說不上來的勁,鼓足了我的勇氣罷了。有人說:通常久病的病人都有一個通病——固執病。我大概當時就犯的是這種病。
一輛紅色的老式桑塔納出租車,載著我和白瑪夫婦爬上了漫坡。他們像是走親戚似的都換上了一身漂亮的藏袍,我的情緒處在極其亢奮之中。白瑪說他們的村子就在四千多米的山上,我的亢奮都沒有被打下去。過巴朗山的時候,我就已經出了狀況。再上四千米,無疑我是在賭命!
來不及推敲此行的得與失,汽車已經進了山。
車行山間,左回右轉,兩邊峰巒陡峙,嵬巖嶙峋,路邊有了積雪,山腰卻出現了墨綠色的云杉林帶。翻過幾道山梁,進入一個廣闊的山中草原。高原的天空,每一個瞬間都有奇異的變化,天上的云游動得很快,像疾駛在高速公路上的車輛。行走在高原上,仿佛離天更近了,你甚至都覺得,只要把手向天上一舉,就可以摘下幾片飛逝的白云來。湛藍的天幕下,有疾駛的白云從頭頂上匆匆閃過;碧空下,連綿起伏的山巒,蕩漾著茵綠色的波浪,草地上有數不清的牛羊,它們有的是褐色的牛,有的是花牛,還有雪白的羊,黑白褐相間,跟拼貼畫一樣。車又往前開了一會兒,草原逐漸開闊,再也看不到低矮的山岡和稀疏的林子了。汽車穿過放牧群,又出現了大片大片的漂亮花,我驚呼:“好漂亮的花!”
“格桑梅朵。”桑吉卓瑪說。
“什么?”我沒有聽懂。
白瑪解釋說:“其實也叫草原菊。我們藏族話叫做格桑梅朵。”
看遠處,邛崍雪山上白雪耀眼。這里就是海拔四千多米的哈拉瑪高山草原。清新的空氣和炫目的風光令人心醉。山峁和道路如同水洗過般干凈。遠處黑色的山底簇擁著一群白色的房子。汽車開到近處才看清,這里的房子蓋得很奇特,就是把山上的石頭集中到一起,干打壘似的插建而成。之所以說它是“插建”而成,是因為房子就是由山石干干地插起來的,甚至連石縫都沒有勾。我當時真想問這種房子漏不漏雨,但因為頭痛欲裂,也就顧不得張口了。
汽車終于在一個叫丹瓦的村子停下來。白瑪說:“這就是我們村。”
我用目光掃描了一下村子:這是一個只有二三十戶人家的藏族人村子,而且居住很分散。因為有汽車開進村子,一下子圍過來好多小孩,穿得都很油膩,身上的味道也很重。我問白瑪:“你們的學校也在村里嗎?”
白瑪說:“在村子的那邊。”
于是,我們一起去看了他們村的學校。學校建在村里以前實行生產隊時的一個舊牦牛棚里。
“怎么只有一個班?”我問。
“哦,我們村有十幾年都沒有過學校了,我是去年才承擔了這里的教學,當了老師,這些學生都是去年才入學的,今年該升二年級了。”白瑪說。
“那今年再有新生怎么辦?”
“那就辦一個復試班。反正這里又要沒老師了,也說不定娃娃們還不來報名呢?”
“為什么?”我心里疑惑,“為什么這里快要沒老師了?為什么娃娃們會不來報名?”我連連發問。
白瑪說:“在村里當老師錢太少,鄉里已經同意調我去鄉里當老師了。”
“那你的這些學生怎么辦?”我真為這里的學生擔憂。
“那就隨他們了。還想上學的,他們自己就會去鄉里上學;不愿意上學的,把學校辦到家門口,他們也不來上。”
“為什么?”我不知道我那時怎么會有那么多的疑問。自從我問第一個“為什么”開始,我就死死地盯著白瑪的臉,我想看清楚他的骨子里到底是不是藏族人。因為在我心目中的藏族人根本就不是他這個樣子的。
白瑪似乎看出了我在盯著他,他耐心地給我解釋說:“我們這里主要靠放牧過生活,有的家也種一點青稞和土豆。一般家里的青壯年和大一點的孩子都要到牧場放牧去,留在村子里的都是已經喪失勞動力的老人,他們在這看家,并撫養未成年的孩子。留在家里的老人們算計著,想自己的孫子要是上學了,就不能跟著自己的兒子學放牧的本事了。等兒子老了,誰照看家里的牛羊馬豬?這么算,還是覺得不劃算。有的家庭確實比較窮,是真的沒錢,根本就交不起書費,所以他們說沒錢。”
我此時盯著的白瑪的臉,變成了一個電視畫面:一個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在陜北的一個山坡上,采訪一個正在放羊的牧娃。
記者問:“你在干嗎呢?”
孩子說:“放羊。”
“你放羊干什么?”
“放了羊賣錢。”
“賣了錢干什么?”
“娶媳婦。”
“娶了媳婦干什么?”
“生娃娃。”
“生娃娃干什么?”
“放羊。”
……
我當時正在病中,看了這段報道后,我的心就已經被孩子的話刺得鮮血淋淋的了。
今天,我親耳聽了白瑪的話,我的心像要被剜出來一樣疼痛。我拖著病身子,艱難地把目光投入到這片遠還沒有進化的寨子里,我發現人類尷尬的處境遍布每一個角落,我仿佛聽見弱者在哭泣,看見文明在被人們層層地包裹了起來,我此時強烈地感覺到我這個剛被別人拯救出來的軀體,馬上就要沖出去拯救別人。我不是社會學家,也不是社會調研者,我無權發表什么高論,但我當時的確有了一種沖動,我想說:“我來這里教這些孩子。”但終因是我一個人到藏地,人生地不熟的,又不太懂藏民的接人待物方式,也怕影響了藏漢關系,所以這句話就沒有出口。
桑吉卓瑪看我不再發問,就說:“去我們家吧,我媽媽說不定都等急了。”這時早有人給她家的老人送信回去了。
白瑪家的房子,跟我在路上看到的房子一樣,也是那種干打壘似的房子。還沒走到門口,一個藏族老人雙手托著一條雪白的哈達迎了上來,當哈達掛到我的脖子上的時候,白瑪說:“這是我媽媽,叫阿卓瑪。”我當時后悔極了,路過縣城的時候,我看到街上有賣藏族服裝和哈達的,我后悔沒有給這位慈祥的老人也獻上一條雪白的哈達。
阿卓瑪說:“招待尊貴的客人不能沒有青稞酒喝,更不能沒有牦牛肉吃。”我當時是什么都不能吃了,但是,當主人唱著敬酒歌向我敬酒的時候,我還是恭恭敬敬地接過來把酒干了。其實我不知道在藏人家飲酒的講究。在藏人家飲酒尤其是敬酒時講究“三口一杯”,即先喝一口,斟滿;再喝一口,再斟滿;喝上第三口,斟滿干一杯。我本來不能喝酒,但因為要表示對主人的尊重,才慷慨而飲。哪知反倒弄巧成拙了。
主人看我豪氣滿天,以為我是“海量”,高興壞了。當我看到又一杯酒放到我的跟前的時候,我都要哭了。
桑吉卓瑪以女人心體諒我,說:“你要是覺得酒喝夠了,就把酒杯扣到桌子上,主人就不會再給你添酒了。”
我趕緊把酒倒進嘴里,然后,立即把酒杯扣到桌子上,用手掌壓住。這時,我的身體難受極了,只想往下躺,不管是在凳子上還是地上。
一個十六七歲的男孩跑進來用藏語和桑吉卓瑪說了幾句話之后,又轉向我:“阿姨,去跳舞吧,我們村沒來過外邊的客人,他們都邀請你去呢。”
白瑪介紹說:“這是我的兒子容中爾甲。”
我心里一陣感動。我喊住容中爾甲,問他:“你住在村里,怎么會說漢語呢?”
他說:“我在成都讀書,所以會說。”
“在你家的旅館里有一個女孩……”
“那是我妹妹,也在成都讀書。”我一下子明白了白瑪為什么要放棄村里的任教,要去鄉里的學校就職了。一雙兒女昂貴的學費,都要靠白瑪和桑吉卓瑪一點一點地精心積攢。
我被桑吉卓瑪硬拖著去了舞場。一架老掉牙的錄音機,放著藏族的舞曲,因為機子老卷帶,跳舞的人們總得停下來去擺弄機子。后來,人們終于耐不住了,“咿呀啦嗦——咿呀啦嗦——”地自唱自跳起來。
村里人跳的是鍋莊,我跟著他們舞了幾下就感到實在支持不住了:我頭疼得眼球都快要憋了出來,耳根子也跳著疼,我甚至可以聽到我的心臟咚咚咚地跳。我說了聲:“我不行了。”就出了跳舞的圈子。慶幸的是,我坐到地下的同時,我按下了我的照相機的快門。照相機為我留下了那最珍貴的一瞬。
最后,我被桑吉卓瑪攙回了她的家。像是做夢一樣,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昨天我還在古城西安,今天我就夜宿在藏人家了!真是不可思議。這一天的經歷,就好像經歷了幾個世紀。尤其是白瑪,我無法解讀他,他讓我對以往藏人的形象有了疑問。但是,想到他竟然有膽略把自己的一雙兒女送到成都受正規教育,也真不失一個明智之舉。在我思忖白瑪的同時,我腦子里顯出牦牛棚中的那些孩子們的幻像……還有那些指望著自己的孫子跟著自己的兒子去學本領的老人們……
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天黑很久了吧?漸漸地,才有星星露出來。從躺著的方向看去,北斗星的勺正對著邛崍雪山的烽燧。怎么不見“秦月依依”呢?我忽地記起有人曾告訴我,滿天星星的時候就不會有月亮。我頓時憬悟,是不是滿天星斗的夜空,就一定見不到月亮?那么明月高懸的時候,還能見到星光燦爛嗎?
夜宿藏家小屋,從窗簾遮不到的地方,仍能見到一小片天,一小片綴滿了星星的天。
川西高原的今夜,沒有月。
鷹
上下一望,峽谷上端接著云天,下端沒入云際;兩岸的山巒連綿形成廣闊的峽谷空間,上空的云也沿峽谷為中線,對峙排開,那一方是玉龍雪山的云隊,這一方為白茫雪山的云隊,好像古代兩軍陣前對峙的長長列隊,雙方留下一條楚漢界——天空有云彩的峽谷。
我從山勢和云的走向看出了空中雖沒有痕跡,在“兩”個峽谷的上下之間,卻是一條清晰的飛行路——鷹路。
鷹不應與鳥雀同道。《莊子》中的昆鵬,展翅九萬里,巨大的翅膀,高遠的視野,必定要有這樣壯闊的鷹路方可飛翔。
然而,一只受傷的鷹引發我發現了一片偉大的天空。
耷拉著一只翅膀的鷹站在墻角的土埂上,鎮定地審視著我。雖然是傷殘者,那雙鐵爪和犀利如劍的目光依然是空中之霸。它的爪后是沿墻而列的刻有咒語的石片。鷹沿墻拐彎,步上寺院正面的土臺,仰著它鐵鉤般的喙,正視著我,告誡我它是一只神鳥。
我看孤鷹雖然耷一只手,但它跳上土臺時,立如山,眾人趕它,它動喙左右還擊,像陣地上拼死相守的戰士。這一形象使我聯想到護法神,壁畫上的護法金剛以一副恐攝的樣子鎮人。據說,這也叫慈悲。
對于鷹神圣不可侵犯的氣勢,我只得甘拜下風般蹲坐于墻角,靜靜地審視了鷹兩個季節。
終于有一天,我斗膽問鷹:“看你這么威武,怎會受傷的?”
鷹說:“一位英雄的獵人擊中了我。”
我奇怪地問:“你是這么稱呼擊中你的獵人?”
鷹不屑地說:“這是獵人第二十次擊中我。”
我更是好奇,問:“為什么會這樣?每次都是這位獵人擊中你嗎?”
鷹冷峻地說:“我是故意的,獵人也是有意的。他每年都在這時擊中我一次。”
我說:“你們為什么要這樣?”
鷹的眼眸瞬間閃過一絲柔情。
鷹說:“二十年前我愛上了林中的蝶后,蝶后也深愛著我……有次我在低空與蝶后相會,被這位獵人擊中……那年,我跟蝶后在這里度過了最甜蜜的春天、夏天……蝶后說,你是雄鷹,是空中的霸主,你應該在云的上端,而不該沉湎在白云之下……我說,為了神圣的愛情,莫說云之下端,就是地獄我也敢闖進去擁你在懷中……蝶后哭了說,你飛吧,去你的云端家園吧,那里有你的鷹后等你……我說,不,我愛你無怨無悔……蝶后更是悲哭地說,你走吧,鷹是萬世不古的圣者,我才是春生秋死的飛蛾,我與你不配……我說,飛蛾秋死,還會春生……我每年春天都來這里等你……”
鷹最后平靜地說:“所以,我每年都來這里讓這位大慈大悲的獵人‘擊落……每年都在這里等我的蝶后。”
我淚流滿面,問鷹:“你等到你的蝶后了嗎?”
鷹仰望蒼天說:“我的蝶后每年春天都來……每年秋天都去……”
我哭出聲,問鷹:“你就為這——每年都來此受傷?!享受你的愛情?!”
鷹騰空之時,犀利的眼神瞥了我最后一眼,說:“是的。深秋了,再見吧。明年我還會來!”
我望不見已入云端的鷹的身姿的時候,云的上空傳來鷹浩渺的聲音:“那位英雄的獵人就是蝶皇……”
“第一個佛是誰?”
辯道:“第一個人是誰?生命無始無終,緣聚而生,哪有第一人?佛也如此,根本找不到第一個佛。”
孤鷹即使受傷落地也不變雀。鷹從不進院中,多立于土臺上。僧侶說土臺是辯經勝者榮譽的寶坐。自從活佛發現這只鷹后,常在心中為它祈禱,讓它聞法成佛。我從現代高僧虛云和尚自傳中讀到他寺廟中放生的雞、鵝,每日都到大殿聽經,變得出家人一般安靜,步態從容。
樹上落下最后一片黃葉……
責任編輯:次仁羅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