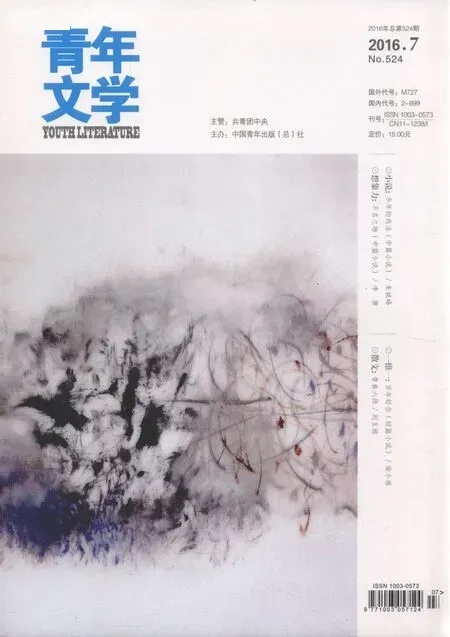百年好合
⊙ 文/徐小雅
百年好合
⊙ 文/徐小雅

徐小雅:祖籍山東臨沂,一九八七年生于廣西南寧。二〇〇四年起參加新概念作文大賽,曾獲一、二等獎(jiǎng)數(shù)次。作品散見(jiàn)于《文藝風(fēng)賞》《山花》《創(chuàng)作與評(píng)論》等刊,有作品被《小說(shuō)月報(bào)》等轉(zhuǎn)載。出版有小說(shuō)集《單純》。現(xiàn)居柳州。
六月里,她有三次想要和丈夫離婚。沖動(dòng)的次數(shù)比上個(gè)月又多了些,她一邊回憶一邊計(jì)算。第一次是女兒婚禮的前幾天。女婿是空軍的地勤,婚禮前無(wú)法回家,整個(gè)婚禮幾乎由她和丈夫一手操辦。這段時(shí)間她和丈夫幾乎每天都在為女兒的婚禮爭(zhēng)吵:喜糖應(yīng)該選哪種,喜酒應(yīng)該擺多少瓶。每一次,丈夫都能津津有味地和她吵上半天。那天她突然想起還未取回女兒的婚紗照,便讓丈夫和她一同前去。出門(mén)前他們又吵了一架。丈夫堅(jiān)持要開(kāi)車,因?yàn)榭煜掠炅恕K齽t認(rèn)為沒(méi)有必要。婚慶公司在一家細(xì)如雞腸的巷子里,車不方便通過(guò)。她也看過(guò)天氣。天空里的烏云已經(jīng)在同一個(gè)地方待了好幾天,但總是來(lái)回徘徊,始終沒(méi)有下成雨。他們拿好照片剛走出婚慶公司沒(méi)十米遠(yuǎn),一場(chǎng)潲雨傾盆而至。她和丈夫退回到婚慶公司的門(mén)前,站在窄窄的屋檐下躲雨。他們都以為雨很快就會(huì)過(guò)去。誰(shuí)知,那朵熟悉的烏云飄了過(guò)來(lái),并如滴入水池的一粒墨水,迅速將天空染成了灰色。丈夫焦慮地從口袋里掏出香煙,將潮濕的過(guò)濾嘴含進(jìn)嘴里。火機(jī)滑輪嚓嚓地響著,卻始終未能將煙卷點(diǎn)燃。周圍的人都看著他們。她突然意識(shí)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kāi)始在公共場(chǎng)所禁煙。丈夫似乎也意識(shí)到了。他將煙卷潦草地從嘴中拔下來(lái),撕成兩截,惡狠狠地摔在地上。出租車在狹窄的巷子里緩慢地駛過(guò)去,沒(méi)有一臺(tái)亮起空車的紅燈標(biāo)志。她站在丈夫的身邊,能聽(tīng)見(jiàn)他胸腔里傳出的憤怒的呼呼聲。果然,沒(méi)過(guò)多久,他不顧場(chǎng)合地喊起來(lái):“我早就說(shuō)開(kāi)車,你說(shuō)不用,現(xiàn)在怎樣?照片全都濕了吧?你為什么總是不聽(tīng)我的勸,為什么總這么強(qiáng)勢(shì)?”
周圍躲雨的人們?cè)俅螌⒛抗廪D(zhuǎn)向他們。她知道,丈夫是故意要出她的丑。越是人多的場(chǎng)合,他越是刻意這么做。老鄉(xiāng)聚會(huì)時(shí),他總是和別人強(qiáng)調(diào):“打出來(lái)的老婆,揉出來(lái)的面。”他說(shuō)得揚(yáng)揚(yáng)得意,仿佛只有這樣才能證明他在家中的地位。但她很懷疑這一點(diǎn)。她只覺(jué)得,丈夫這種劣質(zhì)的性別觀只會(huì)成為別人的笑柄。
她沒(méi)有回應(yīng),低頭看了看女兒的婚紗照。就在剛才,在他們拿到照片即將出門(mén)的時(shí)候,婚慶公司的工作人員好心地追上來(lái),在婚紗照外面裹上了一層厚厚的塑料墊子。偶爾有幾滴雨水打在塑料墊上,留下星點(diǎn)的水珠。她將照片拎起來(lái),把相框墊在自己的腳面上。雨漸漸小了。有些不怕淋雨的人已經(jīng)離開(kāi)。她抬頭看了看,發(fā)現(xiàn)天邊的烏云里有一道橘紅色的金邊。她知道雨快停了。她沒(méi)有猶豫,拎起照片走進(jìn)了綿綿的細(xì)雨中。她聽(tīng)見(jiàn)丈夫在后面氣急敗壞地叫著,但她沒(méi)有回頭。走到路口時(shí),她迅速鉆進(jìn)了一輛剛卸客的出租車。坐在出租車?yán)铮耄辉摵退Y(jié)婚。

⊙ 陳尚云·建設(shè)者
大約是在一九七〇年吧,那時(shí)她在園藝場(chǎng)當(dāng)工人。她十五歲就進(jìn)了工廠。進(jìn)工廠前,父親語(yǔ)重心長(zhǎng)地對(duì)她說(shuō):“要好好干革命。”她對(duì)革命的概念很模糊,只知道這在當(dāng)時(shí)很流行,讓人有種沉甸甸又令人驕傲的氣勢(shì)。父親還告訴她,園藝場(chǎng)里有一個(gè)名叫李海的年輕人,是他朋友的兒子,他已托付李海照顧她。進(jìn)工廠不久她就見(jiàn)到了李海。那是一個(gè)稍顯矮小的男人,比她大三歲。他有一雙如同鹿一般深情又明亮的眼睛,仿佛隨時(shí)都能從眼窩里滴出水來(lái)。不知是出于父親的交代,還是他自己的真心,他對(duì)她頗為照顧。工友們都說(shuō)他對(duì)她是有意的,她嘴上否認(rèn)了,心里卻很甜蜜。可是他并沒(méi)有明確地說(shuō)過(guò)什么,她也沒(méi)有膽量去做更深的猜測(cè)。在那個(gè)年代,過(guò)度的猜測(cè)是一種恥辱的事,她所受到的教育是這樣告訴她的。
后來(lái)工友們給她介紹了現(xiàn)在的丈夫。她對(duì)他沒(méi)有太大的好感,但也聽(tīng)從了朋友們的意思,當(dāng)作是交一個(gè)朋友。他們正常地交往著,偶爾出去看場(chǎng)電影。直到對(duì)方向她求婚,她才驚慌地感到了一絲措手不及。她答應(yīng)他考慮一段時(shí)間。她想著和李海之間未被道破的感情,不太甘心,于是,她找到李海,將一切告訴了他。李海看著她,眼睛在黑暗中如波浪一樣閃閃發(fā)光。他沒(méi)有說(shuō)話,只是點(diǎn)了點(diǎn)頭,然后站起來(lái)走了。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時(shí),聽(tīng)見(jiàn)從遠(yuǎn)方的山頭上傳來(lái)一陣悠長(zhǎng)的笛聲。笛聲斷斷續(xù)續(xù)的,有時(shí)發(fā)抖,有時(shí)低沉,帶著一股無(wú)法言說(shuō)的傷感。和她同宿舍的工友們都在黑暗中坐起來(lái),走到窗前去尋找笛聲的來(lái)源。她知道那是李海。她曾經(jīng)在他的包里看到過(guò)笛子。她的心底涌起一股既甜蜜又酸澀的感覺(jué)。他是一個(gè)怯懦的人,她失望地想。
笛聲持續(xù)了快一個(gè)星期。在白天,她仍然常常見(jiàn)到李海。他似乎沒(méi)有改變什么,仍一如既往地照顧她。她也裝作不知情地繼續(xù)接受著他的好意。直到有一天,李海在節(jié)后返回園藝場(chǎng),告訴她他要結(jié)婚了。她第一次發(fā)現(xiàn),他的聲音如同他的笛聲一樣,低沉中夾著顫抖:“是爸媽給我介紹的,村東頭老王家的閨女。”不知是否是自己的錯(cuò)覺(jué),她總覺(jué)得李海在說(shuō)這句話時(shí),有意將“爸媽給我介紹的”加重了口氣。他的臉上充滿著慌張,似乎有意要向她解釋什么。她在腦海中捕捉著李海對(duì)象的樣子。她曾經(jīng)見(jiàn)過(guò)她一面,好像是在集上。那是一個(gè)典型的潑辣的農(nóng)村姑娘,有一雙比普通男人都要大的腳。在她的故鄉(xiāng),人們還保留著以腳為準(zhǔn)繩的審美觀。她想象著李海對(duì)象的一雙大腳,還未來(lái)得及錯(cuò)愕,一句帶著酸味的話就脫口而出:“什么時(shí)候吃你的喜糖啊?”
他吃驚地望著她,眼睛因吃驚而變大了。她期待著他能有什么話說(shuō)出口,哪怕是幾句惡狠狠的咒罵。但是他沒(méi)有開(kāi)口。李海的態(tài)度刺痛了她。她轉(zhuǎn)身離開(kāi)了。幾個(gè)月后,園藝場(chǎng)關(guān)閉,她去了供銷社工作,李海因?yàn)楦赣H的關(guān)系去了百貨公司做營(yíng)業(yè)員。他們沒(méi)再聯(lián)系。生活變成了兩條路,越到遠(yuǎn)方,分岔越大。后來(lái),她與丈夫訂婚。不久后丈夫在部隊(duì)提干,她隨軍去了一個(gè)南方小城,離開(kāi)了故鄉(xiāng)。
她后來(lái)聽(tīng)說(shuō)李海過(guò)得并不好。他的妻子早逝,沒(méi)給他留下兒女。李海沒(méi)有再婚,也沒(méi)有與她聯(lián)系。直到她的女兒要結(jié)婚時(shí),時(shí)隔這么多年,她才第一次打電話給他。電話里他的聲音幾乎沒(méi)變,只是聽(tīng)起來(lái)更沙啞,更低沉了。她用手指環(huán)繞著電話線上的線圈,想象著李海現(xiàn)在的模樣。突然,她腦海中模糊了多年的影像又漸漸清晰起來(lái)。一雙如鹿般深情的眼睛,隨著時(shí)間的流逝,已經(jīng)蒙上了一層黯淡的灰色。也許他的臉和她一樣,早就布滿了深深淺淺的溝壑。丈夫現(xiàn)在就是如此。他似乎和丈夫是同年的。想到這里,她的腦袋像吃了一悶棍,蒙了。她想到自己稍顯漫長(zhǎng)的婚姻,不由得嘆了口氣,心里剛漾起的一點(diǎn)柔情很快又被壓下去了。她客氣地告訴他女兒結(jié)婚的時(shí)間,并邀請(qǐng)他來(lái)參加婚禮。他在電話那頭客氣地表示祝福,也告訴她有機(jī)會(huì)他一定會(huì)來(lái)。她知道他不會(huì)來(lái),她從他們彼此的語(yǔ)氣中能感受到,即便多年以后,他們會(huì)重新坐在對(duì)面,他們所討論的話題將刻意地繞過(guò)那段朦朧的往事,繞過(guò)與那些往事有關(guān)的一切,將目光落在他們各自的生活上。云淡風(fēng)輕,他們禮貌地微笑著,如同兩個(gè)首次相見(jiàn)的人一樣客氣又拘束。他們將如那朵一直飄浮的烏云一樣,被風(fēng)一吹便輕輕散去,始終無(wú)法下成雨。
每每和丈夫吵架的時(shí)候她都會(huì)想起李海,并忍不住將丈夫和李海相對(duì)比。越是對(duì)比,她越覺(jué)得心塞。如果當(dāng)初她或者李海都能夠再往前一步的話,也許他們的生活會(huì)有很大不同。究竟有什么不同,她阻止自己繼續(xù)想下去。
回到家,她向女兒抱怨丈夫的所作所為。女兒滿不在乎地坐在沙發(fā)上填寫(xiě)請(qǐng)柬,似乎根本沒(méi)將她的話聽(tīng)進(jìn)耳里。她沖上去扳過(guò)女兒的肩膀,叫喊起來(lái):“你到底有沒(méi)有在聽(tīng)我說(shuō)話?”
女兒翻了個(gè)白眼,如同劃清界限一般一字一句地說(shuō):“你自己找的好老公,有什么可抱怨的,過(guò)不下去的話,離婚吧,沒(méi)有人會(huì)攔著你的。”
“你有沒(méi)有良心?要不是為了你……”
女兒冷漠地打斷她:“我不用你為了我。”
她被噎住了。她沒(méi)有想到女兒會(huì)這么說(shuō)。從年輕到現(xiàn)在,有許多次和丈夫吵架過(guò)后,她一個(gè)人順著河堤慢慢地往前走。曾有一對(duì)年過(guò)花甲的夫婦跟著她走了很遠(yuǎn),直到確認(rèn)她不是要自殺,他們才放心地離開(kāi)。她坐在河堤的石椅上,聞著帶有魚(yú)腥味的風(fēng)。風(fēng)濕漉漉的,有如淚水一樣咸。她下意識(shí)地用手去摸了摸自己的臉,是濕的。時(shí)間越長(zhǎng),她越能確定他們不適合在一起生活。如果不是為了女兒,她早已和他離婚。但她不想讓女兒成為單親家庭中的一員。她看到過(guò)許多因?yàn)閱斡H而被嘲笑的孩子,知道這樣的背景會(huì)讓成長(zhǎng)倍加艱難。她沒(méi)有權(quán)力給女兒的生活無(wú)端地增添一道坎。父母和朋友們不是也說(shuō)嗎,為了孩子……她想到這里,覺(jué)得自己高大起來(lái),有種受到贊許而想哭的沖動(dòng)。
女兒結(jié)婚的前一天,氣溫高達(dá)四十度。她一起床就將冷氣打開(kāi)了,將溫度調(diào)至最低一檔。幾個(gè)小時(shí)過(guò)去,熱度絲毫沒(méi)有降低。房間里四處是被燒熱的瀝青味兒。想到女兒明天就要從這個(gè)家里離開(kāi),成為一名新婦,她的心里涌上來(lái)一股被剝離的失落感。這種感覺(jué)在女兒出生前也出現(xiàn)過(guò)一次。那時(shí)丈夫到外地操練去了,她一個(gè)人在部隊(duì)醫(yī)院待產(chǎn)。預(yù)產(chǎn)期已經(jīng)過(guò)去了一個(gè)月,她的肚子卻沒(méi)有任何反應(yīng)。軍區(qū)醫(yī)院里只剩下她最后一個(gè)產(chǎn)婦了。產(chǎn)科的大部分護(hù)士都已休假,只剩下兩三個(gè)準(zhǔn)備考軍校的護(hù)士。那幾個(gè)護(hù)士很年輕,十七八歲的樣子。考試當(dāng)前,每個(gè)人都很緊張。她甚至能從護(hù)士們密集的腳步中聽(tīng)出焦慮感。房間里每天都充滿著火燒般的味道,她第一次知道,焦慮的味道是這樣的。
她在床上輾轉(zhuǎn)翻滾,只覺(jué)得熱。醫(yī)院沒(méi)有冷氣,每天只有一頂?shù)跎仍谒念^頂緩慢地晃動(dòng)。她看著風(fēng)扇在被子上投下的黑影,總覺(jué)得有種被掏空的慌張感。她將手放在肚子上,感受孩子的心跳。這樣的方式能讓她感到平靜。它要比一個(gè)月前活潑了許多。現(xiàn)在,它每天都會(huì)不定時(shí)地在她的肚子里伸展拳腳。她看著自己肚子上凸出來(lái)的皮肉,不自覺(jué)地笑出聲來(lái)。
一個(gè)傍晚,醫(yī)生走過(guò)來(lái)對(duì)她說(shuō):“今天生怎么樣?”
她知道醫(yī)生要打催產(chǎn)素了。前幾天他們和她商量過(guò)這件事。時(shí)間已經(jīng)過(guò)去了太久,每個(gè)人都沒(méi)有耐心繼續(xù)等下去了。她沖醫(yī)生點(diǎn)點(diǎn)頭,說(shuō):“好。”
很快護(hù)士們便來(lái)了。她們將她推向產(chǎn)房。她仰躺著,一路數(shù)著天花板上掠過(guò)的白熾燈。也許是因?yàn)樵卺t(yī)院的緣故,燈光讓人感覺(jué)異常冰冷。她再次將手放在了自己的肚子上。這一次,孩子沒(méi)有給她回應(yīng)。她突然想到,下一刻,它就要從她的體內(nèi)剝離出去,成為一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了。她有些想哭。近一年來(lái),她已經(jīng)習(xí)慣孩子是自己的骨中骨,肉中肉,它的出生,就是骨肉剝離的過(guò)程。但是她知道,即便如此,她也必須接受這一次剝離。就如同多年以后,她知道自己必須坦然地將女兒推向另外一個(gè)男人。
女兒又在房間里試穿婚紗。婚紗一個(gè)星期前就從婚慶公司拿回家了。一開(kāi)始,女兒興致勃勃,沒(méi)過(guò)幾天,她的興致就減少了許多,整個(gè)人全身上下散發(fā)著一股燒焦的熱氣。離婚期越近,這樣的味道也越加棱角分明。這是她所熟悉的焦慮的味道。她不知道該用什么樣的方式去緩解女兒的焦慮。從女兒昏暗的房間里,她想起了女兒出生的那天傍晚,她在恍惚中看到的風(fēng)扇陰影、寒冷的白熾燈以及熱鬧爭(zhēng)吵的知了。醫(yī)院的走廊里充滿著帶著火燒味的熱空氣,她穿的病號(hào)服已經(jīng)被汗濡濕了。當(dāng)進(jìn)入產(chǎn)房,手術(shù)燈亮起,整個(gè)世界突然涼了下來(lái)。
她走進(jìn)女兒的房間,幫助她將婚紗背上的拉鏈拉上。女兒回頭看了她一眼,將目光轉(zhuǎn)回到穿衣鏡前。她皺著眉頭打量著鏡中穿著白紗的自己,似乎感覺(jué)很不適。很快,女兒艱難地伸手拉開(kāi)拉鏈,把自己從白紗中剝出來(lái),將婚紗踩在腳底。這時(shí)候,她才發(fā)現(xiàn)女兒的臉變成了病態(tài)的蟹殼青色。女兒看著她,長(zhǎng)舒一口氣,又低下頭,說(shuō):“媽,能不能不辦婚禮了?”
“怎么能不辦了?請(qǐng)柬都發(fā)出去了,你爸爸的朋友,我的朋友,還有你自己的老師、同學(xué),特別是你爸爸的朋友,都是首長(zhǎng)、戰(zhàn)友,怎么能說(shuō)不辦就不辦了?”
“就是不想辦了。”
“這種事怎么能由著性子來(lái)?想辦就辦,不想辦就不辦?結(jié)婚不是你一個(gè)人的事!你讓我和你爸怎么去面對(duì)我們那些朋友?你自己想想清楚!”
“……”
女兒沉默了半晌,最終抬起頭,一字一句地吐出幾個(gè)字:“你的面子比我的感受還重要嗎?”
“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問(wèn)題……”她感覺(jué)自己的思緒斷裂成了碎片,這種斷裂感讓她惶惶不安。她突然覺(jué)得自己剛才說(shuō)的一番話很勉強(qiáng);什么都說(shuō)服不了,更談不上什么意義。她站在女兒面前,卻覺(jué)得自己的腰不自覺(jué)地彎了下去。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壓迫。突然,她的腦袋里靈光一閃,她想到了最后一個(gè)無(wú)法被駁斥的理由。
“不管怎么樣,我告訴你,結(jié)婚不是你一個(gè)人的事,是我們?nèi)业氖隆D阕约涸趺礃游也还埽悄惚仨殞?duì)我和你爸負(fù)責(zé)!”她挺直腰,惡狠狠地說(shuō)。
女兒沒(méi)說(shuō)話。她安靜了一會(huì)兒,笑起來(lái),笑得像一只怪物。女兒走到她的面前,按住她的肩膀,將她推出了房間,猛地摔上門(mén)。她一個(gè)沒(méi)站穩(wěn),差點(diǎn)跌倒。她下意識(shí)地去擰房門(mén)的把手,房間已經(jīng)被反鎖上了。血沖上她的頭頂,腦子像失去信號(hào)的電臺(tái)一般嗡嗡作響。她不停地拍打著房門(mén),企圖迫使女兒把門(mén)打開(kāi)。女兒小時(shí)候起就有這樣的毛病。每次遇到不想面對(duì)的問(wèn)題,她總是將門(mén)反鎖。她寧愿女兒和自己大吵一架,至少這樣她能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但女兒是沉默的,像是一口深井,而她弱小得如同一粒石子。
她使勁拍打著房門(mén),直到筋疲力盡,女兒也未把門(mén)打開(kāi)。她氣喘吁吁地走到客廳里坐下。丈夫也坐在客廳里。此刻,他正將一只腳搭在沙發(fā)上,弓著背在剝腳跟處的死皮。他一邊摳,一邊齜牙咧嘴地?cái)D出一個(gè)便秘般的表情。她看著他,恨不得抽他一個(gè)巴掌。她忍著氣看著他將扯下來(lái)的死皮放在沙發(fā)上,像排列寶貝一樣擺放整齊。她見(jiàn)他抬起頭,說(shuō):“你生的好女兒!你看看,她是什么態(tài)度!你是她爸爸,你能不能管管!”
丈夫斜著眼睛看了她一眼,隨手抄起了放在沙發(fā)上的小木槌。他弓起手背,用木槌朝著關(guān)節(jié)處敲打著。她知道這樣很疼,從丈夫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來(lái)。每次他這么做的時(shí)候都是齜牙咧嘴的,一邊敲打一邊倒吸冷氣。從退休之后他就開(kāi)始熱衷于這樣做。這方法是他從網(wǎng)上看到的,據(jù)說(shuō)這樣長(zhǎng)期敲打能夠清除掉身體里的毒素。丈夫在退休之前曾經(jīng)腦梗過(guò)一次,他堅(jiān)信自己之所以會(huì)這樣,是因?yàn)樯眢w里有太多的血栓。她和他說(shuō)過(guò)多次,丈夫手上出現(xiàn)的那些紫黑色斑點(diǎn)是皮下出血。丈夫從來(lái)沒(méi)有聽(tīng)進(jìn)去,反倒越發(fā)地上癮了。每天只要是閑著,他就會(huì)拿起木槌拼命地敲打著手背。木槌在他的手上發(fā)出啪啪的聲音,密集得如同在砧板上剁肉。
她有些肉麻。她仿佛看到一片灼人的陽(yáng)光照在自己的眼睛里,將雙眼燒得火辣辣的疼。空調(diào)呼呼地吹著,沒(méi)有半點(diǎn)涼意。她深吸了一口氣,沖上前去奪下丈夫手中的木槌,將它摔到了飄窗上。玻璃發(fā)出砰的一聲悶響。她愣了愣,但很快又回過(guò)神來(lái):“你能不能做點(diǎn)別的事?你生的好女兒!跟你一樣,都是自私鬼,從來(lái)不會(huì)考慮別人的感受!”
丈夫從沙發(fā)上跳起來(lái),繃著一張紫紅色的臉:“你是不是想吵架?是不是又想找事?”
“我說(shuō)的是事實(shí)!你看看你的那些同事,退休前官都比你大,退休之后不都是每天幫著老婆做家務(wù),你呢?除了在家做老爺,你還干了些什么?”
“我一輩子為你們母女兩個(gè)累死累活,都退了還不能休息一下?我這樣做還不是為了身體好,這樣才能給你們多賺點(diǎn)錢(qián)?這也不許,那也不許,你還要不要人活了?”
他咧開(kāi)嘴,看起來(lái)快要哭了。他總是這樣,她憤怒地想。退休之后,每次爭(zhēng)吵到自己無(wú)話可說(shuō)的時(shí)候,他就會(huì)將臉擠出皺褶,如同剛出生的嬰兒一般放聲大哭。朋友們告訴她,這可能是腦梗的后遺癥。她不知道這究竟是不是真的。丈夫的委屈像是有模式一般,每一步都可以預(yù)料。
她知道,接下來(lái),他就會(huì)抬起手來(lái)扇自己的臉,一邊打一邊罵:“我不是人行了吧,我是畜生!”
他慣用這種耍無(wú)賴的方式惡心她。
“你能不能說(shuō)句人話!”
他哭起來(lái),鼻涕順著他的鼻子流下,流到嘴角上方。他使勁吸了一聲,將鼻涕又縮了回去。她看著丈夫嘴上方兩條滑膩的痕跡,覺(jué)得如同生吞了豬油一般惡心。她看著丈夫這副模樣,覺(jué)得他不像個(gè)男人。一個(gè)男人怎么能像潑婦一般耍無(wú)賴?不是說(shuō)男兒流血不流淚嗎,這種事在丈夫身上從來(lái)都說(shuō)不通。嫁給他,真是倒了八輩子霉。
她這么想著,站起來(lái),走到門(mén)口,關(guān)上門(mén)。她倚靠著門(mén),覺(jué)得自己被抽空了。這一刻,她再次體會(huì)了生產(chǎn)時(shí)所感受到的那種剝離感。她感到無(wú)論是她和丈夫,還是她和女兒,像是密度不同的水和油,即使同處一處,但始終無(wú)法相溶。
第三次是女兒婚后的頭一個(gè)星期。女兒婚后三天回門(mén),她忙了一天。女兒回去之后,她感覺(jué)自己終于可以停一停了。人松懈下來(lái),沒(méi)想到,病卻趕著來(lái)了。一開(kāi)始她只是便秘。一連幾天,她每天都在馬桶前掙扎。肚子脹得很,卻什么也排不出來(lái)。她很沮喪,自己是老了,連順利的新陳代謝也變成了一種奢望。她聽(tīng)朋友說(shuō)吃酸奶、芭蕉有助于排便,便將它們列入三餐。頭幾天并沒(méi)有什么反應(yīng)。很快,肚子就如同戰(zhàn)敗的軍隊(duì)般全線崩潰了。這樣的狀態(tài)持續(xù)了好幾天。她以為簡(jiǎn)單地吃點(diǎn)藥就能好。
有一天,她坐在馬桶上時(shí),突然覺(jué)得有一團(tuán)滑膩的東西順著身體滑了下來(lái)。她身上的肉敏感地緊了緊。她意識(shí)到不好了。一定是腸子掉出來(lái)了,她驚慌地想。幾年前她做過(guò)一次痔瘡手術(shù)。手術(shù)的過(guò)程中醫(yī)生發(fā)現(xiàn),原來(lái)她患的不只是痔瘡,還一并患有腸黏膜下垂。術(shù)后醫(yī)生提醒她,不要再過(guò)于勞累,要注意休養(yǎng)。她的確也是小心翼翼地照顧著自己的身體的。沒(méi)想到,女兒婚事一過(guò),這場(chǎng)病就突然地爆發(fā)了。
她從洗手間里走出來(lái),叫著女兒的名字。名字剛出口,她突然想起女兒已經(jīng)去了蜜月旅行,要一個(gè)星期后才能回家。她叫丈夫,沒(méi)有人應(yīng)。對(duì)了,以往這時(shí),丈夫應(yīng)該是和朋友在茶莊里喝茶。她拖著步子走到客廳中間的沙發(fā)坐下,給丈夫打了電話,沒(méi)有人接。她看著空無(wú)一人的房間,覺(jué)得它異常的大,自己異常的小。悲戚感涌上她的心頭,很酸,很澀。她站起來(lái),向女兒的房間走去。房間里還有婚禮當(dāng)天遺留下的彩紙碎屑。墻上的喜字是燙金的,在陽(yáng)光下反射出一股灼人的金光。
女兒出嫁才幾天而已,房間里已經(jīng)開(kāi)始冒出一股淡淡的霉味兒。這讓她覺(jué)得有點(diǎn)冷。
她走到衣柜前,將它打開(kāi)。一股輕微的奶香氣撲面而來(lái)。女兒從出生的時(shí)候起就帶著這樣的味道。她原先以為這是嬰兒所共有的味道。但隨著女兒的長(zhǎng)大,這樣的味道并沒(méi)有從她身上褪卻,反而成為女兒特有的一種印記。這味道讓她感覺(jué)親切,仿佛女兒未曾離開(kāi),仍是她身體里的一部分。她將臉埋在女兒的衣服里,靜靜地嗅著這種氣味。她突然悲傷地想到,這些氣味將隨著她打開(kāi)衣柜而逐漸飄散,消失,最后將被一股陳舊的霉味所占據(jù)。她強(qiáng)烈地意識(shí)到現(xiàn)在只有她一個(gè)人了。
她最親近的人已經(jīng)開(kāi)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而丈夫,也許他和自己想的一樣,都認(rèn)為對(duì)方只是一個(gè)共同生活的伙伴。她想著,頹喪地坐下來(lái),哭了。
最后是妹妹將她送進(jìn)了醫(yī)院。檢查之后,醫(yī)生告訴她需要住院。醫(yī)生的臉看起來(lái)病態(tài)、蒼白,走進(jìn)房間里坐下時(shí)搖搖欲墜。他請(qǐng)她和妹妹坐在自己的對(duì)面,詳細(xì)地和她們講述病情。術(shù)語(yǔ)太多,她們什么也沒(méi)有聽(tīng)懂。妹妹焦躁地問(wèn)著醫(yī)生:“到底是要怎么辦,你倒是講講清楚嘛!”
妹妹的聲音尖銳又粗糙,如同公鴨。這幾年她們已經(jīng)少有來(lái)往,彼此都有自己的家,誰(shuí)也顧不上去問(wèn)候?qū)Ψ健K弦淮我?jiàn)到妹妹還是年初時(shí),妹妹過(guò)來(lái)送年貨。她沒(méi)有進(jìn)家,在門(mén)口站了幾分鐘就走了。妹妹說(shuō):“阿姊,我來(lái)不及坐了哦,我還要去給囡囡的老師送年禮,你曉得的……”她點(diǎn)點(diǎn)頭。從那以后妹妹就鮮少露面,甚至也沒(méi)有電話來(lái)。她賭氣似的也不和妹妹聯(lián)系。然而她還是在病倒時(shí)想到了妹妹,畢竟她們是一母同胞。但是,眼前的這個(gè)叫作妹妹的女人也讓她感覺(jué)陌生。妹妹的臉、身材、聲音和她上一輪的印象相差甚遠(yuǎn)。也許并非如此,只是她對(duì)妹妹的印象仍停留在她剛從故鄉(xiāng)來(lái)的那個(gè)夏天。
妹妹剛和故鄉(xiāng)的對(duì)象離婚,原因是結(jié)婚三年后她仍沒(méi)有生孩子。她鼓勵(lì)妹妹到這兒來(lái)。妹妹抵達(dá)城市的那天,提著一個(gè)簡(jiǎn)陋的皮包,里面只裝了幾件簡(jiǎn)單的單衣。由于長(zhǎng)期坐火車的緣故,她的身上散發(fā)著濃重的汗酸味兒。這樣的味道阻止了她想要擁抱妹妹的沖動(dòng)。妹妹似乎看出了她的心思,臉紅了,怯生生地叫:“大姐……”她的心顫抖起來(lái),最終還是走上前去,輕輕地拍了拍妹妹的背。現(xiàn)在,妹妹的聲音已不如過(guò)去柔和。她的臉也是一樣,四處充滿著龜裂的溝壑。生活的艱難讓所有人迅速地蒼老了,她如是,妹妹亦如是。
她的腦子如氣球一般膨脹起來(lái)。妹妹的聲音被隔離在外,發(fā)出模糊不清的嗡嗡聲。消毒水濃重地沖進(jìn)她的鼻腔,卻沒(méi)能讓她的腦子更清醒些。她看著妹妹和醫(yī)生,他們似乎在爭(zhēng)吵什么,她聽(tīng)不清。她抬起頭,發(fā)現(xiàn)天花板轉(zhuǎn)起來(lái)了。緊接著,視線逐漸變得模糊。這感覺(jué)和每天早晨剛睡醒時(shí)一模一樣。她不受控制地倒了下去,感覺(jué)自己坐的不銹鋼椅子和地面發(fā)出令人倒牙的撞擊聲。這時(shí)她突然能聽(tīng)清了。她看見(jiàn)妹妹一臉驚恐地向自己跑來(lái),尖銳地叫著:“大姐!”
她醒來(lái)時(shí)已經(jīng)躺在病床上。丈夫來(lái)了,在房間走來(lái)走去。妹妹不知道去哪里了,她沒(méi)有問(wèn)。丈夫看見(jiàn)她醒了,走過(guò)來(lái)。她發(fā)現(xiàn)丈夫的臉上全是豆大的汗珠。他的臉有點(diǎn)黑。他時(shí)不時(shí)用手抹一把汗,然后將手中濕漉漉的汗液甩在地上。這是他的習(xí)慣動(dòng)作。丈夫緊張的時(shí)候總是會(huì)這樣。
她看到丈夫這樣總是要罵的:“你像不像個(gè)男人?膽子和雞膽一樣!”
倒不是她真的覺(jué)得丈夫膽小。而是覺(jué)得每每這時(shí),丈夫臉上的肌肉都垂下來(lái),太陽(yáng)穴一跳,臉上的肉也跟著顫抖,像是中風(fēng)病人。
她還未來(lái)得及開(kāi)口,丈夫卻先開(kāi)口責(zé)怪了:“哎呀,你什么時(shí)候生病不好,偏偏要在這個(gè)時(shí)候生病?”
生病還可以挑時(shí)候?她想罵回去,可是肚子卻隱隱地發(fā)脹,最后整個(gè)肚子都擰起來(lái)。她痛得在床上打滾。丈夫的黑臉湊過(guò)來(lái),汗水滴答直落:“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她痛得說(shuō)不出話。丈夫仍然像影子一樣緊追著她不放:“哎呀,問(wèn)你話你怎么不答嘛!”
她掙扎著從身下拽出枕頭,奮力扔到丈夫臉上:“滾出去!”
丈夫抹了一把汗。他嘴里嘟囔著出去了。她聽(tīng)不見(jiàn)他在說(shuō)什么,還能有什么,無(wú)非在抱怨她脾氣暴躁,是個(gè)惡婆娘。從他退休以后,每次爭(zhēng)吵敗陣,他總是要這樣嘟囔一陣。若是吵架的陣勢(shì)再大一點(diǎn),他就要打長(zhǎng)途電話到老家她的妹妹們那里:“你姐姐現(xiàn)在可有能耐了,成天就知道和我吵架。”
妹妹們小心翼翼地打電話來(lái)關(guān)心:“大姐,年紀(jì)大了,有什么事情和姐夫商量著來(lái),吵架傷感情。”
“你什么意思?”
電話那頭吞吞吐吐的:“……姐夫說(shuō)你最近脾氣不太好。”
她用力地摔掉電話。
她躺下來(lái),聽(tīng)見(jiàn)丈夫在病房外大聲地打電話:“喂,小李啊,那個(gè),你阿姨住院了,那個(gè)……”
他一句話總是要說(shuō)上半天。即使說(shuō)完了,別人往往也沒(méi)聽(tīng)懂他在說(shuō)什么。她知道這是腦梗的后遺癥。可是,每每她看到丈夫說(shuō)話時(shí)將臉憋成如公雞一樣的紅色,嗯嗯啊啊的,她的心就如同火燒,忍不住沖他吼道:“到底哪個(gè)?”
丈夫被她的吼聲一驚,變得越發(fā)的口吃了:“那,那個(gè),那……”
他年輕的時(shí)候就有些口吃,由于說(shuō)話慢,她也以為是丈夫面對(duì)自己有些緊張,竟將這一點(diǎn)忽略了。女兒還未開(kāi)口說(shuō)話時(shí)她一直擔(dān)心她會(huì)受遺傳影響,還好,擔(dān)心沒(méi)有成真。
很快,丈夫從病房外重新走進(jìn)來(lái)。他的臉仍是擰在一起,仿佛遇到了很頭疼的事。他走到她的床前,重重地“哎呀”一聲,說(shuō)道:“求人實(shí)在是太難了,你不知道……”
他說(shuō)了許多,她沒(méi)有聽(tīng)進(jìn)去。她知道丈夫說(shuō)到最后,也還是會(huì)告訴她事情解決了。但他習(xí)慣在告訴她結(jié)果之前,總要說(shuō)一大堆話作為鋪墊,仿佛只有這樣才能凸顯他所作出的努力。一開(kāi)始,她還會(huì)對(duì)丈夫說(shuō)兩句“你辛苦了”之類的話,待她發(fā)現(xiàn)這只是丈夫的習(xí)慣之后,她感到厭煩了。她在心里嘆了一口氣,問(wèn)自己,為什么要和他結(jié)婚?
是日久生情嗎?可能更多的是出于女人的虛榮心。她這樣想。她和丈夫還沒(méi)有確認(rèn)關(guān)系的時(shí)候,丈夫已經(jīng)在外當(dāng)兵。他常給她寄照片來(lái)。照片上的丈夫穿著軍裝,身材挺拔,看起來(lái)很是英武。工友們看到照片,說(shuō)話時(shí)夾雜著醋味:“喲,你的對(duì)象是軍官啊?”她只是笑,不置可否。實(shí)際上她還在心里思量著。她知道他脾氣不好,身上還帶著一股從骨子里散發(fā)出的土氣。有一次她去辦事,順道去看他。丈夫的同事安排她在宿舍里等著。她在床上坐下來(lái),覺(jué)得屁股下鼓鼓囊囊的,有些不對(duì)勁。她掀開(kāi)被子一看,天,被子下是一堆穿過(guò)的襪子!她強(qiáng)忍住想吐的沖動(dòng),跑出了丈夫的宿舍。她想,她絕不可能和這種人結(jié)婚。可是她拿著照片仔細(xì)打量著,想到朋友們那些艷羨的眼光,覺(jué)得丈夫越發(fā)地順眼起來(lái)。她的心微微地動(dòng)了。
兩天之后,醫(yī)生通知她要進(jìn)行手術(shù)。醫(yī)生告訴她,因?yàn)樗炎鲞^(guò)一次手術(shù),再加上她本身患有糖尿病,很可能在手術(shù)的過(guò)程中產(chǎn)生危險(xiǎn)。丈夫在一旁,哎呀哎呀地嘆著氣,以至于讓她有將抹布塞在他嘴里好讓他閉嘴的沖動(dòng)。汗從她的背上流下來(lái),浸透了她的病號(hào)服。醫(yī)生交代她好好休息,走出去了。丈夫在她的病房里走來(lái)走去,偶爾在床邊的椅子坐下來(lái),但很快又站起來(lái)在房間里來(lái)回走。病房里不允許抽煙,丈夫便走到陽(yáng)臺(tái)上,點(diǎn)上煙。她仔細(xì)打量著丈夫,覺(jué)得在煙點(diǎn)燃的那一刻,丈夫長(zhǎng)長(zhǎng)地舒了一口氣。他抽完煙,走回病房對(duì)她說(shuō):“那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來(lái)。”
她突然打了個(gè)冷戰(zhàn)。快六點(diǎn)了。六點(diǎn)時(shí)餐車會(huì)來(lái)送病號(hào)飯。他至少應(yīng)該為她打完飯?jiān)僮撸y過(guò)地想。女兒還要兩天才能回來(lái)。她的蜜月還沒(méi)有結(jié)束,接到消息時(shí)急匆匆地往回趕。她沒(méi)有買(mǎi)到機(jī)票,只好連夜坐上火車。
前幾天,她聽(tīng)到丈夫給女兒打電話:“你媽都病成這樣了,你還過(guò)什么蜜月?你怎么這么不孝!”她聽(tīng)著丈夫焦慮的罵聲,覺(jué)得他并不是關(guān)心自己,只是想要迅速找到一個(gè)人來(lái)接替他現(xiàn)在的工作。她很難過(guò)。她覺(jué)得,在丈夫心里,她可能就如同一顆高爾夫球——提起桿子,他希望將她打得越遠(yuǎn)越好。

⊙ 陳尚云·潑墨龍崗
她努力撐起身子,拿起枕邊的手機(jī),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寫(xiě)下遺書(shū)。眼淚掉在智能手機(jī)上,觸不出字。她想,下輩子就算投胎成為一頭豬,她也不會(huì)和丈夫這樣的男人結(jié)婚。
此刻,她和丈夫、女兒,還有妹妹、外甥一家人正圍坐在包廂的圓桌前,慶祝她和丈夫結(jié)婚四十周年。她和丈夫的生日均和結(jié)婚紀(jì)念日挨得很近,這樣一來(lái)也算是做了壽。人們把四十年的婚姻叫作紅寶石婚,以寓意這樣的婚姻并不容易。
她坐在丈夫旁邊的位置上,看小輩們高興地夾菜,聊天。天氣炎熱,包廂里的柜式空調(diào)已開(kāi)至最大一檔。空調(diào)上的紅色綢布還未去除,總是隨葉片的轉(zhuǎn)動(dòng)發(fā)出嘶嘶的響聲。這些并未阻止窗外傳來(lái)的密集又令人心焦的蟬鳴聲。她莫名地覺(jué)得熱,心仿佛被貓爪抓出了幾道熱辣的傷痕。周圍的小輩們不時(shí)湊近來(lái)和她聊上一兩句,或者客氣地給她夾菜,她敷衍地笑笑,不時(shí)用手去揉搓被冷風(fēng)吹硬的臉。
墻角擺放著女兒預(yù)訂的四層蛋糕。飯店里的冰箱放不下,服務(wù)員只好將蛋糕擺在了包廂里,并將空調(diào)開(kāi)至最大,以防蛋糕融化掉。她不知道那幾層蛋糕究竟是如何支撐起來(lái)的。她很好奇,也很擔(dān)心。她總覺(jué)得那蛋糕的邊角好像已經(jīng)開(kāi)始軟化,隨時(shí)都有可能因過(guò)高的溫度而倒塌掉。她想,可能生活也是如此。
丈夫有些過(guò)度的興奮,他喜歡人多的場(chǎng)合。滿桌子的菜,點(diǎn)的幾乎都是他愛(ài)吃的。菜自然是他點(diǎn)的。他從來(lái)不考慮別人,她不高興地想。每次進(jìn)飯店,他總是大包大攬地將菜單從服務(wù)員手中搶先接過(guò)來(lái),點(diǎn)上滿滿一桌。菜時(shí)常剩下,結(jié)賬時(shí),他很豪爽地?fù)]手:“這些要來(lái)干什么!冰箱沒(méi)地方放!”吃飯時(shí),他習(xí)慣將嘴塞得滿滿的。湯汁順著他的嘴悄悄溢出來(lái),隨時(shí)都有可能往下掉。甚至有幾次他一邊含著飯菜一邊將酒灌進(jìn)嘴里。酒喝得太快,他被嗆得連酒帶飯一同噴出來(lái),濺得四處都是。她用筷子敲碗,盡量壓住火氣,平緩聲調(diào):“慢點(diǎn)吃行不行,沒(méi)有人和你搶。”
丈夫用腿背推開(kāi)椅子,刺拉一聲刺耳的響。他站起來(lái):“不吃了。”
她現(xiàn)在已經(jīng)學(xué)會(huì)將丈夫的一切惡習(xí)過(guò)濾掉。比如他旁若無(wú)人地將鼻涕擤在地上,或者把臉埋在碗上,呼嚕呼嚕地喝粥。她以前總是要罵的。現(xiàn)在,她更樂(lè)于將頭扭開(kāi),將視線無(wú)限地往前方延伸過(guò)去,穿過(guò)墻,飛向室外,腦子里閃過(guò)一幕幕場(chǎng)景:飄雪的城市、橘紅色的晚霞、遼闊的草原。微笑浮在她的臉上,她的呼吸逐漸變得平穩(wěn),就像在經(jīng)歷了筋骨酸疼的瑜伽練習(xí)后所做的休息術(shù)一樣,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輕松。
“我來(lái)敬爸媽一杯。”她看到女兒站了起來(lái)。
女兒在結(jié)婚前和她的父親并不親近。人們都說(shuō)女兒是父親上輩子的情人,女兒和她父親卻好像生來(lái)相克。她對(duì)她父親所做的一切都看不順眼。在以往,女兒若看到父親吃飯的模樣,眉頭總是擰起來(lái):“你幾輩子沒(méi)吃過(guò)飯了?沒(méi)有人和你搶!”她覺(jué)得自己有了戰(zhàn)友,忙不迭地補(bǔ)充:“他們家里人都是這樣的,你像我。”丈夫不作聲。
最近的一次吃飯,女兒的態(tài)度突然發(fā)生了變化。她在提醒丈夫時(shí),女兒突然打斷了她:“好不容易一起吃個(gè)飯,搞這么多要求做什么。他愛(ài)怎么吃就怎么吃好了嘛。”丈夫彼時(shí)正在咬著一塊排骨。她坐在他旁邊,聽(tīng)見(jiàn)他故意將排骨咬得咔咔作響。她突然想到了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到的一個(gè)鏡頭,饑餓的美洲獅將羚羊拖到隱蔽的地方,用爪子抵住,用力地從羚羊身上撕咬下一塊肉。咔咔的響聲讓她寒毛直豎。她閉上了嘴。
女兒的聲音中帶著微弱的顫抖,由強(qiáng)至弱,聽(tīng)起來(lái)底氣不足。她能猜到女兒在擔(dān)心什么。按理說(shuō),女兒已經(jīng)過(guò)了那種幻想父母離婚、選擇究竟與誰(shuí)生活的年紀(jì)。她以前也不會(huì)這樣,甚至?xí){(diào)侃自己和丈夫的婚姻:“媽你每次都說(shuō)爸不好,你怎么還和他一起過(guò)?如果換作是我,我早離了。”
她突然有些同情丈夫,為他辯解著:“你爸至少不賭不嫖……再說(shuō),我還不是為了你。”
女兒笑了:“要我說(shuō),你還是不想離婚。”
她的心前所未有地慌張起來(lái)。她在心里問(wèn)著自己,真想離嗎?一開(kāi)始答案是肯定的,可是多問(wèn)幾次,心里越發(fā)地沒(méi)底。她開(kāi)始搜尋各種各樣的理由來(lái):“那還能怎么辦呢?要是真離婚,你就是單親家庭了,以后結(jié)婚人家會(huì)瞧不起的……”她的聲音逐漸弱了下去。女兒看著她,笑得意味深長(zhǎng)。
她現(xiàn)在想,也許女兒說(shuō)得沒(méi)錯(cuò),她可能并不是真的想和丈夫離婚。有多少次了,她已經(jīng)覺(jué)得日子快要過(guò)不下去,但最后也還是咬著牙忍受過(guò)來(lái)了。
她的母親就是一個(gè)很能忍耐的人。母親常常告訴她,作為一個(gè)女人,最大的美德就是忍耐。她在心里鄙夷母親,覺(jué)得她懦弱無(wú)能。她親眼看到母親被父親打罵后忍氣吞聲,但她沒(méi)有幫過(guò)忙,更沒(méi)有去勸慰。她覺(jué)得,這是母親選擇的生活,她應(yīng)該為自己的選擇負(fù)責(zé)。她也暗暗在心里告訴自己,以后她絕對(duì)不能這樣生活。
那時(shí)候的她并沒(méi)有因?yàn)楦赣H和母親的關(guān)系而對(duì)婚姻產(chǎn)生恐懼。她以為,自己有能力駕馭自己的婚姻。她會(huì)挑選一個(gè)完美的丈夫。他會(huì)是一個(gè)身材高大的男人,為了表達(dá)情意,他會(huì)給她念詩(shī)。有了孩子之后,丈夫會(huì)在燈下輔導(dǎo)孩子做作業(yè)。在燈光的映照下,她感到自己正在逐漸融化,并且將繼續(xù)融化下去。這些幻想最終形成了一個(gè)棱角分明、目光清澈的男人形象,和她當(dāng)年崇拜的一個(gè)男明星很相似。
直到訂婚后,她又突然記起了這個(gè)幻想中的輪廓。她用它和丈夫?qū)Ρ戎幸环N吃了虧般的沮喪。不過(guò)她又安慰自己,她有足夠的時(shí)間可以把丈夫打磨成自己想要的模樣。當(dāng)婚姻越來(lái)越長(zhǎng),她終于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重復(fù)經(jīng)歷著母親當(dāng)年所經(jīng)歷過(guò)的一切。她開(kāi)始覺(jué)得,忍耐不僅是一種美德,甚至是一種智慧。每每在與丈夫的沖突之后,她都驕傲地想,她又一次給自己高尚的道德加了光彩……
突然,小輩們隨著女兒一起站起來(lái),舉起了酒杯。他們起哄讓她和丈夫喝一杯交杯酒。丈夫帶著慍氣說(shuō)搞這種東西做什么,坐在椅子上不肯起來(lái)。她站起來(lái)了。她依然是笑著的。她笑著挽住丈夫的臂膀,一臉喜氣洋洋地勸他起來(lái)接受敬酒。她臉上在笑,心里也是在笑著的。她為自己的寬容與大度感到驕傲。
丈夫掙扎了一番,還是站了起來(lái)。他粗魯?shù)嘏e起酒杯,將手臂穿過(guò)她的手臂。小輩們開(kāi)始起哄鼓掌。她仰起頭,將酒一飲而盡。酒熱辣辣的,將她嗆出了一灣眼淚。她突然想起了四十年前她與丈夫結(jié)婚的夜晚,丈夫的戰(zhàn)友們也是這樣起哄讓他們喝交杯酒,讓他們共同咬一個(gè)蘋(píng)果。他們的臉撞在了一起。哄笑聲瞬間占滿了整個(gè)房間。他們祝福道:“新婚快樂(lè)!百年好合。”
在閃爍的燈光中,她看見(jiàn)一條路漫長(zhǎng)地往前鋪開(kāi)。
她看見(jiàn)女兒和女婿。她看見(jiàn)他們用和自己與丈夫同樣的步伐,朝著這條路的盡頭緩慢地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