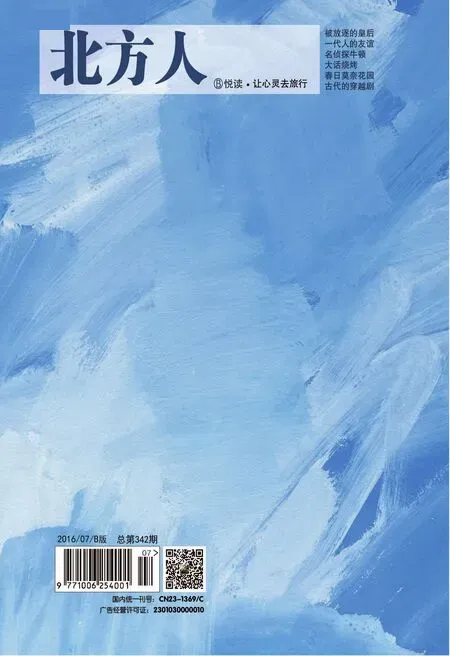行動的力量
文/汪涵
?
文苑·演講
行動的力量
文/汪涵

大家好:
我是汪涵,來自湖南電視臺的一位節目主持人。我做主持人十八年了,主持了十八年的節目,像這樣的舞臺、這樣的燈光、這樣熟悉的攝像師、這樣的觀眾、這樣的氛圍……我應該特別的熟,但是今天,一個人站在這個舞臺上的感覺,非常的奇妙,甚至說奇怪,還好有你們,有現場諸位親愛的觀眾朋友,所以我說主持人應該在舞臺上像春風一樣,他能夠讓舞臺上所有的一切變得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妥帖,就像顧城寫的詩一樣——草在結它的籽,風在搖它的葉,我們站著什么都不說,就十分的美好。
美國有一個特別有名的藝術家,叫做約翰·凱奇,他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寫過一部鋼琴曲,名字叫作《四分三十三秒》。作品是這樣的,演奏家站上舞臺,打開琴蓋放上琴譜,端坐好了以后,四分三十三秒之內手指頭沒有觸碰一下琴鍵,一直就靜靜地坐著。頭十秒鐘大家在等待,心想這個鋼琴師有可能在醞釀情感,慢慢的有一些躁動,慢慢的有人打哈欠了,慢慢的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到四分三十三秒鋼琴師起來,收起琴譜,然后蓋上琴蓋說,我的演出完畢,走了。全場莫名其妙,但是安靜下來以后,所有的觀眾體會到,雖然那一刻什么聲音都沒有,但是他們聽到了琴鍵以外的音樂,自己的心跳、呼吸、小聲的議論、些許的煩躁,所有的這一切仿佛變成了《四分三十三秒》音樂當中的每一個組成部分。
其實我在這里特別希望跟年輕朋友分享的就是,不要輕視行動的力量,也不要輕視個人的力量,用心地去做你認為你該做的每一件事。
就像我最開始,我大概是1996年從湖南電視播音專科學校中專畢業,我沒有讀過大學,我當時進到湖南電視臺的節目叫《男孩女孩》,我們當時根本就沒有節目可做,就有這么一個欄目,每天大家上午就是開會,然后中午到食堂吃飯,下午又開會,然后在辦公室睡覺,然后又開會,但是我覺得那樣的生活,對于一個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人來說,特別的新奇。但是后來我打了很多次報告,都沒有留在湖南臺,然后我就去了湖南經視,就是到目前為止,我的人事關系依然還在的那個電視臺,它是湖南的一個地面頻道。我特別珍惜一個稱謂,我想我作為一個最優秀的節目主持人,后面沒有“之一”的話,很難,但是我可以做湖南經視最忠誠的員工,我愿意在這里待十年、二十年——拿下這個稱號。
我在這個電視臺一開始做劇務,當時我們劇務組有兩人,我們彼此認為是最帥的劇務——我和李維嘉。我們倆也是最快樂的劇務,每天往演播廳扛椅子,扛椅子的時候我就在想,今天扛的椅子有可能會是毛寧坐的,維嘉說,那我這個還有可能是林依輪坐的呢,兩個人每天有很多特別開心的事情。我們那個時候現場有兩百五十六個觀眾,每個觀眾來看我們的節目的時候有個塑料袋,每一個塑料袋里面有五十多件禮品,我就負責每天錄節目的時候往每個觀眾席放禮品:鹵蛋粉、電燈泡、水龍頭、面條、醬油——每天就做得特別快樂,因為我知道放不完的面條我可以帶回家。
然后我就當了現場導演,跟現場所有的觀眾朋友講一些笑話,活躍現場的氣氛,帶領全場的朋友鼓掌,當然我們今天現場的掌聲全都是大家自發的。我記得我們那時候要帶領大家鼓掌,在當現場導演的時候,我是每期鼓掌鼓得最厲害的。記得有一次我們的臺長到現場來看節目,(問)這哪來的現場導演,(說)小伙子你過來,我就過去了,“臺長你好”,“把倆手伸出來”,我說,啊,怎么做節目還帶檢查指甲蓋洗沒洗干凈的?我一伸手,能看到手拍得特別紅,他說,你們看這個現場導演多么的投入,鼓掌鼓得多么的賣力。我當時特別地快樂,因為好多人要去看當時的那個綜藝節目,要花很大的精力、求爺爺告奶奶地拿到一張票,而我場場都在里面,就覺得特別地快樂。
后來又當導演,可以讓我特別欣賞的節目主持人按照我的想法去做節目,哇,還有什么比這更開心的?沒過多久,臺里面做內部的晚會,說汪涵是學播音主持的,你讓他去試試吧。哇,可以在全臺同事的面前主持節目,開心得不得了。當時要做一個節目叫做《真情》,臺長就問我們當時的一個節目主持人:“和汪涵當搭檔可以嗎?”“可以!”然后還問了我們的一個燈光師,“小廖,你覺得汪涵可以嗎?”“不錯!暖場的時候全場觀眾都樂成那樣,讓他去吧。”太開心了,我可以當主持人了。每件事情都是我心里覺得我應該去這么做,而且這么做我特別特別地開心,不管是什么情況我都接受,比如說今天的燈光突然間沒有往昔那么好了、今天的攝像不是你以往熟悉的、今天你化完妝之后,總覺得自己的黑眼袋比平常大很多、今天的嘉賓、今天的臺本、今天所有的一切都那么不如意,趕快在內心鼓掌,因為你的機會來了,我一定要學會很好的忍耐這樣的一個特別尷尬或者是特別難堪的局面,我一定要扛下去。因為面對困難無非三點:第一,渡過了這個難關,你有渡過困難的智慧;你面對困難,你有了面對困難的勇氣;你繞過困難,你有了繞過困難的狡猾,多好。你還要生命教你什么?你還要這個舞臺教你什么?就像塞內加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何必為部分生活而哭泣,君不見全部的人生都讓人潸然淚下。但是我想,他所呈現的應該是這樣一種情緒:既然我們都知道最終的結果是那樣,我們何不開開心心地、歡呼雀躍地、一蹦一跳地朝著那樣的一個歸宿去?因為我們心里面,充滿了太多太多對這個世界認知的美好。
叔本華好像也說過同樣類型的話,就是說如果你關注的是整體,而非個人的一己的生命的話,那么你的行為舉止看起來會更像一個智者,而不是一個受難者。所以我在這里花那么長的時間,跟我所有的朋友分享的就是——不管怎么樣,我們還這么健康;不管怎么樣,我們還能夠這么自由地呼吸也好、鼓掌也好,做你想做的任何事情也好,你什么都不會失去,就算有一天你經過了所有苦難的東西,恭喜你,你知道生命的苦難了。
來之前我就一直在想,我今年40歲,我舍掉了什么東西,當然我也得到了太多太多,得到了我很多受之有愧的掌聲和喜愛,因為我個人覺得主持人只是最后的完成者,如果我們今天現場沒有燈光師、攝影師、化妝師、音頻師,這個節目完全不可能呈現在大家面前,但是所有的鮮花、掌聲給了我們,所以我覺得受之有愧。
“舍得”這個詞我去查了一下,最開始,閻王爺那時候好像在天上,有兩個人說要投胎到人間去,有兩種人生,一種是“舍”的人生,一種是“得”的人生,然后問這兩個人的選擇其中一個說:“我要過‘得’的人生。”另一個人說:“行吧,那我就過‘舍’的人生吧。”于是乎兩個人來到人間,過“得”的人生的那個人最終成為了一個乞丐,因為所有的東西都是別人給他的,他得到別人的資助,得到別人的憐憫,得到這個得到那個;而說要過“舍”的人生的那個人成了一個特別富有的人,他把自己的財富、自己的知識、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一點兒一點兒地給了別人。但是我想,我今天面對這么多年輕的朋友,80后,90后,我們是不是一定要在腦子里建立這個“舍和得”的概念?我后來一想,不應該!因為在這樣的一個社會生活當中,很多時候你舍了卻什么都沒有得到,所以當你心里面有了“舍和得”,認為我只要得到什么,我就舍去什么,如果說舍而不得忙活著是得非所愿,那我們只能得病了,你會怨恨。所以我覺得與其在這里跟大家強調“舍和得”,還不如去考慮“舍得”背后的另一個詞——接受,上天遞給你的東西我們用雙手去接著,捧在手心,當然也沒必要高舉過頭頂,因為每個人都有可能會接到這樣的饋贈。
上天拋給你的東西,用自己的雙肩去承受,不管拋多少先扛著,扛著的目的是為了讓你的身體更加堅強,雙臂更加有力,有一天他饋贈給你更大禮物的時候,你就能接得住。忘記“舍得”這個概念,做你想做的任何讓你快樂的事情,前提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和快樂建立在別人痛苦的基礎之上。除此之外,沒人看見時,你可以蹦著跳著回家,你怎么樣都可以。所以在這里要祝愿所有的年輕朋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一件事,如果你希望在你的一生當中,你往前、往后或者停下來的每一個腳印,當你有一天回過頭的時候,希望它們成為詩句的話,你就踏踏實實地走好你人生的每一步。
謝謝各位,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