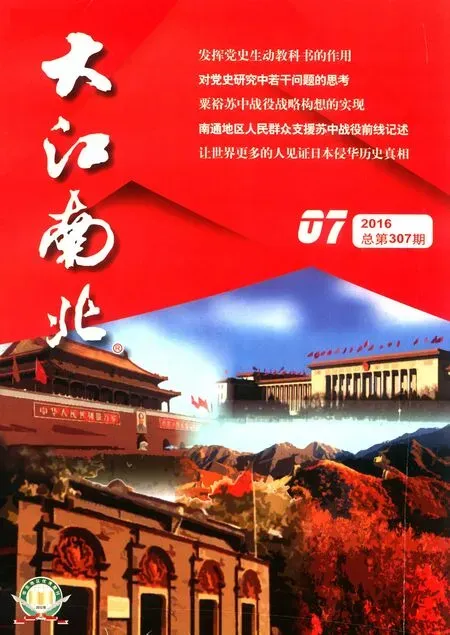70年前,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
□本刊特約記者 鄭蔚
?
70年前,葫蘆島百萬日僑俘大遣返
□本刊特約記者 鄭蔚

日本僑俘遣返之地紀念碑
面朝錦州灣的遼寧葫蘆島港,有一座“葫蘆島筑港開工紀念”碑亭,那是張學良1930年所立。在碑亭后面不遠處的山坡上,還橫臥著一塊紀念碑,碑中間一行大字是“日本僑俘遣返之地”。
這塊紀念碑述說的是中日關系史上極為特殊的一頁: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剛剛散去,仍有一百多萬日僑俘滯留在我國東北地區。這一年5月7 日18時30分,從這里啟程的兩艘登陸艇,滿載著2489名日僑俘,前往日本佐世保港。在其后的3年里,從葫蘆島港遣返回國的日僑俘總數達1051047人,史稱“葫蘆島大遣返”。
回首當年被遣返的往事,多年后重返故地的立石節子女士說:“自己能活著回來,真是不可思議,是我的幸運。當年在中國,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幫助,說不定我已經死了,能活著回來真是我的幸運。”
“東北地區的百萬日僑俘大遣返,說明中國政府和人民認真履行了《波茨坦公告》的條款。《波茨坦公告》第九條規定:‘日本軍隊在完全解除武裝以后,將被允許其返鄉,得有和平及生產生活之機會。’70年前,中國政府和人民盡最大的可能幫助百萬日僑俘回國,體現了受盡戰爭苦難的中國人民的博大胸懷。”曾潛心研究這段歷史的遼寧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原研究員張志坤說。
在人類的戰爭史上,善待戰敗國的僑民和俘虜,尤其是曾深受侵略者禍害的勝利者一方有此人道主義的善舉,迄今為止并不多見,這同樣不應被今人遺忘。
“國策移民”,戰敗后形同棄民
時光回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投降。給全世界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落幕。
“當時,滯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約有660萬人,其中日本軍人(含隨軍家屬)和民間人士約各為一半。這其中,滯留在中國各地的日僑俘多達350萬人,占日本滯留海外總人數的50%強,這350萬人中還不包括被蘇軍押往西伯利亞的59.4萬日軍俘虜。”遼寧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關亞新告訴記者。
1945年9月29日,重慶中美聯合參謀會議提出備忘錄,要求“盡快制定遣送日人計劃”。10月25日,在上海舉行的中美第一次遣送日僑俘會議,制訂了《中國戰區日本官兵與日僑遣送歸國計劃》,明確了遣送日僑俘“先關內后關外”的原則,以及由中國政府負責陸路向港口集中與輸送、美軍組織船只負責海上輸送的實施辦法。
1946年1月10日,軍事三人會議小組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張群和美國代表馬歇爾共同商定,設立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三人小組,由中共代表葉劍英、美國代表羅伯遜和國民黨代表鄭介民,協調負責東北日僑俘遣返。
“為什么中國境內的日僑俘數量如此之多?”在葫蘆島市,記者采訪了曾任葫蘆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錢福云女士。
聽她介紹,1905年9月,日本取得日俄戰爭的勝利后,從沙俄手中攫取了中國東北旅大地區的租借權和從長春到旅順的鐵路及其附屬地。為了在亞洲大陸開辟侵略擴張的基地,日本統治集團提出了“滿洲移民論”,并付諸實施。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以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解決起因于‘土地饑餓’的日本農村問題的唯一出路”制定了《滿蒙移殖民計劃》。日本關東軍還強調移民是“滿洲建國的根本性課題”,必須使大量的日本移民“真正成為新國家的核心”,并制定了《屯田兵制移民案綱要》等文件,將原來的“普通移民”升級為“特別農業移民”,目的是“充實日滿兩國的國防,維持滿洲國治安”。1933年,第一個日本武裝移民團在樺川縣永豐鎮“彌榮村”建立了首個據點。1936年4月,日本制定了《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案》,廣田弘毅內閣正式宣布將把向中國東北移民作為日本的“七大國策”之一。截至到1944 年9月,日本在東北的僑民人數達到了166.2萬人。
在1945年蘇軍即將對日宣戰前,這些日本移民的命運如何呢?張志坤告訴記者,1945年7月,蘇軍對日宣戰在即,關東軍卻確定其防線為“新京(長春)至大連一線以東、新京至圖們一線以南”,這就將絕大多數日本開拓團移民置于防線之外。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8月14日,日本政府還向其駐外公使館發出訓示,強調各地日本僑民“現地定著”,實質上是“就地拋棄”。
張志坤說:“日本戰敗后,近百萬日僑從東北各地逃亡到哈爾濱、長春、沈陽等大城市,陷入缺衣少食的困境。當時的日本人會向東京連發3份電報,哀告‘眼看冬季降臨,約八十萬難民擁擠在南滿一帶,無食物、無住處、無錢,陷入絕境’。但這些電報如泥牛入海,毫無回音。時任東北日僑救濟總會會長的高碕達之助只得派員攜密信回日反映危情,可日本政府依舊沒有撥來一分錢。”
滿目瘡痍,國共協力遣返日僑俘
從“國策移民”到“現地定著”,揭示了這些移民在日本統治當局眼中不過是侵略工具和炮灰。
關亞新研究員說,大多數日本移民是日本的下層民眾,他們也是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戰爭后期,因為日本的兵員嚴重不足,移民中45歲以下的成年男子均被征入關東軍,開拓團剩下的幾乎全是老弱婦孺。當日軍兵敗如山倒,這些移民惟有向沿海地區逃亡。我們在查閱當年的資料中發現,不少幸存的日本僑民講述了他們的親人被死硬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集體槍殺、放火燒死或逼迫自殺的事件。她舉例說,《滿洲開拓史》記載,綏棱縣長山鄉瑞穗村是日本武裝移民所在地,當時共有開拓團員820人,1945年9月17日,代理團長下令全體成員自殺,共有495人當場服毒。當時有的日本婦女不忍心殺害自己的孩子,帶領孩子逃進了山林,最后有52名婦女和孩子得以幸存,有的孩子送給中國百姓收養。而村里監督他人自殺的開拓團干部卻放火燒了村莊后,逃到山上躲了起來,之后逃回日本。
此時,中國政府在積極實施日僑俘的遣返工作。1946年初,國民黨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日僑俘管理處成立,處長由李修業少將擔任。北平軍調部三人小組的協商商定:除安東日僑75000人由東北民主聯軍負責組織,陸路經朝鮮、海路從鴨綠江口登船遣返,在大連日僑270000人由蘇軍負責遣送外,在東北的其余日僑均經葫蘆島遣返。1946年7月25日,中共代表李敏然(李立三)率東北民主聯軍代表團,乘坐美軍專機飛抵沈陽,就遣返共產黨控制區內的日僑俘與國民黨當局磋商,就日僑俘的交接地點、應遣人數、所需經費等達成協議。李敏然代表中共簽訂的《遣送東北中共管制區日人之協定書》明文規定:“保證日人自所在地出發,至葫蘆島登船,沿途不受到強奸、掠奪、侵犯、搶劫、勒索、恐嚇或其他任何不法舉動,其生命財產不受到侵犯。凡日人行經之處當地指揮官應負保護之責,凡有違反上列條款者,需從嚴處罰之。”

登上遣返船的日本僑俘

遣返難民的船“白山丸”
張志坤說:“無論是民主聯軍還是國民黨軍隊,都派出官兵護送日僑俘,每列運送日僑俘的專列都配備武裝警衛。在整個遣返過程中,日僑俘專列沒有發生過一起搶劫、強奸或槍擊的事件。”
7月30日,李敏然乘美軍專機回哈爾濱前,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財務組長王爾純將裝有6000萬元流通劵的箱子交給中共代表團。8月20日,松花江以北解放區的日僑俘正式開始遣返。至10月,民主聯軍共遣返日僑俘28萬余人。
8月20日之后,開始重點遣返國民黨控制區的日僑俘。為了保障日僑俘的遣返,在滿目瘡痍的困難情況下,中國政府和人民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從財力、物力和人力上給予了極大的支持。
寬大為懷,“沒有對日本人進行民族報復”
在葫蘆島市龍灣公園里,有一塊“恩”字碑,碑身后還有6棵銀杏樹。立碑和種樹的是當年從葫蘆島回國的佐佐木宗春老人。
錢福云為記者講述了這位老人的故事:她24歲和中野義雄結婚,婚后沒幾天丈夫就應征入伍去了東北。為思念丈夫,她一人輾轉來到哈爾濱,終于找到了他,但只住了兩天丈夫部隊又開拔了。兩年后,她才得知丈夫已被蘇軍俘虜并在押往西伯利亞途中死去。絕望的她,在葫蘆島海邊欲跳海自盡,意外地被當地的一名大嫂救下,大嫂還給她下了一碗面,打了兩個雞蛋。回國后,她重新有了家庭,并取得了茶道教授資格。2008年,這位日本老人第三次重回葫蘆島,捐資立碑種樹。
解放后曾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教員的東北行轅日僑俘管理處處長李修業回憶說,當時,我們遣送的日僑一百多萬,而遣送的日俘不過數百人,這是因為日軍戰敗后,絕大多數日俘都已被蘇軍押往西伯利亞。但就是這些日俘中,仍有不少有血債。我們在錦州、沈陽、長春待遣站查出的經過受害人指認的有血債的日本軍人、浪人有三十多人。他們原本都換上了便裝,急于逃回日本,以免受懲辦。這些有血債的日本人被查實后,一律轉交軍事法庭。
但對一般日僑俘,中國政府的遣返安排不可謂不周到。關亞新告訴記者,為了讓日僑俘了解有關遣返的規定和日本國內的情況,日僑俘管理處還創辦了日文版的《東北導報》,從1946年3 月17日至1947年9月20日,共在沈陽、長春等地發行790期,發行量最高達3萬多份。為戰敗國的僑民戰俘辦一份使用戰敗國母語的報紙,這在世界各國的報業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
錢福云告訴記者,當時,葫蘆島和錦州的兩大待遣營地,均有齊全的生活設施,臨時的醫院、幼兒園、學校和商店一應俱全,婦產科能同時為30位婦女接生。據不完全統計,有120余人在此安全生產,只有兩名胎兒死亡。
但當時仍有不少中青年男僑民并不服輸,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寬大為懷并不感恩。李修業說,有一次召集各地日僑聯絡處負責人開會,他講話時日本人畢恭畢敬站著,幾次讓他們坐也不肯坐下,但散會后,他的日語秘書就聽到有日本人說:“我們不久還要回來的,到時再叫你們瞧瞧吧!”有的日本人一登上遣返回國的船,馬上從低頭哈腰變得怒氣沖天,船只一離岸就高喊:“我們一定要回來的,你們等著吧!”
最后一艘遣送船離港前,李修業上船視察,所有的日僑俘立即站起身向他彎腰敬禮,但他看出其中有的日本人并不服氣。日僑聯總處負責人野村再三請他講話,他對船上的日僑俘說道:“你們回去以后,要細細地想一想比一比,你們是怎么對待中國人的,中國人是怎么對待你們的?希望你們以后只帶友誼來,不要再帶刺刀來。否則,侵略之念再萌,未來的世界史上恐難找日本的名詞了!”他說完后,日僑聯絡處代表贈送了一面感謝中國政府的錦旗。
由日本人編寫的《滿洲國史》是這么回顧中日關系史這一頁的:“戰爭后期,生活必需物資緊張,強制出勞工,強制繳農產品,中國人對滿洲國,進而對日本人的反感情緒不斷增長一事乃是事實。……但是,并沒有因此發生由于戰爭結束,一舉勃發共產革命,或者對日本人進行民族報復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國人、朋友們,同情日本人的悲慘處境,救濟危難,庇護以安全,或者主動給予生活上的幫助的事例層出不窮。”
(編輯 韋瀟)